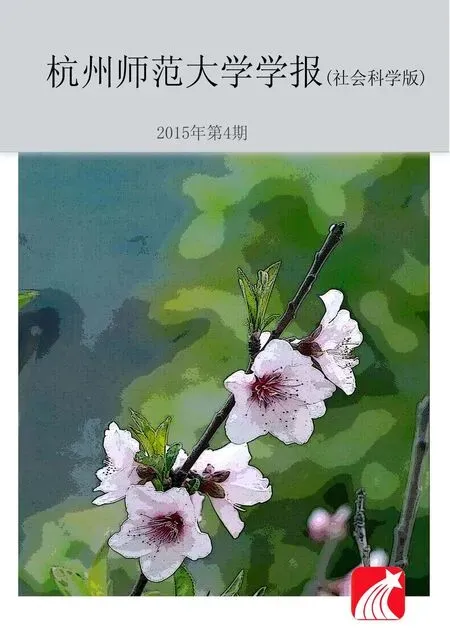跛行的哲学——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或哲学辩护
张尧均
(同济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092)
哲学研究
跛行的哲学
——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或哲学辩护
张尧均
(同济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092)
摘要:《哲学赞词》尽管以“哲学赞词”为题,但实际上却是对哲学及哲学生活的辩护。哲学为什么要辩护?梅洛-庞蒂主要从认识、表达、行动(其中也涉及到哲人与大众的冲突、哲学的现实处境等)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哲学知识的暧昧性、哲学与现实的潜在冲突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系等作了深入阐发,最后指出哲学的生活具有“跛行”的特征,从中也体现出了梅洛-庞蒂哲学自身的“暧昧性”特征。
关键词:梅洛-庞蒂;《哲学赞词》;“哲学辩护”
标题出自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一文①梅洛-庞蒂在“哲学赞词”这一讲稿中两处提到了哲学或哲学家的“跛行”,尽管他用了不同的词,参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59, p.61。,这是梅洛-庞蒂195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就职演讲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这场讲演题为“哲学赞词”(Élogedelaphilosophie,或译“哲学颂”),但在讲演稿中,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赞颂”一词,与此相反,它倒是明确地提到了对哲学的“辩护”[1](P.59)。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篇“哲学赞词”,毋宁说是一篇“哲学辩护”。
但是,既然是一种辩护,梅洛-庞蒂又为何要冠之以“赞词”呢?或者说,“辩护”能够成为一种赞颂吗?更进而言之,如果它是一种辩护,那么哲学又因何需要辩护呢?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这一讲演本身的性质需要它采取这样一个肯定性的标题。尽管法兰西学院一贯强调它的自由原则②梅洛-庞蒂在他的演讲的一开头就提到:“自法兰西学院创立伊始,其职责就不是给予其听众以既有的真理,而是一种自由研究的理念。”Merleau-Ponty, 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13.,但它也有它的某些习惯性做法。比如说,在新院士的就职演讲词中,它要求个人表达其由衷的感激,而且它还“必须对(取其而代之)的去世的院士进行真实可信的颂扬,并对其著作进行正确无误的分析”[2](P.36)。梅洛-庞蒂的演讲词无疑也遵循了这样一种规范,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头就表达了对法兰西学院的景仰,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厕身于其中;他也表达了他的荣幸和感激。紧接着,他说:“我能做的最好的感谢无疑是在你们面前考察哲学家的职能,首先是我的前任们已经恢复和履行的职能,同时这种职能还体现在考察哲学的过去及其现在。”[1](P.14)他随后提到的他的哲学家前任主要是拉威勒(Louis Lavelle,梅洛-庞蒂接任的就是他的席位)和柏格森(Heri Bergson)。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庞蒂明确地把对哲学家职能的考察与对哲学本身的考察并列在一起,也就是说,哲学与哲学家密不可分,而哲学家又体现为哲学家的生活,这样,哲学最终与哲学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哲学就是一种关于哲学的生活。因此,如果哲学值得赞颂或需要辩护,那么,实际上值得赞颂或需要辩护的就是一种哲学的生活。
那么,哲学家的生活又如何与众不同呢?
一
在其讲演的一开头,梅洛-庞蒂就承认,他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内在混乱的人”,混乱的根源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个经典的哲学自述,无疑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而事实上梅洛-庞蒂也的确讲到了苏格拉底)。正是因此,他觉得自己不配厕身于这“永垂不朽”的学术万神殿中,但另一方面,正由于他明白自己的内在混乱,他也从这一混乱中解脱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特别适合于这一神圣之所的,因为法兰西学院素以“自由研究”著称,而哲学,只有哲学才真正契合于这一理念,“这是因为哲学的非知(non-savoir)达到了它的这种研究精神的顶点”[1](P.13)。哲学之为哲学,正在于它以探索整全为己任,但哲学的“非知”或“自知其无知”则又使它不把任何既有的事实看作真理,由此才保证了它向整全的自由敞开。因而,“造就一个哲学家的是不停地从知导向无知,又从无知导向知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的某种宁静……”[1](P.14)
这里的“宁静”就是指从开头所提到的“内在混乱”中解脱出来。之所以说当意识到这种混乱时混乱就被超越了,是因为在这一转向中,混乱自身成了主题。梅洛-庞蒂把这一意义莫名的混乱称为“隐晦”(ambiguïté)*Ambiguïté是梅洛-庞蒂哲学的基本特征,或者可以说是他的哲学标签。这一标签似乎有三个来源:首先是Ferdinand Alqui关于梅洛-庞蒂的长篇评论用了“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ïté”这一标题(载Fontaine,1949年4月号),随后,由Alphonse de Waehlens撰写的关于梅洛-庞蒂哲学的第一部研究著作也用了这一标题(UnePhilosophiedel’ambiguïté,Paris,Editions Beatrice- Nauwelaerts, 1951)。最后,当《行为的结构》于1949年出第二版时,梅洛-庞蒂把Alphonse de Waehlens的一篇同样题目的评论文章放在前面作该书的前言,借此表明他本人也接受了对他的哲学的这一标签。参S.F.Sapontzis.A Note on Merleau-Ponty’s‘Ambiguity’, in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 Vol. 38, No.4(Jun., 1978),note 1.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Ambiguïté至少有如下几层含义:首先是指意义(主要指“知觉意义”或“表达意义”)的多样性,不确定性,甚至歧义性,进而表明意义的敞开性和生成性。当涉及这种含义时,我在本文中一般把它译为“隐晦”。其次也指哲学自身位置的不确定性,哲学无处不在而又无所在。最后,梅洛-庞蒂也用这个词来表明行动或立场的不确定性。当涉及后两层含义时,我把它译为“暧昧”。。隐晦是不可消除的,它根植于我们在世存在的处境,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有限性的体现。但是有两种不同的隐晦:一种是好的隐晦,一种是坏的隐晦。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消除隐晦,而是以隐晦为主题,把隐晦带入到光亮中,赋予它以意义或方向,从而消除它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威胁。这就是好的隐晦。相反,坏的隐晦则“满足于接受隐晦”[1](P.14)而不试图超越它,这是一种真正的混乱。
哲学因而与隐晦不可分解。梅洛-庞蒂认为,能够引向那种“好的隐晦”的人是大哲学家。他把他的两位前任拉威勒和柏格森都看作是这样的大家。拉威勒尽管以“存在的整体”(tout de l’être)或“总体的存在”(un être total)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他非常清楚,要通达这一存在,必须经由我们自身,正是因此,他提出了“参与”(participation)和“在场”(présence)的概念,以此来界定我们自身与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是暧昧的:一方面,我们属于整体存在,后者预先就宣告了我们之所是和能是,另一方面,整体存在又离不开我们,没有我们,它就不再是整体存在,在这个意义,它也属于我们。
在柏格森那里,同样存在着这种暧昧性。他提出了著名的“直觉”概念。哲学通过直觉与事物交融,从而达到对存在的一种整体把握。然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这只是柏格森主义的表面。真正的直觉并非指哲学家消融在存在中,而是回到意识的直接预料或直接经验中去。在直觉中,我们并不是走出自身以通达事物,相反,我们是更深地潜入到自身,体验到自身的绵延,并在我的绵延中体会事物的绵延和宇宙的绵延。这种作为绵延的直接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地生成和展开的过程,因此,直觉也是处在发展中的,它内在地包含着“否定性和隐晦性”的因素。但直觉并不神秘,梅洛-庞蒂甚至说,直觉就是我们的知觉的深入和扩大。如此,梅洛-庞蒂就把他自己的哲学工作与其前任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了。“哲学家的绝对知识就是知觉。……知觉奠定了一切,因为可以这样说,它教导给我们一种与存在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存在就在我们之前,可是它从里面通达我们。”[1](P.24)
然而,单纯的知觉是不够的。在另一个地方,梅洛-庞蒂曾经说过,单纯的知觉只是一种“坏的隐晦”,因为它只是告诉我们一种“有限与无限、内在与外在的混合物”。[3](P.290)为了消除混乱,我们必须借助于语言:“在表达现象中存在着一种好的隐晦,一种能够实现在我们只是观察各种孤立的因素时看起来不具有可能性的事情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把单子的多样性、把过去和现在、把自然和文化汇聚到一个单一的整体中。”[3](P.290)只有表达才能解开混乱的知觉之网,从中抽绎出顺畅的意义丝线。因此,经受着隐晦之混乱的哲学家如果要摆脱这种威胁,就离不开表达。梅洛-庞蒂说,拉威勒和柏格森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最后都走向了一种表达哲学。
事实上,表达也是知觉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知觉中,现象自身就分泌着意义,而表达则是这种意义的凝化和结晶。“人们去洞见事物本身的意向越是强烈,我们越是看到事物藉以获得表达的现象和我们借以表达事物的语词充塞于事物与我们之间。”[1](P.27)
因此,知觉自然地导向表达,只有在表达中,知觉到的意义才获得一种具体的在场,意义的进一步的积淀和传播也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说,无论是知觉还是表达,都呈示着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知觉原初地就贴近存在,它见证了我们与存在的一体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因过于贴近和致密,反而使存在本身晦暗不明,甚至被我们忽略(这就是梅洛-庞蒂“知觉的隐晦”的原因)。因而,为了使存在的意义向我们涌现,我们需要略微松开我们与存在之间的这种粘连关系,表达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表达在我们与存在之间撑开了一个语言空间,它使我们不再面对面地遭遇存在,它在两者之间布起了帷幕,它拉开了我们与存在之间的距离。也是这一间距使存在恢复了它的神秘,使我们有得以领会存在之意义的闲暇。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通达存在的必由之途,或者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
但另一方面,表达与存在的关系仍是暧昧的,表达并没有消除知觉的隐晦,而只是把它转变成了另一种隐晦,即使它是一种“好的隐晦”,但它仍然是隐晦,甚至是包藏危险的一种隐晦。而正视这种隐晦,并坦然地面对它所隐含的危险,则是哲学的“奇异性”(étrangeté)之所在。可以说,唯有哲学才真正懂得表达之隐晦的特质,也只有在哲学中,表达之隐晦才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在哲学的表达中,“哲学家与存在的关系不是观众与表演之间的正面关系,而是一种共谋,是一种倾斜的、暗中的关系。”[1](P.23)
二
表达,更确切地说,哲学的表达之所以具有危险性,是因为这种表达同时设定了“进行表达的某一个人,他要表达的真理及他对之表达自己的其他人。表达和哲学的公设就是要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1](P.36)。也就是说,哲学的表达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家与真理的关系,还有哲学家与他人的关系,但这两种关系并不总是能够同时共存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内在地相冲突的。这样,哲学家所体验到的暧昧就不再只是一种知觉的歧义和内在的混乱了,它更是人与人之间,或者说哲学家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是哲学家所信奉的真理与大众的意见或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消除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篇以颂扬为名的演说中,梅洛-庞蒂更多的却是在替哲学辩护。
梅洛-庞蒂首先举了柏格森的例子。柏格森在内心里赞赏天主教的教理,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当他看到欧洲的反犹主义浪潮汹涌裹卷时,他还是坚决地选择了“留在那些明天将受到迫害的人们中间”,并拒绝了权力机构愿意为他提供的种种方便。柏格森以他的行动证明,对他来说,不存在一种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或拥护的真理。“我们与真实的关系得经由他人。”[1](P.37)但我们真的能够与他人一道通达真理吗?当人们恳请柏格森写一本关于他的道德观的书时,柏格森却明确地说:“从来没有哪个人被迫去写一本书。”[1](P.37)这表明,哲学家既不愿为了真理而放弃大众,也不愿为了大众而降低真理的层次,他想同时维持与这两者的关系。这样,哲学家的立场就必然是暧昧的:
我既不是根据真实,也不只是根据我自己,也不只是根据他人来进行思考,因为这三者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其他两者,牺牲任何一个都是无意义的。哲学的生命永不停息地在这三个基本点上得以提升。哲学之谜(和表达之谜)在于,生命在自我面前,在他人面前,在真实面前有时是同样的。它们就是为哲学提供保证的诸环节。哲学家只能依赖于它们。他永远都既不接受让自己对抗人类,也不让人类对抗自己或对抗真实,也不让真实对抗人类,他愿意同时无处不在,甘冒永远都不完全在任何一处的危险。[1](PP.37-38)
但哲学家能够维持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吗?柏格森的例子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他确实既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也没有因此而对抗人类,同时,他也多少避免了让人类对抗自己或对抗真理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不是始终存在吗?应该回想起苏格拉底!
梅洛-庞蒂说:“苏格拉底的生与死乃是哲学家——在他还没有受到文学豁免权的保护时——与城邦诸神,亦即与他人,及由他人力图提供给他的凝固的‘绝对’形象之间维持着艰难关系的历史。”[1](P.39)从表面上来看,苏格拉底的生活无可指责。他跟其他人一样接受城邦的宗教,给诸神献祭,出席公民大会,在广场上与人交流,参加保卫雅典的战争,甚至当雅典人判处他死刑时,他也拒绝出逃,还论证法律的权威。但人们为什么还是赞同处死他呢?
梅洛-庞蒂认为,人们指责苏格拉底的不是他所做的事,而是他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动机。苏格拉底确实信奉宗教,但他为他的这种信奉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和理由,而“被解释的宗教,对其他人来说就是被取消了的宗教”[1](P.42)。同样,苏格拉底顺从城邦的法则,但不是出于“国家的理性”,而是出于他自己的理性。苏格拉底为他的遵从赋予了一种新的基础,以此暗中取代了早先为城邦及城邦宗教所奠定的基础。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说:“人们在渴望改变法律中遵守法律,如同人们在渴望和平中投入战斗。”[1](P.40)因此,苏格拉底的活动并不是无辜的,他有着一种“实为拒绝的服从方式”。尽管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和其他人一样,但在其他人眼中,苏格拉底始终是独立的,他的所作所为仿佛受着一种“秘密原则”的驱使,人们没法理解他,当然更不能支配他。在雅典城中,苏格拉底像一个外乡人。
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是最典型的哲学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最典型地体现了哲学与意见、哲人与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哲学需要城邦,哲学家只有和他人一道才能通向真理,“不存在没有他们的真理”。正是因此,即使面临雅典人的指控,苏格拉底也拒绝出逃。他一直生活在雅典,他知道他即使跑到别的地方,也不会更能得到人们的容忍。他也很清楚,雅典是最适合于哲学存在的地方;也只有在雅典,哲学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并能在民众中产生它的效能。所以梅洛-庞蒂说:“苏格拉底拒绝逃跑,这不是因为他承认法庭,而是为了更好地否定它。如果逃跑,他就成了雅典的敌人,他就证实了对他的判决。如果留下,不管法庭判他有罪无罪,他都是赢家,因为他要么通过让陪审团接受他的哲学,要么通过自己接受判决而证明了他的哲学。”[1](PP.40-41)苏格拉底以他自身的言行,把哲学带入了“与雅典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城邦也需要哲学和哲学家。“人们正是在哲学家的世界中通过理解拯救了诸神和法律,而且,为了将哲学的领地安置于大地上,需要的恰恰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1](P.42)
但与此同时,哲学又超越城邦。城邦满足于它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哲学却试图把城邦引向更高的善。苏格拉底不停地向各种各样的人提问,但这不是为了显示他有更高的智慧。他在《申辩》中伤感地说:“每当我让某人承认他的无知时,旁观者都以为我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一切。”但其实,“他并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他只是知道不存在绝对知识,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缺陷,我们才向真理开放”。[1](P.43)城邦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其偏见的支配,苏格拉底却试图诉诸理性,来克服他们的偏见。但理性对于大众来说是不可见的,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说,理性于他们只是空疏,虚无和饶舌。[1](P.42)
因此,哲学与城邦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每一个城邦都是特殊的,而哲学却要诉诸普遍的原则。城邦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甚至是盲目地服从,而哲学却试图为这种服从提供理由,“但需要理由的服从已经是太过分了”[1](P.42)。城邦借助宗教来维护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哲学却试图对宗教的原则作出解释,并赋予其一种新的意义,从而暗中破坏了宗教的原有基础。因此,哲学的存在对城邦来说是一种威胁。在哲学家与他人的关系中就存在着这种不安,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偶然的。
但梅洛-庞蒂认为,这种不安对于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乃是哲学的活力之所在。哲学表达的隐晦正是这种不安的产物,著名的苏格拉底式反讽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隐晦的艺术。真正的反讽利用了在事物中确立起来的双重意义,这是哲学表达所具有的“好的隐晦”的体现。“苏格拉底的反讽是与他人的一种有距离然而真实的关系。它表达了这一基本事实: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只是他自身,但与此同时又在他人那里认识自己。反讽试图解开彼此的约束以通达自由。”[1](P.42)反讽在指向他人的同时也反涉自身,它通过揭示人们言行中的矛盾来激发思考,进而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无疑,反讽也会刺痛人,使人恼怒,但它以一种轻松的姿态表现其善意。此外,反讽由于展现了事物和情境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因而能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启发,也颇为有效地掩盖了哲思本身的尖锐性。总而言之,苏格拉底的反讽既是一种保护自身的策略,也是一种展现真实的方法,更是一种指引他人的艺术。在这种反讽中,自我、真理、他人,这三者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项的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了肯定和维护。
梅洛-庞蒂对于哲学表述之隐晦性的论述无疑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列奥·施特劳斯所揭示的“隐微教诲”(esoteric teaching)。隐微教诲与显白教导(exoteric teaching)相对,同样涉及到哲人与真理和大众的关系。就真理而言,施特劳斯认为,所有的古典哲人都认识到,真理不可公示,只能秘传,这首先是因为真理与公众的信仰和意见相冲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关心甚至也不需要哲学和真理,如果公示真理,只会激化哲人与大众间的冲突。因而为了保护哲人自身,也保护哲学,同时也保护大众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免受哲学的冲击,哲人就以双重的面具说话,他以显白的言辞拥护城邦和习俗道德,同时又以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隐微表达讲述真理。当然,有些表面显白的言说同样可能具有隐晦性,因而只有少数真正有哲学天赋的人才懂得这种区分,并透过其言说的表面布局(前后矛盾、反讽、不精确的复述等等)去探究背后潜藏的真理。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的隐微表达不仅仅是哲人在城邦中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激发潜在的哲人进行独立的思考、进而培养未来哲人的方法。
不过,梅洛-庞蒂对于哲学的秘传性不以为然*“苏格拉底的反讽并不是以说得少来打动人心,以便证明灵魂的力量,或让人推测有某种秘传的知识(quelque savoir ésotérique)。” Merleau-Ponty, 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43.,他也不关心隐微言说与显白言说之间的区分。他认为隐晦是表达本身固有的特征,而与所谓的秘传知识无关。隐晦源自语言本身的特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又是知觉含混性的反映,就此而言,隐晦或暧昧是不可消除的,它是我们生存固有的特点。但当哲学以求真为目的时,它就与这种根植于生存本身的暧昧性拉开了距离,也因此导致了哲学家的生活与大众生活的距离。不过,哲学家并不因此就消除了隐晦,毋宁说,他从自身中体验到含混与明晰、实存与本质的距离,而这种内在的间距又进而导致了哲学本身的隐晦和哲学家自身生活的暧昧。由此,哲学家与大众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他的内在分离的反映。当然,哲学家的内在分离一般不会导致其个人生活的危机,但它一旦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却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正是因此,为了缓解或消除这种可能的冲突,就需要哲学的表述本身也采取一种隐晦的手法。在这个意义上,隐晦是哲学的面纱。哲学家借助这一面具既守护着真理的高贵与隐秘,又小心地维持着他与众人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好的隐晦,是哲学之生机与活力的体现。
三
然而,在现代社会,哲学的这种活力正在丧失,哲学家与他人的关系日益疏远。“现代哲学家常常是一个公务员,通常是一个作家,留给他的著作自由承认对立的观点:他所说的话一开始就进入了学术界,在此生活的选择弱化了,思想的契机也被模糊了。”[1](P.39)哲学不再直接面对大众,面对生活,它被封闭在学院内,被凝固在书本中。但是,“书本中的哲学停止了对人进行的拷问”,因此,梅洛-庞蒂说:“有理由担心,我们的时代也在拒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哲学只得再一次高处云中。”[1](P.45)
梅洛-庞蒂在这里提到了古希腊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该剧描写了一个坐在高挂的吊篮里冥思苦索、形容憔悴的苏格拉底形象,他开办学院,招生收费,并无所顾忌地向他们传授诡辩术,如神灵并不存在,打雷只是自然现象,正义没有力量,歪理可以战胜真理等等。这种诡辩的逻辑颠覆了普通民众素来信奉的城邦的宗教和道德基础,但也招致了哲学自身的危险。最后,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在民众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据说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是年轻时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本人也承认,他年轻时曾追随过阿那克萨哥拉,研究几何学和天文学,也就是说,他的灵魂曾经“高处云中”。梅洛-庞蒂似乎也认同这种说法。而且,尽管苏格拉底后来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并发明了著名的反讽术,但梅洛-庞蒂还是认为,苏格拉底最后的死亡与他的轻慢无忌有关,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并没有完全脚踏实地,他也没有把他的反讽艺术贯彻到底。比如说,在法庭上,他似乎过于轻视那些陪审团成员,从而诱发了他们的残暴:“他因此有时被傲慢和恶意弄晕了,有时则顺从于个人的崇高和高贵的精神。”[1](P.44)梅洛-庞蒂似乎想说,如果苏格拉底能在法庭上更谦卑一些,“为法庭提供让其明白的机会”,那么,最后也许就能免于死亡,也能“将雅典从不体面中拯救出来”。[1](P.44)因此,苏格拉底在一定程度上要为他自己的死亡负责。
当然,梅洛-庞蒂在这里提及阿里斯托芬的《云》,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与现代哲学作比较。如果说古典的哲人(苏格拉底)因对理念的激情迷狂而招致了危险,那么,现代的哲学却可能因它的衰老淡漠而死亡。“我们的思想是一种退隐或自省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青春狂热赎罪。”(Notre pensée est une pensée en retraite ou en repli. Chacun expie sa jeunesse.)“我们重新回到这种或那种传统,我们捍卫传统。我们的确信与其说是建立在被洞见到的价值或真理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我们所不情愿的各种传统的缺陷与错误之上。”[1](P.45)哲学不再观察现实,不再与现实接触。哲学因此被凝固或僵化了。这种凝固尤其体现在它对待上帝和历史的态度上。
梅洛-庞蒂吃惊地看到,如今的哲学家已不再像托马斯、安瑟伦和笛卡尔等人那样论证上帝了。在对待上帝时,如今的哲学家要么不容置疑地把它看作是一切的前提,要么就干脆否认它的存在。于是哲学被分成了对立的两极:要么是神学,要么是无神论。然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走向了某种独断的肯定,它们都漠视了真正的人本身。无神论只是一种颠倒的神学,是一种把人当神来看待的人类神学(anthropothésime)。因此,它们都不能被称作真正的哲学,或者说,它们都排斥了哲学。
在梅洛-庞蒂看来,哲学在另一种秩序中确立自己。它基于“认识你自己”这一基本原则,如其所是地看待人本身。人既不是一种绝对的力量,也不是一种解释性的原则,“他只是处于存在之核心的一种脆弱,是一种宇宙的因子,但也是所有的宇宙因子都通过一种永无完结的转换来改变意义并生成为历史的场所”[1](P.47)。人处于跟人相关的一切维面(dimension)的纽结之中,人就是这一纽结本身,但这一纽结的存在却有赖于所有这些维面的存在,离开了这些维面,人也就不再成其所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这些维面及其缠结的认识,而上帝或神圣者(le sacré)只是与这一纽结相关的维面之一,因此,它也应该始终将这一神圣者“置于物或词的关节处”[1](P.49)。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那么,哲学就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上帝,甚至也不是把基督教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改换成哲学的上帝(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而是应该积极地对上帝提出疑问,与神学展开争论,尤其是在涉及对人自身的认识及现世的苦难之际。如果上帝存在,它也不应该是抽象地远离于人的,它应该在人的实在中临现,在人的精神中生成。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游移,它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究竟是上帝在维持着人的人性存在呢,还是相反,为了认识它的存在,应该经由我们的存在……”[1](P.32)
与此相应,历史是人之实存的另一个维度。如果说上帝涉及的是人之最超越、最神秘的维度,那么,历史涉及的则是人之最现实、最贴近的维度。哲学应如何看待历史呢?长期以来,人们要么使两者截然对立,要么把它们视为同一。前者可置而不论,因为它把哲学与历史视作完全不同的畿域,因而可以说是自己把自己给封死了;后者则值得重视,尤其是因为它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完善、最系统、也最具影响力的论述。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哲学观念的生成和展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就像是一出由哲学家导演的戏剧,因此,哲学和历史在他那里是同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是内核,一个是表现。
然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两种观点都错失了哲学与历史的真实关系。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它其实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封闭哲学之上的。这是一种凌空蹈虚的哲学,一种俯视的哲学,它把现实看作是既成的,不再有发展和变化,而世界对哲学家来说则是透明的,就像一幅画卷那样展现在哲学家的眼中,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上帝:哲学“再一次高处云中”。
在梅洛-庞蒂看来,哲学家既不应排斥历史,也不应把自己的观念塞到历史中,毋宁说,他既深入历史的核心,又超越于历史之外。他寻求历史的意义,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预定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内在于人际事件中,并且同它一样脆弱。”[1](P.53)它类似于话语表达的意义,如果抽离来看,每一句话都是琐碎的、偶然的,其意义也是断裂的、破碎的,只有还原到特定的语境,这些个别的话语才联贯起来,意义显示出它的逻辑,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但是这种逻辑和必然性不能超越这一语境而作抽象普遍的推广,它们只有内在于这一语境之中才有效。历史的意义也是如此,它只处在特定的人际事件的内部。追索这种意义的哲学同样处于历史之中,但“它不满足于服从这种历史处境(就像它不满足于其过去),它通过向自己揭示这一处境,通过使这一处境有机会与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建立一种显现其真理的关系来改变这一处境”。[1](P.58)由此,哲学与历史重新统一起来了,但正如在上帝问题上一样,这种统一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统一。
总之,无论是上帝问题还是历史问题,它们都与人的实存息息相关,它们也都是哲学需要加以思考并且从未停止其思考的问题。梅洛-庞蒂之所以重提这些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思想处境中,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有一种日益脱节的趋势。这既有哲学自身的原因,如对其他学科的问题漠不关心,或以为哲学的思考可以代替其他的思考。但更有来自其他学科的排斥,它们不欢迎哲学的横加干涉,它们想要为哲学圈定位置,划定领域。然而哲学是与其他学科同列的一门学科吗?哲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其固定的领域吗?显然不是。哲学的位置始终是游移不定的、暧昧模糊的。哲学的触角既深入到上帝和历史问题中,也深入到生命、灵魂、政治、艺术、科学等其他的一切领域中,但这不是说哲学想要取代神学、历史学或任何其他一门学科。哲学超越这一切之外,说到底,它不是与这些学科或任何其他学科并列的一门学科。就像梅洛-庞蒂所说:“哲学的中心无处不在,而其边界无迹可寻。”[1](P.147)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得不“高处空中”。
四
至此,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跛行的哲学”这个标题的含义了。哲学之所以是跛行的,是因为它没有固属于自身的领域,是因为它始终有一只脚踩在空处,而且不得不踩在空处,因为“它不满足于已经被构成的东西”,它对一切现成的东西、坚实的东西,对所有人们不假思索地肯定和赞同的东西提出疑问。哲学之所以是跛行的,是因为只有哲学才洞悉人之生存的隐晦,它把这种生命和生存本身的隐晦转变成了一种表达层面上的隐晦,它“以一种有意识的象征替代了生活的缄默的象征,以明显的意义替代了潜在的意义”[1](P.58)。就此而言,哲学无疑彰显了我们的生存所蕴含的内在丰富性,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生活中本来只是隐含着的矛盾和张力突显出来,动摇了生活的确定性和稳靠性,给人带来不安和骚动。在哲学的凛凛审视下,人们的立足处不再平坦,哲学使人蹒跚而行。哲学家是跛行者。
哲学家是跛行者,这意味着哲学家是个内在分离的人,在哲学家的身体和灵魂、行动和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也导致了他的行动的迟缓或滞后。哲学家是个思想者,但他的思想掣制了他的行动,或者说他用思想代替了行动。与此相反,大众似乎只是直接地行动而不思考,他们出于激情而行动,而行动又进一步鼓发着他们的激情,他们在行动中抱成一团,但也因此,他们的行动常常带有狂热的性质。“哲学家在这兄弟般的混乱中是一个外来者。即使他从来不背叛,人们从他的忠诚方式也感觉出他可能会背叛,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成为其中一员。他的赞同缺少某种厚实的、有血肉的东西……他并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存在。”[1](P.60)大众不理解哲学家,哲学家的存在是暧昧的。
但尽管如此,梅洛-庞蒂还是认为,“哲学家的跛行乃是他的美德”[1](P.61),因为它避免了狂热和冒进。“论行动的哲学家或许是最远离行动的人:即使是严肃而有深度地谈论行动,这也等于说一个人不愿意采取行动。”[1](P.5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说马基雅维里站在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对立面。哲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关注严肃的人和严肃的事,比任何人都更严肃地关注行动,关注宗教和激情,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或狂热的人。恰恰在他关注严肃本身的时候,严肃变得轻巧了,因为他把严肃转变成了一种思想,仿佛为它蒙上了一层轻纱。正像当他注目他人的轻松嬉戏时,这种轻松却反过来在他的目光下变得凝重,变得陌生。哲学家总是保留着一种反思或一种审慎的隐思(arrière-pensée),他总是实行着一种奇怪的颠倒:在沉重的时候轻松,在肯定的时候否定,“在摧毁之际实现,在保留之际取消”。在哲学家那里似乎没有真正严肃的事,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哲学家那里没有不严肃的事。借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哲学家同时体验了悲剧和喜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最接近生命的整全的人。这是否足以替哲学家的存在辩护了呢?或者说,这是否就是对哲学的赞颂呢?
梅洛-庞蒂事实上还没有走得这么远。在他看来,哲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其实并不那么截然对立。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角色:行动者和理解者。行动者无疑是狂热的,正如某个作家所写的:“所有的行动都是摩尼教徒式的”,然而,人不会始终处于行动中,即使行动也需要思想的指导并追求某种思想,而且,“没有哪个人在他本人面前会是个摩尼教徒”,这种狂热的姿态只是从外在的角度去看才显得如此。[1](P.61)同样,也没有哪个哲学家始终只思考而不行动,或者总是停留在哲学的高空而不回到生活。斯宾诺莎在专制君主的大门上写下“最后的野蛮”,拉缪(Lagneau)为了恢复一个不幸的候选者的资格而起诉大学当局,这都是哲学家们的哲学行动。但这一切做完之后,每个人都回到家中,依然过着平常的生活。哲学并不会完全改变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把哲学家与行动者截然分割开来似乎是不合适的。哲学家生活在现实中,行动者也同样追求真理,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普通人,“我们发现他们对哲学的反讽出奇得敏感,仿佛他们的沉默与他们的谨慎在哲学的反讽中得到了承认,因为言说在这里使他们一下子获得了解脱。”[1](P.61)
哲学的存在似乎由此得到了更恰当的辩护,当然,这一辩护隐含的前提是启蒙。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启蒙后、或者说哲学化了的世界中,因此,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和接受哲学,人们也需要哲学,需要哲学为他们提供一种“心灵鸡汤”式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家是意义的揭示者,他让人们明白大人物在心中所说的某些东西,他更新着他自己和其他人都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隐晦的不再是哲学,而是生活本身,暧昧的不再是哲学家,而是生活在暧昧之中的每一个人。但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都在事件中思考真理,他们共同反对根据教条而思考的自大者,共同反对不按真理而生活的诡诈者。”[1](P.63)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哲学家,哲学家与普通人不再有高下之分,他们只是清醒者与梦寐者、言说者与沉默者的差别:“哲学家是警醒的人,是在言说的人,而普通人则沉默地把哲学的悖谬包含在自身之中:因为,为了完全成为人,就应该要么稍微在人之上,要么稍微在人之下。”[1](P.63)
参考文献:
[1]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M]. Paris:Gallimard,1953.
[2]卡皮.法兰西学院[M].张泽乾,黄贻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Merleau-Ponty.TheMerleau-PontyReader[M].edited. Ted Toadvine, LeonarLawlor.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
(责任编辑:吴芳)
Crippled Philosophy: On Merleau-Ponty’s “Praise of Philosophy”
or Apology for Philosophy
ZHANG Yao-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nPraiseofPhilosophywas a speech given by Merleau-Ponty when he was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French Academy. Although the title of the book was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it dealt with an apology for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al life. Why philosophy needs an ap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erception, expression and action (and also with the references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er and the mass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 on), Merleau-Ponty explored the ambiguit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the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ality,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Ultimately, he pointed out the “crippled” nature of philosophical life, which accordingly exemplified the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 of his philosophy.
Key words:Merleau-Ponty;InPraiseofPhilosophy; apology for philosophy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8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69-09
作者简介:张尧均(1974-),男,浙江新昌人,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现象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梅洛-庞蒂著作集》编译与研究”(14ZDB02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