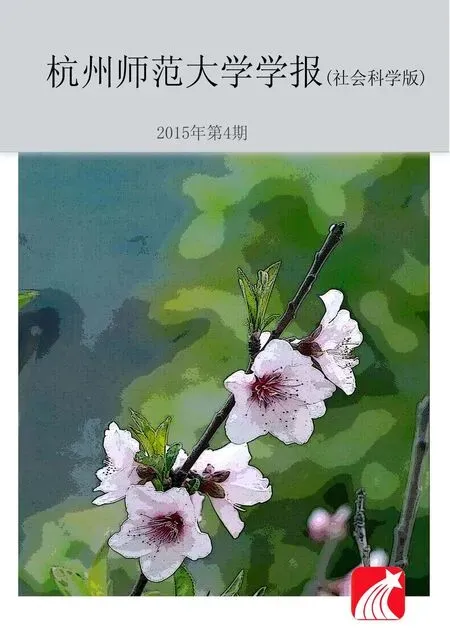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英国学者怀特和纽琳最近揭示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共同体意识,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失偏颇:纽琳只偏重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这一角度,而怀特则把个人和共同体看作对立的概念,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洞察。事实上,华氏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因此我们的相关研究也应该在较为宽广的语境中展开。虽然华氏并没有用过“情感结构”这一术语,但是他的有关思考跟发明这一术语的威廉斯可谓不谋而合:在威氏那里,情感结构意味着一种“深度共同体”,而只有在这深度共同体中,“沟通才成为可能”;华氏在想象共同体时所关注的也恰恰是怎样使上述沟通成为可能,因而他心目中的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度共同体。华氏的诗歌还让人想起艾略特。后者直接把共同体的命运跟对待死者等陌生人的态度联系在了一起,而华氏早于艾氏一百多年就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而且给予了诗意的表达。
关键词:华兹华斯;深度共同体;《序曲》;沟通;陌生人
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共同体情怀”。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纽琳(Lucy Newlyn)跟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怀特(Simon J. White)之间的争论。纽琳于2003年发表了以“《序曲》中的共同体”为副标题的文章,强调华氏的长诗《序曲》(ThePrelude)“旨在以‘诗人心灵的成长’为切入点,进而展示怎样奠定仁慈社会的基础。在华氏看来,从一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来审视自我,不失为最好的角度”。[1](P.59)这一观点受到了怀特的质疑。后者一方面承认“该诗关乎共同体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断定这种意识“被挤压在整个叙述的缝隙之中”[2](P.59),或者说只是在叙述人口中得到了“压制性描述”。[2](P.66)怀特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序曲》在总体上缺失了有关工作和工作共同体的再现”,“缺失了近距离的工作意象”,其原因是作者“想要迎合上流社会读者的期待”。[2](P.64)不过,怀特又强调华氏在其晚期作品《漫游》(TheExcursion)中“致力于探究通向具有正当功能的人类共同体的途径”[2](P.67);“随着《漫游》的杀青,华兹华斯的诗学完成了一种转向,原先它扎根于对个人英雄的再现,此时则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2](P.79)怀特和纽琳的共同优点是揭示了华氏诗歌中的共同体意识,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失偏颇:纽琳只偏重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这一角度,而怀特则把个人和共同体看作对立的概念,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洞察。事实上,华氏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因此我们的相关研究也应该在较为宽广的语境中展开。
为了比较充分地理解华兹华斯的共同体思想,我们有必要以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作为思考的起点。下文就从共同体的定义谈起。
一、深度共同体
在共同体研究史上,德国学者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是一个绕不过的探讨者。他曾经在与“社会”相对的意义上,给“共同体”下了一个经典性定义:“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19)。这一定义跟华兹华斯的共同体情怀十分契合。
在华兹华斯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正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而新型的共同体还未出现,这情形就像阿诺德后来描述的那样,处于社会转型的人们“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4](P.288)那个时代同时也是催人思考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共同体的时代,但是让华氏十分担忧的是,那个“不忠不义的时代”竟有一批“愚蠢先生与虚伪先生……将本不/口渴的羊拼命赶往它们/一向回避的水池”。[5](P.68)这几行诗句剑指当时弥漫于英国社会的唯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潮,诗行中的“愚蠢先生与虚伪先生”则是以葛德汶(William Godwin, 1756-1836)为代表的思想家。华氏曾经一度追随过葛德汶,原因是后者在《政治正义论》(AnEnquiryConcerningPoliticalJustice,1793)等书籍中描绘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氏发现葛氏所构想的是一个由机械主义原则主宰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机械的聚合”(这在“将本不口渴的羊拼命赶往它们一向回避的水池”这一比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而华氏所向往的则是“高于一般机械因素”的[6](P.160)、情理交融的共同体,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丁宏为曾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华氏的“许多诗行可以说是与葛氏的公开商榷”[6](P.155),这一点在我们研究华氏共同体思想时值得优先考虑。事实上,华氏对理性至上的机械主义语境进行挑战的例子很多,下面这几行广为人知的诗句就是典型的例证:“我们那好事的理智,/扭曲了事物美丽的形式:——/我们解剖一切,却谋杀了生命。”[7](P.151)类似的表述在《序曲》中也可找到:华氏反思自己当初追随葛氏时“也动用逻辑/推论,片刻间摧毁生命中的奥秘。然而,恰恰是/这些奥秘,曾经——并且将会/永远——使四海一家,结为兄弟”。[5](P.314)此处的“使四海一家,结为兄弟”显然是一种共同体情怀,并且显然是跟“摧毁生命”的“逻辑推论”以及“谋杀了生命”的“好事的理智”格格不入的。换言之,华氏在憧憬人类的未来时已经意识到,共同体的建设首先要从破除对工具理性/机械主义的迷信入手。
至于该怎样破除上述迷信,华兹华斯有着多方面的思考,如共同体的纽带、人们的共同信念、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人与人(包括死者和未出生者)之间的沟通、人与大自然的沟通,等等。对于这些因素的一些表述,即便未直接采用“沟通”一词,也包含了沟通的意思。例如,人们的共同信念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基础。华氏考虑的各类沟通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即情感——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而这正是唯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体系所缺乏的。虽然华氏并没有用过“情感结构”这一术语,但是他的有关思考跟发明这一术语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可谓不谋而合:在威氏那里,情感结构意味着一种“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而只有在这深度共同体中,“沟通才成为可能”[8](P.65);华氏在想象共同体时所关注的也恰恰是怎样使上述各类沟通成为可能,因而他心目中的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度共同体。
换言之,华兹华斯为追求共同体的深度,十分关注上述沟通的深度。为确保这种深度,他不会就沟通而谈沟通。例如,他在提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时,往往会考虑这些沟通的基石,如人的心智培育,而心智的培育必然会涉及个人独思、反思的场景,尤其是从大自然汲取养料、灵感和启迪的场景。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论述常常遭到误读。前文提到的怀特就曾指责他一度沉溺于“个人英雄的再现”,另一位批评家克拉克也曾断言《序曲》“宣扬个人主义思想”。[9](P.94)这些指责的理由是《序曲》的大部分篇幅所呈现的是诗人独处的画面。丁宏为曾经从华氏笔下“悲曲”意象所代表的“基本的、永在的、普遍的状况”入手,驳斥了那些指责华氏“见河山而不见现实”的观点。[6](PP.6-7)丁宏为还举了《序曲》中批评现行大学的浮躁,同时憧憬理想学苑的例子(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
一个娴雅端庄的所在,反刍
动物的乐园,恬静的生命能自由
徘徊;河旁有苍鹭喜欢伴着
缓缓流水进餐,翠柏尖顶的
鹈鹕孤身独憩,在冥思默想中
沐浴太阳的光芒。[5](P.69)
此处的“反刍动物”、“孤身独憩”和“冥思默想”都有独思独行的意味,但是诚如丁宏为所说,“诗人作为‘反刍动物’(ruminating creatures)不是逃避生命能量,而是力求更多、更细地汲取生活滋养”。[6](P.5)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华氏笔下“孤独者”的形象并非断绝了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就《序曲》而言,虽然大量篇幅展现语者(第一人称叙事者)独处的情景,但是他并非为了独处而独处,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人相处。
这么说的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序曲》语者在孤独中所思考的大都是人类的共同命运。还在学童时代,他便开始独自思考一个人如何从小就“与生机盎然的/宇宙结下患难与共的友情”。[5](P.40)他还提到自己跟柯勒律治从少年时代起就“志同道合”,都“在孤独中追寻着同样的真理”。[5](P.48)诗中“沉思默想”和“独自游荡”的字眼频频出现,但是语者所观所思的对象却并不孤独。例如,第四卷“暑假”中,写他如何在漫游时“回到沉思默想的世界”,可是紧接着就出现这样的文字:“当时/人间的生活也让我产生/新奇感,我爱那些人的劳作,所指的/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惊奇地看到,这安宁的景象犹如/争春的花园,数日不见就现出/不同的姿色,因为(当然不必/谈论某个花园的变化),在这/狭小的山谷中,人们互为邻舍……”[5](P.88)此处,尤其是“我爱那些人的劳作”和“人们互为邻舍”那两句,诗人的共同体情怀跃然纸上。在快接近全诗尾声时,语者有这样一段思考:“……当时我说:/‘该审视社会大厦的基础,看一看/那些靠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们,/劳作之繁重大大超过其所能,/还要承受人类自我强加的/不公正,但他们拥有多少心智的/力量,多少真正的德行!’为做出/这一判断,我主要着眼于自然界的/人类群落,农民耕作的田野/(何必再寻他处?)……我仍然渴望在骚乱中找出具体的事实与情景,引起更贴近我们个人生活的同情……”[5](PP.330-331)学术界对这一段文字的解读一般都聚焦于华氏跟葛德汶的争论(葛氏主张把美德建筑在学识之上,其理由是农民过于愚昧,不足以代表美德,而华氏则认为农民拥有心智的力量和真正的德行)。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诗人在此表达了强烈的共同体关怀,或者说对共同体的深度关怀,因为它涉及了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主要依靠对象,以及(由在大自然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所引领的)共同体伦理。同样具有深度意义的是“更贴近我们个人生活的同情”这一句,它所蕴含的思想跟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同情观”毫无二致(爱略特深受华氏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高晓玲在研究爱略特时这样说:“‘同情’,有时可以被理解为同胞感(fellow-feeling),强调共同的情感体验,以区别于居高临下的怜悯姿态……‘同情’则侧重于主体对他人感受的认同体验,或者说主体之间的情感流通。这种同情经常显现出比冷静的理智更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10](P.11)这段话同样也适合于解读华兹华斯。
其二,《序曲》语者常常独憩于大自然的怀抱,为的是从中悟到共同体的真谛。他在第一卷中强调:“我的灵魂有美妙的播种季节,/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共同育我/成长……”[5](P.12)这种培育看似只跟个人有关,但是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个人心智的培育。前文提到,共同体的建设首先要从破除对工具理性/机械主义的迷信入手,而《序曲》语者从大自然中得到的启示恰恰能帮助他破除上述迷信,如他在“开始追求她(笔者按:指大自然)”后得到的启示:“……有谁会用几何的/规则划分他的心智,像用/各种图形划定省份?谁能/说清习惯何时养成,种子/何时萌发?谁能挥着手杖,/指出‘我心灵之长河的这一段源自/哪方的泉水’……”[5](PP.38-39)传递同样思想的文字在诗中俯拾皆是。例如,《序曲》第六卷和第八卷中就不乏“击败理性主义的片段——惊奇、震慑、变故、机遇和厄运交替出现,抵制理性的钳制”。[11](P.922)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审美情趣和审美判断,而后者正是共同体建设所必需的,所以诗人-语者“常观/大自然的形态,从中获取了审美的/尺度”。[5](PP.133-134)对审美的诉求在第十三卷中又得到了加强;它的标题就是“想象力与审美力,如何被削弱又复元”,而使之复元的是大自然(语者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如下启示):“应以兄弟的情谊/看待卑微的事物,尊重这美好的/世界中它们那默默无闻的位置。/经过如此(笔者按:即大自然的)调教与安抚,我再次/发现,人类社会能给予欢乐,/能承接我的爱与真纯的想象。”[5](PP.328-329)此处的共同体情怀再明显不过了。在同一卷中,语者还坦言大自然帮助他“澄清什么会持久,什么将消逝;面对那些以世界的统治者自居、将意志强加给良民百姓的人们,我看出他们的傲慢、愚蠢、疯狂,不再感到奇怪;即使他们有意于公共福利,其计划也都未经思考,或建筑在模糊或靠不住的理论上;我也让现代政治理论家的著作接受其应有的检验——生活的检验:人间的生活……于是看清,那冠以‘国家财富’大名的偶像多么可怕……”*基本参考丁宏为的译文,个别文字作了更动。[12](P.518)这里的“公共福利”、“人间的生活”和“国家财富”都属于共同体关怀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冠以‘国家财富’大名的偶像”那一句显然是针对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华兹华斯嘲讽斯密的理论,称其为“模糊或靠不住的理论”,这跟他对葛德汶理性/机械主义思维模式的批判是一致的。这种批判一方面有赖于从大自然汲取的审美尺度,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对共同体的深度关怀。
以上分析表明,在华兹华斯的共同体思想中,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威廉斯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社会和个人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长的过程”,[8](P.118)这一观点其实早在华氏那里就生根发芽了。学术界常常误指华氏宣扬个人主义,其实是不理解他深谙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深究个人,就没有共同体的深度。
二、共同体中的陌生人
共同体思想的深度还体现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方面。假如一个共同体容不下陌生人,或者让陌生人受到冷遇,那它就毫无深度可言。华兹华斯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思考。英国沃里克大学乔恩·米教授曾经注意到华氏喜欢描写陌生人相遇、交谈的情景,并称之为“华兹华斯邂逅诗”(the Wordsworthian encounter poem)。乔恩·米虽然欣赏华氏对陌生人的关注,却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华兹华斯邂逅诗中,经常出现比较正式的交谈,经常再现至少牵涉两个交谈者的场面,但是交谈的结果很少是相互理解。人的内心抵制揭示。”[13](P.192)乔恩·米的这番话是对耶鲁大学教授布罗米奇的呼应。后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提出,华氏诗歌给人以这样的总体印象:“每个人的道德动机都很特殊,我们永远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动机,因而也无法对它们作出判断。”[14](P.65)情形果真如此吗?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华氏笔下的共同体就缺乏深度了——缺乏相互理解的“交谈”谈不上深度沟通,因而也构不成深度共同体。
不知为什么,乔恩·米在论证上述观点时“醒目”地忽略了华兹华斯的《序曲》。然而,《序曲》不乏(陌生人相互)深度沟通的例子,哪怕如前文所述,它常常因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受到诟病。在第七卷“寄居伦敦”中,诗人对人们“互为邻舍,却不相往来”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那里的人们/怎么可能互为邻舍,却不相/往来,竟然不知道各自的名姓。”[5](P.171)针对这一情形,诗中有许多正面的描述,都可以看作对共同体的提倡、想象和憧憬。在第二卷“学童时代(续)”中,诗人-语者对柯勒律治这样倾诉:“我的朋友!你在都市中长大,见惯异样的景象,但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最终达到同一目标。为此我才与你交流……”[5](P.48)显然,“为同一目标”而进行的“交流”是一种深度交流。在第四卷里,诗人-语者在旅途中跟一位疾病缠身的老兵邂逅,在开始交谈时,后者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流露,让人觉得/陌生”,但是诗人-语者帮助他在一个农舍里找到安歇之处(在此,农舍主人的共同体情怀也不言自喻),随后便出现了如下动人的一幕:“看到他能在舒适中安歇,我这才/放心,并恳求他此后不再在/路边伫留,如此身体状况,该及时求助于车夫或他人的帮助。/听到我的责怪,他脸上又现出/那种幽灵般的温柔,慢慢说道:/‘我信赖至高的上帝,我信赖从我/身旁经过之人的那双眼睛。’”[5](PP.97-98)这里,“信赖”一词的连续出现,以及“幽灵般的温柔”,表明陌生人已经不再陌生,原先陌生的情态可以通过深度交流来化解。
在第九卷“寄居法国”中,诗人-语者与一位陌生的军官邂逅,两人一见如故,陷入“长谈,/一次又一次,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5](P.247)他们的交谈涉及“一些十分美好的话题”,而且他们都致力于“通过/扩散而不衰竭的知识,使社会生活/公正有序,明净清纯”。[5](P.245)这样的交谈分明是关切共同体的深度。值得留心的是,第九卷几乎有一半的篇幅被用来呈现上述长谈,其共同体情怀呈递进态势。例如,在“使社会生活/公正有序,明净清纯”那一句之后,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列出古代故事里的壮举/……以及世间平民/百姓如何相互安慰,相互/激励……分散的/部落如天上的云朵遍布各方,/却能共持新见,结成一体。/……一边交谈,/一边默思着理性的自由、对人类的/期望、正义与和平,啊,这是/何等的甘美!……”[5](PP.245-246)此处的共同体情怀已经超越了地域、国度,达到了人类大同的境界。尤其令人回味的是“遍布各方,却能共持新见,结成一体”那一句,它体现了关于共同体之根的深度思考。共同体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是扎在某块土地里,还是扎在某种见解/观点中?这在英国历史上曾引起过不少争论。怀特曾把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看作“观点派”的代表,因为他认为共同体“就扎根于某种世界观”,或者说“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世界观”。[2](PP.152,177)依笔者之见,华兹华斯也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甚至更胜一筹。须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华氏的上述诗文还从深层次上回答了陌生人如何认同共同体的问题,以及每一个共同体成员怎样对待陌生人的问题:对每一个具体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与陌生人相遇、相处乃至互相沟通是无法回避的日常生活现象;一个共同体是否有凝聚力,取决于每个成员怎样想象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包括想象陌生人,这是“因为即便在最小的民族里,每个成员都永远无法认识大多数同胞,无法与他们相遇,甚至无法听说他们的故事,不过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存活着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影像”。[15](P.6)也就是说,对每个共同体成员来说,大部分同胞都是陌生人,那么怎样才能在彼此陌生的人中间产生凝聚力呢?华氏的“共持新见,结成一体”实在是精辟的解答。
事实上,与陌生人相遇和沟通的情景在《序曲》中比比皆是。例如,在第十三卷中,诗人-语者强调自己“还珍视另一种经历”:
在能让我静思的地方独行数日,
采撷那些一步步将我引向
智慧的知识;或像个乘风远来的
小鸟,轻盈,欣悦,向陌生的田野
或丛林高歌问候,而他们也不会
沉默,必做欢迎的回声;或当这
快乐的跋涉不再有趣,我会
与人交谈——在荒凉的旷野,面对
前伸的漫漫长路,或在农舍的
长椅旁,在旅人歇脚的泉边;在这样
的地方,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见。[5](P.332)
“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见”,这分明是深度共同体才有的境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境界与“独行数日”并不矛盾——独行的诗人“像个乘风远来的小鸟”,这表明他是大自然的有机部分,而正是在有机生成的、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共同体中,路人相见才会有似曾相见的感觉。这些深刻的寓意,显然未能被怀特们理解,也遭到了乔恩·米们的曲解。我们不妨再举一例,说明华氏心目中陌生人之间沟通所应达到的程度:“……当我开始打量/观察、问讯所遇到的人们,无保留地/与他们交谈,凄寂的乡路变作/敞开的学校,让我以极大的乐趣,/天天阅读人类的各种情感,/无论揭示它们的是语言、表情/叹息或泪水;在这所学校中洞见/人类灵魂的深处……”[5](P.333)这里,“无保留地与他们交谈”、“天天阅读人类的各种情感”以及“洞见人类灵魂的深处”都明白无误地指向了深度沟通。在具有这样深度的共同体里,即便发生乔恩·米所说的“内心抵制揭示”,也肯定是暂时的现象。
在华兹华斯的笔下,还有跟上述情景截然相反的描写,如《序曲》中诗人-语者在剑桥经历的社交场面:“所见惟有浮华的青年:漂亮的/蝴蝶纷纷在眼前招摇,喋喋/不休的鹦鹉在耳边饶舌;人的/内心似无轻重,外部世界/只有浮华俗丽的场景。”[5](P.69)这段描写属于诗人-语者的反思部分——他反省自己曾经喜欢跟同伴们“高声喧闹,在无益的闲聊中/耗去……时光”;此时的分贝很高,却毫无意义,因为交谈者并“不寻求与他人共享内心的/欢愉”。[5](P.62)在这种场面的反衬之下,全诗中频频出现的陌生人相遇、相谈、相助乃至相知的画面就显得更加感人。通过这种对照,华兹华斯传达了一层深意:只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便是陌生人之间也会有深度沟通;相反,若无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即便是熟人之间也只能形同陌路,沟而不通。
在华兹华斯的词典里,“陌生人”还包括所有的死者。他的许多诗歌中都出现了坟地和出殡队伍的意象,如《漫游》第二卷中的一幕:诗人-语者和漫游者(the Wanderer)在旅行途中跟一支送殡队伍相遇,他俩被出殡者所唱的挽歌深深打动:“在坟墓中您的爱是否被人感知?……”[16](P.63)对诗人-语者和漫游者来说,那位躺在灵柩里的死者肯定是陌生人,但是那段歌词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那歌词说出了华氏心中的境界: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应该包括那些已故的人们,尽管他们可能只活在很遥远的年代。当漫游者目睹出殡者庄重地、轻轻地安葬死者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哪一个旅者目睹此情此景,/不管他来自多远的地方,不管他有多么陌生,/会不承认博爱的纽带呢?……”[16](P.69)用博爱的纽带连接生者和死者,这不失为一种共同体情怀。诗中更发人深省的是漫游者和独居者(the Solitary)之间的一段对话:独居者把他所看到的一个下葬者称为“倒霉蛋”,而漫游者则称那些安葬在郊区墓地的死者为“有福之人”,理由是“他们生前收获千般爱,/死后总有人悼念”。[16](P.70)当时在场的诗人-语者也表明了态度:“独居者(称死者为‘倒霉蛋’时)带着一丝有嘲讽意味的笑容,/这让我颇感不快……”[16](P.70)也就是说,华氏对这个独居者所代表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描绘的图景中,那些已故者往往是家庭、社会/共同体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在名诗《我们是七个》中,七兄妹之一的小姑娘在姐姐珍妮和哥哥约翰相继去世之后,仍然坚持自己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全诗的情节围绕她跟诗人-语者“我”之间的对话展开):
“有两个进了天国,”我说,
“那你们还剩几个?”
小姑娘回答得又快又利索:
“先生!我们是七个。”
“可他们死啦,那两个死啦!”
“他们的灵魂在天国!”
这些话说了也是白搭,
小姑娘还是坚持回答:
“不,我们是七个!”[17](PP.24-25)
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对话,除了传递小姑娘对家人的真挚情感之外,还具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小姑娘真情流露,实际上是给诗人-语者上了一课;对于后者来说,珍妮和约翰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是他确确实实被小姑娘的回答所打动了,因而对那些已故的、从未谋面的同胞们多了一种新的认识,一份新的情感——从“回答得又快又利索”、“坚持回答”和“说了也是白搭”等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诗人-语者对小姑娘的钦佩、认同,以及有关文化层面的反思。
当我们重温华兹华斯有关“陌生人”(包括已故同胞)的思考时,我们不禁会想起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相关思想。艾略特在《文化定义札记》(NotesTowardsTheDefinitionofCulture,1948)一书中对当代人的家庭概念(其实跟共同体概念有关)提出了批评,因为后者往往只包括生者,而且大都不超过三代人。针对这一现象,艾略特阐述了自己的文化思想:“当我说到家庭时,心中想到的是一种历时较久的纽带:一种对死者的虔敬,即便他们默默无闻;一种对未出生者的关切,即便他们出生在遥远的将来。这种对过去与未来的崇敬必须在家庭里就得到培育,否则永远不可能存在于共同体中,最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18](P.44)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艾略特此处直接用了“共同体”一词,直接把共同体的命运跟对待死者等陌生人的态度联系在了一起。应该说,华兹华斯早于艾略特一百多年就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而且给予了诗意的表达。
参考文献:
[1]Lucy Newlyn. “ The Noble Living and the Noble Dead”: Community in The Prelude[M]//Stephen Gill.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Wordsw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Simon White.RomanticismandtheRuralCommunity[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Ferdinand Tönnies.CommunityandCivilSociety[M]. Trans.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Matthew Arnold. 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M]//Kenneth Allott.Ed.ThePoemsofMatthewArnold. London: Longmans,1965.
[5]威廉·华兹华斯.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M].丁宏为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6]丁宏为. 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William Wordsworth. The Tables Turned[M]//M. H. Abrams. Ed.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 Vol. 2.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6.
[8]Raymond 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1.
[9]Timothy Clark.TheTheoryofInspiration:CompositionasaCrisisofSubjectivityinRomanticandPost-RomanticWriting[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高晓玲. “感受就是一种知识!”——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知作用[J]. 外国文学评论,2008,(3).
[11]Susan Wolfson. The Illusion of Mastery: Wordsworth’s Revisions of “The Drowned Man of Esthwaite”,1799,1805,1850[J].PMLA,1984,99(5).
[12]William Wordsworth.TheCompletePoeticalWorksofWilliamWordsworth[M]. London: Edward Moxon, Son & Co., 1869.
[13]Jon Mee.ConversableWorlds:Literature,Contention,andCommunity1762to1830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David Bromwich.DisownedbyMemory:Wordsworth’sPoetryofthe1790s[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5]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1991.
[16]William Wordsworth.TheExcursion:APoem[M]. New York: C. S. Francis & Co., 1850.
[17]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诗选[M]//杨德豫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18]T. S. Eliot.NotestowardstheDefinitionofCulture[M]. Croydon: Faber and Faber,1948.
(责任编辑:吴芳)
The Deep Community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YIN Q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Recent studies by Lucy Newlyn and Simon White have shed light on a sense of community as revealed in Wordsworth’s poems, but they have either laid an exclusiv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a community or put the notion of individual in antithesis with that of community, thus losing sight of their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ordsworth’s views on community are, in fact, multi-dimensional and develop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must therefore approach the issues concerned by examining them in a broader context. Although Wordsworth never used the term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his views coincide with those of Raymond Williams who invented the term: by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Williams means “the deep community” that makes “communication possible”. What concerns Wordsworth in his imagined communities is exactly how to make the above-said communication possible, so his ideal community is nothing short of a deep community. Reading Wordsworth’s poems is reminiscent of T. S. Eliot, who forged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fate of a community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strangers, including the dead. It remain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Wordsworth anticipated T. S. Eliot b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at their thoughts, though similar, were rendered more poetic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Key words:Wordsworth; deep community;ThePrelude; communication; stranger
收稿日期:2015-05-19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9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