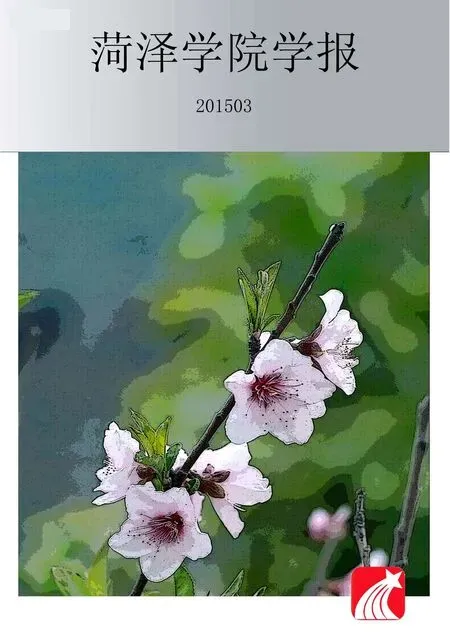《诗经》与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谭本龙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作为我国早期出现的两部重要的诗歌文学经典,《诗经》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后世,楚辞则以浪漫主义文风成为后继文学发展的滥觞。虽然二者艺术风格不同,但在艺术形象塑造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诗经》中关涉女性形象的诗篇超过三分之一,这些形象自然朴素,特点鲜明,生动地再现了周代女子的日常生活。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更多,而这些形象却旖旎飘渺,与《诗经》中的大为不同。细致分析二者中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原因,对深入理解两部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现实主义诗风的典范,《诗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氓》中的弃妇、《卷耳》中采摘卷耳菜的思妇属于普通劳动女性;《卫风·硕人》中的庄姜、《巢鹊》中将要出嫁的姑娘则来自贵族家庭,阅读这些篇章,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形象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和劳动场面为具体背景的。楚辞作为浪漫主义诗风的开山之作,人物原型大都取自幻化的神女或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如山鬼、湘夫人和少司命等等,尤其是《离骚》中的宓妃更为典型。将来自不同的创作原型和背景的审美形象仔细对比,发现二者在具体审美形态上有以下几点差别:
外貌特征不同。《诗经》中凸显的是女子的自然朴素,是一种不施粉黛的纯粹的美丽,多直接用“窈窕”、“美”、“姝”、“娈”、“淑”、“清扬”等表示美好的词语去直接刻画女性之美。如《周南·关睢》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郑风·野有蔓草》之“有美一个”,《邶风·静女》之“美人之贻”、“静女其姝”、“静女其娈”,《陈风·东门之池》之“美孟淑姬”、《鄘风·君子偕老》之“清扬宛兮,宛如清扬”,等等。即便是有所修饰,选取的也都是自然界中的事物来比拟形容。《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郑玄注:“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通过反复咏叹,用月亮之皎洁来比喻美人之白皙。《周南·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歌用自然界中的桃花来比喻女子姣好的容颜;《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用树叶的娇嫩来比喻女子的年轻芳华。《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美人是《硕人》中的庄姜,她虽然是一名贵族妇女,但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236的美感:“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虮,齿如瓠犀,螓首峨眉。”以自然之物柔荑、凝脂、蝤虮、瓠犀、峨眉等作为喻体来进行比拟,有一种清新自然之感。
再看楚辞。楚辞作者常常借助华美的服饰和精致的佩饰来装扮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酩些,娘光吵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甜,艳陆离些。”《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华丽的装束几乎成为楚辞女性的共同特征。除了整体服饰的华丽,她们对于细节也十分关注。许多楚辞作家对奇异的服饰非常钟爱,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哀”,因此,他们笔下的女性对于精美的佩饰也有着特殊的喜爱。《招魂》:“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可见,像“袂”和“佩”这样的佩饰是《楚辞》中女子随身之物,她们不会放过一点能使自己绽放光彩的机会。在描绘女子外貌形象时,楚辞中多选取艳丽色调的词语来烘托女子的千娇百媚。《大招》之“朱唇皓齿”、“粉白黛黑”、“青色直眉,美目顿只”,多彩的颜色使得这些女性更加娇媚迷人,从头到脚都给人一种华美艳丽的审美感受,也给历代读者一种挥之不去的视觉冲击。因此,她们的美不同于《诗经》中女子的简单朴素,而全部是精心雕琢。钱钟书先生曾说:“和中原女子‘淡如水墨白染’不同,大凡楚国漂亮的女子无不如‘画像之渲染丹黄’。”[2]这是对《诗经》中女子和楚辞中女子形象特征差异最为深刻的评价。
在身材体态上,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诗经》在审美上更加注重实用性,体态健美,身材高大成为当时评判女子美丽的标准。《诗经》中多次用“硕”、“敖”等表示高健硕大的词语来描写女子的身材体态,体现出女子的力量之美。《陈风·泽陂》描绘女性时说:“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兰,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泽之陂,有蒲与菡。有美一人,硕大逐步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这是一个男子赞美心仪女子的一首诗,显然“硕大逐步且俨”的女子是他们心中向往的意中人。《诗经》中的贵族美人庄姜,她除了有美丽的容貌,同时也拥有着“硕大颀颀”、“硕大敖敖”这样高大的身材,这也成为她被评为美人的重要因素。
楚辞中的女子则多体现阴柔之美,对于身材的描写也多侧重纤细和柔弱。《大招》所说的“丰肉微骨,调以娱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为:“言好女之状,腰支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约而束之也。”[3]218宋玉笔下的东家之子“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也正是这种柔美形象的体现。“楚王爱细腰,国人多饿死”,楚灵王喜好腰身纤细的臣子,朝中大臣均节食瘦身来迎合这种审美趣味。楚王所好的细腰虽并非女子之腰,但对男子尚且有如此要求,可以想见的是,一个像《诗经》中那样长得“硕大敖敖”的女子,怎么能在国人中立足呢?这也能从中窥测出当时社会以瘦为美的审美风尚。女子不再以身材高大为美,纤细的腰和秀长的脖颈成为楚辞中女性所追求和向往的。这种审美标准也促使楚辞中的女性多具有柔美、娇弱的体态,根本无法把她们与劳动生产联系起来,这与《诗经》中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看来,同样是描写女子,但是《诗经》和楚辞对其描写则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人物风貌。
除了外在审美形态,二者性格特点也不同。《诗经》中的女性大都吃苦耐劳,性格直爽,具有阳刚之美;而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温婉哀怨的,似乎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愁绪。最能突出两者性格特征差别的就是她们在爱情表达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诗经》中的女子对爱情的表达更加简单而大胆,很少有忸怩作态之势。她们渴望美好的爱情,更会敞开心扉主动追求。《召南·摽有梅》的女子大胆地说:“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积极鼓励男子向自己表白爱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是表达女性对爱情的渴望,更是对男主人公的大胆鼓励。《郑风·狡童》中的女子则是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对男子的喜爱与期许:“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事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言语中甚至透露着甜蜜的气息。《郑风·褰裳》中的女子则更是大胆而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心上人的爱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言语中还透露出对自己的充分自信,反映了性格的率真与可爱。这些女性不仅敢于表达心中所想,也能在爱情中全力以赴,爱得大胆而热烈。《柏舟》之“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正说明了女子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而勇敢地挑战束缚,态度坚决而强烈,“惠而好我,携手同归”(《诗经·北风》),能为了爱情全力以赴,这种勇敢与坚毅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楚辞中女子对于爱情的表达却显得相当隐晦,她们多选择含蓄的方式表达。她们追求爱情但是却屡次遭到阻碍,始终得不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九歌》中的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结束,神女们总是因为各种无奈的原因不能获得圆满的结局。荷衣蕙带、来去飘忽的生命女神“少司命”,也无法主宰自己,面对爱情,只能发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哀叹,最终还是要“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转身惆怅别去;其他如湘夫人驾舟北上,可仍然迎接不到恋人;披着薜荔系着女萝,含睇宜笑,身形窈窕的神女山鬼认真地采兰花,挽杜衡,把自己打扮得风姿绰约,美丽迷人,并不畏路途遥远前去赴约,可最终也只能独自品味爱情失意的痛苦,发出“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叹息,也能在秋风飒飒草木萧萧中黯然离去。尽管她们有着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望,忠贞与坚持,可依旧逃离不掉“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悲剧结局。她们的爱情愿望就像是“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一样落空于现实,无法实现。整个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都弥漫着哀伤的情绪。
此外,在女性形象塑造的手法上,《诗经》楚辞也有所不同。《诗经》中多是直接描绘女子的外貌和形态特点,如描写庄姜,直接写其外貌的姣好,由静到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还有直接刻画其心理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点,《邶风·雄雉》曰:“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直接的心理描述,把女子对爱人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女子多情的性格特点也呼之而出。楚辞中女性形象的刻画虽然也有直接描写外貌和心理的场面,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对东家之子的描写:“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但是楚辞中最常用的手法还是利用场面来从侧面烘托人物的形象,使人物形象在场景中得到完整的表现。《九歌·山鬼》中的女神山鬼,精心准备了去见恋人,诗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路途的艰辛与环境的恶劣,“爬巫山”、“采灵芝”,苦苦等候,从白天等到黄昏,登高远望却只有茫茫的一片大海;另一位神女湘夫人,等不到湘君,于是不畏路途的艰险,自己驾着龙舟北行寻找。对环境的精心描写从侧面烘托这些女性在爱情中表现出的这种热情与主动,为了追逐心上人的不辞辛苦,锲而不舍,正体现了她们对于爱情的专注与执着。《少司命》从一开始就描写了一个芳香素雅的氛围,“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余。”美好高雅的环境正是为少司命出场所作的重要铺垫,这与少司命的形象气质相得益彰。
《诗经》和楚辞对女性刻画出现的差异性,在地域文化中可以找到多种成因,同时与创作主体的社会阶层也有联系。
地理环境影响民族性格,也是形成不同文化习俗的主要因素。《诗经》产生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北方民族坚毅勇敢的性格。加之不稳定的政治和连年的战争,使得他们隐忍,内敛,崇尚武力,具有阳刚之气。而楚辞则形成于长江流域,相比于北方,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易于生存,这使得南方人民柔弱、多愁善感。而险峻的自然地貌也使他们多具有奇特的想象。这种由自然地理形成的民族特征在文学上则体现为不同的审美标准和取向。
文化差异决定人的审美取向。《诗经》与楚辞中的女性差异与南北两地不同的文化承袭也有一定关系。《诗经》时期,北方的礼乐制度还处于不完备的状态,与后代相比,女子所受的礼法约束相对较少,仍然能够保持自我,对自身的感情可以进行大胆的表白与追求。而产生于楚地的楚辞在很大程度上受楚地巫文化的影响,巫术和祭祀活动是很多形象塑造的灵感和源泉,这为楚辞的浪漫主义之风提供了养料。《九歌》就是巫文化下的典型代表。王逸曾说:“《九歌》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3]282很多女性形象的神话色彩及其体现出的神异的朦胧之美都深受其影响。
人属于不同的阶层,阶层不同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也有差异。《诗经》的作者大多是底层的社会民众,其所见所感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点滴,他们的视角处于所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下,加之固有的文学素养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现实气息,表达方式也多是直白而简洁的。
楚辞是文人创作,作者的生活环境远离下层民众,同时他们的文学素养使其创作更多具有文人气息,描写刻画也更为细腻生动。楚辞的代表屈原,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身为楚国显贵,接触的都是上层贵族的生活,他笔下的女子形象都具有高贵的血统和身份,常常寄托着自己个人的理想与情感,人物形象就变得虚幻、朦胧有内涵。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就是“女人”,用“女人”象征自己,象征自己的遭遇与追求,花草、鸟兽、服饰、美女,在他的笔下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王逸《楚辞章句》早就对此作过表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兽臭物,以比奸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3这与《诗经》中简单、直接的劳动女子形象截然不同。
[1]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