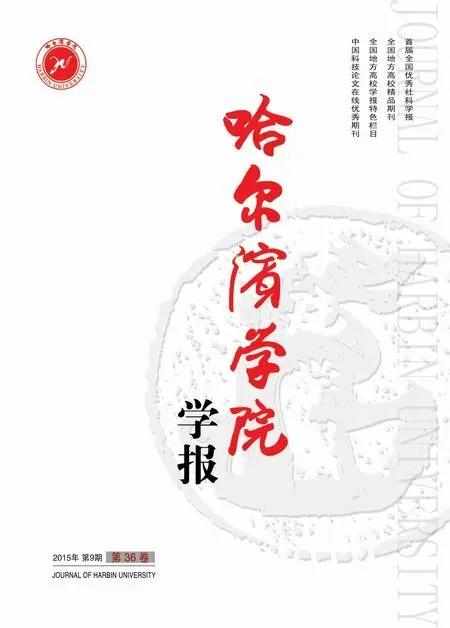以抗争求生存——论《空床日记》中的女性主体性构建
黄晓玲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以抗争求生存——论《空床日记》中的女性主体性构建
黄晓玲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摘要]如何解构男性话语、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的重要主题。作为女性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一直致力于构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空床日记》中,她从解构父亲主体形象来消解父权,从女性形象的颠覆来解构传统女性形象,创立自己的话语模式三个方面来建构女性主体性,使女性成为真正的言说主体,最终阐明女性在复杂的社会中对自我的追寻和人生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女性主体性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莲娜·西克苏认为,父权社会消音了女性的话语,女性被剥夺了表达的能力,处于失语状态,是被言说的他者;她们没有表达自我的能动性,没有自己真正的话语权。在英国文学史上,直到1813年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问世,才为女性的主体地位打下了基础。之后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大批女性作家。进入20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夫、莱辛继承并发扬了19世纪女作家的传统,主张从女性的内心世界来刻画女性,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玛格丽特作为20世纪后半叶的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她的每一部小说也都是现代知识女性对生活道路的一种可能的尝试,这种种尝试体现着现代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的艰难历程。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迄今为止已有多部反映女性心声、探问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优秀小说问世。她的《空床日记》发表于2002年。①
国内对于《空床日记》的研究迄今为止并不多,其中期刊九篇,硕士论文三篇,研究角度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主题研究,如未怡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七姐妹的重生主题》,探寻了现代女性的一个追寻的主题,她们寻找自我的价值,追寻更理想的生活;[1]叙事研究,如相菲、徐建纲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小说〈七姐妹〉的女性主义叙事解读》是从热奈特的叙述理论入手,对《七姐妹》进行了女性主义叙述的解析;[2]女性研究,国内对于《七姐妹》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有一定的研究,如胡君、孙周年的《论〈七姐妹〉中女性存在的孤独困境》对女主人公坎迪达·威尔顿进行了解读,认为孤独是一种理性认知的人生态度。[3]玛格丽特在其创作中,一直致力于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女性自己的话语权。但对于《七姐妹》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研究者并没有涉及。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在社会生活关系,家庭生活中的独立自由地位。德拉布尔在她的小说《空床日记》中,意从解构父亲主体来消解父权,从女性形象的颠覆来解构传统女性形象,创立自己的话语模式三个方面,来建构女性主体性,使女性成为真正的言说主体。
一、父亲主体的解构
父亲是男权统治者的中心,是理性、力量、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他作为一家之长主宰着其他人的命运,神圣不可侵犯。对父亲形象的颠覆和解构是女性作家从男性文化秩序的阴翳中走出的结果,是女性由无意识觉醒到自主觉醒的一次华丽蜕变。
在《空床日记》中,玛格丽特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妖艳的茱莉娅”“富有外国情调的阿奈”“精力充沛的杰罗德尔太太”等众多女性形象,来展示女性的多彩世界,而父亲的形象则没有正面出现,多是通过女性的话语淡淡带出。在玛格丽特突破常规的女性主体书写中,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形象大体有“背离家庭的安德鲁”“同性恋者巴克利先生”及“坎迪达的杀人犯情人”。
“无父”文本是一种隐性的弑父,玛格丽特用遮蔽的话语策略,把男性从女性的生存空间中移置出来,以空缺的结构形式否定父亲的权威和权力,通过对父亲形象的摧毁、父亲的不在场等方式驱逐和消解父权。在《空床日记》中,玛格丽特主要以两种方式消解父权,其一,父亲形象都是由女性主体介绍出席,一直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以安德鲁为代表。其二,父亲们以不健全的人格出现,如安德鲁的出轨,坎迪达情人的入狱以及同性恋杰罗尔德先生。
在《空床日记》中,与小说中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对比的是男性角色,他们不仅没有作为男性主体出席,即使被女性提及时,也只是言片语,作为他者身份的男性失去了自己的言说能力。安德鲁是小说的男主角,但却从未正面出现,一直是作为他者被坎迪达在日记中提起,“我注意到在这本日记里已经三次提到安德鲁了”,“他是长相十分英俊的英国人,在各方面表现很出色”,“他是大家迷恋的对象”,“他对于我来说成了英国最爱慕虚荣的人,最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在小说中,安德鲁以一个“他”的形象出现,玛格丽特打破了“菲勒斯中心”的男权文化。
男性的集体失语现象还体现在小说中另外两个男主角也都是以不健全的人格出现。在离开萨福克小镇后,坎迪达开始了新生活,在伦敦的情人一直没有正面出现,在日记中极少出现的频率却也能使其性格得以呈现。“我的情人在大联合运河淹死了人,进了沃尔姆监狱,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但是我怀疑他是故意的。我在那儿趟过水,可是水只到我的膝盖”。作为坎迪达在伦敦的情人,本应该频繁出现在其日记中,但事实上出现极少,并以凶残杀人犯的形象出现。同时七姐妹中只有辛西娅有着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巴克利先生温和而善良,但 “巴克利先生是一个同性恋”。同性恋的描写祛除了男性气质,剥夺了男性作为父亲的权利,男性的神圣也就不复存在,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主体被解构。在《空床日记》中,男性被贴上了落后腐朽、凶狠残暴的标签。
在《空床日记》中,男性基本丧失了叙述情节的功能,以被言说者的形象出席。这种“父性缺席”的文本模式极大地消解了不可冒犯的父权意识形态,使“菲勒斯中心”的男权制文化秩序消隐于历史的舞台,让女性有足够的文本空间去书写被压抑的主体意识,从他者的边缘客体地位走向成熟的主体性地位。
二、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
在女性写作中,女性作家往往超越菲勒斯文化传统,努力寻找具有颠覆性的概念。长久以来,菲勒斯文化传统中女性作为家中的angel,应该对丈夫顺从,对儿女们倾注所有的心血。然而在《空床日记》中,坎迪达面对不幸的婚姻选择离开,她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她想要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与此同时,她也忽略了作为妻子的职责。“他总是想要得到我从未给予,也从未得到过的东西。也许,这些罪恶正是从我的不足中才慢慢滋长起来的。”她一直冷漠地和丈夫保持距离,从未给予他所想要的,他们彼此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在萨福克的最后几年里,坎迪达的所作所为不再像一个淑女。为一些小事发脾气,下午睡眠时间很长,在行为举止上有轻度的精神错乱和更年期症状。在学校里,她不肯出力帮忙,在学校工作人员剪掉贝母属植物时,对他大叫大嚷。她不再支持丈夫。她从丈夫的床上下来,说她喜欢独自一人睡,借口说是睡眠质量太差,老是失眠。她老是晚上盗汗,皮肤却还是干干的。坎迪达用她原初的思想观念来解读他们的婚姻关系,当长久地付出得不到回报并换来的是背叛,她选择叛离而不是重归于好,逃离传统的妻子角色,也是坎迪达走向自我成熟的道路。
H·奥特曾说过,“母女关系本是女人的人际关系中最具亲和力、最柔韧恒久的关系,是人在其真实、在其此在的深层里所遭遇到的真实,是最特殊的生命体验”。[5]然而《空床日记》中,坎迪达对女儿们却是漠不关心。她以嫉妒和不信任的目光死死盯着俊俏的大女儿伊泽贝尔。她从没去芬兰看过二女儿埃伦,对她的境况也从来不了解。发现装腔作势的三女儿,控制不了自己强烈的反感。波伏娃也曾提出:“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6]在婚姻生活中,坎迪达不仅被丈夫抛弃,女儿们对其也是不冷不热。而坎迪达对母亲形象的反叛和解构,对本应该是和谐的母女关系的挣脱和否定,也意味着女性在自己努力挣脱束缚的过程中的艰难与痛苦,意味着女性对自身的深层发现:拒绝慈母形象对女性的压抑和角色规定,这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使之渐趋成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女性在社会上开始享有了比较广泛的平等权利。新世纪的女性摆脱了“屋子里的天使”的狭隘角色,投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前所未有的平等和自由。《空床日记》中的坎迪达在与丈夫离婚后,毅然决定离开小镇萨福克。在离开萨福克后,她选择了“伦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去往伦敦时,萨福克小镇的人们“都认为我搬到伦敦去是丧失了理智了”。但是,人们越是反对,坎迪达却认为“在伦敦,某种激动人心的事情会发生的”。在开始自己在伦敦新的生活的时候,她“有些紧张有些兴奋的提着手提箱爬上这肮脏的劣质公用楼梯,跨过门槛,走进属于自己的生活”。小小的房间里“摆放着我学生时代用的一张书桌,一把手扶椅和一个书柜。一张小小的饭桌,配上四把木椅”。“情况大致如此,这是我的小小王国”。这让我们不由的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开篇伍尔夫就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7]仅从字面上看,这是在说明女性创作的基本条件——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特定环境才能做成事情。在《空床日记》中,坎迪达作为一个新女性的代表,最终她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她“得到了一笔钱”,因此也就能开始自己的意大利之旅。“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是女性的栖身之所和理想的逃世之地,也是实现自我意识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屋子,女性才可以将强悍的男权意识尽可能排除在女性世界外。女性的生存处境与房子和经济地位有关,想要实现自我,女性必须争取到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小小王国以及自己的收入。
三、女性话语的书写
在女性作家的眼里,女性主义文学是对男性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颠覆,是对作为语言本身的男权话语的拆解,是对女性话语进行重新书写。“女性写作”的观点源于法国女性主义者海伦娜·西苏,她强调女性写作对于女性主体的重要性:“我要讲讲妇女写作,谈谈它的作用。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意志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②《空床日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写作典范,小说从多个女性的生活入手,以多重叙事角度和叙事声音结构上来打破男性作家主导的单一的叙事角度以及叙事声音。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空床日记》通过叙述角度的不断变化,来打破父权制语境下单一的叙事角度,书写女性自己的话语,建构女性主体性,使女性真正成为思维主体与言说主体。《空床日记》共四部分:“她的日记”“意大利之旅”“埃伦的说法”及“尾声”。第一部分“她的日记”是主人公坎迪达以第一人称叙,采用日记的形式叙述了其学生时代以及婚姻生活。第二部分“意大利之旅”,采用了全知视角,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七姐妹的旅行,以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全方位关照。第三部分“埃伦的说法”则颇有新意的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看主人公的性格和突然离世,用他人的口吻重新叙述坎迪达的婚姻生活,有利于读者进一步从他人口中来认识主人公。而这一部分中死亡其实也只是主人公想象出来的“死亡体验”。第四部分的“尾声”,坎迪达重新回归,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参加二女儿埃伦的婚礼。小说的第一部分,玛格丽特用第一人称的“我”作为话语主体,用第一人称来突出以女性为主体倾向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方式在简·奥斯丁、伍尔夫以及莱辛等传统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中也被广泛运用。作为后现代女性作家,玛格丽特则打破常规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对叙述视角进行多重的转换。直到最后一部分“尾声”中第一人称的回归,也象征着坎迪达走出人生的困境,带着新的人生感悟回归生活。由于叙述视角的经常性转换,造成许多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很多的误解,但是深入阅读之后会发现,这其实是坎迪达在自我寻找过称中的心理空间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叙事声音”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是身份和权力的代名词,兰瑟曾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出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作者型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即第三人称叙述;个人型指“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即主人公叙述;集体型指“一系列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它既可以是第三人称全知,也可以是主人公叙事。[8]集体型叙事“她的日记”中,坎迪达以第一人称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但同时又穿插了作者型称叙述的小标题。比如:“她不顾疑虑,鼓励自己继续探究”。到“意大利之旅”的作者型叙述,坎迪达由叙述者又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以一个全知视角看待她们的整个旅行。第三部分“埃伦的说法”,埃伦以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的身份来看她的母亲坎迪达的生活,又回到了个人型叙述。第四部分的“尾声”还是以个人型叙述,主人公又切换到坎迪达。让我们看到以不同女性视角出发看待问题的不同。在西方,话语权威长久以来一直为白种男性所主导,女性想要在男性主导话语的挤压下获得话语权,就得贴近主导社会权力,借助其社会常规,或者变换写作策略,从内部瓦解其权力机制,从而呼出自己的声音,建构女性话语权威。
玛格丽特通过变换叙事视角,调整聚焦模式,以女性视角观察世界,女性变为主动观察者,而男性却成为被观察、叙述的客体,颠覆了传统男权叙事中女性被观察、被客体化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话语权,赋予女性评判周围人和事的特权,增强了女性叙事权威,体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张扬女性意识的思想。
在传统小说中,男性人物是规范和价值的标准,代表强势话语。但是在《空床日记》中,玛格丽特通过日记这一独特的形式,从而采用了主人公以女性为主体的叙述视角,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自己的命运。从解构父亲主体来消解父权,以女性形象的颠覆来构建新的女性形象,以女性的视角和语言描述了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主体经验, 最终书写了她对女性在这复杂的社会中对自我的追寻和人生意义的探讨,用以唤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
注释:①本论文中的中文翻译均采用了林之鹤的中译本《空床日记》,也有译者将其译成《七姐妹》。以下相关引文均引自此书。
②转引自顾雁翎、郑智慧,《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女书文化》(台北),1999年。
[参考文献]
[1]未怡.论《七姐妹》中的重生主题[D].四川外语学院,2011.
[2]相菲,徐建纲.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小说《七姐妹》的女性主义叙事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6).
[3]胡君,孙周年.论《七姐妹》中女性存在的孤独困境[J].文艺评论,2010,(2).
[4]德拉布尔,玛格丽特.林之鹤.空床日记[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
[5]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6]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7]弗吉尼亚·吴尔夫.贾辉丰.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9]苏珊·S·兰塞.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张新潮
[收稿日期]2015-01-22
[作者简介]黄晓玲(1989-),女,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09—0110—04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9.024
To Survive by Struggl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 in “Seven Sisters”
HUANG Xiao-l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How to deconstruct male discourse and construct women’s own subject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feminist writing. As a representative feminist writer,Margaret Drabble has been devoting to constructing women’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Seven Sisters”,the writer destructs the paternity by deconstructing their subject images,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female by oversetting the female image,and develop his own discourse model. The three aspects a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so as to make women the real discourse concern. Therefore,the women’s pursuit of self and meaning of life in the complicated society is expounded.
Key words:Margaret Drabble;“Seven Sisters”;female subj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