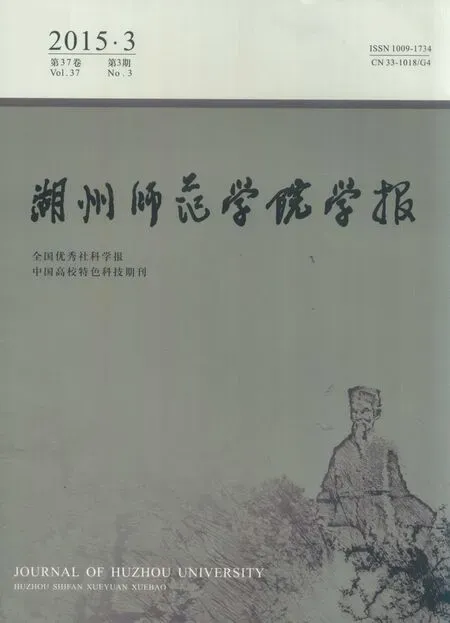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女性存在空间*
宋雪玲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310007)
魏晋时期,向来被认为是女性自由和解放的重要发展阶段。魏晋时期的女性存在空间,笔者将其分为社会空间、家庭空间以及情感空间。目前学界关于魏晋女性存在空间的研究,基本都将眼光聚集在女性的社会地位之变化上。[1]通过对《世说》有关女性条目的细致考察以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可知魏晋时期妇女的自由度曾被估计得过高了。笔者认为,魏晋时期的女性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魏晋时期女性仍居于礼教与非礼教之间的尴尬境地,在社会和家庭中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情感上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依然根深蒂固。因此魏晋时期的女性存在空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魏晋女性的社会空间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个人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这种局面刺激了人们内心重情感、重个性的独立思想的产生,在思想史上历来被认为是人的自觉的时期。所谓人的自觉,即指人对本身存在价值的重新体认。与前代相比,魏晋时期的女性,由于受玄风的影响,某些妇女可以像男性一样受到良好教育,拥有自己的财产,等等。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相对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度不应被估计得过高,以下具体论之。
第一,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女性仍然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即使是家世显赫的女性也依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世说·言语》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颍,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2](P103)
这则材料被列于“言语”篇,本意是为彰显乐广能言善道从而逃避灾祸一事,但是我们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当时女性的地位是何等低下!这则材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政权,为了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大封同姓诸侯王。这样避免了外戚宦官专权,但也为西晋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这一则故事就发生在司马颖讨伐司马乂这段时期。尚书令乐广在朝中拥有隆望,又是司马颖的岳父,司马乂自然担心他向着自己的女婿,所以对其进行盘问。乐广为了保住一家的性命,神色自若地说“岂以五男易一女?”顿时司马乂去掉了疑心。从表面上看,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乐广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短短一句话,使全家转危为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五男易一女”,在当时的社会是谁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舍此一女,则被认为是人之常情,因此这句话也得到了司马乂的认同。作为一个堂堂尚书令乐广的女儿,也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筹码而已。
第二,在《世说》话语环境里,女性也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如,《方正》篇载: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2](P365)
这则故事描述了一个道别的场景。临别流涕,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这里,周叔治的行为却被鄙夷了。被鄙夷的理由是“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即认为临别送行流泪,是女子的行为,正因为是女子的行为,所以才遭到了鄙视。其中侧面反映的士人对女子的态度显而易见。
另外,据《世说·德行》记载: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馀事,惟忆与郗家离婚。”[2](P48)
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东晋时期,王家是名门贵族。郗道茂和王献之少年夫妻,情真意重,志趣相投,两情洽洽。王献之风流蕴藉,乃一时之冠,新安公主仰慕已久,便离婚要求皇帝把她嫁给王献之。最终王献之忍痛休了郗道茂。王献之对道茂一直心怀愧疚,在他奄奄一息之际,做法的道士问他平生有何憾事,他长叹道:“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后悔与郗家离婚。”王献之在这则言语里,讲到“郗家”,仍然没有提郗道茂之名,这应是社会风气使然,女子处于家的笼罩之下,处于父兄的笼罩之下,即使是名门贵族,也难以摆脱固有的依附地位。
二、魏晋女性的家庭空间
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家国一体,社会的各种关系与家庭关系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夫、妇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构成元素,无论在什么时期,家庭关系都是社会关系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儒家主张以“孝”治天下,就是把天下看作是家庭的推衍扩展。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空间相比前代有了一些松动的趋势,地位有了一些提升,正如有学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结束和正统儒学的衰微,注重个体自我的存在成为新的核心价值观念,女性也试图从儒家的伦理纲常中挣脱出来,在婚姻家庭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大胆表露自己的情感,把握婚恋的自主权,追求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凭借才智在家庭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P31-35)这在《世说》中都有记载。具体地说,《世说》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处境尚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魏晋时期不乏在家庭生活中甜蜜和谐的女性,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世说·惑溺》载了以下两个故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2](P1075)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2](P1080)
这两则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荀粲惑溺”、“卿卿我我”已经成了形容爱情甜蜜忠贞的常用语。唐李贺在《后园凿井歌》中感叹:“情若何?荀奉倩。”其中的典故即是出自“荀粲惑溺”的故事。“卿卿我我”说的是古代著名吝啬鬼王戎之妻的故事,王戎在古代是个吝啬鬼的形象,但是由这则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生活美满而宽容的另一个王戎。这两则材料中都透露着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在魏晋时期,某些女性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尊重与真爱,有了不同往昔的地位了。
第二,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女子对家庭生活有了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直言批评自己的夫君。如《德行》篇记载“谢公夫人教儿”条: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2](P46)
谢安的妻子是沛国刘眈女,这则故事反映了她和谢安教子的不同方式。我们也应该看出另外两个问题,首先,在这则对话里,作为女性身份的谢公夫人,已经担任了教导子女的重任;其次,作为女性身份的谢公夫人,已经能够正面对夫君提出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已经基本实现平等对话了。
另外,如《贤媛》第十九又有一则关于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才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2](P820)
谢道韫是东晋著名才女。她出身于晋代王、谢两大家族中的谢家,乃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出身富贵。而谢道韫嫁到王家之后,非常看不起她的丈夫王凝之。《晋书》本传曰:“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4]](P2102)王凝之是个书法家,但迂腐至极,深信五斗米道,以至于兵临城下,他还不相信孙恩会杀他。仍浑浑噩噩,最后死得糊里糊涂,真是可悲可叹。避开王凝之实际的才能不说,谢道韫敢于直面鄙视王凝之,已经显示了独立意识的强化和升华。
第三,魏晋时期多数女性仍处于夫权的压制之下,处境仍相当尴尬。如《世说·任诞》载刘伶病酒的故事如下: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2](P857)
这亦是一则画面感超强的故事。刘伶是个酒鬼,《晋书》本传曰:“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4]](P1375)刘伶是个相貌丑陋的人,淡漠不语,喜欢交游。而且,其游戏人生玩世不恭到极致。这则材料历来被作为一则“魏晋风流”的确当证明,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将这则材料放在一个家庭之中,放在一个普通女子狭小的情感空间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另一种悲伤了。其中寥寥数句: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我们从中应该能够看到一个软弱的无奈的尴尬的不被理解的一个普通妇人的形象,“涕泣”而谏,其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期待,包含着多少包容与无奈。而后世阅读此则材料的人,也往往把目光集中于刘伶的放浪形骸之上,对其行为大加称道。一句“死便埋我”,简简单单,而谁又是这“魏晋风流”的被动接受者和受难者。
三、魏晋女性的情感空间
关于《世说》女性的情感空间,历来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婚姻家庭的角度阐释的,而综览《世说》,可见魏晋时期女性在纯粹的情感方面,仍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魏晋时期女子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仍然有一股潜流,就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表现为女子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为女子对爱情的固守。
《世说·惑溺》记载了著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2](P1078)
这则材料里的女性是西晋贾充的小女儿,也就是西晋皇后贾南风的妹妹。韩寿是贾充手下的官员,韩寿长得帅气潇洒。贾充每次召集手下的官员议事,贾充的小女儿贾午都要从窗户偷看,一眼看到了韩寿,立刻被他的帅气征服了。于是主动追求韩寿,贾充只好顺水推舟,把女儿贾午许配给了韩寿。在这个故事中,贾女痴情、大胆、主动,表现了对自由爱情的自觉追求。
另外,《世说·贤媛》篇载: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2](P822)郗嘉宾,即郗超。他的妻子是汝南周闵的女儿,周马头。郗超死了之后,周马头的兄弟要把妹妹接回家,而周马头却不愿意。她说:“活着虽然不能和郗郎同居一室,死了岂可不和他同葬一穴!”表现了对爱情的执着坚守。
第二,《世说》妒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感情空间依然狭小。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为妒妇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生长的土壤。生性妒忌的女性,历来是被抨击的对象。如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因善妒被废;晋惠帝贾妃妒忌其他妃子怀孕,害人无数;连文学作品《红楼梦》中薛蟠的妻子夏金桂也因为妒忌,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很悲惨的下场。《世说》中也有不少妒妇的形象,这些妒妇的出现,我们如果从男性的角度视之,可能觉得她们实在不可理喻;然而,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正是女性对情感空间被压迫被冲击的极端反抗,其中有自我意识觉醒的意味,亦饱含着当时女性情感空间的狭窄。
《世说》中最有名的妒妇要数贾充的后妻郭槐。《世说》载其故事: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2](P1076)
郭槐之妒,可谓登峰造极。贾充前妻李婉,是一位才女,出身名门,端丽贤淑。贾充娶了郭槐之后,郭槐妒忌,每当贾充出门,都生怕贾充是到前妻李婉那里去,所以总是使人跟踪。如果说郭槐因一位才女而怕丧失自己的地位,因而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地位低下的乳母都防范有加,的确是妒到了极致。
另外一个妒妇的例子,说的是谢安的妻子: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2](P817)
谢家的歌妓在跳舞,她不让丈夫看见,而且搬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恐伤盛德。”其实,这显然是女性内心脆弱的表现,生怕男子因为外界的诱惑而转移心思,从而丧失自己的地位。而从根本上讲,妒性越强的女子,生活得越辛苦,因为她们为自己的一切付出了太多的心思,往往在与人与事的频繁争斗中,弄得鱼死网破,结局未必全都如意。这也意味着她们情感空间的狭小和内心的极度脆弱。
第三,魏晋士人对门第之婚和女性改嫁有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是女性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贞节观的束缚。
魏晋时期士庶之间有着严格的婚姻界限,周一良先生认为:“六朝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5](P81)因为“宦”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稳固的基础,而“婚”则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关于魏晋时期人们婚姻观念的变化,宁稼雨先生已有详细的论述,强调了魏晋时期的门第之婚。[6]宁先生的论述有足够的依据,并整理了《世说新语士族婚姻谱》,但是仍有例外。如《世说·任诞》篇载阮咸故事: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母也。[2](P864)
阮咸,是阮籍之侄,也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这则材料是说,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马去追。追上后还穿着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匹马回来,说:“人种不可失”。阮孚即阮咸与此婢之子。在此,阮咸不仅突破了士庶界限,而且突破了民族界限和一般的伦理纲常。《世说·假谲》载了另一则故事,表现了当时魏晋士人对当时女性改嫁现象的宽容。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2](P1008)
尚书令诸葛恢的女儿先是嫁给庾友,庾友死后,诸葛女誓不再嫁。但是,其父诸葛恢仍然答应了江虨求婚。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改嫁一事还是能够接受的,甚至还持有比较支持的态度。但她的改嫁似乎包含着被迫的意味,说明在内心里还是存在着比较深刻的传统思想束缚的痕迹。
[1]李朝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J].作家,2008(12);李桂娥.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进步的妇女观[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4).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张小稳.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魏晋南北朝婚姻伦理的一个维度[J].伦理学研究,2014(3).
[4]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的变化[J].广州大学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