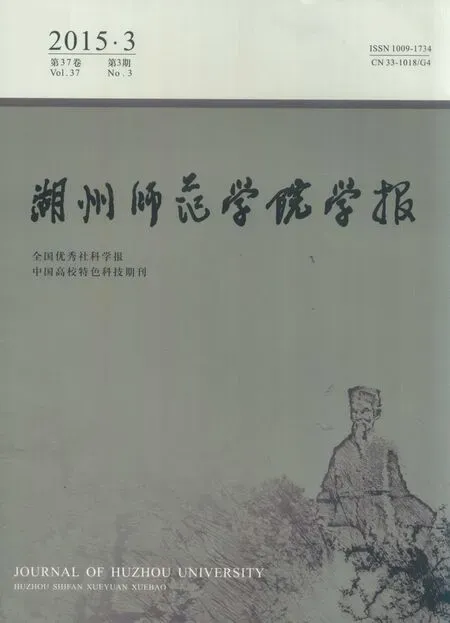民初遗民诗中的帝京想象与书写*
陈义报
(湖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湖州313000)
辛亥鼎革,在革命党人是“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1](P99)而在部分前清官员和士人心目中则是天倾地陷、神州陆沉。他们纷纷流聚天津、青岛和上海等海滨租界,成为了视“民国乃帝国也”的逊清遗民。关于他们的分布情况,据刘禹生《世载堂杂忆》引用胡小石的观察:“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中坚也”。[2](P136)除此之外,天津、北京、广东、四川、江西等地尚有部分遗民,著名者如鼎革后仍留居京城的帝师陈宝琛,南京的陈三立,定居在南昌的胡思敬,广东的汪兆镛、陈伯陶以及辛亥后出走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他们虽流散各地,但皆心怀魏阙,对曾经的帝京念念不已,在诗歌中一再吟咏感怀。这种吟咏感怀更多的是对旧时帝京“盛世景象”的一种想象和书写。在他们的书写中,帝京已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实体,而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经想象和回忆建构的文化风景,更是一种与他们身历之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的“王道乐土”。
一、暮年心绪与青春记忆
民初逊清遗民诗人大多出生于咸同之际。时至民国,大多已过天命之年,不少人甚至已过花甲,人生暮年伴随着辛亥鼎革一起来临。1912年,沈曾植62岁,陈三立59岁,郑孝胥53岁,陈宝琛64岁,瞿鸿机62岁,陈燮龙55岁,冯煦69岁,梁鼎芬53岁,缪荃孙68岁。有鉴如此,缪荃孙感叹到:“旧友相逢均白首,天涯何处买青山”。[3](P187)暮年心绪,可见一斑。
1912年四月,胡思敬自南昌来到上海,见到了一批故知旧交,这些故知旧交以“流人”自我指称,纷纷类聚于海滨沪渎:
苏庵居海藏楼,避不见客。节庵为粤人所忌,谋欲杀之,狼狈走免,身无一钱,僦小屋以居。子培伪称足疾,已数月不下楼矣。[4](P216)
由胡思敬的观察可知,遗民们暮年遭逢国变,普遍颓唐萧然、境况不堪。辛亥鼎革,旧有的社会秩序解体,士绅阶层日益边缘化,而顾念前朝且不仕民国的遗民更是与主流社会互为隔绝,暮年心绪与家国之悲重叠勾连,反映在诗文中自是满目的意兴萧然、感伤颓唐。鼎革后的郑孝胥销尽雄心:“少年南北行万里,销尽雄心最可悲。今日沧桑千万恨,高楼淙雨夜谈诗”。[5](P227)瞿鸿禨对春伤怀,幽怀故国:“故园开遍不可到,繁英飘泊纷西东。天涯坐对转惆怅,徒余泥雪随飞鸿”。[6](P9)陈宝琛春滞京师,彷徨无主:“老更伤春滞帝城,海天南际是柴荆。百花无主谁司命,一雨何铿急洗兵?”[7](P145)可以说,遗民们凡眼所见、凡耳所闻、凡手所触、反足所践,几乎都能引发亡国之恨,人生之悲,随之而起的意兴萧然、感伤颓唐就成了遗民诗歌中最醒目的情感底色。
与精神上的意兴萧然、感伤颓唐相比,生计问题或许更为急迫。遗民们由于不仕民国,也就没有了稳定薪俸,故大多面临着很严重的生存危机。①当时遗民大多生计困难,但有两类人生活无忧,一类是在民国享有书画盛名者,如郑孝胥,可以靠卖字画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另一类是在前清积累了较多的财富,民国后可以在海滨租界当一个富足的寓公,如陈燮龙等。于是许多人无奈选择了鬻卖书画、题主,有些选择了史馆、修志②遗民选择史馆、修志等一开始还是受到遗民内部非议的,因为这有出仕民国的嫌疑。比如当赵尔巽被袁世凯邀请出山主修《清史》时,遗民内部就非议四起。后遗民生计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遗民也纷纷加入史馆和修志的队伍中,如沈曾植、吴庆坻、朱祖谋、章梫、王国维等都曾参加了《浙江通志》的修撰。最后遗民对此问题的共识是:涉足民国政坛即为不义,但参与文化事业则不为不义。等以之谋生。但这还只能是少数人能为之,于是多数遗民皆困顿不堪。比如王乃徵,辛亥后“闭门不出,攻苦食淡”。一次所居之地遭窃,衣物皆被小偷盗走,几乎不能下床,需其他海上遗民资助,方才度过难关。[8](P484-486)还比如杨钟羲,沈曾植在《雪桥诗话序》中曾描述其辛亥避居沪上困苦之状:“圣遗居士避世于北江之尾,陋巷湫尘,蓬藿拄径,十笏之室,圭窦彻明。时在寒冬,冰雪在地,北风振叶,踵其户者,若窥袁夏甫之室,御王孝尼之车,陟匡君之庐,而见灵均之泽也。”[9](P1321)由上可知,杨钟羲的居所简陋至极,几乎不蔽风寒,可以想见其生存状况之恶劣。
如果时光流转,回到同光时期的帝京,那正是大多遗民的青壮年时期,情况完全是另一番天地。民初遗民们的功名与仕途大多开始于同光时代。③遗民中多数有进士功名,如陈宝琛、陈燮龙、胡思敬、瞿鸿禨、陈三立、沈曾植、梁鼎芬、冯煦、缪荃孙等,但也有些只有举人功名,如郑孝胥、林纾,其中罗振玉、王国维只有生员功名。他们大多数人都经过科场搏杀进入科举顶层,一举实现士人功名之梦。进士及第后,许多人都进入翰林,或分发部曹,做起了虽清贫但悠闲的京官。这些京官过起了娱情金石、酬唱诗酒、议政而不废论学的生活。在京城,士人们还有许多各种名目的雅集。所谓“京朝士夫朋从之乐”,常见的“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为欧苏二公寿”,一班风雅之士聚在一处,“野寺看花,凉堂读画”,当然被视为“不可多得之胜事”。[10]
如今清屋既社,暮年又流寓海滨,回念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与京师的繁华喧嚣,遗民们更是对过往的帝京充满着诗意的想象。比如陈夔龙在暮年回忆自己年轻时在帝京的快意生活:“先帝龙飞之二载,我偕计吏初游燕。一击不中狂呼酒,日日长安市上眠……散衙有时谋一醉,不惜三百青铜钱。天桥酒家尽识我,自惭才调非青莲”。[11](P932-933)诗中的帝京生活潇洒适意,诗中的人物狂狷似开元盛世时的李白,毫无末世文人的委顿与狭促。
相比陈燮龙,沈曾植对于帝京更为熟稔。沈曾植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北京,诚如自己所言,“我生于燕长于燕,横街珠巢四十年”。自1880年中进士后分发刑部直至1898年丁母忧南下,其在刑部、总理衙门等京官任上度过18年。在京师,沈曾植与李慈铭、袁昶、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王仁堪、王仁东、盛昱、黄绍箕等清流名士交游密切,他们诗酒雅集,切磋学问,品评时事,足迹遍布宣南万柳堂、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长椿寺、报国寺、松筠庵、陶然亭等诸多京师胜迹。这一青壮年的美好韶光与帝国的中兴之治交融在一起,犹令晚来流寓海滨的沈曾植念念不已,在1915年所写的《逸社第七次集会于庸庵制军寓,分咏京师胜迹得陶然亭》[9](P930-932)中深情回溯往事,追忆昔友:“重黎生昔共登险,据地坐想姚朱歌。后来人事多复多,二李二王盛黄载酒时经过”。重黎即为袁昶,二李是指李文田、李慈铭,二王是指王仁堪、王仁东,盛指盛昱,黄指黄绍箕,他们皆为沈曾植好友,诗酒唱和,经常来陶然亭聚会。甲午后,维新思潮激荡风云,包括沈曾植在内的一批有志于变革的京官士子经常聚在陶然亭慷慨激昂,纵论国事,正如诗中所写,“鸡儿年秋谈士诧,此亭乃为齐翟下。中秋圆月照尊晕,坐听诸儒说王霸”。可旧京丽影终究伴随着家国沧桑和个人的青春时光一同远去,国变之痛如影附形,挥之不去,“何况天倾西北地缺东南触触共工头,何况龙化为鱼鼠化为虎封狼驱黑生不休,”。在沈曾植等看来,而今的世道混乱不堪,共工撞坏了支撑天空的柱子,使得大地失去天平,鱼、鼠等小动物却化身为豺狼虎豹等罹祸人间。
与陈燮龙、沈曾植不同,因独特的遭际,陈宝琛和梁鼎芬似乎无法真正在帝京的回忆中沉醉,现实的伤痛使得他们总是将旧日帝京和今日民国以一种触目惊心的对比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散发出浓浓的历史兴亡之感,诸如陈宝琛的“咸同贞元际,缅想余悲辛”。“只道王城堪大隐,那知春色是他乡。”“园林无恙风景殊,觞咏大难主宾美。”[7](P146-156)梁鼎芬对于帝京旧事故人的怀念也是充溢着感伤,如《潘学士丈宅重过感赋》:“入门处处总心悽,旧梦新怀说不奇。缉雅堂花供酒赋,定香亭月见诗题。当年但觉寻常事,回首真令八九迷。一语告公应一笑,千雲青竹有惊棲”。[12](P234)潘学士乃同光重臣、清流领袖潘祖荫,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惹恼慈禧时,幸亏潘祖荫搭救。梁鼎芬在京师时与潘也是时相往来。“当年但觉寻常事,回首真令八九迷。”可谓经历今夕强烈对比的遗民们共同的人生体验。
与上述遗民相比,帝京一开始似乎没有给王国维留下美好的记忆。1906年,王国维因罗振玉举荐,得以进入学部任职。在尤为讲究出身的学部,王国维以一介生员功名自然不被同僚所看重。同时,他也无法融进当时京师的主流文人圈子,只在词和戏曲研究中自得自乐。他是这样描述自己首次进入京城的感受:“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征人一日换缁衣。金马岂真堪避世,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13](P485)但辛亥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出走日本,在大海彼端的日本京都,王国维追忆帝京的山山水水,寻常景物似乎也呈现出诗意的美感:
……左转弹琴峡,流水声潺潺。夕阳在峰顶,万杏明倚天。暮宿青龙桥,关上月正圆。溶溶银海中,历历群峰巅。我欲从驼网,北去问居延。明朝入修门,依旧尘埃间。[13](P190)
相比上述诸人,陈三立在帝京呆的时间最短。1886年、1889年他曾在京师分别参加过会试、殿试,加起来不过短短几个月,后在清时再未踏足京城,①民国后,陈三立一直在南京、上海、杭州、庐山等南方与一批遗民酬唱交接。1933年,其子陈寅恪接陈三立去当时的北平定居,直至1937年去世。陈三立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1915年,在一次雅集上,陈三立回忆帝京,感慨不已:“自别京师三十载,江湖落魄天无梯。当年计偕二三子,一趁薄醉寻轮蹄。……尔来铜驼鼠荆棘,承平故事过者迷”。[14](P935)“承平故事过者迷”,可谓道出了遗民们的心声。在民国后老暮穷愁的个人与时代语境里,帝京的过往都化为了想象中的吉光片羽。遗民们从帝京的追忆中萃取他们的所需的符号,从而构筑起自己记忆的美丽城垣。
二、“跼天蹐地”与帝京风华
辛亥后,各路遗民从四处流聚天津、青岛、上海等海滨租界,其中上海尤盛。胡思敬在《吴中访旧记》中就对国变初遗民汇聚沪上的情况作了初略描述:
予既在沪,则从陈考功伯严访故人居址。伯严一一为予述之曰:“梁按察节庵、秦学使右衡、左兵备易卿、麦孝廉蜕庵,皆至自广州。李藩司梅庵、樊藩司云门、吴学使康伯、杨太守子勤,皆至自江宁。赵侍郎尧生、陈侍御仁先、吴学使子修,皆至自北京。朱古微侍郎,新自苏州至。陈叔伊部郎,新自福州至。郑苏庵藩司、李孟符部郎、沈子培巡抚,皆旧寓于此。[4](P216)
但沪上远非遗民的乐土。对此在沪上生活多年的王国维有切肤之感,在《彊村校词图》序中说道:
古者,卿大夫老则归于乡里。……故古者有去国,无去乡。……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于是趋海滨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贤,亦往往而在。然二地皆湫隘卑湿,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胥于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亲,又加以老侮焉。夫入非桑梓之地,出非游宦之所,内则无父老弟子谈宴之乐,外则乏名山大川奇伟之观,惟有朋文字之往复,差便于居乡。[15](P101)
因此,遗民们是不会把沪上作为其真正心安之所,他们也因之以“流人”自我指称。比如陈三立的诗歌中就大量出现“流人”:“流人为起舞,只媿欠衔杯”。[16](P663)“海隅集流人,过逢互摩抚”。[16](P482)“海隅聚流人,峋濡保暮齿”。[16](P673)沈曾植亦如此:“寒食王周三月春,还家上冢越流人。”[9](P791)“永嘉为记流人目,昼闭荆门草色深。”[9](P609)他乡共入流人簿,闭户谁知纣绝天?”[9](P1105)“华亭吾故县,未肯仞流人”。[9](P996)这里的“流人”既有无国无君、忠贞无着之义,也有对沪上的疏离隔阂之感。这种疏离隔阂还在遗民的诗文中还有其他表现,比如陈三立还在文章中就经常使用“跼天蹐地”来形容沪上狭窄束缚不自由的感觉,如《散原精舍文集》卷七《蒿庵类稿序》:“跼天蹐地之孤抱无可与语,辄间托诗歌以舒其伊郁烦毒无聊之思”,[16](P896)卷八《雪樵诗话续集序》:“避乱沪渎,跼天蹐地”,[16](P914)卷十《俞觚庵诗集序》:“然海滨流人遗老,跼蹐番市楼壁之下,类足迹不窥境外”。[16](P943)
“跼天蹐地”不仅是一种物理性的压抑和禁锢,而且也是一种遗民群体外对遗民的精神压制,比如钱玄同对遗民就出语激切:
今之“遗老”,则因为自家人赶走了洋鬼子,恢复了故业,而帮同洋鬼子来反对自家人;其人格之卑猥无耻,正与张弘范、吴三桂一样。[17]
吴稚晖针对当时几个有声望的遗民,用鄙夷的口吻说道:
什么遗老不遗老!真正的遗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隐其姓名,饱薇蕨以没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风头的遗老,好比康有为哩,陈宝琛哩,郑孝胥哩,罗振玉哩,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挟有另一种谝
法的痞棍。昼伏夜动,名之曰鼠窃亦可。[18](P511)
这种舆论给遗民以很大压力,连素来自傲的郑孝胥曾都在诗中感叹:“亡国大夫诚可耻,避居海滨幸逃死。……苟活仍遭举世非,杜门犹被千夫指”。[5](P234)无奈与不甘充溢其间。
与沪上“跼天蹐地”的身心压抑相比,遗民的心安之所即是往昔的帝京。自清代以来,因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汉族士宦多集聚在宣南。这里建有大量的会馆,“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皆建会馆以资憩息”。[19](P3)这些会馆成为了士人交流的重要平台。尤其是每三年一次的会试,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汇聚于宣南,实际已成全国士人的一大盛会。这里书肆林立,著名的琉璃厂书肆则“凡古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群集于是,几无他物焉”。“而琉璃厂地点适中,与文士所居密迩,又小有林泉,可供游赏,故为文人学士所常至,书市乃应其需要而设”。[20](P4)另外,宣南的市井民俗也颇为诱人。这里戏园林立,还有著名的天桥,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百样吃食汇聚一堂,呈现出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多少游人不忆家”的盛景宣南。总之,以宣南为代表的京师与沪上的“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相比,更为余裕悠闲、风雅舒展,故深为士子文人青睐。
相比如沪上遗民“无父老弟子谈宴之乐,外则乏名山大川奇伟之观”的困窘,帝京则有许多可供士大夫春秋佳日宴集觞咏的场所。“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①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83页。转引自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 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 页。在宣南附近,就有诸如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长椿寺、报国寺、松筠庵、万柳堂以及陶然亭及窑台等京师胜迹。这些精庐古刹、城市山林,因士大夫的频繁光顾而成为独特人文景观。士大夫至此,吟诗题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流传有序的掌故系统,正如黄濬后来所言:“累朝掌故,多属于僧窗,一松一石,每有佳话,浮图幢塔,所系尤弘。”[21](P13)我们以1888年沈九月份沈曾植的交游活动为例,看看当时京城士人宴集游历情况:
九月二日(10月6日),与李慈铭、王彦威、黄绍箕、徐定超、杨崇伊、吴讲、袁昶同游天宁寺。
九月九日(10月7日),赴安徽馆雅集,鲍临、吴讲、徐宝谦、袁昶、王彦威、黄绍箕、徐定超、徐琪、杨崇伊、濮子潼等在座。
九月十三日(10月18日),赴琉璃厂书肆,晤李慈铭、濮子潼。
九月十九日(10月23日)王彦威来。午同人宴集,王彦威、濮子潼、吴品珩等在座。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7日),与李慈铭游陶然亭。[22](P97-98)
由上可见,相比沪上的“跼天蹐地”,晚清士人在帝京的生活是悠闲、雅致与舒展的。这种宴集觞咏、结伴同游的生活对传统士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而帝京又给予这种生活方式以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因此当清民鼎革,移民们流寓海滨之时,那些与他们过往青春紧密联系的京师胜迹在遗民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比如沈曾植用“芦荻萧萧夏亦寒,何况霜朝与雪夕”描述陶然亭秋冬之交苇花如雪的美景,用“此是春明掌故亭,雍乾诗事征纤积”表示对陶然亭“累朝掌故”的称赞;[9](P928)冯煦念念不忘京师“金台夕照”的气魄:“我昔北征滞人海,驱车屡过黄金台。遂宇百重激繁吹,交衢十丈飞嚣埃”;[23](P934)陈三立对龙树寺的古槐记忆深刻:“奇形五爪喧万口,仰视枝干檐瓦齐。儒酸哪识龙虎气,但喜丑怪出角圭”;[14](P935)王乃徵对崇效寺念念不忘:“帝京名刹盛金碧,栋宇荒寒最兹寺。独有灵光耿不灭,一幅残縑动人思”。[24](P936)另外,诸如林开幕对长春寺、缪荃孙对碧云寺、杨钟羲对慈仁寺、瞿鸿禨对天宁寺等,都在诗歌中加以书写。
三、“五代式民国”与“皇明极盛时”
清屋既社,民国肇始,换来的似乎不是“前途光辉灿烂”的民国,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五代式民国”。有关对民国初年负面的描述在时人的诗文、日记中比比皆是。就在满清将灭未灭的辛壬之际,中国已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胡思敬曾对此有个一个总体观察:
是时,京津初遭兵劫,百物荡尽,十室九空……军士露刃,蠢蠢欲动。江淮盗匪横行,白昼掳杀,无人理。百货雍滞不行,工商俱困。京朝贵官及各省方面大员同时失职,四方糜烂,无田可归,则寄贿迁孥,混迹海滨,苟图自活。富者杜门不出,贫者至不能举炊,绮绅之祸,于斯为极。[4](P215)
虽然略显夸大,但基本符合事实。其他类似表述还有很多,比如恽毓鼎就认为民国是“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并忧虑“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25](P580)陈三立更是对民国现状极为不满:“辛亥之乱兴,绝羲纽,沸禹甸,天维人纪寝以坏灭。兼兵战连岁不定,劫杀焚荡,烈于率兽。农废于野,贾辍于市。骸骨崇邱山,流血成江河。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16](P943)他的这种感受与他本人的生活经验有关。辛亥后,他曾有过多次逃难的经历。
对于民国,不惟遗民们不满,就连立宪派、革命派亦感到失望,蔡济民在其著名的《书愤》诗中感慨“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亦感慨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26](P104-105)革命党人尚且如此失望痛心,遑论逊清之遗民。
既然眼下的民国乱如五代,那么昔日的帝京在时光的过滤下愈发散发出迷人的一面,其经过遗民们想象的累积更是逐渐幻化为他们心目中的“王道乐土”。今夕对比间,遗民们唏嘘感慨,仿佛白头宫女在落寞之际缅怀盛世唐明皇,说不尽的无限感慨与沧桑。在今夕对比中,当下的不堪不仅使得康乾盛世无从追寻,即便同光或光宣亦令人惘然。为此,诸如“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陈宝琛)[7](P133),“何必追伤乾道事,重论光绪已酸辛”(梁鼎芬),[12](P214)“风流渺矣乾嘉年,后来想从思光宣”(吴庆坻)[2](P935)等诗句就多次在遗民诗中出现。甚至到1925年,在复辟希望愈来愈小,许多遗民都相继过世的背景下,陈燮龙还在诗歌中哀叹“衣冠幸不挂神武,想见皇明极盛时”,[28](P663)足见想象中帝京的盛世光景已经成为遗民的内心精神支柱。
在今日的对比映衬下,想象中的帝京越发显得富足太平。在陈燮龙笔下,帝京是“尓时帝京丽景物,海波不扬燧无烟。五侯七贵盛珂马,前门车毂声喧阗,东市列珠玉,西市罗肥鲜。……绝似汴京全盛日,樊楼灯火星钩连。”[29](P33,七编卷一)在瞿鸿禨笔下,帝京“昔在乾隆新梵字,有举不废从因仍。当时物力席全盛,金涂宝烛交晶莹”。[30](P933)梁鼎芬沉醉于光宣的美好:“我生始作上京客,到处都闻乐岁声”。[12](P220)
因着民国的战乱频仍,帝京及其那个时代对于某些民国知识人也有着别样的魅力。比如自称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始终对遗民报以“同情之理解”。他在为挽悼王国维所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这样写道:“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日。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31](P12-13)这首诗几乎可以概括民初逊清遗民对于前清乃至帝京的完美想象。陈寅恪作为新一代知识人,与逊清遗民隔着一辈,在许多方面与遗民等传统士人拉开了距离,但由于家世以及文化取向等原因,他笔下的光宣几类同于开元盛世,帝京更是人才荟萃,声光四溢。
其实对帝京进行宏大书写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在辛亥追随罗振玉东渡后,暂时定居日本京都。壬子(1912)年,作著名长诗《圆明园词》,铺陈晚清史事,诗人先是追忆同治中兴初起时的君臣和谐、政治清明:
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归欃抢回日月,八方重睹中兴年。联翩方召升朝右,北门独对西平手。
接着王国维用其诗词中少有的宏大而亮丽的笔触描述朝廷威仪和盛世光景:
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隥道盘行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火树千花发,不数名珠彻夜悬。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銮驭。长乐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丹陛大陈三部伎,玉巵亲举万年觞。[13](P117)
揆诸史实,王国维的描述确实有拔高美化之嫌,诗中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让人无法将“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隥道盘行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与内忧外患交接不已的晚清联系起来。可置身于民国的王国维们要的本就不是一种历史的“实然”书写。在今夕对比中,他们诗歌中努力呈现的是帝京的一种“应然”状态,是真实历史的一种“镜像”。
四、忠君情怀与帝京想象
流寓于海滨租界,身历纷乱频仍的民国,帝京在遗民心目中,不仅仅是曾经的宴集酬唱之所,也不仅仅是有着大量精庐古刹的悠然之地,更是治道二统完美结合的“王道乐土”。这种“王道乐土”以君臣纲常为基点,并由此而生成并规范各种社会人伦秩序。因此,“君”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帝京的象征,忠君也就成为遗民帝京想象最基本的情感肌理和核心内容。故当幼帝溥仪逊位之时,一批遗民如丧考批,无异于天崩地裂和精神生命的终结。如缪荃孙当日在日记中悲愤写道:“闻上已逊位,清国遂亡,自此以后,偷息人间,与已死何异”。[32](P2449)沈曾植更是哀恸不已。据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中说:“某夕,侍者以一号外入,视之,则逊诏也。我辈乃同起北面而跪,叩首哀号。闽人王叔庄跪地不起,大呼曰:‘国破君亡,臣不欲生矣’!又数日,余复见先生,问先生曰:‘事已如此,我辈将如何’?先生泪流满面,执余手而言曰:‘世受国恩,死生以之,他非所知也’”。[33](P1051)梁鼎芬于此更是有偷生、孤儿之感,其诗言道:“千怀无一语,今日是他生”。[12](P205)“孤儿失母凄凉雪,孀女怀夫决绝春”。[12](P208)“早死宁知非幸事,偷生相见尚衍期”。[12](P212)
这种忠君情怀还表现在某些特定的仪式上。每逢特殊日子,向北叩拜就成了遗民们对北方帝京及其君主的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恽毓鼎在其《澄斋日记》中就记到:每逢阴历的正月初一时,家家户户将进行祭拜,恽毓鼎总会带着家人,一同朝北方宫阙方向行三跪九叩之礼。刘承干则“每逢三令节,北向衣冠肃,既愿圣长寿,亦祷明复辟”。[34](P96)这些仪式都隐喻着自我对大清的忠贞。
不仅如此,“北望”这一特定语汇还成为了遗民诗中一个独特的意象,比如陈燮龙:“座中俱是望京客,一片心常北斗悬”。[28](P932)沈曾植:“北斗阑干倚望眸,风物仿佛亭中秋。身在南藩且无预,心悬魏阙怀千忧”。[9](P932)郑孝胥:“恐是人间干净土,偶留二老对斜阳。违天苌叔天将厌,弃世君平世亦忘。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危楼轻命能同倚,北望相看便断肠。”[5](P224)即使到了遗民大多离世的1925年,陈燮龙还被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之句所感染,即作辘轳体诗五首,遥想故国与君父,伤感不已。
遗民北望之思君,首当是光绪和慈禧。其中,光绪皇帝在位长达34年之久(1875一1908),其在位之时正是大多遗民的青壮年时期,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光绪朝取得功名,然后进入清帝国的官僚体制之中。光绪一朝大事不断,诸如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庚子事变以及清末新政等,大多遗民都是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光绪励精图治的进取形象和开明的改革态度使其获得绝大多数遗民们认可和尊敬,戊戌后一直被压抑的特殊遭遇更使其在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光绪皇帝已经成为某种意象,既与国家所遭遇到的深痛巨创紧密相关,也与清末士大夫阶层的爱恨荣辱紧密相连。林纾1912年12月12日在《平报》上发表《崇陵哀》,对光绪大加赞美:
景皇变政戊戌年,精诚直可通重玄。夕下诏书问民隐,晨开秘殿延朝贤。无方可雪中华耻,卧薪先自宸躬始。立宪求抒西顾忧,维新先忤东朝旨。可伶有用帝春秋,几几流窜到房州。……
清帝国的覆亡加剧了士人们对光绪的怀念之情,故光绪的灵枢和葬身之所崇陵在士人们的心中便有了神圣的地位。这种情愫随着国变发酵,日益浓厚,可称之为“崇陵情结”。“崇陵情结”几乎成为遗民们一项共同的心理。其中,梁鼎芬最为积极。1912年冬天,其为崇陵募捐而四处奔走。据说,除了带头捐款之外,他还在北京琉璃厂订制了两百个瓷瓶,在崇陵装满雪水之后加以密封,然后发送给各地的王公大臣和前清遗民,甚至还亲自登门说明崇陵工程停顿的情况,最后募得了一笔巨款。因着这一事件,有关“崇陵”之话语这一时期的遗民诗经常出现。如瞿鸿禨《壬子晚秋,梁节庵诣梁格庄叩龙輴仰瞻崇陵地宫,捧石以归,兼贻鸿禨宝藏,恭志崇陵片石词》中说:
我亦当年捧日人,不驱蝼蚁辜恩厚。驽下徒伤先帝明,流离暮齿复何有?六谒孝陵风鱼绝,典刑再见亭林叟。[6](P1)
吴庆坻《节厂提刑前辈奉崇陵栽种树株之命请急暂还,残腊北行,樊山设饯寓园,酒罢乃为长歌以送之》:
俭德垂衣忆景皇,寿宫迟起万年堂。一从永弃臣民后,弓潟桥山渺帝乡。[35](P738)
慈禧作为晚清实际统治者达五十年之久,遗民们对其感情是复杂的。许多遗民在晚清其实都不是保守顽固之人,相反,许多人都有经世之心与对西学的具体认知。①整体来讲,遗民群体在晚清基本是“中体西用”的信奉者,他们在“中体”上毫不动摇,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西用”的一概拒绝。相反,他们许多人在晚清都是“新学”的积极响应者和学习者,比如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在戊戌维新期间都有革新的意识和行动。对于许多在甲午后渴盼变革的遗民来说,慈禧发动的政变乃至庚子时期的作为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比如郑孝胥对慈禧就做负面评判,国变后他对孟森等人说:“革命党魁,君知其为何人乎?景皇帝为君主立宪之党魁,反对立宪者,孝钦也。有孝钦反对立宪于前,遂有庆王、摄政王伪饰立宪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党魁非他,即孝钦是也;庆、摄助而成之,亦其次耳”。[36](P1400-1401)并在诗中直白写道:“毒后憎诸贤,要领膏锧斧”。[5](P268)林纾也说:“然德宗果不为武氏所害,立宪早成,天下亦不糜烂到此。罪大恶极者那拉氏”。[37](P319)但遗民中仍有人将慈禧作为清帝国的象征,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比如王国维:
……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却因清暇话平生,万事何堪重回首。……[13](P117)
无论遗民将多少故国之思和帝京想象寄托于光绪和慈禧,但他们毕竟只能代表过往。辛亥之后,紫禁城的象征,清遗民心中真正的“君”是逊帝溥仪。溥仪生于1906年阴历正月十四日,因此,每逢正月十三日便成为遗民们的“万寿节”。这一天,全国各地的遗民,尤其是京津地区的遗民,都会整肃衣冠,入宫朝谒。距离北京较远的地区,则以群聚酬唱等其他方式为溥仪祝寿。根据现有资料,从1917年到1927年,以逸社成员为主的上海遗民一共举行过九次万寿节集会。参与者一般在十几人至二十余人左右。[38](P138)
万寿节集会是清遗民表达对故国故主情感的重要场合,也是他们加强内部联络,增强自我认同,同时也是积蓄复辟力量的重要时机。集会时,一般在遗民私宅正屋的中央设立溥仪的座位,并挂上他的画像或照片,燃烛熏香,然后,众遗民按官品排班跪拜,三呼万岁。跪拜时,为郑重,一般要穿前清朝服。对此,陈夔龙有诗云:“呼篙还著旧朝衫”。[29](P3,八编卷一)事后,一般还写诗恭纪其事。陈燮龙对此多次以诗纪之:“龙颜日角画图挎,烛穗炉香篆影斜。青琐班行谁首列,白头闲坐发长磋”。[29](P3,八编卷二)“呼篙排荤凤扶云,老鹤延龄帝座分”。[29](P3,七编卷二)总之,虽然已经不可能再有光宣朝万寿节的那种排场,但他们仍然忠心耿耿地保持着君臣之间的礼仪。
五、余论
帝制的猝然终结使得民初遗民这群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士人遭遇到了措手不及的惊愕。猛然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不是一个普遍王权的时代,处境也与历代遗民殊异。那完全是历史经验之外的考验和抉择。对于这种不同,王国维有深切的认识:“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39](P212)
“道乃出于二”预示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临,这种变局一方面使得遗民们的忠君及气节坚守有一种历史的“虚妄”色彩,另一方面却又使其在20世纪中国日益激进的历史大潮中自有一种意义。与陈寅恪同时代,并对遗民充满“同情之理解”的胡先骕曾对遗民之追求帝制有过一番解释:“彼生于君主时代,仕于君主时代,自幼所受之教育,皆适应于君主时代者,则求不欺其心以随世俯仰,必以王室倾覆为一生中最大之不幸,亦犹民主政治下之士君子,决不愿帝制之复生也。……故以吾辈青年而抱忠于清室之志,则为妄谬,在清室旧臣,则反以入民国仕反为可鄙矣”。[40]
遗民诗人在帝京想象中肆意书写着心中的“王道乐土”,企盼着君主制的重新来临,这种被人称作“拉车屁股向后”①鲁迅语。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康有为、严复、刘半农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则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物。详见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536页。的行为和思想自然得不到同时代以致后代的真正理解。那么,这些逊清遗民忠君乃至要恢复帝制的内心动机到底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沈曾植于1917年张勋即将复辟之际代拟的一份《复位奏稿》来说明,其中言道:
为沥陈国情敏诸复位以拯万姓事。窃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以立者非他,则君臣大义、尊卑上下定位而已矣。有史以来,吾中华国民以五伦五常建邦保也,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达道,要必借君臣道立,而后四者得有所依而不紊,五常得有所统而可推。民彝自天,欧亚殊性,犹目睛肤色之不同,不能削趾以适履者也。廿载以来,学者醉心欧化,奸民结集潢池,两者相资,遂成辛亥之变。……臣等蒿目时艰,病心天祸,外察各国旁观之论,内察国民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政体不适吾民,实不能复以四百兆人民敲骨吸髓之余生,供数十政客毁瓦画墁之儿戏。[22](P449)
这份奏稿基本上可以视为逊清遗民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和文化宣言。由奏稿可知,遗民们渴慕和坚守的是一种宇宙和社会的永恒秩序,而这种秩序简言之就是三纲定位,五伦归位,如此整个社会才尊卑有序,人伦和谐。这种秩序是遗民们整个帝京想象与书写的最核心内容和终极追求,也是陈寅恪所说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31](P12-13)他们对清室的特殊感情也正是这种“抽象理想”具体投射之后的自然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的趋新文化对遗民们所坚守的旧文化否定的过于决绝,以致两者之间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也导致激进主义无所牵绊,一路狂奔,其历史后果不言而喻。因此,对于这种“抽象理想”的关注和体悟,当更能使我们对遗民们报以一种“同情之理解”。
[1]蒋梦麟.新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刘禹生.清道人轶事//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缪荃孙.缪荃孙全集·诗文2[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4]胡思敬.退庐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从刊初编第45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5]郑孝胥.四月十八日夜示中照//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瞿鸿禨.超览楼诗稿(卷三)[M].1935年刊本。
[7]陈宝琛.藏趣楼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沈曾植.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清人说荟[M].据扫叶山房1928年石印本影印.
[11]陈燮龙.天桥酒楼//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3]王国维.浣溪沙//王国维诗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4]陈三立.龙树寺古槐//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5]王国维.王国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6]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M].语丝,第20期,第5版.
[18]吴敬恒.溥仪先生//吴稚晖先生全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19]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20]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2]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冯煦.金台夕照//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4]王乃徵.崇效寺红杏青松卷子//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5]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M].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2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7]吴庆坻.净业湖李文正故宅//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8]陈燮龙.天桥酒楼//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9]陈燮龙.花近楼诗存[M].北京书店,1985年影印本.
[30]瞿鸿禨.天宁寺塔镫//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1]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2]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3]钱仲联.广清碑传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34]林志宏.民国乃帝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5]吴庆坻.节厂提刑前辈奉崇陵栽种树株之命请急暂还,残腊北行,樊山设饯寓园,酒罢乃为长歌以送之//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6]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M].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7]李家骥.林纾诗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8]朱兴和.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39]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王国维全集(第14卷)[M].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40]胡先骕.书评:评赵尧生香宋词[J].学衡,1922(4).
——评杨剑兵《清初遗民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