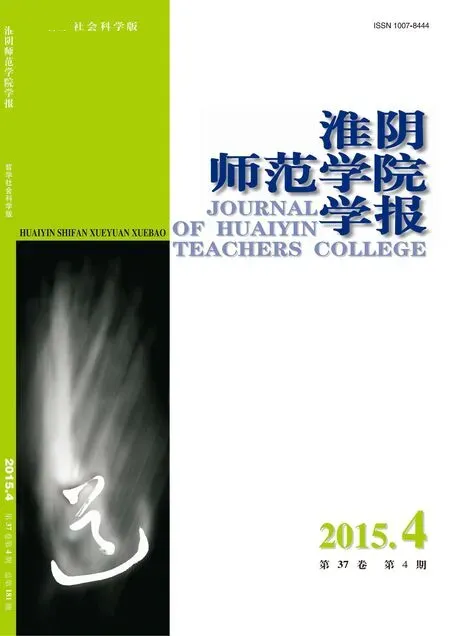旧派文人文化视野中的都市伦理1920—1937
王进庄
(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上海200235)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使旧派文人面临着双重压力:旧礼教和新思潮从前后两个方向双面袭来。旧礼教余威尚存,新文化又给予他们恶谥。一方面,他们是与传统持久保持联系的一代,但绝非全部认同,他们只是承继了传统文化中保守有序的一面,对旧礼教一直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新文化意义建构和金钱所引发的家庭解体、人格堕落颇多微词,对“文明”“自由恋爱”等观念,对五四新文化核心价值——“德先生和赛先生”,都高度质疑。确实,旧派文人突破不了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他们根本的价值尺度,是与五四新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经常有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一个可以发掘出现代意义的故事之后,要加上一段训诫的套话,或斥责金钱万恶,“种种因缘,莫非受了金钱的播弄,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上一年之中也不知发生多少?”[1]或者批评社会万恶,“龌龊社会,愈弄愈糟,我们日与解除,不能够学屈平之众醉独醒,又不能学庄子之逃虚入悬,一身成赘,万感如山”[1],或者指责青年沉沦,“上海地方真是个五(污)浊世界,骄奢淫逸一天进步一天,青年子弟们堕落的亦不知道多少”[2]。1920—1937 年间,面临着双重压力的旧派文人有很深的伦理焦虑,但这种伦理焦虑不同于封建礼教,也不是“改良礼教”。封建礼教承认尊卑贵贱、上下等级的合理性;以专制主义完全扼杀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即五四新文化所批判的“吃人”意象);以家国同质同构体系来维系统治者治国治民的基础。“改良礼教”反映在家庭关系中,是指既承认后天萌发的七情六欲,承认男女青年恋爱的权利,又保留着对传统儒教的父慈、妇从、子孝的认同。这是1910年代旧派文人典型的伦理道德观。到了1920年代,旧派文人很少表现在家长专权下呼唤爱情而又怯懦的性格,他们真正的伦理焦虑来自于由金钱和新思潮所引发的家庭解体,婚恋关系的任意轻率,性关系解放,人格堕落的都市现实。旧派文人试图合理规划现代世俗生活和家庭伦理秩序,但他们没有能力提出一套系统的道德伦理准则来回应和挽救这种溃败,就像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之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生成发育出一种依赖法律等形式机制的公正执行,关注公共秩序的市民社会的伦理。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旧派文人在对都市罪恶的一般性感受中,深入到人性和人伦关系的深层,探讨了家庭伦理的现实,特别是自由恋爱的道德底线、寡妇再嫁、女子堕落、男女平等后的男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文学史发展看,这些都是同时代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和1910年代的旧派文人思考甚少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则完全是被压抑者的释放式表达,很难用伦理的规范加以约束;新文学的启蒙视角有一部分就是反伦理道德的启蒙,挣脱伦理的束缚往往是与爱情叙事、家族叙事纽结在一起的。1910年代旧派文人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创作,营造的是一个鬼魅丛生、是非混淆、价值颠倒的世界,“小说中的嬉闹缺乏明白的道德讯息,小说终了,坏人不见得遭报惩,社会秩序也未必除旧布新”,正如王德威所说的“闹剧风格”[3]。而骈文言情小说只会用不太拂逆旧式礼教风范的方式去为爱情赞美或哭泣。所以1920—1937年间旧派文人的创作是从内部纠正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和言情小说的路子,不只有谴责和暴露,而且写积极面,试图提出一些维系人伦的道德文化准则。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物质文明日进,而道德日益坠落”的忧虑。物质的进步与道德的堕落,情爱的自由和伦理的失控往往并举,这些都是都市生活深化和忧虑加深的表征。
一
对旧派文人而言,都市除了是兴奋和神秘的源泉,又是一个“恶”感重重、荒淫无耻、堕落、邪恶之地。都市为什么比农村的、传统的社会更容易被感受为“恶”呢?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简单,人口流动性小,家庭同耕一块土地,日常的行动和关系都发生在大家庭之内,因此形成了从家庭出发的伦理道德体系,并且由家庭伦理推导出国家所必须的各种伦理。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对道德伦理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的依附性强,个人倾向于按照客观化的要求塑造自我。而在现代都市,“首先,现代城市是由异质人口构成的。这种异质性反映在如下事实中:没有一个超越所有群体结构的单一价值系统……其次,规范结构的异质性和分离性,造成没有一个单一的监督和控制行为的‘道德秩序’”[4]。就是说,伦理道德这个统一的非形式机制被打碎了,都市中的“异质人口”的人们采用“正规的、间接的、非个人的关系”(即社会学家所说的次属关系)交往,自然倾向于从固有的价值结构和道德体系中解放出来,摆脱传统农业社会中所受到的控制和监视。“人们愈是彼此缺乏联系、隐姓埋名,社会解组的程度就愈高;社会解组的程度愈高,越轨行为就愈多。”[5]以《房客小史》中描写的多个房客为例[6]:第一个房客是胖太太,有一个女儿叫阿巧,一个月至少要有三夜住在外面,要是整月住在家里,收房钱就要“约日脚了”;第二个房客男是大烟鬼,女是梳头阿姐,靠典当生活;第三个房客是小学教员,喜欢画裸体写生;第四个房客是宁波阿嫂,趁丈夫外出,自己去轧姘头,碰到人说姘头是她的兄弟;第五个房客是假道学,调戏宁波嫂嫂;第六个房客是郎中,和扬州大块头同居,大块头后被郎中妻子打走了;第七个房客是一个女人,有两个情人,轮流上门……可见,在都市环境中,都市人呈现出与传统生活截然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状态。金钱日益成为操纵家庭、男人女人之间关系的砝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旧派文人耳闻目睹的是一幕幕传统家庭破灭后混乱、滥情、失去秩序的现实图景,违反伦理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旧派文人自然“恶”感重重。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处理这些关系构成了伦理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转型期的都市,传统大家庭迅速解体,伦理失范。新的父子、母子、兄弟、夫妻、恋人、主仆、婢妾、邻居、熟人、同僚、朋友等各种关系都进入了旧派文人的视线之中。但表现最多的还是家庭里的各种关系和社会上各色男女的关系。
在上海,“传统的,以宗法农村为基础的价值已转化为核心家庭广泛的社会交际,和被社会学家通称为是‘社会的’文化”[7],抓住家庭伦理,就捕捉到了都市伦理的脉搏。他们沿袭了传统伦理中重视家庭、重视秩序的意识,但又不同于传统伦理或礼教中把家庭或秩序看作机械的、本质的道德因素。旧派文人承认自然感情,承认男女青年恋爱的权利,反对家长专制,这些是在1910年代的言情小说时期就鲜明地提出来的原则。但同时又倾向保守,持有既要自由恋爱,又要服从家长专制的原则。两者矛盾时,往往是后者压倒前者,家长专制扼杀了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的悲剧仍在上演。面对子女无力反抗而被折磨致死的悲剧结局,旧派文人唯有对青年男女掬一把同情之泪,感叹父母的固执和与愚昧。传统的宗法观念,要使他们从正面批判家长的专权,解除青年的伦理负累,拥有一种向新路走去的开拓精神和勇气,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不过事实上,这种类型的小说所占数量并不多,在创作总量中不会超过十分之一。
旧派文人真正的伦理焦虑来自于由金钱、新思潮、情欲所引发的家庭解体,婚恋关系的任意轻率,性关系解放,人格堕落的都市现实。在旧派文人看来,由义务引发的人伦关系是善行,个人“进入一个家庭,就是克服利己主义的开始,因为进入家庭是一种对仁慈的奉献和参与”[8]20,如夫妇之坚贞是对性本能的约束,子女孝顺父母是两者关系的道义化(当然并非排斥自然感情,中国古人视孝道为修身行仁之始)。善恶的评判是伦理的核心。如果是由金钱或直觉所引导的人伦关系,那么它就是“恶”,这就是旧派文人对都市的重重“恶”感的根本来源。比如说夫妇由性本能结合,但随即转为纯粹精神性的关系,这就是“善”;如果男女自由恋爱,追求解放,同居、结婚、离婚或再婚,“陷于淫欲”,就是“恶”。《嘴唇底教训》中认为支配人类的是性,于是女子的身体摄住了男性的“思想”[9]。《丽丽》中男子用物质挥霍得到舞女的青睐,在“黄金买卖的交易所”中买了“一个桃红色的梦”[10]。人伦关系的建立普遍陷入“淫欲”或物语,旧派文人对自由恋爱的道德底线、寡妇再嫁、家庭成员之间冷漠和彼此倾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善恶评判。
自由恋爱是市民所熟知的主张,市民们期待着那摆脱了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新家庭”,因此一直宣讲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离婚,等等,总的倾向是否定婚姻的稳定性和情爱关系的固定性,释放人的欲望,满足追逐异性的渴望。对旧派文人而言,恋爱是旧派文人向往的,但自由恋爱是他们反对的;解放是他们向往的,但解放不是自由解放。市民理解的自由恋爱、解放与旧派文人发生了差异。旧派文人从来的立场是以夫妇关系永续为常道,以离异为不得已之变道,这个尺度从来没有放松过。但都市社会的恋爱方式和状态不由他们决定,失去理性、德行的恋爱遍地开花。他们逐渐开始反思自由恋爱的真相和恶果。真相是——“自由恋爱,不过是情欲的变相”[11];“自由恋爱风行,一般的男女假了这个名且任意胡行朝合暮离”;“‘发生恋爱’是一切真情、奸情、卷逃、诱拐的代名词”[12]。长篇小说《雨中花》[13]注目于女性在都市空间的堕落问题,写温旅长的妻妾都有猎取男性的手段,温太太把姘头男扮女装,堂而皇之引入闺房之中,姨太太们都有情夫,且“妻妾通同一气,所有被俘的男性,不分畛域,抱着公开制度,大家有份”,“赫赫炎炎的旅长公馆,表面上是军阀,实际上是龟阀”。可见,自由恋爱一面是浪荡之人借自由恋爱名义为自己谋肉欲上的利益,结果爱情变成“假爱情”,男女关系混乱,婚姻濒临危机和解体;另一面是被伤害、遗弃和堕落。这都与旧派文人对爱情和家庭的想像大相径庭,所以他们明确反对“野蛮自由结婚”,不允许“自由女”、浪荡子亵渎美好的爱情和家庭,并“对‘自由’产生恐惧,反有着逃避‘自由’”[14]的一面。
寡妇恋爱是旧派文人开创的写情题材。寡妇恋爱,如果是出于生计的艰难或者客观因素,在他们笔下是可以容忍的;如果是牺牲自己以行婚姻不变之常道,那就是品德高尚;如果向情欲投了降,那就是被批判的对象。周瘦鹃的《十年守寡》中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守寡十年,却不讲名分与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同居生子。“叵耐他(她)那一颗芳心没有化成他(她)丈夫坟上的石碑,也不曾伴着他(她)丈夫同埋地下。苦守了十年,到底战不过情欲,只索向情天欲地竖了降幡。”世人态度变化,都虚情假意了,女儿也不理睬她了。作者对中国传统习俗对再醮妇的议论持批评态度,但也对王夫人“偶然被情丝牵惹”出的罪不无遗憾。[15]旧派文人对伦理、道德的简单评价体系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始终也没有建立“婚姻和家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和一个爱的共同体,其中充满了夫妻间的、儿女的和父母的爱”[8]119的现代社会伦理观。
旧派文人呈现的家庭现状往往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冷漠、紧张,甚至造成彼此的倾轧和心灵的伤痛。旧派文人很喜欢写的一种视角和主题是:家庭中的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要养活一大家子,父母、兄弟、妻儿的无尽索取让其无法承受。这些忍辱负重、肩负家庭经济责任的主人公最后只有用消失或死亡来逃避的故事无疑是金钱日益成为操纵家庭成员之间的砝码的真实写照。这段时间侦探小说兴盛,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宋悟奇探案”、朱羽戈的“杨芷芳探案”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系列等几个侦探系列都在此一展风貌,且大都把视角对准了家庭或社会伦理。张碧梧“家庭侦探宋悟奇探案”系列在《紫罗兰》上连载,各种案件都发生在熟识的人、亲人或邻居之间,甚至因家庭矛盾冲突到极端而产生血案。其中《一睡不醒》[16]中的主人公卖文为生,勉强维持家庭生活较高的物质水准,父亲和妻子索取无度,他承受不了,自杀而亡。《内外交攻》[17]中伍蕴才失踪后被发现尸身,宋悟奇推断是自杀,探查一番,自杀原因是:他在交易所里做买卖亏折了,他夫人又因打花会把一家所有输个精光。“他固然是心地太狭窄,他夫人却应该担负最大部分的责任。”《一睡不起》《内外交攻》两篇侦探小说的构思视角颇为相似,这些忍辱负重、肩负家庭经济责任而又只有用消失或死亡来逃避的知识者形象无疑是旧派文人的自我写照。而私家侦探与官家侦探之不同在于必须有侠义心肠,不能受金钱势力的指挥。当私家侦探的,“虽然也拿当事人的酬报,但非秉有义侠心肠不行,因为破案与否以及是非黑白之权,完全都操在他的手里……侦探的天职和律师差仿不多,原是侦查案的真相而保障人权”[18]。程小青借霍桑之口表达对官家的司法制度和侦探强烈的不满,斥责他们的“省事的秘诀”——把被害者的贫富贵贱作为处理的标准[19]。朱羽戈笔下“杨芷芳探案”中的杨芷芳面对一起为惩治重婚男人而施行的诈骗案,直言道:“我们办事原只求我们的良心安贴和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假使女士的事情,没有违背公道,或和法律抵触,我们也决不做这不完全法律下的忠仆的。”[20]私家侦探们俨然是金钱时代的正义伸张者,都市社会的侠义君子,也是旧派文人进行善恶评判的化身。
二
旧派文人的伦理观是都市“现代性”到来时市民知识分子本能的反应。与其说它继承传统伦理,不如说它从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借鉴一种中庸,允执其中,不过激,讲究秩序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现代性,无论是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的规划,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就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21]旧派文人试图把以德性修养和僵化凝固化的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转换功能,转换为一种秩序方式;伦理道德的对立面不是无法论证的天理或家长专制,而是社会运行的惯性法则。基于此,旧派文人反对放纵情欲、见异思迁,赞成一夫一妻制的稳定家庭。有的学者认为旧派文人“反对‘爱情至上’的非理性,而将爱情客观化为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和严厉的市民伦理”[22]。这种评价虽有所拔高,但他们反对离婚,反对单方见异思迁,反对本能欲望向外乱注与泛滥,赞成一夫一妻制的稳定家庭,肯定女子在获得解放后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张家庭经济结构上的男女平等,诸此种种,都体现了一种旧派文人试图合理规划现代世俗生活的信念。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诸如“贵义贱利”“崇公黜私”“重本抑末”[23]对个人道德提出很高的要求,但在都市社会中,伦理道德溃败,金钱主义一旦不受遏制,马上就会变成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同样冲击着风雨飘摇中的都市家庭,演绎出一幕幕的人伦惨剧。旧派文人从市民伦理的角度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保有对家庭的一份脉脉温情。不排除有些观念有些保守,如对寡妇再醮的伦理立场,但总体而言,他们将浪漫爱情还原为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秩序,剔除了金钱等异化因素,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态是相应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租界是化外之地,旧派文人活跃其间,凭借的文化资源是相当驳杂的。除了在某些笔记中还看得见一些封建道德的彰显,充满着因果报应、忠孝节义的教训,大部分资源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精神,特别是儒家中庸之道、人伦秩序和人道主义温情占了主流,也有讲道家勘破虚荣、强制色欲、放低生活程度的言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也是弥合心灵裂缝,消弭争斗的灵药:它可以令罪犯变成“圣贼”;教堂的钟声、教士对爱的宣讲令能使交战双方各释其昔日的宿怨,从而消弭兵祸,改变政局。这些资源融汇了古今中外的文化气息,构成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图景。
对旧派文人所构想的现代图景而言,破坏力最强的是金钱和新思潮两种事物。
都市中金钱魔力巨大,它可以否定先赋身份和社会地位,甚至重构等级;它可以使消费自由度大大增加,满足市民对物欲的追逐。丹尼尔·贝尔认为,都市“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24]。在旧派作家笔下,上海的商业化、都市化进程使个人在都市中成为“自由人”,可以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追求目标和行为方式的理性化思考;交往中理性和货币因素被看重,情感能量和伦理束缚也随之减少。传统社会的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既肯定物欲和人欲的客观存在,又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重视人的精神修养,鄙视粗俗和贪婪的欲望,如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道家的“为无为,则无不为”。都市理性则冲击了传统文化的禁欲主义本质,让物欲在都市的特定环境里恣意生长,达到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目的。
都市中,大多数生存的利益和价值都被算计得清清楚楚,物质欲望的爆发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量入为出的理财方式和消费模式,金钱成为控制人伦的最大法宝,人们可以把一切东西都量化为价值,以金钱为砝码,予以称量,包括感情世界。《春水微波》中母亲洪氏的生活准则就是金钱——用女儿丁慧因的容貌卖钱。开始把她送给叶兆熊做妾,见婚后“说给的东西也不见指派下来”,就把女儿诳回家来,以办重婚罪为由要挟叶家,终于得到了房子、现款等物。叶兆熊失踪后,洪氏又默许其公公叶老爷迷奸其女,获得金钱。丁慧因出场时还只14岁,充满幻想,在一系列打击后,恨自己的母亲,恨自己的一生,最后自沉黄浦江。[25]金钱崇拜下的人情尖刻、世态炎凉也是反复被书写的主题。传统孝道被抛至一旁,子女对于父母、父母对于子女的意义被重估。《迎新春》中娶了富人家女儿的老人,儿子们不以为父,春节之中,老太太受人追捧,到处玩乐,什么事都没老父亲的份,他只有醉倒[26]。还有因金钱的流动性特征(金钱的得到或者失去)显示了都市人的势利嘴脸,从巴结到打骂,态度转变在一瞬之间。《老鸨式的父母》中的王老太太在女婿有钱时,不停地奉承,把女婿放的屁来香比梨膏糖,女婿穷时,说他讲的话臭过黄狼屁[27]。滑稽的语言给速成财翁当头棒喝,也给以金钱为认知理念的市民辛辣的讽刺。可见,传统人伦在金钱作用下断裂、变异,割裂了父子之恩、兄弟之爱、夫妻之情。旧派文人不可能认识到都市繁荣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品格结构,“金钱万恶”是他们在人们被金钱主宰,道德意识处于混乱状态下的一种诅咒和呼吁。
旧派文人所理解的新思潮、新文化、新人物与五四所倡导的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个性主义、公共意志等属性的精神有不小差异。就他们看来,新思潮等于废家、非孝、公妻、找小丈夫、离婚,核心是“自由解放之说”,即自由恋爱和性开放。他们把所有破坏家庭、放纵情欲、伦理失衡的事都概括为新思潮的影响,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新的人伦关系有内在的焦虑。小说《流星》写方苟丕(谐音放狗屁)是“新文化中的健将”,“新得不得了”:要脱离家庭关系,“乐得非孝”;要“平等”,称父亲为“仁兄”;对于新文学很有经验,做新诗,三天做了三百首;被一个名叫尤昌(谐音优倡)的新式女郎追求;任废家同盟会的名誉会员、非孝会的会长……最后成了叫花子,生了一身杨梅大疮。[28]汪仲贤续写《僵先生》[29],把僵先生老婆阿金姐写成是一个“能发表革命的谈话”,“也能将各种新名词运行得头头是道”,生活腐化又因工会活动惹来巡捕的强势女子,最后僵先生逃走了。这个“方苟丕”、阿金姐就是他们理解的新思潮、新文化凝结而成的怪胎。这种怪胎形象荒唐而又生硬,展示的是旧派文人对反对家庭专制主义、提倡个人意志的新思潮的内涵一无所知。
怎么处理封建家长与子女冲突的“新旧矛盾”,是旧派文人和五四新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旧派文人从传统社会中走来,对孝道没有鲁迅式的反思,对孝道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温情和想像,批判新文化家所提倡的非孝主义。周瘦鹃“要使人知道,非孝声中还有一个孝子在着”[30],创作了赞美传统孝道的小说《父子》,后受到郑振铎和郭沫若的批评[31]。王钝根针对郑振铎和郭沫若的批评,写了小说《嫌疑父》。医学博士何百止是“矫枉过正会的会长”,“鼎鼎大名世界最新思潮大家”,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一日在抢救维新怪杰陈德淫时,发现陈德淫贴身携带着其母的照片,他停止了抢救,因为陈对他有“父的嫌疑”,后因救治停止,陈死去。因为新思潮的逻辑是:“朋友舍身救朋友的命,便是荣誉的英雄,儿子舍身救父的命,便成了极不名誉的孝子。”篇末钝根附识道:“瘦鹃做了一篇《父子》,写一个儿子把自己的血补救老子,就有人大骂瘦鹃,不该提倡行孝,我想在这非孝的时代,瘦鹃还是说孝,真太不识时务,所以特地做这一篇,替瘦鹃忏悔。”[32]现代都市社会,受了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男女多数率性而为,敢于对抗或忤逆家长,有极大的自由活动能力,他们不再徘徊在父母之命和个人自由行动之中,往往是自己有处置自己身体和命运的能力。对此,父母只能无奈。“今日之中国社会已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父子夫妇就业于不同机关,故大家庭之崩坏,固在必然。而父母子女随职业之不同,恒分居异地,故即小家庭之家庭意识,已必然淡薄。”[33]在几部连载的长篇小说中,独子、独女或者一儿一女现象增多,几乎没有《家春秋》中的几房几子的大家族结构,缺少老太爷、老祖宗的形象。例如,《上海春秋》中陆裁缝一儿一女,陈家一个儿子(陈老六),《春水微波》中一个女儿(丁慧因),《歇浦潮》中钱如海两个女儿,陈浩然一个儿子(陈光裕),汪皙子一个女儿,《新歇浦潮》周树雄一个儿子(周少雄),张家两个女儿。从社会学的理论来说,在传统大家庭的上尖下柱形的金字塔结构中,位于顶端数量稀少的第一代往往有比较强的操纵后代能力,如《红楼梦》中的贾母。而大家庭解体后的小家庭,子女位于倒金字塔结构底端,对上代反而有比较强的反操控的意愿和能力。但在都市社会中,男女学生通过求学、就业或者成天在外花天酒地直接参与社会,极大削弱了父母管辖的势力。父母往往对情爱关系复杂,爱在各种娱乐、社交场所活动,思想活跃的子女管教不住。如《新歇浦潮》里就写了一个女子BB,本来也是好人家的女儿,被家教的男先生勾搭,珠胎暗结,家中父母见生米煮成了熟饭,只能糊里糊涂将女儿许给他。“哪晓得教书先生家中还有妻有子,他在这里做了几年现成女婿,吃她们、用他们,逢年过节还要拿她们些回去养活妻儿老小”……等到BB家里陷入经济恐慌的时候,教书先生忽然托故出门,数日之后打从邮政局寄来一封退婚书。“BB当初既不曾同他正式结过婚,此刻当然也提不出什么交涉,虽知上了此人的老当,然而已悔之无极,只能够抱恨终天了。从此以后BB便落花无主,飞絮因人。”后来她和外国人恶克司结交,在当时也是十分稀少的。[34]“新思潮”造就了众多欲望放纵的“社会之花”,成为某些不良行为得以实施的借口,破坏了规范化、合理化的现代家庭结构,成为都市累累罪恶的元凶之一。对“新思潮”集中火力的批判,是旧派文人缓解伦理失控焦虑的方式。
在上海,传统文化已是强弩之末,统括不了拥有新式生活,接触大量新信息的青年男女,而外来的强势文化在远离本土的空间里也充满着扩张、腐烂的质素。陈思和先生指出海派文化的最大特色是繁华与糜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35]但新型文化在破坏和毁灭中催生新生命的力量很少被旧派文人所感知。旧派文人透过伦理的尺度,看到的是都市的罪恶、堕落和放纵,掩盖了对很多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且旧派文人的伦理是复杂的,并没有统一的道德文化体系,议论事物有多重标准。最后只有落到金钱万恶、社会万恶上,或者用报应说来涤荡污秽,显示出思维力的薄弱。比如说《新歇浦潮》穿插了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在孔子文家当差的高升花钱买了一个老婆,老婆不甘服侍丈夫,被丈夫视为大逆不道之人;高升生病,要妻子割肉饲亲,妻子不允,遂起了杀妻之念;后来高升杀妻后自杀。作者的议论是:“高升女的不甘服侍丈夫,固然错的,但因所偶非人,究属情有可原。高升杀妻,罪有应得然而积愤在抱,又着迷于主人妇女应顺从丈夫的一番言语,以至一发不可收拾,也不能说他完全残暴。但子文说的话确是历古相沿,圣人所垂为世训的大道,当然没错之可言。或者说中国婚姻制度不良,实乃其中的大错。然则倘非此女的父母贪高升茶礼重,又何致有此一段因果,所以说来说去只能混称它一句金钱万恶罢了。”[34]作者一方面认为妇人理应从夫,遵循三从四德,一方面又同情女子所遇非人和认同她拒绝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一方面又谴责高升妻子的父母贪恋钱财,思维混乱,多重标准,最后只有归结为“金钱万恶”。
质言之,伦理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民间形态之一。传统文本中的个人多生存在大家族中,伦理一般以家族、族群等为中介,国家很少直接面对个人,除了在专制和极端的情况下,个人才要直接面对国家承担伦理重担,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海租界乃化外之地,国家缺失,伦理道德的中介(家庭)崩坏,都市伦理当然只能面对都市个体,来探索出一种具有现代性、个人性的伦理观念。旧派文人用批判的姿态对都市伦理的众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建构一套系统的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最后“伦理”不得不变成一种口号,叙事上表现为一种“卒章显其志”的粗俗结尾。
[1] 王蕴章.寒炉夜话[M]//礼拜六,1922,一百五十三期.
[2] 陈家驹.一个堕落的女学生[J].礼拜六,1922,第一百六十七期.
[3] 王德威.“谴责”以外的喧嚣——试探晚清小说的闹剧意义[M]//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73.
[4] 康少邦,张宁,等.城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68.
[5] [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张宁,朱欣民,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0.
[6] 二房东.房客小史[J].金刚钻月刊,1934,九集.
[7] 佩培·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M]//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123.
[8] [意]丹瑞欧·康波斯塔.道德哲学与社会伦理[M].李磊,刘玮,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9] 胡越中.嘴唇底教训[J].珊瑚,1933,三卷十二号.
[10] 郭兰馨.丽丽[J].珊瑚,1934,四卷二号.
[11] 红柳村人.离婚的商榷[J].红杂志,1924,七十期.
[12] 王醉蝶.苦乐[J].紫罗兰,1927,二卷第二十三号.
[13] 程瞻庐.雨中花(共二十回)[J].金刚钻月刊,1933—1934,第一集—第十集.
[14] 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M]//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04.
[15] 周瘦鹃.十年守寡[J].礼拜六,1921,一百一十二期.
[16] 张碧梧.一睡不起[J].紫罗兰,1926,一卷第二十二号.
[17] 张碧梧.内外交攻[J].紫罗兰,1927,二卷第二十三号.
[18] 张碧梧.重圆记[J].紫罗兰,1927,二卷第十六号.
[19] 程小青.断指党[J].礼拜六,1921,一百零一期.
[20] 朱羽戈.杨芷芳探案:银海明星[J].紫罗兰,1929,四卷第十七号.
[21]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J].文学评论,1999(1).
[22] 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0.
[23] 汪洁.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0-89.
[2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25.
[25] 王小逸.春水微波[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26] 周瘦鹃.迎新春[J].紫罗兰,1926,二卷第四号.
[27] 程瞻庐.老鸨式的父母[J].红杂志,1922(三).
[28] 无诤.流星[J].礼拜六,1922,一百六十九期.
[29] 汪仲贤.僵先生(三)僵先生一僵再僵[J].金刚钻月刊,1933(二).
[30] 周瘦鹃.父子[J].礼拜六,1921,一百一十期.
[31] 西谛.思想的反抗[J].文学旬刊,1921,四号;郭沫若.致西谛先生的信[J].文学旬刊,1921,六号.
[32] 王钝根.嫌疑父[J].礼拜六,1921,一百十七期.
[33]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5.
[34] 海上说梦人.新歇浦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87-588.
[35] 陈思和.海派文学的传统[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