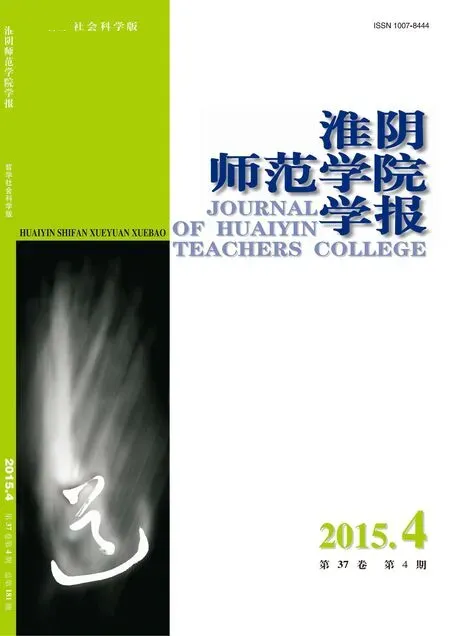近20年现代传媒与新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陈树萍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从1990年代开始,新文学与文学社团、文学出版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文本之外的各种因素与现象对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影响,而这一影响在此前的“文本中心”研究中是被忽视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纸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府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1]。
在“重写文学史”的理性思考下,现代出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影响。大众文化与传播等理论大量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原有的作家作品研究形成卓有成效的补充甚至是“重写”。就近20年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由文学内部向外部转变的研究路径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出现了众多具有启发性与开创性的成果。
一
“重写文学史”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一文对此后的现代文学研究有着很强的示范性。这一论文显示出当时学界的一个新认知:如果仅仅是对文本的重新解释以及一些轶文的发现,那么“重写文学史”就有可能变成一句空话。王晓明因此深入探讨《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在文本之外到底对文学史发生了什么影响。在重新审视《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的过程中,王晓明发现五四文学传统并非简单的“崇尚个性”便可以概括,在文本之外,五四文学还有着不为后人所认真辨析的另一个传统:“仅仅用文本——譬如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作为依据,那自然会得出五四文学是崇尚个性的印象,也就自然只能说,这个传统确实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外部压力下逐渐消失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但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注意到五四时期的报纸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社会的文学机制,注意到这个机制所造就的一系列无形的文学规范,譬如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那种集体的文学目标高于个人的文学梦想的观念……如果把这一切都看成五四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大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不是就能有一些新的解释呢?”[2]
与此同时,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陈思和则在精神史的范畴讨论现代出版在形塑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方面的重要性。“现代出版事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知识分子在调整了安身立命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调整了生存的方式和实现自我的方式,仕途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比较实在的倒是祖先们筚路蓝缕开创而来的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则有力提升了出版事业:“唯有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贯彻其间,出版事业才会有较大的发展。商务、中华以至后来的开明、北新、生活、文化生活等出版机构,均为目光远大、理想崇高的知识分子所掌握。”[3]
在文学研究者积极进入这一建立在学科交叉基础上的学术探究之外,出版专业学者亦对这一问题表示持续关注之意。其中,王余光与吴永贵在出版史著述方面的努力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历史学与出版学基础。两部专著的作者有师承关系,且合作甚多。《中国出版通史·8·民国卷》(王余光、吴永贵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合著版”)与《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吴版”)是他们的代表作。首先,两部专著编纂体例大致相当而详略有别。二者都对民国时期的出版状况进行发展历程、法律与管理、经营活动、出版家群体、出版与社会文化、出版物等方面的分类描述。但吴版加强了对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这一现象的论述。其次,两本专著都对新文化运动中生长起来的新书业作了大量描述与论断。在商务、世界、中华三家现代出版巨头之外,对亚东、泰东、北新、开明、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上海杂志公司等新书业的代表作出详细描述,并不因其规模不够宏大而有所忽视。尤其是吴版不仅继承而且强化了合著版为出版人作列传的传统。将合著“出版家群体”这一章细化为“大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与“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两章,尤其是突出了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赵景深、鲁迅、巴金、张静庐、沈松泉、汪孟邹、汪原放、赵家璧等新文学出版名家。这样设置章节的结果凸显了“人”在出版史中的意义。再次,吴版增加附录“有关出版法律法规及书业章程”,为读者提供一手的原始资料。
王余光与吴永贵对新书业的重视远在修撰出版史之前,这由199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贡献》(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以下简称“《贡献》”)与《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王余光,以下简称“《初探》”)二书可见一斑。《初探》分为绪篇、新图书出版业的形成、译书与西学引进、古籍出版与古籍整理、教科书与教育发展、丛书、工具书与文化普及六部分,已经初步展示上述两部出版史的雏形。《贡献》为三人合著,以个案分析见长。全书分为三部分:新图书出版业的三足鼎立(描述商务、中华、世界三巨头)、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劲旅——亚东图书馆、新图书出版业的世纪工程——《四库全书》的出版与研究。《初探》对新图书出版业的整体把握以及《贡献》对个案的细致描述相得益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两部专门以新图书出版业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实为奠基之作。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自省以及对传播、出版专业知识的嫁接导致了传媒与现代文学这一研究方向显示出勃勃生机。《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编,2003)与《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程光炜编,2005)两本书收录了从1990年代至2005年的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而事实上,这两本论文选的作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几所高校,而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者远非此数。相关研究专著也从1990年代的寥寥可数到今日之繁多。就有关“现代传媒与新文学”这一论题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的收获。
(一)整体性观照研究。这以《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马永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路英勇,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现代出版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秦艳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周海波,中华书局,2008)、《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1928—1930)》(刘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为代表。
马氏所著《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以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为研究时间段,着重分析现代出版兴起的因素、作为文学变革策源地的公共舆论、文化传播的三个效果以及最终导致对新文学的选择。如果说,马著初步勾勒了现代文学发生前以及发生瞬间与现代传媒之间关系的话,那么其他专著则着力于新文学发生之后与现代出版之间的互动。路英勇以出版人身份介入五四新文学出版这一论题,在强调出版业对新文学的生成学意义之后,对新文学的各种出版物进行有代表性的分析,如期刊《新青年》《新潮》对新文学诞生的意义;以胡适《尝试集》为代表的亚东版新诗集所具有的同人认同之意义;新文学社团所办的文学大刊《小说月报》与《创造》季刊各自的成就与地位;新文学丛书的出版问题等。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路氏抓住了五四新文学出版物中的亮点,借此阐释新文学与出版之间的认同与互动,绘制出五四时期文学出版的路线图。
秦氏所著《现代出版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首先提出1930年代文学出版的三个问题:阶段性特征、大众化倾向以及商务化追求。其次则进行左翼、京派、海派三类文学出版物,主要是文学期刊如左翼的《萌芽月刊》与《北斗》、京派的《骆驼草》与《文学杂志》、海派的《现代》等的分析。在期刊之外,秦氏又以1930年代最具有文学出版特色的开明书店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分析个案,探究文化人巴金等的出版理想及其实践过程。在对1930年代文学出版的探讨中,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出版贡献是不能忽视的,秦氏对《良友文学丛书》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探讨多有闪光点。秦氏在挑出1930年代的文学出版关键人物、重要事件、重要出版物的基础上,在文学与出版的双重维度中成功再现了1930年代的文学生产现场。
周海波所著《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其早期《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这一研究基础之上的深入之作。《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以高度的概括性见长,如对这一论题的问题意识、相关特征、传媒与文学间的流变、传媒与启蒙运动、传媒与知识分子群体等的探究显示出跨学科的思辨力。在全书的后三章则深入文学语言、文体与现代传媒之间关系的研讨。在系列问题研讨中,可见作者建立在现代社会观念之上的现代文学史观,实现了重构现代文学史的内在冲动。
(二)有关新书业出版机构、出版人的个案研究专著开始出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刘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孙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陈树萍,上海三联书店,2008)、《邵洵美:出版界的堂吉诃德》(王京芳,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等。
刘纳从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合作与分裂中发现了出版机构以及刊物对一个新生文学社团的意义。泰东接纳创造社,为其登上文坛提供了最初的基石,创造社则为泰东赢得了文化资本与商业利润。但刘纳发现,这一文学史上最具青春激情的遇合提示着势力、圈子等在文学事业中的力量。刘纳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几乎每一位新文学人物都属于某个‘圈子’,而空头的圈子几乎是没有意义和意思的——它只能通过刊物产生影响力。同时‘如果圈子中的主要人物抱有造就‘统一中心’的目标,这目标也只能借助刊物来实现。”[4]
孙晶则以吴朗西、伍禅、巴金、陆蠡、丽尼等于1935年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为研究对象,在作家与出版社、文学出版物两个方向上展开这一研究。创建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人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与出版理想让这一小型出版社为1930年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研究注重发掘巴金、鲁迅、曹禺、李健吾、靳以、陆蠡、何其芳、九叶派等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之间的多重关系及各不相同的表现方式。在有关出版物的研究中,孙晶以其标志性出版物《文学丛刊》以及翻译类丛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删繁就简而又清晰明了。通过对“人”与“书”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分析,孙晶总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编辑特点,即平民色彩、包容百家沟通南北交流、推举文坛新秀、遵循艺术审美原则、出版系统化等。[5]由孙晶的研究可以发现巴金等创办者是真正忠实于文化理想而能摒弃逐利商业思想的出版者。
《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北新书局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这一新文学出版的“老大哥”是如何与鲁迅、周作人等知识分子合作,推动五四新文化的传播。陈树萍通过对北新书局的期刊出版、书籍出版、书局与作者之间关系等的分析,全力打捞一个被遗忘的新书业文学出版“老大哥”的历史。在重现北新出版业绩的过程中,该著对《语丝》《奔流》《北新》等刊的研究建立在重读期刊之基础上,侧重于分析编辑者、作者的社会人文关怀与文学想象,由此重新审视这些期刊在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中的意义。在对书籍的研究过程中,陈树萍借用出版与传播学知识,由此发现出版商在理想与利益之间的徘徊。该著在对北新书局与文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不拘泥于史料呈现,而是从同气相求的文化背景与性情出发,勾勒北新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以及其他作家之间的互动、信任以及龃龉。
就以上三部出版机构的个案研究而言,都有力描摹与阐释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在现代文学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在作家与现代出版这一论题的相关研究中,王京芳所著《邵洵美:出版界的堂吉诃德》是第一部从出版与文学两个维度上对邵氏进行现代文化人意义判断的专著,改变了邵氏的“唯美—颓废诗人”这一单一诗人面相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风流轶事主人公形象。首先,该著对邵氏诗歌创作与西方诗人史文鹏、戈蒂耶等的对话与吸收的辨析是第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探究邵氏诗歌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剥去邵氏艳情、浮夸、颓废的外表,直抵其现代人的柔弱心灵。此外,在掌握了大量邵洵美生平活动的基础上,王京芳将邵氏的出版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诗人、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期刊出版,这以狮吼社、金屋书店为中心;后期则是以出版家身份从事文化期刊出版,这以时代图书公司与第一出版社为中心。[6]由前后两期的变化可以发现,邵氏从出版业的“票友”变成行家里手,而其身份的变化亦可以展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上海所能触摸到的文化生存空间。
(三)期刊的个案分析。新书业的出版实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二是书籍。在这两者之间,期刊因易于得到传播学理论的支持而更吸引研究者。《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董丽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张涛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是对1920年代期刊进行个案分析的佼佼者。《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与《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程光炜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两本论文集收录了相关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论文。
张涛甫以1920年代一代名刊《晨报副刊》为讨论对象,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维度上展开对五四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与报刊合作问题的研究,这是本著最大的成功。张涛甫将《晨报副刊》视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在辨析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三任编辑不同思想理念之外,发现1920年代知识分子对苏俄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剖析周氏兄弟在《晨副》上的作为,明确《晨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呵护之功,并以《晨副》对冰心、沈从文的培育作为生动例证。在大量的人与副刊关系的研究基础上,作者指出:由于副刊具有广泛的社会接受基础,利用副刊来做启蒙工作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便捷优势。《晨副》是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给知识分子提供的一个难得的“公共领域”,但还比较脆弱,很不稳定。[7]尽管对《晨报副刊》所开创的公共领域有着相当的理想好感,但作者还是清醒认知其脆弱的一面。
董丽敏对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与现代性想像之间的深切纠葛进行研究,注意分析《小说月报》上的翻译、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小说创作与“现代性”相遇之后淬炼而成的面貌。值得赞赏的是,该著在“现代性”的照耀下,对《小说月报》革新之缘由以及编辑者之变换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尤其是在阐释1921年革新《小说月报》最力的沈雁冰很快便辞去主编之位而由郑振铎接手这一问题上,作者没有沿袭常见的因新旧文学争夺阵地而导致的“新文学一次不得已的妥协”之说,而是在分析沈、郑二人在性格、人脉、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各种异同之后发现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变化,还因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并未能获得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主流的完全认同,尽管鲁迅也曾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倾注大量心血。而改换编辑的决定也表明商务立足于民间而淡化其现实关怀的一种独特现代性。[8]
与张涛甫、董丽敏对刊物穷形尽相、以博士论文之篇幅进行研究相比,更多的单篇论文以敏锐抓住刊物精神特质或某个鲜明特色取胜。《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收录有《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陈平原)、《〈语丝〉时期的苦雨斋弟子》(颜浩)、《“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李宪瑜)、《〈现代〉诗歌的历史定位与艺术探索》(孙玉石)、《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以〈无轨列车〉、〈新文艺〉与〈现代〉为中心》(葛飞)、《〈长河〉中的传媒符码》(吴晓东)等。《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则在收录王晓明、陈平原的文章之外,还收录《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李欧梵)、《王进珊与〈申报〉文艺副刊》(徐瑞兵、郑娟)、《〈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刘震)、《〈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李怡)、《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吴福辉)、《1928年的文学生产》(旷新年)、《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雷世文)、《“新诗集”与“新书局”:早期新诗的出版研究》(姜涛)、《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社团与报刊考辨》(钱振纲)等。
由以上两部文集收录情形可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新青年》得到研究者的无比重视。相对于王晓明1991年时对《新青年》功利主义、剑走偏锋与绝对主义思路的激情发现,十年之后(2002)的陈平原试图站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双重维度中对《新青年》作全面审视。《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一文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晶。全文对《新青年》进行以下六个问题的研究: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这6个问题分别涉及《新青年》的同人精神、编辑方针的确定与变动、《新青年》如何推动新文学的发生以及取得的成绩、《新青年》历史记忆的建构这样一些杂志生存以及历史记述的关键点。《“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李宪瑜)与《〈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刘震)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出发切入《新青年》研究,试图在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层面赋予“通信”栏目以现代思想传播的意义。李宪瑜之文认为这一持续时间最久的栏目以其“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性质讨论了近现代中国许多重要的社会与思想问题,对现代学术思想的传播、现代白话文的写作以及现代杂志的编辑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刘震之文则注意爬梳《新青年》建构“公共空间”以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发生器的过程,指出其瓦解是因政党意识形态的介入。该文以《新青年》为个案,思考的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发声以及发什么声音的问题。
由上述两本论文集可以发现,在《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副刊》这三个研究热点之外,《语丝》《现代》也是吸引研究者讨论的对象。颜浩之《〈语丝〉时期的苦雨斋弟子》剖析周氏小品文、民间文化趣味等文学文化思想在俞平伯、废名、江绍原三位弟子中的传承。孙玉石与葛飞之文都涉及《现代》这一标志着现代派走向文坛前台的刊物,孙文注意分析其中的诗歌创作,葛文则注意这一刊物上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共生”问题。
(四)对现代出版与新文学传播关系的考察常常与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密切相关。因现代文学社团聚集文人最有效的手段便是通过创办同人杂志与出版文学书籍而实现。文研会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而正式获得文坛话语权;创造社依靠泰东图书局实现了自办杂志《创造》季刊与出版丛书的梦想,打破了他们所言的文坛垄断;因《语丝》而聚的同人则是推动北新书局问世的重要力量……就现代文学社团而言,积极地拥抱现代出版,借助出版展示自身是立足文坛的不二法门。因此,近年来的社团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对这一问题表示足够重视。由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可谓是佼佼者。该书系收入的《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庄森,东方出版中心,2006)、《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陈离,东方出版中心,2006)、《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石曙萍,东方出版中心,2006)、《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咸立强,东方出版中心,2006)、《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廖久明,武汉出版社,2011)、《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刘群,武汉出版社,2011)等皆显示出这一倾向。
庄森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以“人”为主干,探究杂志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等的遇合。庄森对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动机“祛神话”,认为陈氏的初衷是迫于生计,抉择以“办刊为生”。其次则发现了蔡元培为陈氏编造假学历、履历从而获得教育部的任命。最后辨析后期新青年社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无关系,《新青年》则因色彩左倾而被租界查封。[9]陈离对语丝社的研究则是在勾勒《语丝》周刊诞生原因的基础上,对周刊主编周作人、鲁迅、柔石、李小峰各自不同的编辑风格进行论述。此外,语丝社与北新书局、莽原社、未名社、狂飙社等的交集也尽在观察视野之内,其间所涉及的杂志与出版物亦在论述范畴之中。咸立强在对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早期合作进行研究之外,更注重对创造社出版部进行早、中、晚期三个时段的分期研究。创造社出版部开创作家自办出版机关的先河,并引发了同人间商业化与政治化的分歧,从而上演了文学、政治、商业之间的三重纠葛。咸立强将创造社同人判断为流浪型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解构力量,从而催促着文学的新陈代谢。刘群的新月社研究在对《晨报副刊》《新月》月刊、《诗刊》《诗选》等新月社重要舞台进行分析之外,还特别对新月书店的创办给予重视。廖久明在狂飙社的研究中,对这一社团的出版活动多有阐释,如《狂飙》周刊、《莽原》周刊、《弦上》周刊等以及丛书等。这一社团成员可被视为在新文化思潮激荡之下觉醒的一代青年,他们的勇敢甚至桀骜不驯,都构成了现代文学的生动面貌。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之外,《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陈星、朱晓江,上海三联书店,2009)与《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李秀萍,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亦是很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陈星、朱晓江在考察白马湖作家群流变之时,注意分析这一群体的写作出版活动催促了开明书店的发扬光大,从而以一个文学群体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写下光彩一页。李秀萍对文研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进行详尽分析,对文研会的期刊以及丛书展开编辑、传播学意义上的论述。
在上述专著与论文之外(大半是以博士、硕士论文为基础),尚有大量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在现代出版传媒的视野中观照现代文学为切入点,这里且以博士论文作为综述样本。《五四新文学语境的一种解读——以〈晨报〉副刊为中心》(卢国华,山东师范大学,2006)与张涛甫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基础上进行相关论述的企图相反,卢国华致力于对《晨报》副刊的商业性以及倡导新文学的努力的分析。《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清末民初的出版活动为中心》(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2008)在从印刷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时,指出“印刷现代性的展开为新的民族一国家、文化建设的想象和建构开辟了另外的空间。‘印刷大于出版’局面的形成直接带来了众多中小型文艺类出版机构的创立。出版和印刷的分离使更多不同专业、不同诉求的人卷入到‘编辑出版’行业,从而导致多元而有活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10]。《开明书店·“开明人”·“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邱雪松,华东师范大学,2010)在探究知识分子与出版的联姻之时,特别注意到开明书店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鲁迅文学经典与现代传媒的关系》(张红军,辽宁大学,2011)通过对现代报刊与鲁迅创作的语言、文体选择的关系来说明现代传媒对于鲁迅文学创作的潜在规定性。此外,该论文还分析了鲁迅对于现代传媒的影响。《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叶红,东北师范大学,2010)对新月诗派的研究以相关传播媒介研究为基础。《预告、呈现、揭示——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胡明宇,苏州大学,2012)选择“广告”这一传播手段展开相关研究,表现出现代文学的丰富性。
三
以上研究综述并未能对近20余年的“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这一方向之下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只是举起重要者、关键者进行评述。在此之外,有必要指出的是:
(一)大量史料性质的发掘之文并未进入这一综述范围。这既是因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也是因这些史料性文字多数并未展开相关议题的论述。但它们提供了后续研究最为重要的史实基础。
(二)因是进行概括类型的综述,难免有些研究成果未能悉数收入。为免遗珠之憾,特补录于后。《“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姜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从出版角度介入现代新诗的创作、出版与接受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8章。上编主要是进行新诗集出版与阅读研究,因此涉及读者接受与新书局亚东、泰东的出版问题。下编则以《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女神》为个案,讨论“新诗集”如何呈现新诗、新诗合法性与历史定位等问题。这一研究在以“新诗集”为讨论对象时,便已经站在现代文体与现代出版的双重视域中,从而为现代文学与传媒关系的讨论划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金宏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则是以出版专业视角进入新文学的版本批评。作者在通论版本本性、异本的形成与修改、研究的角度方法、版本谱系与原则之后,重点展开对《雷雨》《屈原》《天国春秋》《风雪夜归人》《蚀》《八月的乡村》《无望村的馆主》《怨女》等新文学名著进行多版本的分析。这一系列的分析有力弥补了新文学相关作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盲点。最后一部不可不提的研究成果是由钱理群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分别担任分卷主编的三卷本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三卷本以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个阶段的划分,即1915—1927、1928—1937、1938—1949 为断代标准,从而分出三卷。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从而构建现代文学史的这一努力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通过文学广告回到最初的作品诞生与流通的现场,且采用编年体与书话的叙述方式,无疑是用一种活泼、自由的方式重新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蜿蜒多姿的河流,让读者充满发现的愉悦与期待。当文学史用这样一种新颖、生动的形态问世时,不得不说,这是近20年来“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这一议题之下最丰硕、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收获。
[1]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4.
[2]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J].上海文学,1993(4).
[3] 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1993(3).
[4] 刘纳.社团、势力及其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
[5]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8-16.
[6] 王京芳.邵洵美:出版界的堂吉诃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4.
[7] 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7-230.
[8] 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4-127.
[9] 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10] 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清末民初的出版活动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