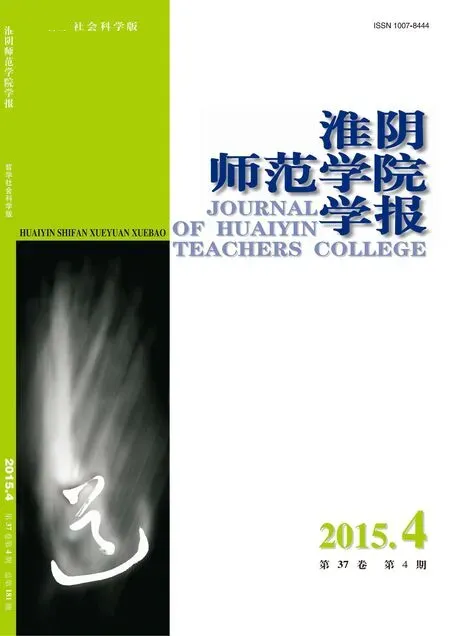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七):科学知识与政治
——大卫·凯里对布赖恩·温的访谈
布赖恩·温, 大卫·凯里
【科学哲学·如何认识科学】
“如何认识科学”(七):科学知识与政治
——大卫·凯里对布赖恩·温的访谈
布赖恩·温, 大卫·凯里
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并被应用于公共领域的,是布赖恩·温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总是由社会情境所决定;知识潜在地是无限的,但在某一给定的时刻,我们所能涉足的知识却相当有限。因此,在某一给定的情境中,视什么为知识总是成问题的,而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谁可以决定视什么为知识。这些问题通常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判定标准以决定什么是有益的,科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公民更能胜任于提出这一标准。有关核能的公共调查——“温士盖调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当下的基因学研究,已经用基因与复杂细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幅新图景,取代了全能基因的形象。介入这一复杂环境,不可避免地要求判定什么需要关注,而什么又可以忽略。
科学知识;建构;协调;温士盖调查;基因学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栏目中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在当代生活中,技术的影响无所不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主导着我们的做事方式。然而,科学和技术却几乎处于政治决策的范围之外。从未有选民对原子裂变或跨生物体的基因移植进行过投票;也从未有立法机构对iPod或互联网进行过授权。因此,我们的文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悖论之中。我们颂扬自由与选择权,但却又屈从于作为现实宿命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所带来的文化变革。今天的“思想”栏目,将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如何认识科学”,其主题是探讨政治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我们邀请到英格兰北部兰卡斯特大学的布赖恩·温,目前,他在一家旨在研究基因技术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机构任副主任;同时,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上,温也是英国最为知名的撰稿人和研究者之一。“如何认识科学”栏目由大卫·凯里主持。
凯里:1942年,一位名为罗伯特·默顿的美国社会学家,曾写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文章题为“科学的规范结构”。如其所言,科学由如下四个原则所引导: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后来,人们普遍使用其首字母缩写CUDOS来代指这些原则。CUDOS的要点是:科学中包含着一个至高承诺——真理;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科学家应该牺牲其所有狭隘的个人关注点——此为普遍性,所有私人利益——此为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以及先前所有的智识承诺——有组织的怀疑。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科学的这种英雄形象仍然发挥着某种文化牵引力的作用;但到了70年代,一场源自英国的智识运动对其发起了激烈挑战。这一新思想最初的两个中心是巴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那里的学者主张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进行彻底的修正。在这些学者看来,科学是一项社会事业,正如其他社会体制一样,科学中也充满着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权威的迷信。在他们看来,科学的禀赋奠基于其社会组织中的,并非借助某种英雄般能力而可以立足于社会之外。
布赖恩·温是这一智识运动中的一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入了爱丁堡大学的科学论小组,但其兴趣不同于他的某些同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研究科学实验室中的情况,要么分析科学争论——他们试图观察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建构之中的科学知识。布赖恩·温力图理解科学知识是如何将其嵌入到公共领域之中的。他忍着重感冒,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温生长在英国西北部的一个乡村,凭其学术能力进入了剑桥;在剑桥,他于1971年获得了材料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工程材料的属性。他说,直到那时,他从未真正思考过科学政治学。不过,他当时遇到了一次足以改变其命运的谈话。
温:我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导师问我是否要做博后。当时我确实学得很开心,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呢?因此,做博后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我回答,好的,非常好,我愿意。接着他说,那好,就你想做的写下一些想法,然后提交给我,我们在一到两周后讨论。接下来我就在思考我要做的计划。当时恰是石油价格开始飞涨的时期,所以,每个人心中所想的除了能源还是能源。而我恰好又是一个材料科学家,所以我想,我应该能够对此做一些有益之事。什么样的智能材料能够提高能源利用率并节省能源呢?我就此写了几点想法之后,就去见我的导师;但他却视我如火星来客,你应该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他对此不屑一顾。过去,他作为我的导师,我们处得非常愉快;而现在他对我的计划不屑一顾,我极为失望。于是,我离开他并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一起去喝了一杯。我向皮特吐诉遭遇,因为我非常迷惘,也非常失望。皮特却说,布赖恩,打住吧,想想看,你们系——我们所说的是剑桥材料科学系——的资金来自哪里?难道它不正是世界范围内顶尖材料科学系之一吗?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可我当时却并不知道答案。我在剑桥呆了6年,而我并不知道这一简单问题的答案。这位朋友在政治上比我更加警觉、更加清醒。于是,我便停下工作并开始观察,有意到处看看。当然,毫不奇怪,维持系科运转的大部分不义之财是来自军事或准军事机构。在博后阶段,如果我想研究那些可用于坦克、导弹或其他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之上的新一代合金材料,那么金钱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果我所考虑的是那些具有科学趣味和社会用途的东西,那么,也就[与那些机构]毫无利益关系,进而可想而知,也就没有资金了。于是,当时我开始反思,这也许并不是我的余生想做的事情。我确实不想把我的生命变为军工集团的附属物。
凯里:布赖恩·温对此的认识,促使他从科学进入了新兴的科学论领域。他去了爱丁堡大学,并投身到那些开始用新视角来反思科学的文献之中。对涉足该领域的任何人而言,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著作是其中的关键文本之一。
温:1962年,库恩出版了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该书真正勾画出了科学作为文化实践的各种方式。在看待自然的方式问题上,人们有各种特定的、仍发挥作用的教条式承诺,而针对这些承诺,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在此意义上,科学是文化性的。他所称谓的方法论承诺和理论范式,能够反映这些内容。这就是范式这一知名术语的真实由来。因此,在任何给定的专业领域中,某些特定的理论承诺并不必然会成为科学怀疑主义和怀疑式的判决性检验的对象;相反,它们事实上是观察、分析和检验在其中得以展开的框架。因此,换句话说,[科学中]存在着教条的重要因素。库恩的一篇著名文章就以“科学中教条的功能性角色”为题。*库恩这篇文章的准确名称为“科学研究中教条的功能”。参见,Thomas S. Kuhn, The Function of Dogma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 C. Crombie ed., Scientific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echnical Invention,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61, pp.347-69.——译者注。因此,在库恩看来,现代科学本质而言就具有某种模糊不明性。他称之为必要的张力。
凯里:科学在自由探究与教条承诺之间的这种张力,成为布赖恩·温的一个关键思想。比如,它解释了为何科学能够承受一定数量的对立证据或库恩所谓的反常。
温:当我们遇到一个无法在现存理论框架内——这适用于我们谈论的任何一个专业,无论它是固体物理学、轨道化学或其他任何专业——得到解释的反常时,我们就会抛弃现有理论并寻求一个更好的理论吗?事实并非如此。如库恩所言,任何理论从其产生之初就面临着反驳。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理论来说,总会有反常存在,反常总是与之相伴。关键之处在于,科学家们能否说服自己暂时悬置和搁置反常,因为他们坚信反常终将得到解释。随着理论的进步,人们将能够解释这些反常。
凯里:托马斯·库恩促使布赖恩·温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事业,用温在其第一本书中所言,是“合理性与惯例”的混合物。这颇令人吃惊,甚至可以说是震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谈论的自然科学一直享有一种超常特权。其他形式的知识可能会被环境所塑造,而科学则是对自然本身明晰的揭露。人们认为,科学家所信任之事,恰恰就是真实之事。
温:因为它是真的,所以人们相信它。这就是对科学真理的说明。但是,当你真的去考察科学家为何会相信他们所相信之物时,上述说法又毫无意义。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真的而相信它们。它们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科学家相信它们的原因。在接受了6年的科学教育之后,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我知道事实就是这样。那么,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如果我们说科学真理需要一种社会学的说明,这是否意味着科学真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建构的?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自然没有发言权?我认为,人们在此常会犯一个关键性错误。说某事经由社会协商而被建构为一种信念,难道就意味着自然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吗?根本不存在合乎逻辑的理由。因为多数情况下,当我们针对可被视为有效知识之物进行建构和协商——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时,我们同样在其中嵌入了一个问题,它管用吗?你知道,我们尤为不需要那些不管用的知识。这里的关键之处在哪呢?确保某种知识能够管用,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性的说法。换句话说,我们想使它尽可能真。但是,当你进一步深入到这个问题之中时,你会说,既然这样,那么,针对什么目的而言它是管用的?什么算是管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社会性的问题。什么算是管用的,人们对此各持己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知识的恰当目的上也是观点各异,我们正是由此切入到许多当代问题之中的。
凯里:布赖恩·温对科学知识恰当目的的兴趣,使他走向了政治的方向。与爱丁堡大学的同事一样,他关注科学知识如何被制造、如何被体制化之类的问题——他称之为新社会学的圈内方面——但最让他着迷的是科学转向公众的方面。
温:从剑桥到爱丁堡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赤裸裸的、无处不在的政治世界,而科学正是在这一世界中才得以存在、得到资助并得以应用的,如此等等。于是,我睁大眼睛去查阅有关如何制造科学知识的所有圈内资料,不过,我同时也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环境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是核能问题。所以,我一直对公共领域的科学知识问题感兴趣,在公共领域中,有趣的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矛盾性,更涉及公众观点。
凯里:布赖恩·温从已故美国社会学家、当时执教于康奈尔大学的桃乐茜·内尔金(Dorothy Nelkin)的工作中获得了这一政治转向的灵感。她当时正在研究政治争论中科学的角色,例如,当时有关在康奈尔附近的卡尤加湖上建造一座核电站的政治争论。
温:桃乐茜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好的。风险太高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此类科学的断言都受到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的左右。科学家们都受雇于政府、飞机制造业或核工业,所以他们会表达一种观点。那些倾向于环境的科学家,则会表达另外的观点。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观点在某些决策情境中遭遇,桃乐茜所要考察的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并且与通常所说的科学神话恰恰相反:当人们将两种对立的科学观点放到一起时,它们仿佛都成了假说,而真理便从这种混合物中出现。你是知道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检验,而另一方则又对最初一方进行检验。真理便从这种混合物中产生,接着,共识也就产生了。这是科学知识发展并进步的标准神话。而桃乐茜所展示的是:在公众领域,当比如说围绕核风险的两种相反的科学观点彼此面对时,常常会发生什么;最终所发生的事情是,每一方仅仅进行更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事情变得更加极端化,在技术上更加煞费苦心,新的论证被带入;但双方固守自我并深入挖掘证据而非真正提出某种一致的和单一的科学真理。上述情况向我们提出了关于科学观点是如何被架构的各种问题。这种架构真的就是问题所在吗?这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
凯里:桃乐茜·内尔金发现,公众领域敌对的科学观点倾向于自我坚守,而非走向中间立场。这启发了布赖恩·温:处于争论之中的科学的内容可能并不像他所谓的架构一样重要,首要之事是什么决定了科学是如何被利用的。1977年,当他参与一项有关核能的公共调查时,他自己确认了上述发现。当时的问题是,被称作THORP(热氧化物再处理工厂)的核燃料后处理工厂是否应该添加到已经相当巨大的、位于塞拉菲尔德的坎布里亚海岸的英国核能综合设施体中,布赖恩·温就在距此不远的地方长大。这一调查被称作“温士盖调查”(Windscale Inquiry),是由英国高等法院法官贾斯蒂斯·帕克先生——主持的一场超过100天的公众听证会,之后裁定工厂可以建造——主导的。布赖恩·温作为反对THORP工厂的倡导者和一个观察家,追踪了整个过程。5年后的1982年,他就“温士盖调查”出版了一本名为《合理性与惯例》的著作。该书表明,此项调查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在其中,政治决定被伪装成了科学决断。
温:在那本书中,我主要讨论并分析了此次调查中的法官是如何对合理性进行十足经验主义的理解的——走入自然,发现答案。自然会告诉我们真相。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使用科学方法以专业方式对事物进行考察,进而,我们将会发现自然所告诉我们的答案。它是否安全呢?位于塞拉菲尔德的THORP工厂是否安全呢?我当时试图告诉法官的是,看,THORP工厂还没有开始建造,它并不存在,它对自然还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去那里也看不见它;我们实际上所能做的就是考察前景和回顾以往。专家们对先前工厂的运转说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证据,已经可以对之进行调查。他们兑现承诺了吗?我告诉他,在对已经发现的证据进行切实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哦,不,他们并没有做到。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针对这一工厂——从其使用的材料等方面来看,该工厂的辐射强度较其前身要高20多倍——所作出的承诺?这是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的。因此,事实上,他们上次就做出了错误的承诺,人们对此为何不严肃对待呢?或许,他们这次也会做出错误的承诺。
他并未认可我的观点,他只是说,不,我们可以走出办公室并检测一下环境后果,看看它的风险是否太高。于是我就说,是的,你是知道的,无论THORP工厂是否应该被建造,它终究是一个政治问题;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合法的。你根据各种各样的社会观点——不管是你想要接受的社会观点、还是你试图回避的观点,诸如此类——做出选择。这一过程当然会涉及证据、理性和科学,但只是局部涉及。事实上,科学并未承担全部。帕克负责此次调查,在其所提交的报告中,仿佛科学决定了真理;而律师们则帮助提供了真理得以揭示的专业依据。如此呈现方式,简直就是在呈现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真正做出此类决策的神话。它将合理性作为一种权威仪式加以使用。因此,某种意义上,合理性在此成为公共论坛中的一种消遣。我认为,在现代社会所使用的风险话语中,人们能够发现此类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挥着作用。它不仅是一个核能问题,而且也是生物技术、转基因产品和其他各种事物的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要进行风险评估,确实如此;但是也要揭开那些在貌似纯粹的科学话语中起作用的社会和政治承诺。
凯里:对布赖恩·温而言,“温士盖调查”是由政治启动的。他当时就告诉BBC说,它“像被卷入一个漩涡一样”。他认为此项调查的这一特征,部分原因在于调查的开展方式。他确信,一个明显的政治决策被伪装成了一项技术和科学的决断。但这样的状况也让他感到忧虑,因为它处于危机之中。温士盖,后来被称为塞拉菲尔德,统辖着英格兰西北海岸的大片区域,就在离布赖恩·温成长不远的地方。它最初是军事设施,在二战期间生产军需品,1947年后为核武器生产原料。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增加了民用核反应堆,该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综合体,以至于爱尔兰和挪威政府曾经要求关闭它。特别是因为1957的事故,温士盖综合体也给周围的英国乡村投下了长期的阴影。
温:两个军事生产反应堆之一失火并失去控制地烧了好几天。负责人只是三缄其口,完全保密,没有通告,仿佛任何事情都未发生。所以,散发出来的物质吹散到当地的农场,实际上就散落在帕特德勒(Patterdale)地区,当时我就生活在那里——我在1957年大概是10岁,它烧了好几天,结果大量的强放射性物质散发到英国甚至英国以外的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控制它,对此不测事件也没有什么B计划。他们作出决定,唯一可做之事就是承担以水灭火的风险。但是,他们被吓傻了,这样做实际上可能产生氢气,进而引发一场氢爆炸,就像切尔诺贝利大爆炸一样。于是,他们所能做的基本就是把消防带中的水浇到堆芯——当时被烧得炽热——上,看能否浇灭它。真的就像是祈祷的时刻,你应该能想象得到的。他们清楚,如果出差错,他们将必死无疑。然而,这一办法起作用了。他们成功浇灭了它。工厂里的人说,确定火被浇灭之后,他们就立即锁门并丢掉了钥匙,根本不想了解里面溶化了的混乱状况。不过,此后他们一直忙于拆卸工厂,并且也已经拆除了最早的反应堆。因此,现在它正处于清理过程之中。
凯里:1957年的温士盖大火以及与之相关的秘密,是1977年温士盖调查的一个重要背景事件。198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后,当放射性同位素再次袭击坎布里亚乡间时,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布莱恩·温研究了它对当地牧羊农民的不幸后果,这一研究,为他此前有关教条在科学中的角色的陈述,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在此,我想详细追踪这一故事的发展。故事发端于放射云,它在切尔诺贝利上空形成,并扩散到了北欧和西欧。
温:首先发生的是,放射云抵达英国上空,其主要成分是放射性铯,另外也包含放射性碘及一些锶,这些放射性物质都来自切尔诺贝利。它飘过斯堪的纳维亚,降落到欧洲大陆,而后又到达英国。事故发生后,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一周的时间。斯堪的纳维亚已经散落了大量的放射性铯,甚至都影响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地区的驯鹿。放射性铯非常容易引起降雨。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存在放射云的某一特定区域遇到降雨,那么,在雨水从云中降落地面的过程中,你会染上大量的放射性铯。这就是在坎布里亚地区发生的情况。事实上,那天我正在湖边散步。我对那个周末记得非常清晰,因为有一场非常大的雷阵雨。大雨真的倾盆而下。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但事实上人们已经遇到了高放射性物质。
凯里:最初,有人说这种含放射性物质的雨是无害的。居民们被告知水是安全的,农民获得保证,他们的羊也没有受到污染的威胁——在荒山或岩群山丘上放养的羊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但当地后来的情况发展,却给人们带来了某种不安。
温:受切尔诺贝利放射尘影响的大部分当地农业人口,1957年时就已经生活在那里,他们当时如果不是成年人的话,也是孩子。当地的农业文化即便在当下也是非常稳定的。农场在代际传递,父母会告诉子女大量信息,传递牧羊技能;然而,历史当然也会被牢记,这其中就包括1957年我们所遭受的欺骗:那场大火带来了辐射,但却无人告知我们。因此,当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到来的时候,专家仍然说,哎呀,这里毫无风险,没有问题,你们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又如何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些人呢?我们该如何信任他们?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问题是,跟踪记录呢?先前的经历呢?对许多当地人来说,先前的经历就是在1957年大火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撒谎,他们掩饰,他们只是保密多日却从未告知我们任何真相。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就这次他们释放出的信息而言,这是用完全逻辑的、合理的方法达成的判断。
凯里:这些怀疑被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所加剧。科学家们最初告知农民一切正常,但接下来,他们便不得不修正其表述。
温:起初科学家们说,没有问题,无需担心。即便那些收集房顶流水以便引用的人也被告知,完全可以饮用——没有任何问题。你们的饮用量不会构成威胁。因此,每个人都认为,没有问题,一切照旧。在接下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大概到了6月中旬,事情发生了改变。当然,科学家们一直在监测各种物质。他们检测了湖区的羊羔,发现它们已经高于欧洲干预水平——每千克活畜重量中含1 000贝克(放射性活度单位),这与所检测的动物种类无关。于是,他们不得不说,好吧,应该实施禁令。但他们又向农民作出保证,禁令只需持续3周,一个月之内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他们所说的理由是,当时尚未发现超过干预水平两倍高的情况,他们所做的每项检测都显示低于每千克2 000贝克。羊身上的放射性铯的生物半衰期大概是21天。生物半衰期不同于物理半衰期,因为前者用以衡量羊排出放射性物质的速度。所以,科学家们说,21天后所有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将会减为原来的一半。这样,3周之内就完全可以低于1 000贝克了。因此,一个月的禁令期,就可以克服这种情况。这就是他们对农民的保证。然而,到了7月中旬,一个月过去了,检测显示放射性物质的含量根本没有下降,依然高于干预水平。于是,他们的预测——这是第二次预测——依然失败了,依然受到了经验的驳斥。
因此,他们当时事实上被迫采取了无限期禁令。在当时,这显然是一个大麻烦。湖泊和丘陵地区并没有多少天然牧场,冬天更是一无所有。所以,在湖区,你所能做的主要就是在春天饲养大量的羊羔,然后在夏天养肥它们;但冬天来临之前必须卖掉它们,因为你没有东西喂养它们。如果你留下它们,它们就只能挨饿了。因此,正常的做法是在10月销售季卖掉它们。这样,它们在某处低地牧场被养肥,而后被卖掉以供食用。但是,这一无限期禁令却让农民们想到了后面的事情:事实上根本不能将羊卖掉。而且,考虑到如若不花费巨大成本购入干草,羊也将无草可吃,这才是最大的灾难。
凯里:人们在被污染了的羊的羊毛上打上橙色标记。农民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要么几乎毫无所得地卖掉被污染的羊,要么相信科学家持续做出的预测:问题即将消失。
温:即便在实施无限期禁令时,他们依然坚持最初的信念,污染将会减轻,只不过持续时间会长一点。因此,这是教条不断被重复提出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们依然陷于其既存的信念之中:污染将会减轻。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相信。因此,他们继续对农民说,没问题的,持续时间可能会长点;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标出你被污染的羊。如果你想卖羊,完全可以。但这显然无视这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毫无所得地卖掉它们,他们在经济上将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所以,农民们在坚持着——当时我们正进入1986年8/9月——一忍再忍,希望如科学家们告诉他们的,污染将降到干预水平之下。然后他们就能把羊作为没有被污染和未被标上橙色标记的羊而出售。所以,许多农民一直在坚持着,后来他们感到可能完全被科学家们欺骗了,因为污染水平并没有降低。于是他们开始认为——在我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我就此引用了对农民们的采访——科学家与政府合谋试图将他们赶出农业,因为政府倾向于在当地发展旅游业。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官僚主义的、经济性的灾难,事实上也同样是科学上的灾难。
凯里:政府想把农民赶出农业的推测仅仅是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提出的一种解释。另外一种流行观点是,人们将切尔诺贝利放射云归咎为实际上是1957年温士盖大火所带来的污染,这也表明人们并未预期到污染的长期性。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并无多少恶意,但这同样引起了布赖恩·温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家们的兴趣。真相是,科学家们自以为了解牧羊地区土壤中放射性铯的辐射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
温:最终结果表明,科学家们持续犯错的原因是,他们一直采用一种用来刻画碱性黏质土壤中放射性铯的辐射状况的模型,这些土壤属于低地土壤。这并不是人们在湖区岩群山丘上所获得的那种酸性泥炭有机土壤。在酸性泥炭有机土壤中,植物上的放射性铯再被雨水冲刷进入土壤之后,它们具有化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活性。因此,它确实进入了土壤,但仍然可被植物根系所吸收。
凯里:在碱性土壤中,铯不会进行化学结合。
温:确实如此。在碱性土壤中,如铯一类的原子可以被硅酸铝吸收到硅酸盐中,接着就被固化了,不再可能被带进植被而再次污染羊群。所以,这就是科学家们做出的设想,但他们并没有反思过这一设想或扪心自问这一设想在湖区岩群山丘地带是否有效。他们就是如此犯错的。这就是科学家们作出错误预测进而给出错误保证的依据。
凯里:布赖恩·温最终追踪到了给出坎布里亚禁令的科学家们所依赖的信息源。事实表明,位于牛津郡哈维尔的英国原子能研究基地大约在20年前进行了此项研究。该研究基地的物理学家检测了各种土壤类型中放射性铯的辐射状况,其中也包括坎布里亚岩群山丘地带的土壤。但他们只对放射性物质的分布和渗入深度感兴趣。布赖恩·温发现,他们丝毫没有关注对坎布里亚山区而言的关键问题。
温:他们没有考察化学和生物学活性以及植被的再污染问题。他们的报告甚至并未谈及植被。他们关心的是暴露于放射尘中的人。这就是他们的风险模型,它决定了要考察什么,决定了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决定了可以忽略什么。他们注意到,降水发生后,放射性物质会渗入土壤。不过,在不同类型的土壤中,放射性物质必须渗入得足够深,才能保证生活在被污染土地表层的普通人不会因辐射而损伤性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育能力,因此,他们的问题是,放射性物质渗入足够深要耗费多长时间。这就是他们所使用的风险模型。这是十分清楚的。我想,没错,这一可行的暴露模型,是从大气检验方法中得来的。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考察一下食物链模型,也没有考虑过食物污染这一潜在问题。所以,他们错失了抓住切尔诺贝利放射尘和羊污染问题诀窍的机会。
凯里:从羊农的立场来看,他们必须信任、应该遵从的那些科学家,竟然将不适合当地情况的研究作为依据,这简直糟透了。但是,布赖恩·温发现相关研究实际上确实存在过,只不过被全然忽视了;布赖恩的这一发现让故事变得更加有趣。20世纪60年代,就职于哈维尔的科学家正在检测用以放射性土壤的纯物理模型,与此同时,农业研究委员会(ARC)的研究人员已经调查了坎布里亚的争议性问题。被污染土壤中的放射性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活性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温:ARC的研究人员并没有使用与哈维尔的科学家们相同的实验方案,他们的方案实际上是在各种农业场点的自然环境中、在检测了各种不同的土壤和植被之后做出的。其报告明确指出,放射性铯在酸性泥炭有机土壤中的活性要比在碱性黏质土壤中高得多。所以,有些科学家事实上明确指出了放射性铯会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我感到困惑不解。在同一个国家中,两所有胜任能力且装备精良的科学机构,处理同一个问题,即放射性物质及其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怎么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我的答案是:在哈维尔原子能研究基地的物理学们都来自于核工程和核物理学领域——也许少数人来自放射生物学领域,但却拥有物理学的背景。而农业研究委员会的农业科学家却不一样,他们是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因此,两个机构使用着不同的实验习惯,拥有不同的理论资源,对所发生之事采取了不同的模型,并为截然不同的利益而工作。农业研究委员会的兴趣点在农业——植被、土壤、天气类型及其对放射性物质的环境分布的影响。我的意思是,对这一科学故事本身的社会学考察是非常有趣的。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科学文化,相互并无交流,更不用说彼此碰面了。也可以说,他们根据1986年所了解的情况,生产着不同的资料和不同的观点,从而针对切尔诺贝利放射尘的可能后果向政府和农民提出建议。
凯里:与农业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的研究相比,原子能研究基地的科学家们会对全然不同的问题产生兴趣,布赖恩·温为此提供了解释:不同的范式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纲领。但是,为什么1986年坎布里亚的科学家们会进行错误的研究呢?布赖恩·温也对此进行了调查,并由此衍生出这一科学侦探故事中最为有趣的曲折情节。他发现,农业研究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被吸收到了联合国的一项更为庞大的研究中:放射尘对人类的影响。一旦被整合到其他的研究之中,它就完全不在负责坎布里亚禁令的科学家的视野之内了。
温:先前的工作只是简单地消失了。它不再是可用的知识,因此也就不为人知了。于是,并不存在一个持续的研究过程,存在的仅仅是一个持续忽视的过程。并没有人有意这么做,没有要故意隐瞒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将之整理成文的理由之一是它具有巨大的政策意义。它教导我们,或应该教导我们,对我们自认为所知之事要略加谦逊。此类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和历史的一个结果。实践仍在继续,但我们事实上却忘记了我们曾经所知之事。因此,例如,我们自认为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后果又了解多少呢?或许我们对之知之甚少;或许,在能够做出预言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像我们自认为的那样控制风险——我意指智识上的风险;或许,意识到这些会使我们以一种更加谦逊的态度对待此类事件。这就是此类历史反思给我们带来的实际政策意义之一。
凯里:坎布里亚受到了切尔诺贝利放射尘的持续影响,或许可能是爆炸所在地之外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5年后的1991年,据《新科学家》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大约有600个农场的500万只羊仍处于某种管制之下。直至今日,某些农场仍受影响。当然,这不能全部怪罪于那些检测肉类污染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这些科学家们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不知道的所有情况,某些最严重的后果本来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例如,本来可以把羊群从山丘赶至山谷,用那些未污染的干草喂养,以便度过这一最糟糕的时期。但它们却被留在了被污染的牧场上,因为科学家们教条式地坚持了一个过去曾经有效却错误的模型。对布赖恩·温来说,整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永久教训是——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或应该通晓一切,但了解你所不知之事总是有益的。
布赖恩·温目前是基因学(Genomics)社会和经济方面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首席研究员。如其名称所示,这一研究中心的目的是,考察社会和经济利益影响基因学研究议程的各种方式,并确保公众在这一领域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刚才他所谈及的诸多相关问题已经进入了这一新的科学前沿——如其所言,特别是与知识相伴的无知向未知领域扩展的各种方式。近些年来,基因技术的现实和商业应用蓬勃发展——例如,北美种植了大量的转基因作物,而且种植范围还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尽管人们曾经认为基因的作用机制是非常简单明确的,但基因学的基础研究却表明这一问题越来越复杂。在布赖恩·温看来,现在是公布2000年首份所谓人类基因组草图的关键时刻了。
温:自从沃森和克里克发现双螺旋结构以来,基因学的最根本教条一直是,每一个基因密码对应于一种蛋白质,一种蛋白质产生一种生物性状——不管它能够抵抗还是容易感染某种疾病,不易还是容易谢顶,或者其他什么疾病。不管这些性状无关紧要还是非常重要、不容小觑,最根本的教条都是:一个基因,一种蛋白质,一种性状。大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基因发挥什么作用——某种基因产生某种蛋白质,进而产生某种性状——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基因而做任何事情,以真正改善人类的方方面面——改善我们的健康,增加牛的产奶量,如此等等。以这一核心教条为基础,人们预期在基因组中约有15万个不同的人类基因。然而,事实上发现的人类基因大概有2万到2.5万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实际上还在逐渐下降,所以,现在不是大约2.5万个,而是下降到2万个。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只有如此少量的人类基因,那么,这一核心教条就无法获得支持了。人们按照基因决定论这一线性模型,应该需要解释大量不同的生物性状,但现在却没有足够的基因来创造这些性状了。
凯里:按照DNA模型,基因可以解释一切,人们为此欢呼雀跃;上述发现却表明基因数量不到最初预计的五分之一,这实际上只是近来对人们的这种乐观态度的打击之一。后续的基因研究也已持续不断地增加这一简单的基因功能模型的复杂性和[人体内的环境]情境化(context)特征。然而,与此同时,基因组的商业应用却在迅速扩展,生物技术也得到蓬勃发展。布赖恩·温现在所试图研究的就是这一矛盾现实;在过去,他的兴趣点特别在于基因组是如何被展现给公众的。
温:就我个人来说,贯穿我职业生涯始终的一个主题是: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并被应用于公共领域的。而现在,基因组、生物科学和一般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已经越来越进入公众的视线。商业利益也牵涉其中,而各个国家又都试图维持其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现在,地球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想成为一个有知识竞争力的社会,而生物科学则被视为那只能下金蛋的大金鹅。我们所要做的必须是以正确的方式施加投入,这也就意味着要对社会研究进行投入,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社会能够真正热情地接受那些从生物技术中产生的所有预期创新。这是人们看待此类事情的共同方式,不仅科学家而且政策制定者都如此。并且,人们时常也会发现,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社会研究议程的制定,也要以能否向被动的公众传递科学所带来的任何创新为依据,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例如,我可以向你援引欧盟的报告,它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这是在一次餐会上,英国的政府部长们亲口对我说的。这是你们的工作,是你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应该传递的,要确保公众接受科学所提供给的东西。按其定义,科学是一种公共利益,不管它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是的,时常可能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错误,但最终结果是有益的,在社会层面上是有益的,你们应该确保它得到社会的赞赏。我想说的是,抱歉,我有几个问题:今天的科学所制造出来的科学知识,是各种偶然性的社会和历史因素的一个函数,而不是仅仅说,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某种非社会的、完全自然的源泉,而且这一源泉可以使我们享受到无休止的泡沫式好处。它并不是这样。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议程并不只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影响有关,它也关注知识的生产过程。
凯里:知识如何生产的问题,将我们带回到了本节目的起点:布赖恩·温指出,科学的目的总是由社会情境所决定。知识潜在地是无限的;但在某一给定的时刻,我们所能涉足的知识却相当有限。因此,在某一给定的情境中,视什么为知识总是成问题的,而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谁可以决定视什么为知识。对布赖恩·温来说,这些问题通常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判定标准以决定什么是有益的,科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公民更能胜任地提出这一标准。现在布赖恩·温从基因组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例子。当下的基因学研究已经用基因与复杂细胞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这幅新图景,取代了全能基因的形象。介入这一复杂环境,不可避免地要求判定什么需要关注,而什么又可以忽略。他说,从他看到的科学文献来看,这是确定无疑的。
温:当你考察人们描述科学的方式以及那些试图澄清此种复杂性的科学策略的使用方式时,你会发现,这需要你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进行选择。你可能想尝试并将你所感兴趣的内容模型化,而为了达成这一模型,你必须减少正在处理的以及在模型中起作用的参数的数量。所以,你需要降低复杂性。我读过的一些科学论文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在那些参数中进行选择,以便帮助我们找到可能的治疗干预路径。你会说,很好,没有问题,这对社会确实有益,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有计划地忽视了大量其他的参数以及在复杂的细胞生物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大量其他的相互作用。事情可能变成这样:当我们出于对分子复杂性的这种治疗性关注而开发出新药品、接着出于帮助他人的初衷而将这些药物分发给他们时,一些无法预期的、令人讨厌的副作用可能会从那些被忽视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谁为此负责?我们对产生副作用的那些相互作用并不了解。那么,我们本该了解吗?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如何提出问题的?又是什么使得我们只关注某些特定的参数而忽视其他参数呢?所以,就像创造知识一样,也存在一个创造无知的问题。我们创造出一些限制,使得我们只究其一。因此,问题总是,我们寻求这种知识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了介入而追求知识,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知而如此做的,我们是以技术的方式在做。这就是为什么我所在的研究领域将这整个范围称为技科学而不仅仅是科学的原因。它不再仅仅是清白无辜的知识,我们更需要作为社会的技科学担负起责任。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荣江译,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鹏博士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N0
A
1007-8444(2015)04-0442-08
2015-04-26
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
布赖恩·温(Brian Wynne),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基因学经济和社会方面研究中心副主任,《合理性与惯例》(RationalityandRitual)一书的作者,《误解科学》(MisunderstandingScience)一书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