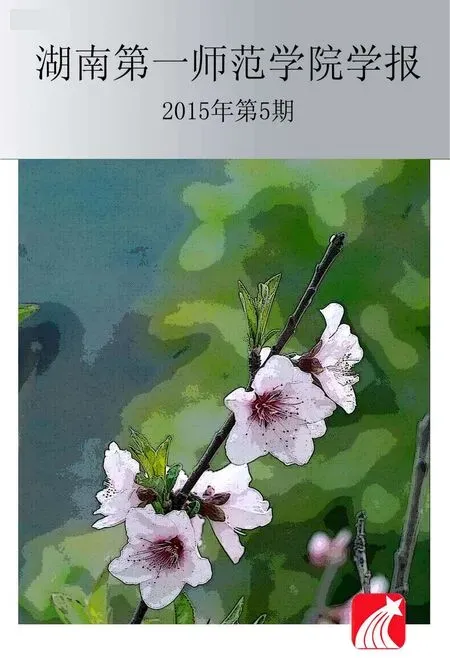论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叛逆与发展
戴日新 ,李 奕
(1.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素质教育部,湖南 岳阳 414000;
3.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外语部,湖南 长沙 410004)
女性主义始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法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原本是主张妇女解放、平等与自由的运动,世界解放运动史表明,女权主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和社会行为,一个社会单独考虑女权或考虑性别易于顾此失彼,只有将女权与女性结合起来,从女性引向女权,再从女权引向女性,才能拓展人们认知视野。女权涉及性别差异和两性权力,从性别方向切入,顺势研究两性权力深层次内涵,从而更深地揭示男女平等形式下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女性主张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倾向、女性话语男性化趋势、以及女性话语自主性增强,这既是对传统翻译译论的背叛,也是对传统译论的发展。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60年代,由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猛烈地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社会各个层面,也间接催生了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跨文化交际传统媒介——翻译及翻译理论。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索绪尔在19世纪曾十分重视外部因素即广义的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语言反映社会现象、社会观念并促进社会的发展,除非人们能掌握储存在每个人脑里所有的词语和语法[1],但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语言只有在社会性集体运用中才能完全存在[2]。所以,语言的存在规律就是只能凭借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而存在。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语言与世界存在着镜象效应,彼此反映对方,如果没有两者中的任一方,也就缺失了另一方,语言与社会现实或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因此,闭门造车的语言,不能反映社会或世界的现实;反映社会或世界的语言,如果不能积极地,能动地把握社会现实和世界的本质,当然只能是文字游戏[3]。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明确论证了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具有对存在能动的反作用。语言作为表达思维意识的物质外壳,能更深地影响社会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语言学家推崇备至的“萨皮尔一沃尔附假说”同样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语言还能够反过来作用于人思维与精神的构建”[4]。这样,许多语言表达的存在以及语言本身形成机制的衍生和利用,会积累式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女性首当其冲,因为女性有着对语言的敏感和应当的天然。在我们潜意识里固化、石化、前景化的所有由语言所指和能指的所有观念,会以约定俗成的语词、语音、语句或修辞方式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处事观念、态度、行为、以及方式,当然也包括翻译行为和结果,女性主义翻译行为和结果。
多年来,人们司空见惯地常常将性别隐喻中,因为归化或异化翻译手段遇到的文本系翻译不确定性归纳为“不忠的美人”。结果,翻译活动喻体,成为与女性社会地位等同的比喻,女性社会地位受到的歧视不知不觉迁移进入语言,语言的这种属性亦至于此。原作文本具有的唯一性使原文文本具有权威性,并且形成与译文文本的主体性和附属性关系。传统文化中以父权、男权、子权占中心制统治地位的观念,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道德会下意识地直接移植进翻译活动,使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语言活动也被纳入相同思想意识形态范畴,视为依附的、次生的成分,进而被碎片化和女性化。女性的性别歧视与翻译潜意识中的处理在共同的历史纵向和横向节点上有了同一性,从而开辟了结合两者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5]。当女性主义成为社会主导思潮之后,必然在女性话语或语言里,也就是在同语交际或异语跨文化交际中表现出来。这样,研究人员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对翻译行为和结果影响的作用力,指明严重的性别歧视存在于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6],并具体地表现在语言文字或词汇上,从而引起人们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传统译论是否还可以为继。
二、女性主义:传统译论的叛逆与发展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解构性或批判性理解。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起来则形成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视角和途径。女性主义翻译观意识到社会女权的发展也为自身从事社会跨文化交际活动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从隐性或无形、从后台或辅助,变为显性或有形、前台或主体。女性主义翻译观声索的主体地位日益明显,女性主义主体性倾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否定,然后再加以建设性阐释,从而丰富并发展了独特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一)叛逆传统译论,发展标准新内涵
自从人类产生翻译行为那一天起,也许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标准设定为“忠实”。传统翻译理论关于翻译标准的核心只能首先是“信”、“忠实”或“精确”,认为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以原作作者写作思想意识和写作主旨为核心,重视译者对原作和作者的服从,不得越雷池半步,将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固化为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并且在翻译行为和意识形态里,用语言来表述和维护这种关系。显然,外表上看,这种“忠实”似乎是翻译的一种必然,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古今中外共性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表现为男女性别的差异导致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这些意识形态同样充斥在作品,即原作的字里行间,如果以“忠实”为翻译理论的核心标准,完全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相适应。此时的传统译论“忠实”只能为逝去的性别歧视或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做垂死的挣扎。正是基于这个观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坚决实现对传统译论的“忠实”观的叛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者认为,语言中既然充满了性别歧视,反映着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与文化,并且翻译的“忠实”理论标准正试图将这种文化“弘扬”下去,这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背道而驰。更何况,所谓翻译的“忠实”标准,与其说通常是意味着全面剥夺女性的话语权[7],倒不如说是将不公平、不平等的被动话语权、话语思维方式和话语文化强加给女性读者。因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在翻译中要求回归性别的公平和正义,要在原文文本向译文文本转换中实现女性翻译活动的主体性,从自在变成自立,再变成自为,在实践中大胆履行自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宗旨创新与变革、颠覆与叛逆[8]。从女性社会政治视角、以女性的平等权力方法进行翻译操纵,是社会层面上广义的“忠实”,远远大于翻译技术层面上的“忠实”。广义的“忠实”是建立于正在、已经或将要变化的女性社会地位和平等政治权利之上。
简言之,从这一点分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确是当代能够起到促进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历史作用力,也客观上揭示了翻译新理论标准形成的规律,即翻译标准应与社会发展同步,并反映社会文化形态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新变化,显然,这对传统译论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二)叛逆传统译论,前景化译者主体性
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译论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对立统一模式决裂,同时,也摒弃了译者忠实于原作的主仆从属模式,创新提出原作与译文与时俱进的翻译标准,使译文对新时代女权运动的成绩负责、对女性主义运动成果负责、对性别公平权力的实现负责,实际上是对整个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负责。
要实现如此多的责任,必须保证原作的翻译需要,以女性主义翻译时空观来表现社会时空的进步。以语言文化来固化这种进步,共享时代的共生共荣。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必定要延伸原作的生命周期,拓展原作的生命时空,使原作以另一种或几种形式在另一个社会语言文化时间与空间里发挥原作应有的影响。这种作用与女性翻译理论倡导者主张的女性主义译作主体性相关,尽可能从原作剔除存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是女性主义主体性翻译行为的目的和过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的全新的“性别译者”术语,但该概念也只是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引起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学术意见,可见,主张译者的性别主体性是有意义的。同时,译者性别主体性理论丰富并发展了对原文文本内涵的理解与发掘。以前只有一个“忠实”的层面,现在可以有一个“创新”的层面。可以输入与时俱进的社会认知和进步,这无疑增加了社会和谐性和认可度。译者主体性或者说女性翻译行为主体性,以否定“忠实”译论理论为斗争的形式,支持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与内涵的实现,以不容否认的方式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的创造性给予了肯定。许久以来,传统翻译理论界以“忠实”和“等值”为基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剥夺了译者的社会责任心和创造的原动力,翻译行为的阶段性成果只能是阶段性的,译文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庸。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仅仅是派生的、附属性、做嫁衣的、或非创造性的。
现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译者的主体性与原作的客观性并置,共同推向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这对于女性主义译者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强化女性主义译者性别角色的同时,也重新界定了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丰富了原作与译作关系内涵,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及主体性作用,对于消除性别歧视、主张性别的社会政治平等、发展先进翻译理论有现实意义。
(三)叛逆传统译论,消弥译语性别歧视
就翻译的策略和技巧等微观层面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活动,希望从中获取相关的原则或社会学理论依据,借以彻底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首先从经典作品的翻译着手,强调使用女性主义语言及两性兼容的语言的策略和技巧,展开了翻译理论创新的篇章。在对《圣经》、《论语》、《红楼梦》等作品的翻译推介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关于用女性主义语言和两性兼容的语言的阐释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争论,其意义是深远的。女性主义语言或两性兼容的语言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是对传统译论的背反,也是传统译论内涵的拓展与外延的丰富;同时还创新了人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这同样是对传统译论的发展。世界上事物并非绝对的对立统一,相反,有时会共轭相处,相得益彰。女性主义翻译者宣称,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使用相应的、既成的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表现女性在文本中的主体性地位,让译作的多声中含有女性的声音,让多声中的女性声音从隐性转化为语言中的“可视”、“可听”和“可信”。在这一翻译理论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以及运用一些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超越男权语言的成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也让一些新的表达丰富了今天的生活,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女汉子”、“女爷们”等,不但是女性话语男性化的表现,也是女性主义翻译观性别抗争的阶段性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只是建立在相应的词汇表达、结构、翻译策略与技巧之上,是远远不够的。
三、叛逆与发展传统译论:策略与技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总是要先行的。有先进的理论才会有先进的行动,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以创新女性主义翻译观为担当,以开创女性翻译观的全新历史为己任,为自己设定了翻译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任务,即不但从理论上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而且在具体的理论实践表现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和技巧也必须要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这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具体表现:增补、前言和脚注和操纵或劫持[1]。
(一)增补的策略
人们对增补的翻译策略并不陌生。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视线内的增补策略,是旨在通过增补策略,消除两种语言差异的性别歧视,而实现译文文本平衡或顺应的创造性的翻译行为,这与传统译论理论工作者说的补偿有点相似,但立意完全不同。增补是指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或转换,如“fe-Male”或“huMan”中的大写字母“M”,喻指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意图,是直截了当地表现对性别歧视的挟抨击,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女性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有意识的警觉与干预。
(二)前注与脚注的策略
加写前言和脚注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实践中的重要策略与技巧。
前注与脚注是翻译过程文本设计的重要结构要素,也可以成为突显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时空表现形式和场所,突出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与传统译论被动性和从属性之间存在的广泛差异性。女性译者翻译主体性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的策略和技巧策略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用方法,可以更加广阔的领域解释原文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创作意图、创作效果,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可以使读者更好地参与现实社会、进入译者心理世界,与作者、作者心声、人物、人物心声、读者和读者心声,实现多声相互交汇,从而突出译者译作的发力点和指向,让读者们关注译者的身份。
女性译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呼声、平等权力呼吁,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阐明了女性译者为纯理论的或具有政治幻觉的想象而巧妙利用语言文本性别资源的意义和目的。
(三)诗学操纵理论的谋略
操纵的谋略又称之为劫持或把控策略。操纵策略是诗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翻译活动里,指女性译者依据自身观点、根据自身观察视角、基于自身兴趣爱好,对原本非女性主义认知观点做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观念的操纵,通常表现为以下方面的操纵。
首先,对原作风格的操纵。原作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原文文本过程中从原文文本中发掘出的作者创作的个人风格,即作者的创作个性;而原作风格的改变取决于译者自身的风格。译者风格具体表现为译者对所选作品题材风格、口味、或文体的改换或操纵。具体操纵的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工作者倡导要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运用的诸多技巧等。原作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具体结构要素由作者和译者智商、情商和趣商组成,也就是传统的世界观、创作天赋和个人喜好,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石化,成为固定模式[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下的译者乐于探索,驾轻就熟,为女性的平等语言地位奋斗,常常有意识地收集其他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当然也不会放弃男性作家的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译成译者所在的母语,进入译者母语文化体系,以创作新词、新语、新表现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或文化的叙述程式,扩大意义表现,推出自身主张,亦即借题发挥,因势导利[10]。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在众多的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词汇成了社会政治主张的砖块,也成了女性主义者的武器,成了主张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手段,通过对词语折衷化、变性化、中性化、性别色彩消解、无性化或直接女性化来创作文章,女性主义译者也同样以这些手段或另类手段操纵,使翻译作品具有女性主义的特质、特色、特点,以此声称自己的女性权利和女性社会地位,借以巩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其次,女性主义翻译者在实践上主张译者的操给性,要求对译文进行女性主义为指向的再创造。主张女性主义译者对翻译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修饰、涂抹、改写或迁移,重建女性主义专用词汇,在语言运用上突显女性主义译者风格和性别的政治主张。当然,不满足中性化或无性化词语使用的女性主义译者,更乐意探索一些极有意义的阴性专用词汇,如早先的“chairwoman”、“postwoman”以及今天极有时代气息意义的常用词“conductress”、“presidentress”和“translatress”,显然,这是一条必然之路,会越来越趋势明显[11]。女性主义话语表现的操纵可以有细微的调节,如:No air-conditioner,it is fucking cold.
(1)没有空调的车厢真他妈的冷。
(2)没有空调的车厢真他妈妈的冷。
(3)没有空调的车厢真他娘的冷。
(4)没有空调的车厢真他母亲的冷。
(5)没有空调的车厢真冷。
当然,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众说纷纭,观点有时会有极左、偏执、情绪化的现象出现,如果不暇思索地从根本上否认以结构主义或语法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就必然会陷入误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主客作为客观、融合作为对立,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引向歧途[12]。因为过于强调翻译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甚至歪曲翻译活动的本质[13],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结语
女性主义自进入翻译理论以来,就在不断增强自身理论建设中否定不合时宜者,结果也就将不合时宜者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内容,开拓了新的发展视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成功地解构了原作思想意识形态,动摇了原作渗透的男性霸权主义,为人们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许多原理如等值、等价、对等,或许多术语如文化差异、译者主体性、以及语言本质等问题找到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发展的发力点,这对于翻译理论体系建设是有意义的。
[1]Flotow,L.Translation&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of fem inism[M].Manchester:S t.Jerome Publishing.1997.
[2]L 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 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 iterary Fame[M].L ondon&New Y ork:Routledge,1992.
[3]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47.
[4]王华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观[J].宿州学院学报,2011(4):39.
[5]徐翠波.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探[J].长江大学学报,2011(4):60.
[6]张曼曼.女性主义翻译观[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7):42.
[7]马丽娜.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之浅探[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2):127.
[8]张彩霞.小议女性视角下的翻译忠实观[J].出国与就业2011(12):35.
[9]周颖.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9):65.
[10]邢慧娟.漫谈女性主义与翻译[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32.
[11]张静.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风格影响[J].四川教育学报,2007(9):73.
[12]华灵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谈[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2(4):29.
[13]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4.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