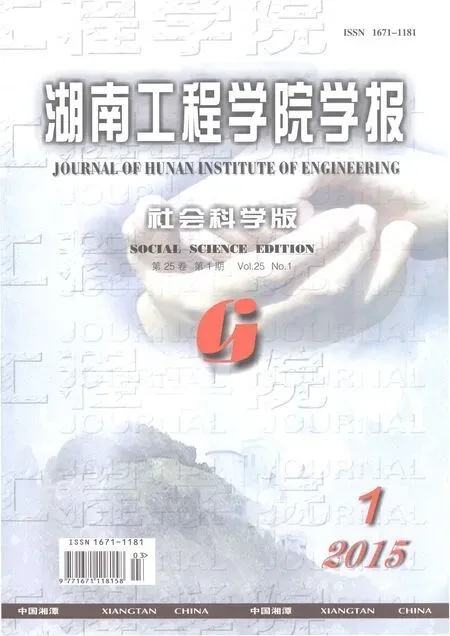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疫灾防治措施的特点
杨鹏程,冯小对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疫灾防治措施的特点
杨鹏程,冯小对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政局混乱,战争频繁,经济凋敝,瘟疫肆虐,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带来的危害。这些防治措施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防疫理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防治措施由愚昩向科学转变;现代化交通、信息技术应用于防疫;西医西药在防疫中作用凸显;防治过程中官方主导,社会化趋势加强。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疫灾防治措施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政局混乱,战争频繁,经济凋敝,瘟疫肆虐,民众水生火热,苦不堪言,政府和社会各界尽其所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带来的危害,防疫思想也逐渐发生改变。与明、清相比,呈现出湖南公共卫生尤其是防疫事业由传统方式向近代化嬗变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 防疫理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防治措施由愚昩向科学转变
明、清时期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控制疫病方面,表现消极被动。尽管仿照宋、元旧制,在各地设立医官、惠民药局,但由于疫病并不像水旱灾荒那样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官府相对较少关心,因此设立医官和惠民药局的事,不被重视,有的药局渐渐荒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1]即便地方官员有关心民众疾苦之心,经费、药品、医疗人员的匮乏也成为制约防疫治病的因素。
民众在应对瘟疫中往往只能听天由命,由于贫穷和医学知识的匮乏,多把瘟疫视为疫鬼作祟所致,较多采用消极行为来避免瘟疫。《大公报》批评时人不懂公共卫生、把瘟疫与鬼神迷信联系在一起的愚昩行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自然食吃习惯了的,只知各人打扫门前雪,凡关于公共应举办的事通通丢在脑后,从没有人过问。事前既不知共筹预防之策,事后又不知合谋善后之方,一遇有变,上上下下,都讲些神怪的话,敷衍塞责。”[2]
曾有人在桃源县住了两个月,发现“那地方的人民遇有疾病,吃药的狠少,请巫酬傩,赎魂买命的事,一日总有几处。敲锣、击鼓、吹牛角的声音入耳不断”。“每到点灯时候,就听得金鼓之声,聒震达旦。问那地方土人,说是巫师行法,开洞请神,闭洞送鬼。有时前往观看,见巫师头包红巾,手执大刀,在堂中乱舞,那旁人说是替病者斫鬼。有多少的亲戚朋友作贺,又将那覆在底下的土碗翻开,便是抢魂,那一种鬼鬼祟祟的行为,可疑复可笑。”[3]
1922年衡阳“虎疫(指霍乱——引者注)流行甚烈,每日平均约死二至三人。一般人民不知防疫方法,只深于迷信,故迎天符大帝及府县两城隍诸神出巡,冀迓神庥,驱除瘟鬼。自阴〈历〉六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二日止,禁革五荤,虔诚祷祝,每街团各装演故事龙灯……此外各家建设章醮,求神保安宁者不知凡几,然病疫未见减少。昨日闻有染疫者四五人,不过数个钟头即行毕命云。”[4]
是年“长沙明都、大贤等镇团总,因为现在瘟疫流行,特举行迎神游街大会,将什么龙王、金容大帝派八人由庙内抬出,游行各乡镇,驱除瘟疫。与会的人大约有六七万,护街的龙有七八十条,旁边看热闹的人更不计数。”[5]
1924年,“赵省长(恒惕)以天降淫雨,兼旬不休,大水为灾,伤及禾稼。除令各县知事虔诚祷晴外,特于昨日午后七时,乘株萍专车,亲赴衡山南岳圣殿,上香祈祷”。[6]上行下效, 7月12日,长沙天晴水退,长沙知事曹献廷,不是迅速组织救灾,而是“必以之归功于迎接入城之陶、李两真人”,“令导神游街,谓可收瘟摄毒。”《申报》报导了这一荒诞场面,略谓城内外250余团,于7月14日(六月十三日)执持乐鼓仪仗,扮作鬼怪,歌唱小调,游神者3万余人,耗费计数万元。而省署居然派出军警到场,以军乐队为前导,“陶、李两真人各乘八人绿呢肩舆,每乘以武装军警各数名护卫”。对于这类怪事,该报评论说:“吾湘文化……最近始稍有进步,经此一〈举〉,足以抵销而有余”。[7]
史称湘人“信鬼好祀,病不延医,听之神,则楚之旧俗,又非特一邑也。”[8]缺医少药,缺钱少粮,面对瘟神为虐,无助而又无奈的民众只能乞求神灵以正压邪,拯救芸芸众生。
在许多地方,当局甚至采用了非常愚眜可笑的迷信方法防治瘟疫,1920年辰溪就发生过提前过年防治瘟疫的闹剧:
辰溪时疫流行,发源于知事公署与狱署。囚犯一日死四人,渐传及四城。北门外隅,一日死十七八人,城内外死亡相继,人人自危,于是迎神建醮,舞灯唱戏,无所不至,而瘟疫终不可减。张知事自谓福薄德鲜,不能荫护人民生命,拟即辞职,以让贤能。而味同鸡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遂妙想天开,仿溆浦避瘟过秋年之故事,爰定于阳[阴]历八月二十一日过年。饬各保正四门鸣锣,大声疾呼过年休息三日,如有不遵,罚洋六元。人民为生命计,为自卫计,导演热心,家家贴对联、糊门神、收香钱、舞龙灯。锣鼓之声与鞭炮之声相应答,可谓极一时之盛。其对联有“过年恰在中秋后,去病何须半夏方”,又有“才过中秋刚五日,又是民国第十年”。[9]
用提前过年治瘟疫的方法并不是辰溪和溆浦的发明,1918年河北通州就用过“提前过年治瘟”的办法而被內务部斥为“变乱国章、过深迷信”的“谬举”。[10]这种办法无异于传统的“冲喜”,是于事无补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乐此不疲,实属愚昧无知。但也有人认为以过年为由大放鞭炮,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有杀菌消毒的作用。这种办法甚至早在淸朝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就在施行了:
广州城厢内外,疫症流行,居民见死亡之多,均觉不寒而栗。多方祷禳,终属无灵。于是好事者创为度岁之说,谓另易岁首,方可祓除不祥。遂以四月初一日为元旦,而于三月廿三四日举行祀灶之典。一唱百和,举国皆然,纸店灶疏为之售罄,从前每张不过一二文者,今则出至十余文而不可得,亦一奇事也。现各家门首均刮洁净,帖换宜春,闾阎气象,忽又一新矣。[11]
但是,随着西医传入,人们对疫病认识加深,政府与民众防治疫病的观念发生了改变,逐渐积极主动正视疫病,由以治疗为主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主、防治并重。及时有效采取适当预防措施,有利于降低死亡率,防止疫情范围扩大。民国前期湖南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关预防瘟疫的办法,如《警察厅严防瘟疫办法》、《警厅防疫办法二则》、《警厅布告防疫办法》等等,强调预防瘟疫的重要性,还要求民众注重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通过大力宣传提高了人们的预防意识和素质。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恶疫蔓延较之兵灾水旱,更为猛烈”,“然设不早为防止,诚恐更趋激烈。今宜由警厅购办大宗防疫药品,逐日洒扫街市,并令居民同时购办以洁净其居宅。其贫民无力,则由公家派卫生警察代为布置。更认真取缔各熟食店及各种食物小贩,毋得以不时不洁之物入市”。[12]
面对瘟疫,只有在正确的指导下,及时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才能立足于全局,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病的传播、蔓延。民国前期湖南省的部分政府官员和社会有识之士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变被动为主动,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

二 现代化交通、信息技术应用于防疫
随着近代航运、铁路和汽车事业的兴办,使得交通便利。朝发夕至,“千里江陵一日还”,为现代化防疫提供了保障。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湖北、湖南两省商绅的请求,成立官督绅办的“两湖善后轮船局”,经营两省内河航运。局务分设汉口、长沙两地,就此开辟了湖南近代内河航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湖南修建筑了萍潭铁路、粤汉铁路湖南段,以便解决湘煤外运的问题,同时也为民众出行提供了方便。1921年湖南长潭公路竣工,“龙骧长途汽车公司”租用长潭军路,购买大小客车10辆,于1922年8月正式开始营业,为湖南经营汽车运输之始。1924年,湘中、湘南、湘西汽车路局分别成立,官督民办,境内公路续有修建,至1929年,湖南共建成公路463公里。[13]交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信息传播,人才、技术交流与沟通。
新型通讯工具和传播媒介产生和应用,加速了疫情信息的传递和反馈,大大加强了宣传功效。古代传递信息个人多靠书信往来鸿雁传书,官府靠驿站飞马递书,速度慢,范围小,费时长,对疫灾这种急需紧急处理的事件十分有碍。电报、电话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可以迅速传递疫情信息,上传下达。1889年岳州邮政局成立,为湖南第一个近代邮政机构,稍后湖南又设长沙、常德两个副邮界,隶属于汉口总局,逐渐形成按运输工具不同分为步班邮路、船舶邮路和火车邮路三位一体的邮政网络。1908年湖南共设有长沙、岳州、城陵、湘潭、醴陵、衡州、常德、辰州、洪江等9处电报机构,1905年长沙开始设电话局。近代邮政的诞生和电报、电话的使用,对于缩减报告疫灾的时间及传递疫灾灾情信息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政府及时掌控疫情并针对性地制定防疫方案。报纸通常是宣传预防疫病信息的有效载体,通过专业人士编辑和发行,传递灾情速度加快,信息集中可靠不仅让民众及时了解疫灾信息,稳定和安抚了民心,还提高了民众卫生防疫的素质。此外,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有利于迅速运送防治疫苖和药品。
防治瘟疫过程中新信息手段的运用,多种防疫措施的采用,使得卫生防疫的视野更为广阔,手段更显灵活,信息和经验交流更为灵通,逐步实现了卫生防疫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跨越。
三 西医西药在防疫作用中的凸显
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医中药,在治疫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应对东三省鼠疫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它的局限性。1910年9月俄国境内发生了鼠疫,通过铁路进入中国满洲里,并迅速蔓延东北各地及关内,造成东三省鼠疫大爆发。疫情蔓延引起了清廷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应对这场鼠疫中医束手无策,中医“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中国当时没有微生物学研究机构,但清政府选派的总医官伍连德恰好是国内仅有的几位受过严格微生物学训练的专业人才之一。他通过染疫尸体解剖、显微镜观察、血样样品分析等现代医学的手段,找到了这次瘟疫的真凶——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传播。因此伍连德立即向朝廷汇报并提出建议,并指挥各项防疫事宜。除成立专门防疫机构和组织外,还采用如交通检疫、隔离、埋葬、焚烧、消毒等一系列西式防疫措施。哈尔滨的疫情得到控制后,伍连德将重点集中在长春、沈阳等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次年三月东北各地鼠疫全被肃清。[14]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鼠疫,被以中国为主的一支小小的防疫队伍在几个月内彻底扑灭,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不仅拯救了千万生灵,而且成效显著。因为是运用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基本按专家的建议采用科学的办法控制疫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不到百日内获得彻底成功,使得晚清社会从上至下对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崇拜。可以说东北三省防疫的成功使中国开始正式承认和接受现代西医,并运用西医西药来防疫治病。1919年秋长沙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中,每日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孔道大同社社员黄国英从上海制购参合中西药料的普济药水,专为救济时疫急症而制,在上黎家坡府学宫随时施放,其效颇佳。”[15]说明西医药品广泛应用于救治疫病患者。随着社会各界逐渐接受西医西药,其在救治预防疫病的过程中作用日益显现。
1919年醴陵瘟疫暴发,“一日之间,死者一二十人不等”。 瘟疫发生于城东门一带,“始觉头痛,或肚涨下泄之症”。 醴陵本地医疗条件不足,“请美国医院设防疫所二处,随时诊治施药。”[16]教会医院在防治瘟疫方面功不可没。
四 防治过程中官方主导,社会化趋势加强
明清时期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关注有限,遇到瘟疫流行,官方控制力量较弱,往往主要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富户以及民间慈善人士进行救疗,这种个体行为作用极为有限。民国前期为新旧交替之际,中国近代医学正处于转型起步阶段,湖南政府官员逐渐扮演重要角色,积极领导和引导其他社会阶层参与卫生防疫事业。警务处设卫生科管理卫生防疫事务,至少说明政府并没有漠视人民生命,尽量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疫灾。以临时防疫处为例,除了湖南军政长官赵恒惕、谭延闿等人直接参与外,省城相关行政机关办事人员均有加入,而且不计薪酬。官方在人力方面的投入一定程度上确保防疫措施实施的力度。但由于期间军阀混战,政局乱象环生,政府卫生职能还不健全,经费和技术短缺,官方起的作用有限。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治瘟疫的趋势越来越强。社会团体展开各种形式的救助活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官方力量的不足。一方面政府只能在少数重要地区设临时防疫医院和隔离所,社会力量则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创办分布更为广泛的临时防疫医院和施诊处,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疫病患者的需要。如1924年省城长沙瘟疫暴发,一日之间,死者一二十人不等,由于临时防疫处下设的防疫医院有限,疫病患者日趋增加,湖南卫生会联合防疫处增开数处施诊处,随时诊治施药,极大方便了民众。[17]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在宣传预防疫灾的广度和深度比官方实际达到的效果明显。1925年大旱期间湖南卫生会开展了演讲20次,听众3万余人;散发传单6种计20万份,图画200张,报纸宣传50万字;并组织防疫处,办理医院、隔离所各一处,检查所5处;征求暑期卫生演讲员1000人,分向各县村演讲,普及50余县,听众10万余人;举行预防秋疫运动,演讲10余次,散发传单5万份。[18]
1913年秋,长沙组织了一个“妇女社会服务联盟”,获得了市卫生科和雅礼医院的支持。该团体定期举行卫生教育讲座、发放卫生知识宣传品,同时还开展大规模的儿童种痘,受到了当地人的称赞。[19]
湖南卫生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博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大公报》(长沙)的社论称:
甚么衙门,甚么机关,不是替小百姓做事的;甚么党,甚么社,不是替小百姓做事的;甚么会所,甚么团体,也不是真心替小百姓做事的。现在在这长沙城中,我认为是替小百姓做事的,是比较的真心替小百姓做事的,有两个会:一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20]
疫灾防治实质上为官方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官民合作运动,既利用政府权威来保障整体措施系统有序的运行,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有效优化社会可利用资源配置,迅速阻断疫灾传播。
从其实际效果来说,民国前期湖南应对疫灾的成绩值得肯定,不仅挽救了广大民众的生命,还使卫生防疫开始走向近代化、制度化,逐渐形成了近现代卫生防疫体制。时人逐渐认识到在中国从事公共卫生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公共卫生建设对防治疫病保障民众健康和发展经济、提高国家地位都具有重大作用。这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了对环境卫生的改良与建设,提倡饮用污染较少的水,加强了对井水、河水等居民饮用水的管理,改良公共厕所等。通过广泛的卫生宣传,人们的卫生观念也得到一定提高,逐渐懂得疫病预防的重要性,也为疫病防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湖南著名卫生专家张维在《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一文中指出:“民族复兴是个经济问题,任何民族的兴旺和衰落,都以经济条件为枢纽,白种人能有今日,产业革命实在是一个主因。可是经济条件是一个复杂错综的条件,中间包含着种种的原素,而健康问题,确为其一。所以跟着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的,就是对公共卫生的重视。那里的公共卫生,虽仍不免带着封建制度遗留的臭味,不能完全超脱慈善事业的范围,而其趋向和端倪很显然是走上社会经济的道路。嗣后产业越发达,公共卫生越蜕化为社会经济之一部,到最近而纯粹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反之,“公共卫生的进步和发达,一定是民族复兴的征象,而欲民族复兴,公共卫生之不可忽视,可想而知。”[21]
民国前期湖南瘟疫肆虐,造成极大危害,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应对瘟疫时所采取的预防救治措施是积极且有成效的。近代湖南卫生防疫行政机构的形成及其初步发展,为疫病防治提供了必要的组织管理和技术支持。同时湖南省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预防传染病规章制度时,注意到湖南的实际情况,既遵从中央政令,又从实际出发,把政令和本省实情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而建立起了一套“分工明确,资源优化配置”的近代卫生防疫机制。其中预防救治措施主要由防疫行政机构、防疫法规、疫情汇报制度、交通管制和隔离、清洁消毒、应急防疫医院、防疫宣传等要素构成,这套防疫机制的基本运作和完善并非一蹴而就,它萌芽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前期,至民国后期才较为完整地建立起来,表明湖南卫生防疫事业在逐渐迈向近代化,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体现。
总之,民国前期湖南卫生防疫事业虽然存在着许多局限与不足,但在当时纷乱的政局、有限的财力和低下的科技卫生条件下,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政府为主导的防治机制,标志着湖南卫生防疫事业近代化的开端,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给整个社会和民众的防疫观念和行为带来了深远影响。
[1]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M].中国书店,2004:92.
[2] 驱蚊的妙法[N].大公报(长沙),1924-07-07.
[3] 桃源祭鬼之风俗[N].大公报(长沙),1919-10-30.
[4] 衡阳特约通讯[N].大公报(长沙),1922-08-22.
[5] 昨日的迎神游街会[N].大公报(长沙),1922-07-11.
[6] 赵省长亲祀南岳虔诚祈晴[N].大公报(长沙),1924-06-29.
[7] 长沙水灾中之怪剧[N].申报,1924-07-22.
[8] 风俗:华容县志·卷一[O].明万历刻本.
[9] 辰州时疫之流行[N].大公报(长沙),1920-10-12.
[10]通民除瘟之新法——提前过年[N].大公报(长沙),1918-11-3.
[11]过年却疫[N].申报,1894-05-09.
[12]防疫[N].大公报(长沙),1918-06-09.
[13]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368-369.
[14] 王 哲.国士无双伍连德[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78-81.
[15]慈善家救济时疫[N].大公报(长沙),1919-08-30.
[16]关于防疫之所闻[N].大公报(长沙),1920-08-15.
[17]湖南防疫会议[N].大公报(长沙),1924-08-15.
[18]大公报十周年纪念刊[N].大公报(长沙),1925.
[19](转引自)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1912-1937)[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132.
[20]真心替小百姓做事的[N].大公报(长沙),1924-02-26.
[21]张 维.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J].中华医学杂志,1993(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pidemic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in Hun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27)
YANG Peng-cheng,FENG Xiao-dui
(Institute of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7)saw the political chaos,frequent wars,economic depression and plague epidemic in Hunan.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had taken some positive steps,to a certain extent,alleviate the epidemic disaster.These prevention measure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active concept of the epidemic disaster prevention,scientific control measures;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prevention;western medicine;official involvement;and the strengthened social tre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7);Hunan;epidemic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2014-09-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S03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1011109Z);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基金项目(09k078);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杨鹏程(1949-),男,湖南华容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灾害史。
K258
A
1671-1181(2015)01-00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