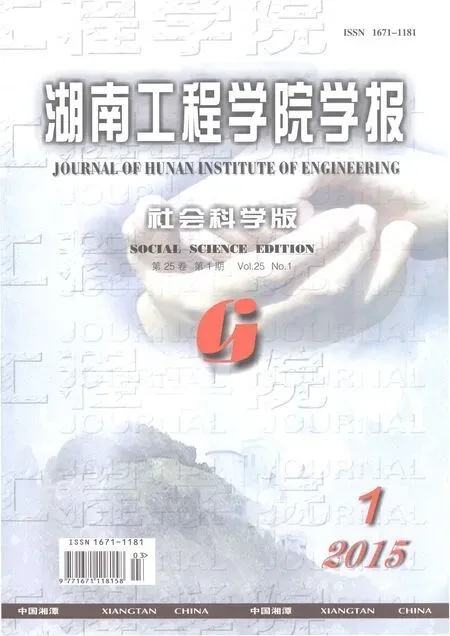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周良发,丁玲玲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安徽 淮南 232007)
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周良发,丁玲玲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安徽 淮南 232007)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并利用“道”来改造世界。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知识分子面临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
余英时;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问题,历来是思想文化界深度关切的热门话题。作为极具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士与中国文化》(初版1987年,再版2003年)堪称知识分子研究的典范之作,谈锋所致,涉及知识分子的源起与流变、品格与特质以及日益边缘化等一系列核心议题。细细品鉴余英时先生的相关论著,文章拟对先生这一研究论域进行初步的学理剖析,为今人审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提供一管之见。
一 知识分子之源起考
古代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与之大体相当的是“士”。而“士”的出现的具体年代,现已不可考,兴起于商周之际则是大多学者的共识。余英时先生没有对“士”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抉隐发微,而是认为“士”的出现与“道”的观念密切相关,故孔子有“士志于道”、“君子谋道”、“君子忧道”之论。虽然“士”和“道”两个术语先于孔子而存在,但其涵义却与孔子时代迥然有异。
(一)春秋以前之“士”
余英时先生认为,商代卜辞“卜人”,便是“士”之一种,商周文献所谓“多士”、“庶士”、“卿士”,大抵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并认为春秋之前的“士”大多在政府担任各种公职,“古代各种低层官吏如邑宰、府吏、下级军官之类大抵都是由士来充任的”。[1]95故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顾炎武《日知录》亦云“谓之士者大抵缘有职人”。周代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教育内容,所以受过“六艺”训练的人也称为“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而出任不同的职事”。[2]1相传孔子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可推知他懂得“数”,而且他本人曾对弟子说:“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御”和“射”是孔子深入研究的两门艺业,这为他以后致力于“礼”和“乐”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孔子之前的“道”尚不具有形上的抽象意义,大体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篇论述颇详。他说:“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明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祝淫。”可见,此时的“天道”是具体而微的,主管着人间的祸福吉凶,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
基于这种认识,余英时先生指出春秋之前的“士”只是“职事”之人,尚不具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究其因缘,余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视角作了周详精湛的学理剖析。西周社会的结构层次自上而下分别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很显然“士”处于贵族阶层之末端。由于贵族可以世袭身份爵位,所以不但垄断了诗、书、礼、乐等各种知识,而且占据了各级政府的主要岗位,致使“士”的地位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其限制之情状,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呈现:在政治上,“士”被束缚在各种具体的“职事”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王官学(诗书礼乐)之内;在身份上,“士”处于贵族阶层之下。在他看来,正是这三重因素致使春秋以前之士难以形成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缺少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与批判,故而不能视为知识分子。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士”对现实社会完全没有批判绝非事实,只是他们的批评大多是职务范围内的“局部的、具体的讥讽”,这显然与春秋时代的士“志于道”相去甚远。
(二)春秋战国之“士”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春秋时期“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各种具体的职事中蜕变出来,成为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论其原因,余英时先生从秩序崩坏与社会流动两个层面进行说明。
先谈秩序崩坏。在西周制度下,“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层级,其下便是平民百姓,即“庶人”。然由于封建秩序的崩坏,遂使“士”的地位骤然下滑,并逐渐与“庶人”合流,并列在同一社会范畴之内。余先生认为这一转变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并从大量存世文献寻找理论依据。例如“士、庶人舍时”,“士、庶人不过其祖”(《国语·楚语下》),“台宴士、庶子”(金文《邾公华钟》),表明时人已将“士”、“庶”称谓并用等量齐观了。
再论社会流动。社会秩序的崩坏促进了社会流动,加剧了不同阶层的升降变迁:一方面“庶人”有机会上升为“士”,另一方面“士”大批下降为“庶人”。无怪乎公元前509年,史墨发出这样的感慨:“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余先生认为,这里的“三后”并非专指虞夏商的王族,而是泛指自古以来一切亡国公族和没落贵族的后代。至战国时代,“士”不再属于贵族阶层,而成为四民之首。“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士”属于大夫士,那么春秋战国之“士”则具有了士大夫的风尚。
对“士”来说,由贵族阶层变成四民之首固然是身份的裂变,但就其发展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忧的是因贵族头衔的滑落而失去了职位的保障,进入了“士无定主”(顾炎武语)的状态;喜的是从固有秩序中解脱出来,思想不受“定位”的限制,在精神上获得了解脱。甚至可以说,这种解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终使“士”可以“思出其位”了,推促了超越精神的泛起,进而向社会辐射他们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而超越精神正是“士”批判社会现实寻绎超越世界(道)的必要前提。无独有偶,“道”的观念也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原始“天道”观出现动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左传》昭公十八年),其次是孔子以来的诸子发展了“人道”观,进而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合一”的道论。
身份的裂变与“天道”观的变化,遂使“士”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3]33虽然传统之“士”与现代知识分子仍有很大差别,但二者均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价值观念的维护以及思想文化的传承。

二 知识分子基本特征
“天道”观的嬗变以及“天人合一”的出现,说明“道”的重心已从“天”转向“人”。这对先秦诸子学尤其是儒家影响甚巨,以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无不彰显人的主体性。由于主体的凸显,“士”对“道”的超越精神的追求秉持“即世间而超越世间”的态度,进而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余英时先生说:“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不但适用于先秦时代的儒家知识人,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后世各派的知识人。”[2]13缘于这种理解,余英时将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概为下述两点。
(一)利用“道”改造世界
“道”的形上意义是指人类的精神理想,世界的普遍法则。所谓利用“道”来改造世界,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士”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观照世间的物事,并援引顾炎武与李颙之论佐证。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李颙亦云:“如明道定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二曲集》卷十六《书牍上》)。此处“救世”、“经世”皆有改变世界之意。在他看来,这种精神特质上起春秋下及清代,始终贯穿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系之中。
不过,士之“救世”与“经世”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有着正反两种方式。其正面方式是出仕为官。“士”之出仕必须以“道”是否彰显为现实依据,因为他们将“以道自任”作为终极意义的关怀。正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虽然“从道”实践起来比较困难,但它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比如,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程颢诸人虽身在官场位居要职,但他们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本色,以天下之重为己任,用“道”来改变现实社会。其反面方式是现实批判。由于超越精神的出现,士可以“道”为准绳来批判社会的是非曲直,护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余先生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批判,即“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若天下无道,那么“议”则是不可避免的。“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说苑》卷十九《脩文》)“辨然否”即“明是非”,且以“道”为判断基准。汉代以降士之社会批判尤烈,甚至达到了“贬天子”的高度,“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阮籍集·大人先生传》)。就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从先秦孔子至清代戴震,无不在“明道”的同时承担社会批判之职责。
(二)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未必高于其他民族国家,但他们历来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稍微翻阅古代典籍,我们便会发现诸如“修身”“修己”之类的名词术语屡见不鲜。“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墨子·贵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老子》第五十四章)。古代之士为何如此讲究“修身”、“修己”?余英时先生从历史深处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可从两个方面作出解释。其一,时代变迁所致。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遂使一部分“士”以重振周朝礼仪制度为毕生志业,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在此时代背景下,先秦诸子大多致力于“礼”的改造与发挥,使“修身”、“修己”之涵义出现嬗变,由原来的身体修饰转向精神上的修养。此处所引孙子、墨子、老子三家之言,所论“敬”、“义”、“德”显然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孔墨之论虽以“君子”为对象,其实质则以“士”为主体。这不是说“士”之外的人就不需要修养,只是诸子所论之修养大体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其二,超越境界相关。时代变迁只是知识分子注重精神修养的主要背景,而超越精神才是他们重视修养的内在根源。也就是说,古代之“士”注意“修身”“修己”与“道”密不可分。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综而观之,“修身”便是“行道”。余英时先生指出,孟子所谓“修身”应当从其“知言养气”之“不动心”与“浩然之气”处求解。在孟子的思维世界中,“浩然之气”必须和“道”、“义”结合起来,使“养气”之人可以直接触及超越境界的“道”。也正因为有了“道”,才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修身”、“修己”离不开“气”与“心”并非孟子一家之言,尚可从荀子那里求得印证。荀子说:“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可见,“治气养心”以得“道”几成先秦诸家共同接受的理论。
余先生指出,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注重精神修养,主要是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正。由于“士”之超越精神既没有(西方的)教会可以依靠,也没有系统的“教条”(即教义)可资凭藉,“正统”和“异端”更是缺乏客观标准,所以“道”的惟一保证便是士人的内在修养,它为仕人改造世界提供思想观念上的支撑。
三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借助科举制度与政治联姻,士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朝辅助君王治理天下,在野领导民众管理基层。然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帝制的终结,士人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与“士”相较,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仍是社会的重心,还是边缘化了?余英时先生认为,清末民初的易代鼎革遂使“士”从社会中心的地位退了下来。“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3]7换而言之,传统士人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是现代知识分子难以望其项背的。
不过,从传统之“士”转向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一蹴而至之事,其间伴随着漫长而痛苦的抉择,其中既有时代灼伤的阵痛又有迷惘彷徨的挣扎,既有自我灵魂的救赎又有凤凰涅槃的新生。加之传统帝制的崩塌没有立即在思想文化上引起太大的改变,更没有触动民众的心理层面。因此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依然保存了浓厚的士人情结,社会也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只是这种尊重局限于社会民众的心理层面,“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它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4]35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学界关注颇多成果甚丰,余先生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进行剖析。
(一)政治层面的式微
政治权力的式微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主要标识,正如余先生所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4]37维新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尚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而辛亥革命期间的章太炎、宋教仁等知识分子却处于政权的外围。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无疑喜欢会党人物,对于章太炎与宋教仁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特别重视。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传统中国改朝换代的共同特征,即“打天下”时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而“治天下”则应将政治主体转移到“士”身上。清末民初政权易帜无疑产生了大量的边缘人,怎样把这些边缘人组织起来,则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他看来,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内部充斥着大量的边缘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边缘人政党集团。从此边缘人占据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却不断从权力中心撤退,直到完全边缘落寞化。
平心而论,国民党初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在本质上也颇具知识分子风范。但由于中山先生的离世,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便越来越疏离知识分子,转而培养和接纳了大量的“党棍子”。所谓“党棍子”略同于今天的“混混”,这无疑表明国民党的基层干部犹如地痞流氓一般。对此问题,余先生以北伐前后的国民党与胡适等知识分子关系的变化为例加以说明。北伐之前国民党与胡适等知识分子颇为友好。据说孙中山本人对胡适相当尊重,还请他从学术观点评价其“知难行易”学说。然北伐以后,胡适发表评论文章《知难、行亦不易》却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批驳。也就是说,夺取政权后的国民党与胡适等人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恰好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当然,国民党上层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王世杰、陈布雷之流,但在中下层“党棍子”的层层包围之中也难免自我异化了。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强势推行“党化教育”,遂使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尚存的一丝好感亦化为乌有。
(二)文化层面的边缘
虽然“知识分子”的界定历来歧义纷呈,但知识文化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的身份标识。没有知识文化的支撑,知识分子显然缺乏身份的合法性。但余英时先生认为,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式微,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也日益边缘化。而文化领域的边缘化,无疑标志着知识分子面临合法性危机。他说:“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4]40同样处于边缘境地,但是知识分子的抉择却迥然相异:政治层面的式微,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毫无抗拒之力;而文化领域的边缘,却与知识分子密不可分,甚至具有推波助澜之功。究其原因,余先生从鲜活的史实中寻找现实依据。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为西方文化所震慑,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避居日本之际,正值日本学界西化高潮之时。此时大多日本学者(如福田渝吉、中村正直)倾慕西方文化,并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恣意裁剪本国文化,甚至认为凡与西学相异者则是日本落后之根源。而且多数日本学者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坚信人类社会的演替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这种社会史观无疑影响了梁启超等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遂使他本人也以西方史学的模式来检视中国历史。稍后兴起的“国粹派”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表面上好像是要发掘并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实质上则是挖掉了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代之以西方的价值”。[4]40国粹派主将邓实甚至认为中国与西方之不同在于前者尚处于“耕稼”时代,而后者已进入“工贾”时代。基于这种情形,余先生说:“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是在这个时期(1905—1911)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的。”[4]41
其次,“五四”新文化期间。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虽以西方价值观念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毕竟还要对古代典籍进行一番省思,并对许多传统思想进行现代诠释。“五四”时代情况则大相径庭,提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反对以中国经典附会西方现代思想,甚至“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4]42其结果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用他们不甚了解的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填补文化上的真空,由此造成“双重的文化边缘化”。应当说明的是,余先生此论并非抨击或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甚短,且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向西方寻找真理”,显然没有深入西方文化的中心,更遑论熟谙西方文化之意涵。鉴于这种观点,余先生沉痛地说:“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4]43东西方文化上的双重缺失,使得知识分子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
余英时先生从政治与文化双重层面深度剖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认为他们无可耐何地边缘化了。不可否认,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总体上处于下行之势,但这种下行趋势只限于社会与政治层面,而在文化领域却表现出更大的张力。诚如许纪霖所言:“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5]3美籍学者张灏亦持此论:“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6]43这充分说明,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的同时,却迎来了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儒学热”与“国学热”的兴起,无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海外传人,余英时先生承续了先师钱穆的学术旨趣,从思想史的视角考察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剖析社会思潮,与时论大多偏重文化层面而漠视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脉络有着显著差别,其论说无疑包含着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然囿于学术视野的局限,余先生之论没有脱离传统儒家的理论窠臼,仍以儒家“士君子”的家国天下观检视知识分子,这显然把知识分子的特质和功能狭义化了。撇开知识分子是否已经边缘化暂且不论,对于当下正遭遇社会治理与文化焦虑的双重困扰的中国来说,的确需要他们提供一种持续奋进的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颇有微词,认为它带有浓郁的革命气息,主张以比较中性的“知识人”取其代之。傅铿在《知识人的黄昏》一文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知识人”具有更强的形象魅力,且与人们常说的“文化人”一词相当接近。[7]79-85至于哪种称谓更加合理,笔者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余、傅二先生的提法确实值得学界进一步深思和探讨。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三联书店,2005.
[3]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张 灏.时代的探索[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7] 傅 铿.知识人的黄昏[J].读书,2013(4).
Yu Yingshi’s Outlook on Intellectuals
ZHOU Liang-fa,DING Ling-l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7, China)
Since 1980s,Yu Yingshi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s adding vigor to his academic thoughts.He thinks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eve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o used “Tao” to change the world.Intellectuals particularly value their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ao’s solemnity and purity.However,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are faced with the double marginalization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Yu Yingshi;Confucian intellectuals;intellectuals
2014-06-08
安徽理工大学基金“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研究”(2012yb009)。
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K203
A
1671-1181(2015)01-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