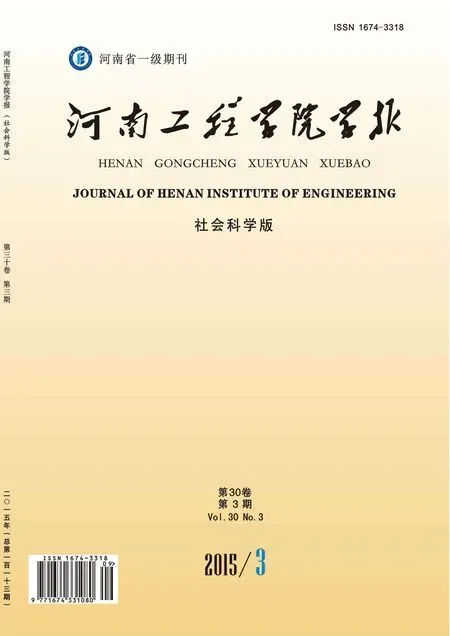雷雨后的一片清凉
——《平静的生活》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形象探析
李奕源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雷雨后的一片清凉
——《平静的生活》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形象探析
李奕源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根据托多罗夫“叙述语法”理论的启示可以发现,《平静的生活》中的外在事件和主人公“我”的内心变化分别形成平衡结构,这构成文本的表层结构。相对应的,文本的深层结构则可进一步描述为:主人公“我”是如何在生命的疾风暴雨中追寻到平静的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两点密切相关,一是文本中引人注目的“三次死亡”,二是“我”与克莱芒的形象特征。在同故事叙述视角的运用下,“我”由内而外展示出睿智坚强的品格特性。这些品格是“我”在艰难中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我”能获得最后的圆满也离不开智者克莱芒的指引。
《平静的生活》;玛格丽特·杜拉斯;平衡结构;同故事叙述;观察者
《平静的生活》(Lavietranquille)①本小说选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王文融译)。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第二部作品,出版于1944年底。在此书历时两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经历了丧子之痛,闻听了最爱的小哥哥保罗的死讯,承受了丈夫被关进集中营的惶恐……这些痛苦的感受,不自觉地注入文本,使文本获得厚重的生命沉淀,生活、死亡、孤独等关键词成为文本探讨的主题。与杜拉斯诸如《情人》《广岛之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等其他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与声誉,但杜拉斯的才华已在其中展现锋芒。目前国内针对《平静的生活》的评论文章寥寥,且过分拘泥于文本的主题,而忽略了其艺术手法。对于杜拉斯这样个性独特的作家的作品而言,这明显是不足的。杜拉斯在晚年重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评价它“很精彩”,并提醒读者:“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1]那么,我们能走向文本的什么地方呢?
一、故事的平衡结构与“三次死亡”的意义
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们认为,叙述性文学作品存在着一种“叙述语法”,可以把整个文本视为一个标准陈述句的展开。“名词(人物)和形容词(特征)或者动词(行动)的组合便形成了陈述。”[2]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散文诗学》(PoétiquedeLaProse)中通过对《十日谈》中故事的研究,认为故事的叙述是通过人物行动的变化来完成的,一篇理想的叙事以一个稳定的局面开始,紧接着这种平衡被一种力量打破转为不平衡的状态,经过诸多周折和努力后,最终又恢复平衡。由此故事类型延伸出来的另一种叙事结构称为“转变”。一方面,在转变类故事中,只出现叙事线路(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第二部分,即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转到一个最终的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不是一个特殊的动作(一个动词),而是人物的自身素质(一个形容词)”[3]。事实上,以上两种故事平衡结构的过程都体现为不断的“转化”。“转化”的实质,根据托多罗夫的界定,指的是叙事中的某些项目向它的对立面转变。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我们来分析《平静的生活》的结构承载着什么样的转化。小说以“我”弗兰西娜“在比格——离开比格——回到比格”为叙述轨迹,形成了一个圆形形态。在这个圆形的故事形态中,以“我”为中心,一方面叙述一家人的境况和遭遇的不幸,另一方面则深入展示“我”的内心。这两条主线可以看作独立的平衡结构,第一条主线属于转变类故事,第二条主线则有完整的叙事线路。两个平衡结构相互交融,但是它们在时间层面上的推进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这就形成文本的张力和趣味。小说开篇便交代了故事发生在比格农庄,弟弟尼古拉将舅舅热罗姆殴打至死,原因是“我”对舅舅和尼古拉妻子的不伦关系的告发。从一开始,维雷纳特家便被死亡笼罩着,它注定是不幸的、失衡的。但是此时“我”的内心却是平静的。“我”认为舅舅这个“东西”罪有应得,因为他花光了我们全部财产,让我们从上流社会跌落下来,并导致“我”未出嫁,多年孤身的尼古拉弄大克莱芒丝的肚子而不得不娶她。舅舅是所有不幸的根源,“死了算什么,作为我们自由的开始”[4]17。接着克莱芒丝离开比格,尼古拉与露丝热恋并开始他的长远计划,“我”与情人蒂耶纳在一起,虽然父母变得有些神情恍惚,但是整个家庭显示出复归平静的迹象,而“我”的心情却由平衡转向失衡。克莱芒丝的出走触动同为女性的“我”,让“我”联想到家庭的种种混乱。更重要的是“我”察觉到了尼古拉对我的隔膜和露丝对蒂耶纳的非分之想。至于蒂耶纳的想法“我”是无法猜透的,因此,“我”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对的,露丝的移情别恋导致尼古拉最后选择卧轨自杀。故事结构与“我”的内心世界都达到了严重的失衡。看着尼古拉那支离破碎的尸体,“我”号叫着奔跑几个小时。家庭就这样,像极尼古拉的尸体,被死亡冲击得支离破碎,“我”决定到T市度假。在面对大海的独自思考中,在自责与肯定自我的矛盾情绪、内心平衡与失衡交替的轮回中,“我”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并从弟弟和舅舅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恰恰此时,旅馆一名男子为了向“我”示爱而下海游泳并溺亡。当其他人指责男子的死是因为“我”的不作为时,“我”却不受其死亡的困扰并坚持自己当时的选择是对的。最后,“我”回到比格,在智者克莱芒的指引下,怀着勇气和平静的心态,回到家中面对蒂耶纳,获得和蒂耶纳结婚的完满结局。故事的结构和“我”的内心世界复归平衡状态。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完结了。结构主义往往将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前者是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后者则需要通过某种认知模式去探知其内在联系。上述描述可基本视为文本的表层结构,对于它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解读呢?
劳拉·阿德莱尔(Laura Adelaide Lyle)在《杜拉斯传》(MargueriteDuras)中对《平静的生活》进行了解读:“小说里有三次标志性的死亡”[5]——舅舅之死、弟弟之死、陌生人之死。诚如以上对文本结构所作的分析:外在故事与主人公“我”的内心变化存在着诸多不相对应的地方。笔者认为,正是这三次死亡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形成的原因:这三次死亡改变了“我”的内心想法,改变了“我”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情感。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认识是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关于事物知识的过程,是行动的基础和结果;情感则是人对客观对象和自己态度的内心体验,是所有行为模式动机的要素之一。可见,外在事件与人的认识和情感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我”所经历的死亡——确切地说,“我”是直接或间接造成死亡的罪魁祸首——在“我”追求平静的生活中是如何产生作用的?用托多罗夫的术语来讲便是死亡如何实现“主观化转换”,使“我”对同个事件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论〈平静的生活〉的死亡主题》中,舒凌鸿认为:主人公在他人死亡的关照中“完成对爱和生命意义的找寻”,“与海德格尔‘向死而在(das Sein Zum Tode)’的死亡哲学殊途同归”。[6]这对我们留下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死亡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死亡视为偶然事件,与自己无关,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向死而在,便是把死看作是最本己的可能性,保持对死亡的知觉,从死亡的体验中反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懂得这一点,人才能够坦然直面死亡,从而拥有高度的自由去实现自身所特有的可能性。首先,舅舅的死是开端。“我”之所以认为他是不可救的、应当被抛弃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憎恨舅舅毁坏“我”的种种利益。这是无视生命的表现。舅舅死亡之前“我”尚未经历其他重要死亡,从而无从感悟人生意义。弟弟尼古拉的死亡则是舅舅不幸的延伸。截然相反的是,尼古拉的死让我痛苦,失去理智,而这仅仅因为尼古拉是“我”想“搂抱他,亲他嘴”[4]5的小弟弟。但是无疑尼古拉的死是促使“我”去思考死亡、人生的重要因素。它让“我”意识到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和死亡的不可替代性。在海滨散步的那些日夜里,“我”明白了:尼古拉死了生活还在继续,“我”应当作为一个具有别样美的女人而活着,这与尼古拉“为爱而死”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的。死亡被关在笼子里,“我”才真正感到生命的存在。所以当所有人都指责“我”目睹陌生男子的溺亡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我”虽难受却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暮色中“我”并不是很确定陌生男子是否沉下水去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敬畏死亡,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陌生男子为了向“我”示爱而下海游水,这恰恰是无视死亡的表现;倘若他对此举并不后悔,那么他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则像尼古拉的死一样轰轰烈烈。正是这三次死亡深刻改变了“我”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情感,在回比格的路上,“我”再一次想到舅舅,发现自己对舅舅的仇恨已烟消云散。“热罗姆要的是被人倾听。可大家都瞧不起他”“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对他说几句客气话。”[4]159
不过,这三次死亡并不能解释文本如何形成独特结构和深刻内蕴的全部。毕竟这样的死亡归根到底是关于别人的,“我”从感悟中摆脱痛苦并不能代表终极考验,真正与“我”自身密切相关的是“我”与蒂耶纳的爱情走向。小说结尾,“我”回到比格后依然不敢面对蒂耶纳,直到在智慧的克莱芒的指引下,“我”才真正拥有平静的心态,作出自己的选择。克莱芒成为最后的关键人物。当然,“我”最终能获得圆满,这与“我”的形象或者性格特征,也就是托多罗夫所指的“人物的素质”是密切相关的。无论如何,“我”就是“我”,在追寻平静的生活中得到胜利。作者在小说结束处富有意味地写道:“天黑了,十月的夜晚,雷阵雨后一片清凉。”[4]181
二、“我”的叙述与其所创造的“我”的形象
我们先谈谈经典叙事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同故事叙述是“叙述者与人物存在同一个层面的叙述。《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同故事叙述的一个例子。当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时,如在《永别了,武器》中,同故事叙述可以进一步确定为对自身故事的叙述”[7]171。 在《平静的生活》中,“我”是故事中的主角,同时也是叙述者,也就是说,“我”在叙述关于“我”的故事,因此,可理解为同故事叙述。同故事叙述,叙述者不仅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且往往决定了读者目光的聚焦点,甚至干涉读者对情节与人物的判断。同故事叙述是有意识的美学抉择的结果,绝不是直抒胸臆的自传的标记。那么,这种叙述视角运用到本文中又能获得怎样的艺术效应呢?
同故事叙述者“我”是一个观察者,读者通过追随“我”的眼光,看到了维雷纳特一家的不幸与矛盾,看到了各个人物的行为与做派,看到了T市海滨浴场发生的事情,甚至直击“我”的内心世界。“我”就像一个取景框,故事与“我”纷繁的思绪靠着这个取景框移步进入叙述视野,得以层层展开形成平衡结构。同故事叙述者“我”同时是一个引导者,在展开人物故事的关键转折点时,“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读者“我”的判断。如尼古拉跟露丝在一起后便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各种计划时,“我想他是打算和露丝·巴拉格结婚”,“这是他一厢情愿,她肯定没有这个想法”[4]70。由于“我”洞悉和掌握了其他人物不为人知的秘密及我作为叙述者的地位,所以,这些判断是可靠的,它们在透露故事发展趋势的同时,让读者的眼光更多聚焦到对人物形象的思考上,并感知到“我”清醒、睿智的人物形象。总之,具有双重身份的“我”近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有趣的是,文本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视线上的盲点——对蒂耶纳的无知。“我”不知道蒂耶纳为了什么缘故来到比格农庄寄宿“我”家,蒂耶纳“想认识你们”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直到故事结束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给出答案。对于蒂耶纳的想法,“我”似乎是永远无法猜透的,比如他面对露丝的引诱时,比如他知道“我”造成热罗姆之死时……叙述者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无知。这些无知成为“我”烦恼的根源之一,成为“我”某些行动的催化剂。“我不得不借尼古拉的手杀死热罗姆,为了引起蒂耶纳的好奇心”[4]133;回到比格后因为无法把握蒂耶纳对露丝的态度,“我”选择暂居克莱芒住处。应该说,恰恰是这个叙述上的盲点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影响了故事的平衡结构,并且将一个年轻女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展现得极为出色,这是作家有意为之而产生的艺术效果。
除以上之外,同故事叙述者“我”的叙述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叙述中夹杂着明显的评价性语言,而且对此并不避讳。正如申丹教授所言:“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她往往不像第三人称叙述者那样客观,而是倾向于从自身体验出发,对自己所观察的对象寄予同情或表现出其他情感。”[8]例如,“有一刻,我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他(奄奄一息的热罗姆)的汗湿、冰凉的额头。他正在我手下慢慢死去。这是一件被抛弃的、不再去救的东西” 。“他(尼古拉)躺在铁道上,贴着铁轨。被爱火烧得滚烫的头颅靠着清凉的铁轨,那不是对我的爱。”[4]13短短的几句话已将“我”对热罗姆和尼古拉的感情展露无遗。这样的叙述包含着观察、描述、感受的多重功能,创造了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叙述出来的故事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二是不经意间构建了叙述者的心理世界,易于与读者形成对话的关系,由此开拓审美的维度。当然,“我”的心理世界和情感世界更直接的建构来自文本的第二、第三部分。在这两部分中小说很多篇幅偏离叙述,直接将强光照射在“我”内心的游离之上,“我”成为一个看点。“我”先从审视自己开始:“我是谁?我一直把谁当成了自己?”[4]106“我”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更多是别人的过去,“我”在比格为一家人操劳不得安宁。对蒂耶纳的思念也时刻折磨着“我”,但是它也让“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女人活着,并且只有自己决定着身心归属于谁。“我”为尼古拉轻率而悲惨死去感到自责,但也赞赏他为爱而死的执拗;“我”知道糟糕的热罗姆希望讨我们欢喜,他要的是被人倾听,但“我”也觉得他得为他的行为接受惩罚。这些接连而来的死亡,最终让“我”明白死也是生命的过程,“我”也没有任何死去的原因,“我”得让父母余下时光活得快乐,“我”得告诉一直想动身去旅行的蒂耶纳“去吧”。“我”发现“根本没必要厌倦。我将拥有平静的生活”[4]97。从以上字里行间中,“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立体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我”是一个敢爱敢恨、情感细腻、关心他人、睿智坚强、具有独特美的生活胜利者。正是“我”具有了这些品格特性,才能在死亡和不幸中涅槃,变得成熟强大,拥抱平静的生活,获得完满。
综上所述,同故事叙述——“我”叙述“我”的故事,除了对故事平衡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之外,更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极大的便利。首先,作为权威的叙述者,“我”能更充分表达对事件和其他故事人物的态度及情感,读者透过“我”的评论感受“我”的性格特征;其次,叙述者“我”掌握说什么不说什么的权力,有能力将读者的眼光从故事转移到自己身上来,直接把内在世界敞向读者,让读者窥见“我”的内心深处。一个立体、深刻的人物形象由此而来。人物形象的解读对于主题的把握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作为观察者的克莱芒与“高山”的隐喻意义
《平静的生活》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人物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也并不复杂。克莱芒是其中的一个边缘人物。文本中提及克莱芒的篇幅基本集中在第三部分短短的最后一节,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克莱芒才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直接参与到故事中。在这之前,克莱芒都是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或者言语间接出现在读者视野中。作者是吝啬的,只给予克莱芒寥寥几笔。应该说,克莱芒的人物形象是容易被读者忽略的,也似乎从未进入评论家的视线中。但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反复提醒我们,叙事分析的关键就是要注意叙事中的所有成分。例如,费伦(James Phelan)指出,叙事本身就是一种修辞行为,就像一个句子,借用各种修辞手段使力图表达的意图、情感倾向更容易被读者认同和接受。[7]15也就是说,文本总是充满智慧和设计的,故事中的任何成分都是有意义的,小说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实际上,克莱芒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克莱芒来自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事情,与维雷纳特家有什么渊源……这些问题,我们无法从文本中找到答案。唯一能推测出来的是克莱芒在维雷纳特家的身份——雇佣者。“我”回到比格,在路上碰到克莱芒。“小姐回来了?”[4]168紧接着“我”询问克莱芒家里的情况和农事,他有条不紊一一做了回答,他是熟知一切的。在早些时候,“我”在T市收到蒂耶纳的来信,信中提道:“克莱芒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并且劝他留了下来。”[4]170由此可见,对克莱芒的这种身份推测是能够成立的。有趣的是,作为雇佣者的克莱芒唯一的事情似乎只是每天跟着他的羊群。热罗姆葬礼的时候,所有人都去了,包括作为外人的蒂耶纳和行凶者尼古拉。“我”因为要照顾幼小的诺埃尔而留在比格,那时“我”看见“克莱芒在齐耶斯山顶上放羊;他的狗尖叫着在山丘上跑”[4]135。克莱芒就是这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始终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克莱芒是沉默的,“他低垂着眼睛,整张脸被帽檐的阴影遮住,看不清他的五官,他变得不像自己了。只有几道闪现的皱纹,给人衰老中止又永无止境的感觉。他不会有更多的皱纹,他的话也绝不会更多。坐在我身边的克莱芒,像时间一样无声无息”[4]37,他活像秋天来临前的一棵树。在“我”暂居克莱芒住处的几天里,他每天都很晚才从比格回来,“我不问他那里的情况,他也闭口不提”[4]173。当然,对克莱芒的解读不能只停留于此。文中几次提到的“齐耶斯山”一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高山”在人类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批评家弗莱(Northrope Frye)在《神力的语言》(WordswithPower)一书中认为,高山是人类居住其上的苍茫大地与深邃天穹间的联系。[9]《诗经·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10]一句,便将人类对于高山的崇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茅盾指出:“原始人设想神是聚族而居的,又设想神们的住处是在极高的山上……希腊人对于奥林匹斯山的观念就是由此发生的。中国神话与之相当的,就是昆仑。”[11]正如《山海经》中谈道的:“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百神之所在。”[12]高山被认为是诸神所在之地,而诸神无非是智慧与光明的象征。也就是说,高山是凝聚着智慧与光明的,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13]。中外文学作品不断地拓展高山的内涵。戏剧大师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在其作品中,便常常将高山当作安静纯洁的精神家园。《小艾友夫》(LittleEyolf)中,沃尔茂在高山地区游居了一段时间,正是受其宁静的环境熏陶而开始思考人生的责任,回家后放弃了枯燥的论文工作,投入到为残疾儿子小艾友夫谋取幸福的事情中。《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WhenWeDeadAwaken)将高山描写成终年积雪覆盖、远离俗世尘秽的心灵寄居之地,鲁克贝教授最终与他精神上的伴侣爱吕尼一起走向了高山。由此可见,高山一词已超越其地理上的概念,指向一种精神、一种象征。
在《平静的生活》中,克莱芒居住于齐耶斯山上,并没有与维雷纳特一家一起居住在农庄的同所房子里,他由此获得一种独有的俯视视角,得以在高处目睹一切。克莱芒总是出现在别人的叙述中,甚至除了“我”其他人未曾留意过他。“某个时候,克莱芒穿过院子,回他齐耶斯山上的住处。他提着一桶羊奶,路过时瞧一眼我们六个快活人围坐的照得雪亮的餐桌。他扭过头去,举起帽子跟我们打个招呼就走了。除了我,没人看见他经过。”[4]46但是克莱芒却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观察着维雷纳特一家的不幸和欢乐,“事情一发生,克莱芒就知道:冬季、雨水、霜冻、孩子、死亡。他对人对事没有任何偏好,避免发表自己的意见”[4]171。与维雷纳特一家的动荡相比,克莱芒始终是平静如一的。上文我们提及的克莱芒“话少”式的沉默与安静的生活方式现在看来是充满智慧的。是的,高山让克莱芒获得智慧。同为观察者,“我”看到的只是人物的行为和做派,克莱芒看到的则是生活的真面目,它的美与丑。“我”成为克莱芒的观察对象。小说最后写道“我”回到比格农庄,但是依然没有勇气去面对与蒂耶纳之间的感情,于是选择跟克莱芒上齐耶斯山,“我”把它当作“藏身地”。“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在没有离开比格之前,“我”便崇敬克莱芒那样的生活方式,并向往已久。从前当克莱芒从院子穿过时,“我不敢朝外面看太久,怕他们发现此刻其实我不在他们身边,而跟克莱芒在一起,走在我记得离此非常远的已然昏黑的路上”[4]46。 到了第三天,夜里下了骤雨,早晨太阳出来了,“克莱芒敞开了屋门和朝向树林的窗户。我觉得我病好了”[4]177,满怀平静地回到比格。“我”从齐耶斯山和克莱芒那里神奇获取力量,懂得了要像克莱芒那样“选择了自己的位置”[4]175。与其说克莱芒是真正的生活观察者,不如说他是平静的生活的象征。高山由此在《平静的生活》中同样获得隐喻意义。
[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M].桂裕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5.
[2]〔美〕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98.
[3]〔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M].候应花,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68.
[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平静的生活[M].王文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M].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249.
[6]舒凌鸿. 论《平静的生活》的死亡主题[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12):11-15.
[7]〔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71.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02.
[9]〔加〕诺斯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8-207.
[11]茅盾.茅盾说神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9.
[10]严明.《诗经》精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4-215.
[12]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293.
[13]张福清.宋诗导读[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108.
Cool after a Thunderstorm——On Story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ofLaVieTranquille
LI Yiyuan
(CollegeofLiberalArt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velation from Todorov′s theory of narrative grammar , we can find that in La Vie Tranquille the external events and the change of "my" heart of the hero, form respectively balance structu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ccordingl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text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how did the hero "I" pursue the quiet life in storm.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wo points, one is the obvious " three deaths" expressed in the text, another is the image feature of me and Cle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skill of Homodiegetic, "I"show a wise and strong character from the inside to outside which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how "I" could persevere in difficulty, and the final success "I" could ge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guidance from wise Clement.
LaVieTranquille; Marguerite Duras; balance structure; homodiegetic; observer
2015-03-21
李奕源(1988- ),男,广东潮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写作学。
I565.07
A
1674-3318(2015)03-0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