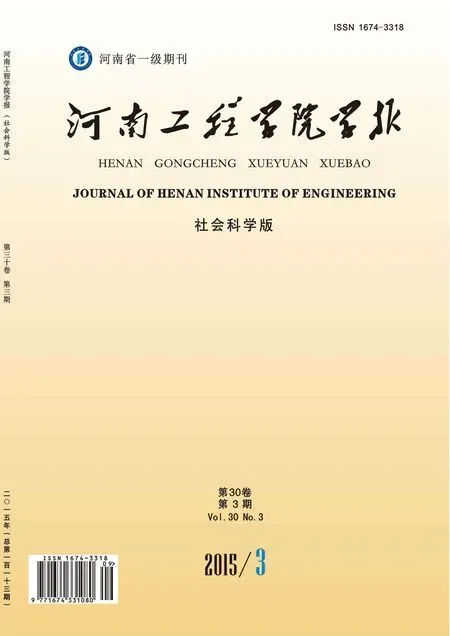贺麟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和探索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232007)
贺麟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和探索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232007)
作为权威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毕生钟情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但他同时将学术视野投向康德及其哲学。其缘由大体可归为德国古典哲学演进的内在理路、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若合符节及现代中国与康德时代之德国的社会情境相似等三种因素。基于“中西会通”的学术理念,贺麟对哲学翻译理论、康德著作译名作了深度探讨,对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近现代学人的康德研究予以细密爬梳。贺麟对康德及其哲学的关注与译介,对后辈新儒家运用康德哲学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贺麟;康德哲学;康德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贺麟毕生致力于“新心学”体系的构建,力图为儒家思想找到一条新路,同时汲汲于西方文化的译介,希冀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思想文化资源。除了阐释和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的经典著作,贺麟对康德哲学用力颇多,数度撰文介绍康德哲学及其思想传承。通览贺麟研究之现状,学界对其关于康德及其哲学的研究尚无充分认识和评定,很有审视剖析之必要。细细研读贺麟的相关论著,文章拟就这一主题展开初步的学理探讨,进而管窥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会上的哲思印迹。
一、关注康德哲学之因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贺麟的名字是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翻译和述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如学者葛力所言:“在我国解放前后,研究和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当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应当首推贺麟先生。”[1]256作为国内极具权威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为何将目光投向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且多次著文述介康德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深究其因,可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梳论:
(一)学术理路演变所致
贺麟毕生钟情于黑格尔哲学,其关注康德哲学盖因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具有内在承续性,康德哲学是通向黑格尔哲学的源泉,若要研究黑格尔哲学,“非先从康德哲学出发不可”“治黑格尔哲学的人,没有不先治康德哲学的”“康德哲学最后逻辑地必然要发展到黑格尔哲学上来”。[2]129贺麟认为,康德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如斯,还对西方现代哲学影响至深且远,故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应该上溯到近代承先启后的大哲康德,尽管后来的哲学家对他的学说备加非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来驳诘他,他却终不失为现代哲学的源泉……现代西方哲学各派哲学家受他影响的程度有深浅的不同,但没有任何人是和他了不相涉的”[3]25。
(二)康德哲学特质使然
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孜孜以求中国现代化的可行路径。新文化派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主要推手。但在新儒家看来,道德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故倡道德以弥补民主之不足。康德对科学实证与道德法则的形上致思正好契合了新儒家的理论谱系,进一步说,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有着某种天然的相似性”,即二者皆属于“内省的致良知的路径”[4],都关注伦理道德、内在良知和主体的行为动机。也许正因为此,一时间国内学者响应渐隆,康德的学术著述遂成他们创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固有资源,鲜有称异者。对此现象,蔡元培在康德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曾作过力透纸背的描述:“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在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迷茫的世界里,特别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它能使最完美的知识和至高的道德的时代潮流融合在一起,并使崇高的永恒真理得以发扬。”[5]501
(三)社会发展情境相似
1925年,大学时代的贺麟发表《论严复的翻译》,决心“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2]125。他之所以关注康德及其哲学,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德两国社会情境极为相似。在他看来,现代中国与康德时代之德国在政治、学术、文化上都极为相似:政治上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学术上启蒙运动方兴未艾;文艺上浪漫主义消解而现实主义勃兴。康德对时代问题的形上思考,对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无疑具有极其可贵的借鉴意义。如是,贺麟说:“其重民族历史文化,重有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顽,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觅与鼓舞,对于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吾人既不舍己鹜外,亦不故步自封,但知依一定之理则,以自求超拔,自求发展,而臻于理想之域。”[2]126
二、关于康德哲学之探索
由于贺麟的学术旨趣不在康德及其哲学,故其没有撰述系统的康德研究专著,然也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如《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大旨》《时空与超时空》《辩证法与辩证观》《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细品慢读这些文章,便可以从中发现他对哲学翻译的阐释、康德著作译名的思考及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重要问题不乏若干独到见解。
(一)哲学翻译理论
现代新儒学研究者郑家栋指出,贺麟虽然终究未能构成自己的新儒学体系,但就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思考的深度而言,他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冯友兰等人。[5]500郑氏之论前半句因非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对于后半句,笔者认为,并非虚空夸大之辞。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贺麟的理论创制与体系构建稍逊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诸人,然在译介西方哲学的成就上却是其他新儒家无法企及的,其黑格尔、斯宾诺莎经典著作中译已成国内权威译本,“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黑格尔的道路”[2]240。
或许得益于多年从事西方哲学译述,贺麟对哲学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功名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2]15也正因爱智之学的多年浸润,贺麟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哲学翻译理论,尤其是对著作译名的论述可谓精彩绝伦。他说:“讲到翻译介绍西洋大哲的名著,则对于译名一事,却不可轻易放过。在别的地方我都很赞成经验派的荀子‘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的主张……但在哲学的领域里,正是厉行‘正名’主义的地方,最好对于译名的不苟,是采取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态度。尤其是中国现时之介绍西洋哲学,几可以说是草创时期,除了袭取日本名词外,几乎无‘定约’无‘成俗’可言,所以对于译名更非苦心审慎斟酌不可了。”而“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2]127。鉴于这种认识,贺麟就哲学翻译问题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第二,要有哲学史基础;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新名以译西名,但须极审慎,且须详细说明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慎重态度,不可随便采用。正是在这种翻译理念的支配下,贺麟对黑格尔、斯宾诺莎哲学作出简汰精当的阐发和翻译。其译文“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故而“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2]1。而他着力向中国思想文化界述介康德及其哲学,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更新、思想启蒙运动之展开大有助益。
(二)康德著作译名
贺麟对康德哲学的探索首先表现在对其著作汉译的译名考辨上,他认为,“译名正确与否,与对康德哲学本身的透彻了解与否相关”[6]141。根据自己的翻译理念,他对康德哲学著作的译名作了学理探讨和初步翻译。贺麟主张将康德的三部哲学经典译为《纯理论衡》《行理论衡》《品鉴论衡》。“论衡”一词首见于东汉王充的同名著作。“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即评定时论之价值的天平。贺麟借用该词以中译康德的批判系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认为康氏著作具有“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7]1180之功用。在他看来,康德三大名著的书名最好能够表示为如下图式:
真——知——知——科学——《纯理论衡》的题材
善——意——行——道德——《行理论衡》的题材
美——情——审美——艺术——《品鉴论衡》的题材
此图式能否精准地标识康德三大哲学之内在旨要,笔者才疏学浅,故不妄加评判,贺麟意在让读者从三部著作的书名即可窥见其哲学的核心义理。在他的思维世界中,《纯理论衡》即“纯知理论衡”之略,《行理论衡》即“纯行理论衡”之略,而《品鉴论衡》若译为“判断力论衡”则无法彰显审美之意,故而意译为《品鉴论衡》以示对于美的欣赏进行批评研究。
行文至此,诸君也许心存疑问,那就是贺麟为何建议将“三大批判”译成“三大论衡”?对此问题,贺麟有一卓见,进而作出颇为精细的解释。他认为,普通的批评叫作批评,系统的重要的批评则叫“论衡”,并进一步指出,批评与怀疑相近,与判断相反,而康德哲学只可说是批而不判,所以“批判”一词不可用于康德著作译名。鉴于这种理解,贺麟认为,康德哲学对于后世哲学具有“批导意义”,故其著作不可泛泛译作批评,亦不可译作有独断意味的批判。言下之意,康德哲学“只是批评研究知识的能力、限度、前提、性质,为‘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导言’奠立基础,以作先导,而自己不建立形而上学的系统”[6]145。
贺麟的分析可谓条理清晰,想必令人信服。然自康德著作中译以来,“三大批判”的译名前后虽略有差异,但大都译成“批判”或者“批评”,其生前念兹在兹的“论衡”一词并没有被学界采纳,这无异于从根本上废黜了贺麟对康德哲学译名之思的学术价值。比如当前学界熟知的“三大批判”的译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版(韩水法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李秋零译)和人民出版社版(邓晓芒译),一概译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必惊异,也不要过于惋惜,因为贺麟生前曾说“提出这些译名纯系供参考商榷的性质,并没有强人从己的意思……也许因为对于康德哲学各人的了解不同,因而译名不同”[6]145。职是之故,笔者认为,“论衡”的提法虽未被学界认同和采用,但不能执着于“译名之争”而完全否定贺麟对康德著作译名的精深思索。
(三)康德哲学传播
近代以降,由于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抗争败下阵来,遂使先进的中国人萌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念头,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2]90。因为失败最初表现在军事方面,故国人引进西学理应首选坚船利炮,由此致使西学东渐经历了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次第阶段。基于学习西方的实用主义立场,作为思想文化之一的康德哲学传入中国甚晚亦在情理之中,以至于“认真客观地历史地钻研、评述、批判、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更是近期的事了”[2]90。
虽然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是太长,但一经引入中国即受到众多学界耆宿的重视,其学术研究无疑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人认知、接受、会通康德哲学的知识谱系。站在学术检视的历史维度上,贺麟将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成三个时期:前期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这是介绍康德哲学的启蒙阶段。此时国内相关的介绍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传播者往往以佛教义理和中国哲学述介西方哲学,难免有些牵强附会,故国人对于康德及其思想只有初步的感观印象,尚无全面深刻的学理认知。中期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这是译介康德哲学的草创时期。此时已有学者根据康德原著进行研究和译述,并进而发掘其思想上的派系和师承*1924年《学艺》杂志6卷5期出版康德专刊,收录15篇关于康德的学术文章,如《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张铭鼎)、《康德知识哲学概说》(范寿康)、《康德伦理说略评》(罗鸿诏)等;1925年《民铎》杂志6卷4期出版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专号,认为“康德哲学是康德以前的哲学的归着点,康德以后的哲学的出发点”,收录15篇有关康德的译著文章,如《康德传》(胡嘉)、《康德哲学的批评》(吴致觉)、《康德理性批评梗概》(杨人楩)、《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张铭鼎)等。。但在贺麟看来,是时康德研究尚显片面,缺乏深度,更无体系,介绍也因研究者的经历、学识、观念及兴趣而有所侧重。后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时学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立场系统研究康德及其哲学。贺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康德“研究成就显著,也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加之翻译工作认真系统”[2]90,这显然为今后深入研究康德哲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除了划分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阶段,贺麟还从史学的视角对近代以来国内著名的康德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作出涸泽而渔式的梳理和评述,为国人勾绘了一幅翔实周博的康德哲学东渐图。近代以来国内的康德研究者为数众多,相关研究之细密、规模之广泛,若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丝毫不过分,以至于本文不能细致周详地全部呈现,这里仅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1.康有为
贺麟指出,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介绍康德星云说的思想家。虽然康有为《诸天讲》有些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从中却能看出当时康德曾初步涉历西方科学史,试图用西方科学成就来解释自然”[2]90。在介绍星云说的同时,康有为也关注到康德的不可知论:“然天下之物至不可测,吾人至渺小,吾人之知识至有限,岂能以肉身之所见闻而尽天下之事理乎?”[8]92
2.严复
严复以译介西方政治、哲学著称,故有“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9]351之誉。严复历来重视经验论和归纳法,但他译介穆勒名学时曾不厌其详地大谈康德的不可知论,尤其是在《天演论》下卷“佛释”“真幻”“佛法”诸篇中。贺麟认为,严复大肆发挥康德不可知论并将其与佛学的不可思议等同起来,只“满足于实证主义重经验归纳的感性知识,而拒绝从哲学方面来深入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确是受到他的学识和时代的局限”[2]94。
3.章太炎
作为辛亥革命的理论宣传家,章太炎基于无神论的立场批评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上帝存在说,并从佛教唯心论的视角对其时空论和“物自体”加以驳斥,认为“以我为空,或以空间时间为空,独于五尘则不敢毅然谓之为空,故以为有本体名曰物如”的学说,乃是“不知五尘同时是相分,此诸相分同是依识而起”。[10]404但在贺麟看来,章太炎“误解了康德的时空说”[2]97,因为“康德并未说时空是绝无,而是说它们是先验的感性形式,人们凭这些感性形式才能纳事物于时空加以认识”[2]97,故觉得章太炎“只是从佛学唯识论来批评他所不甚清楚的康德学说”[2]97-98。
4.梁启超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发表许多介绍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这其中包括他对康德及其哲学的若干思考。贺麟认为,梁启超是康德哲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鼓吹者,并把康德哲学与中国佛学、阳明心学糅合一起“相互印证”“共相发明”。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尊其为“百世之师”“暗黑时代之救世主”,进而宣称“康氏哲学大近佛学”,[2]100又以阳明心学融会贯通。基于此,贺先生说:“梁启超能在当时极力把西洋哲学传播到中国来,特别是把康德哲学着重介绍过来,这不可不说他有一些筚路蓝缕之功。”[2]100-101
5.王国维
1903年王国维写了一首《康德象赞》:“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在能知,不存在物。”[2]102也就是说,康德哲学的精华在于时空因果这些范畴,皆是知物之式,我们凭这些式来认识事物,但只能认识事物之现象,而物自体却难以体察。王国维而立之年即转向中国文论与戏剧,虽然贺麟认为“康德对于王国维来说只是一个阶梯而已,这并不全由于他缺乏哲学的根器,而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尚未成熟到可以接受康德的学说”[2]102,毕竟他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用功颇深、成就卓然,故蔡元培有言“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学的第二人则推王国维”[9]354。
6.蔡元培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以革新现代大学教育闻名,亦是民国初年著名的美学家,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指出审美主体受到美感的熏陶,就能“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划)分人我的偏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11]361。蔡元培对康德的哲学美学颇为关注,1916年写成《康德美学述》,系统论述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在他看来,康德的美学是其哲学精华,能综合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要点,从而达至最高的统一精神境界。他说:“康德的哲学,是批评论。他著《纯粹理性批评》,评定人类知识的性质。又著《实践理性批评》,评定人类意志的性质。前者说现象界的必然性,后者说本身界的自由性。这两种性质怎么能调和呢?依康德见解,人类的理性是有普遍的自由性,有结合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作用。由快不快的感情起美不美的判断,所以他又著《判断力批评》一书。”[9]21-22对于蔡元培的评述,贺麟颇为称道,觉得他“综合和融汇康德的三大批判,提出了艺术、科学和道德三者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的几句名言,是值得我们传诵深思的”[2]104。
以上清末民初学人对康德哲学的述介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若要在此领域深耕细作并能融会自创体系,则需假以时日待条件成熟。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哲学研究渐成蔚为大观之势:1923年,张颐率先将西方古典哲学引入中国大学的哲学课堂;1927年,张东荪等人创办国内首个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哲学评论》;1935年,中国哲学会成立,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的研究;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会的设立有助于系统地译述和介绍西方哲学。在专业刊物和组织机构的有力促动下,康德哲学的译介和研究渐成气候,此中冠绝群伦者则首推张东荪和郑昕二位先生。张东荪的《道德哲学》着力于康德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对如何理解《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提出颇为系统性的独到见解。郑昕的《康德学术》是我国第一部康德研究专著,其独到之处有三:一是着力阐发康德哲学的逻辑主体,二是将“物自体”与“理念”结合起来,三是经验中一切事物皆受主体法则的限制。
三、对于贺麟研究之思考
通览其一生治学,贺麟学术思想的核心之点是“会通中西”,此方面于《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三部学术著作已初现端倪,只是没来得及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倾毕生功力为“中西会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他对黑格尔、斯宾诺莎哲学的翻译及对康德哲学所作的细枝末节的述介,而这些细枝末节未必不能让人窥见某些真实的面相。作为现代新儒家之早期代表,贺麟率先关注、译介康德及其哲学,对牟宗三等后辈新儒家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其热情倡引下,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重构儒家思想,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一个立论基点,进一步说,康德的道德哲学为现代新儒家重新审视、梳理、阐释儒家传统提供了理论前提,遂使现代新儒学蕴含浓厚的康德主义色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浪潮席卷华夏大地,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迎来了经济自强,然随之而来的人情冷漠、道德滑坡等现象亦令人心怀忧惧,如何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有鉴于国民的道德危机,学界近年来时常泛起“回到康德”的呼声,企望以康德的道德哲学携手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提升国民的道德素养。这里所说的“回到康德”具有双重意涵:在理论层面上,意指康德哲学作为元理论能够导引当代中国的思想再启蒙;在实践导向上,是说康德哲学作为方法论可以引领今人理解、汲取优秀的传统思想。至于怎样运用康德哲学,目前学界还没有让人普遍接受的实施路径,然亦有学者对此论域有所涉猎,如杨庆中撰文指出儒学的当代复兴需要学习西学,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可行途径,[12]朱国华著文认为,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需要从西学的中国化汲取思想文化资源,[13]只是杨、朱二位没有具体论述康德与儒家之间的相融相摄而已。不过他们都意识到西学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就足以令我们钦佩贺麟当年的远见卓识。虽然贺麟关于康德及其哲学的学术文字朴实无华,也没有站在一个让人生畏的高度去评定清末民初学人的康德研究,但他的学养、才华、性情、文采、功力仍能从字里行间流泻与彰显,这毫无疑问是其学术思想成就的一个重要面相。综观其学术致思,贺麟偏爱黑格尔远胜于康德,然其寥寥数篇文章竟摹写了康德学术人生真实而又超拔的境界。他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和探索所生成的慧识至今没有消失,并以其特有的神采给我们以智慧之感。
[1]葛力.贺麟先生与黑格尔哲学[M]//宋祖良,范进.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3.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高全喜.从回到康德到回归休谟[J].读书,2010(12):16-24.
[5]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7] 王充.对作篇[M]//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康有为.诸天讲[M]//姜义华,朱荣华.康有为全集(1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章太炎.建立宗教论[M]//章太炎.章太炎全集(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杨庆中.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6):10-13.
[13]朱国华.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J].天津社会科学,2014(6):100-107.
He Lin′s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n Kant′s Philosophy
ZHOU Liangfa
(Depart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Huainan232007,China)
As the authoritative expert on Hegel, He Lin had a lifelong interest in Hegel′s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y, but he also cast the academic vision to Kant and his philosophy. Its reason can be roughly normalized as three factors such as the inner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lassic philosophy, the match of Kant′s moral philosophy and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he similar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Germany in the era of Kant. Based on the academic idea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ster, He Lin made a deep study on philosophy translation theory of Kant and titl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he carefully ran through the spread of Kant′s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modern scholars′ study on Kant. He Lin′s concern and translation on Kant and his philosophy undoubtedly has a positive guiding role that the younger Neo-Confucian used Kant′s philosophy to interpret the modernity of Confucianism.
He Lin; philosophy of Kant; study of Kant
2015-06-02
2015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项目(A2015035)
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B516.31
A
1674-3318(2015)03-0029-05
——贺麟人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