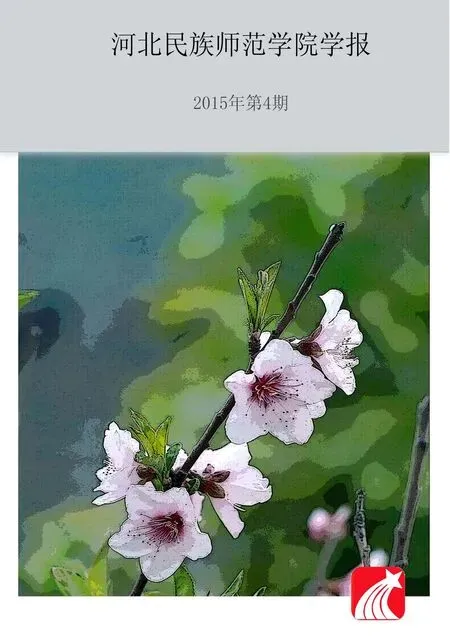汉魏晋南北朝行体诗文体形态研究
徐爽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32)
汉魏晋南北朝行体诗文体形态研究
徐爽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32)
本文针对题目带“行”字的诗歌,即行体诗进行研究。主要分三部分,行体诗的含义、行体诗的语体和行体诗的篇章结构,并纵向以时代划分,试图梳理汉魏晋南北朝行体诗歌的文体形态。
行体诗;文体形态;文体结构
题目末尾用“行”字的诗歌始见于汉代,但没有确切作者记载,如《妇病行》《孤儿行》等,还有一些歌行连称的,如《短歌行》《长歌行》《怨歌行》等。行体诗创作数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著增多,且都是文人独立创作。唐代歌行体诗歌也很多,但与唐前歌行二字标记的诗歌文体区别很大。本文专门研究唐以前行体诗的文体形态。
一、“行”的由来与意义考
学术界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有多篇论文对“行”的意义进行考辨,至今未有明确定义。其原因是大多学者将“歌行”与“行”混淆,由此推断“行”之含义,不免失之全面。其实六朝以前行体诗宜作为一独立诗体,区别于“歌行”之“行”,且“行”的含义不必拘泥于对该字的解释。
(一)行体诗之“行”的两重含义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说到对文体分析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
解释行体诗“行”字的概念,可按这一思路。
很多题目带“行”字的诗都存于乐府诗中。乐府诗分相和歌词、鼓吹曲辞等十三类。据《宋书·乐志》:
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又《杂曲》下载:
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
把“行体诗”和引、歌、谣“诗”等七种诗歌体例并称为“诗之流”,足见当时文人对诗歌细微区别的敏感程度。“行”字最初含义是走路。据《说文解字》:
行者,行也,人之步趋也。
用“行”字定义诗歌,与这个字的词性的微妙变化分不开,即动词性发展成为名词性的意味。据《广韵》引《尔雅》:
行,景迹,又事也,言也。
按照刘勰的文体分析习惯,行体诗的“行“字,极有可能是《尔雅》所释“行”字本义的最初含义:述说事情,言抒心情;又因其通常作为相和曲加以演奏,《说文解字》的解释,则启示我们行体诗具有节奏特点:急促频数。
行的音乐含义不可忽视。除上文引《宋书·乐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叙述送别司马相如时,有:“为鼓一再行”一句,司马贞作索引云:“行者,曲也。”颜师古注曰:“行,谓曲引也。”由此可推论,行字的含义早期又与音乐有关。司马贞明确说“行”是曲,必然有他当时的依据。仅从现汉魏时期所存行体诗歌,都是入乐歌唱的;颜师古注的“曲引”即一段曲子的序曲。总之,“行”在诗歌里,肯定与音乐歌唱有关。
由上,以“行”标题的诗歌,其含义有二:叙事言说(心情等)和乐曲。这可从一些文献中得到证明,据沈约《宋书·乐志》[2]载:
晨上秋胡行武帝辞
北上苦寒行武帝辞(六解)
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八解)
就其一条分析。晨上,表示时间及事情本身;秋胡行,是曲子;武帝是作者。从题目可归纳出这是武帝用秋胡行这个曲子,作辞叙说晨上这件事,并表达自己的心情。剩余两条同理。
行作为乐曲,还可参考《宋书·乐志》[2]的记载:
唐尧古务成行(古曲亡)
玄云古玄云行(古曲亡)
伯益古黄爵行(古曲亡)
第一则,古今乐录曰: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第二则,古今乐录曰:玄云。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才也。第三则,古今乐录曰:伯益。言赤乌衔书。有周以兴。今圣皇受命。神誉来也。这三则均歌颂圣皇事迹,唐尧、玄云、伯益代指圣皇,即事件的人物,后面则是“以何而歌”,即用“古务成行”、“古玄云行”、“古黄爵行”演奏。这样的标识,大概有用某曲歌某人某事的意味。
由此,行最初应具有音乐、事件双重含义,缺一不可。
(二)“行”与先秦古歌关系考辨
歌行连称的习惯可能因为二者最初有密切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古歌。据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许多具有“行”字含义的先秦古歌,行、歌之间有或隐或显的关系,具体包括言情和叙事两方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行体诗的含义。
1、古“歌”诗咏唱人物的行进及心情
如逯本《涂山歌》下注引《吕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於是涂山人歌曰云云。”禹出行来到涂山,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当地人此歌记录这一出行过程;名为《涂山女歌》的诗篇,其注释也引用了这则材料;《去鲁歌》下注引《史记》:“孔子相鲁,齐人遗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番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曰:吾歌可夫。歌曰云云。”孔子劝解桓子,不要沉浸女乐不顾政事,作歌一首并离开鲁国。孔子行而后又歌。
2、古“歌”诗咏唱某一事件的行进过程
《岁莫歌》引《晏子春秋》:“景公筑长庲之台。晏子侍坐。觞三行。晏子起舞曰云云。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惭焉。为之罢长庲之役。”酒行三杯过后,起舞歌之,这是进行的事件核心要素,晏子作《岁莫歌》,与“觞三行”、“起舞”同时发生,具备了传统的“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诗歌元素、音乐元素、舞蹈元素相结合,这与乐府清商曲辞保存的“行”题诗歌类似,因此可以推论行体诗与先秦古歌的原始形态中都具有诗、乐、舞三元素,都是借此来记事言情的。只是从“歌”到“行”,经历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化过程。
以上几首诗歌可推论二者关系:某人发出“行”的动作或发生与之相应的事件,而对应的古歌都是记载或者反映该动的诗,上文提到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为鼓一再行”也不出此类。这是由先秦到汉代延续的规律。据此,有学者推断“行”的意义是“行旅”或“移动”的音乐是不够精确的。最早在先秦,“行”的曲子是作为歌诗的内容存在,在汉乐府兴起以前,“行”还不是一种独立的题材或曲调。“歌行”连称,或有歌某一行动之意,歌作曲调,行是内容;随后“行”衍变为独立文体,进而与歌重新结合,此时行为曲,歌为内容,成为某歌以行曲演奏的形式。
总之,行和歌的关系,最早是与诗歌中的活动有关,进而发展到诗、舞、曲结合,演变为以“行”为结尾的独立的诗篇。唐代的歌行诗则又另当别论。
二、行体诗的文体形态与发展流变
行体诗产生于汉代,文人拟作盛于魏晋南北朝,唐代则衍变为歌行体。行体诗歌的音乐性、叙事性本论文都有专门论述,本节重点讨论行体诗语体、结构特征和功能,以及发展流变。
(一)行体诗的语体
行体诗写作自由,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几乎是最灵活的一种诗体。汉代行体诗有四言、五言和杂言,五言诗占多数,约60%。汉乐府诗歌出现三言句式,是楚声大兴的标志,声势短促急切。行体诗的杂言体多三言与五七言穿插的句式,如《薤露》(《泰山吟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抒发感情,三言文字短促的句式,暗合生命的易逝。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3]。很多汉代行体诗已与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区别不大,其形式整齐,对仗工整。行体诗如《长歌行》《相逢行》等,其写作技巧已相当纯熟,与古诗十九首不相上下。
从魏朝开始一直到隋朝,诗歌多以五言为主,但有些古题乐府,作者扔沿袭旧制,倾向于用四言歌之。如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又曹丕《善哉行》其一:“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通篇是整齐的四言,此类诗歌大多歌咏人生哲理、军旅生活、生命体验等,大抵因题旨精深,又成为拟作惯例,故用雅正的四言体。
魏晋南北朝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创制的艺术性达到了相当高度,其中,行体诗几乎涵盖了所有句式。纯三言有鲍照的《代春日行》:
献岁发,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芳袖动,芬叶披。两相思,两不知。
六言有虞信的《怨歌行》: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
还有历来得到普遍认可的七言开山之作——曹丕的《燕歌行》。此略。
杂言体如陆机《月重轮行》,也颇有代表性:
人生一时,月重轮,盛年安可持。月重轮。吉凶倚伏,百年莫我与期。临川曷悲悼,兹去不从肩,月重轮。功名不勖之……独长叹。
一诗之中,涵盖二字至七字所有句式,行体诗形式的自由程度可见一斑。这类形式极自由的诗歌,题目基本都是文人新拟的,鲜有拟作乐府旧题,可以看出魏晋六朝文人的创新意识与对前代文化的尊重。而五言体占行体诗总数90%以上,正印证了钟嵘《诗品》:“五言居文词只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的诗歌时代风气。
(二)行体诗的文体结构
行体诗的文体结构至多有五部分组成,即题目、艳、正文、趋和乱。其中题目具有沿袭性、时代性,有别于普通五七言诗歌题目而类似于词;艳和趋是音乐的标志,类似序曲、尾曲。这五部分相互关联,又能独立地承担叙事功能,共同构建行体诗独特的文体叙事结构。
行体诗题目与五七言诗、古诗题目不同。首先,它明显具有沿袭性。历代文人通过不断拟作,使行体诗的题目得以延续。题目拟作频率与诗歌主题流行度和作者的喜好程度有关。有的诗歌题目即限定了主题,如《从军行》一般写军旅题材,《燕歌行》多抒发思妇相思之情,《相逢行》一般是穷富相遇展开对话;与此相对,有的行体诗歌虽然题目不同,内容、主旨也可以类似,如《董逃行》和《升天行》,乍看毫无关联,实均写求仙之事。行体诗的题目与词牌又不一样,首先词牌限定的是格律,内容、感情是独立的,因此同一词牌,不同作者所作,主题几无重复。
其次,行体诗的题目具有时代性。文人对行体诗的题目选作频率差距很大。经统计,历代文人拟作最多的题目依次是《从军行》19首、《艳歌行》14首、《短歌行》11首和《怨诗行》(含《怨歌行》)9首。其中《从军行》创自魏朝,不是汉乐府旧题,但其“后来居上”之势,一是因为符合历史背景,二是体现了诗人关注现实、关注军旅题材的情怀;再如,受魏晋清谈风影响,魏晋名士对生命本体的关注大于以往,像《短歌行》对生命宽度、长度的理解、表现人文哲学的题目盛极一时;又南朝时宫体诗兴盛,女性多成为诗歌吟咏对象,加之南朝民歌吴声、西曲的影响,《艳歌行》、《怨诗行》这类题目得到文人的偏爱。
应该注意到,题目选择还有作者的个体差异性。西晋拟作行体诗创作较多的诗人,陆机29首,傅玄22首;刘、宋时期,鲍照21首,谢灵运16首;齐、梁时期,沈约14首。其中,陆机、傅玄偏爱三曹所作行体诗题目,谢灵运又多沿袭陆机,鲍照则善于自拟新题,形式为《代××行》。
艳、趋、乱是行体诗独有的文体结构,都具有叙事功能[4]。只在汉魏时期的行体诗中偶见,后来就完全消失了。
(三)行体诗文体形态的发展流变
行体诗的创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不断的“拟”与“创”中变化的。以下从文体形态上探讨其发展情况,包括艺术风格、篇章结构、语言技巧三方面。
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性,包括音乐、表演、叙事技巧,它在汉代是经采诗官在民间收集,入乐表演的。现存汉代行体诗,虽然只能看到文本内容,但是从《乐府诗集》征引《古今乐录》《乐府古题要解》等书的题解看,这些诗歌都是入乐或本身就为曲名的。魏晋行体诗延续了这一制度,但新制作品是有选择性的谱曲而非首首入乐。能够入乐表演的,多是皇室成员的作品或者受皇室喜爱的旧题,即有一定政治意味在里面。而文人的创作的文本作为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数量远大于入乐作品,行体诗的音乐性逐渐减弱,直到六朝几成徒诗。相应地,行体诗也从重表演性、灵活运用叙事技巧转为叙事以抒情、作诗以自娱的诗歌。汉代行体诗以演为第一目的,所以多片段式叙事和典型化的对白与动作描写,同时兼顾舞台效果。到了南北朝时,叙事题材不断扩大,谢灵运、鲍照等人的作品,多叙出游活动,是诗人寄情山水生活的写照。行体诗由重叙事转向叙事以抒情,艺术性和表演性就相应减弱了。
行体诗很多同题诗歌,虽经历代拟作,却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篇章结构,这是文人刻意摹仿的结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相逢行》,又名《相逢狭路间行》(《长安有狭斜行》类似)。汉古辞作是先设计一个邂逅询问的引子“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接下来是借旁白人之口,问出“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继而向“少年”介绍遭遇的这位“君家”:从家的富丽堂皇到其成员的高贵舒适,一一道来。后代拟作此题目的,齐梁时期最为突出和典型。有荀昶、张率、梁武帝、庾肩吾等,开头均是“狭路相逢”,如荀昶的“井陉一何狭,车马不得旋”,张率“相逢夕阴街”,梁武帝“洛阳有曲陌,曲陌不通驿”等等,其从主题到篇章结构完全依循古辞旧制,几成定势。
同样应该重视的,还有行体歌辞拟作在语言体制上效仿。如《短歌行》魏武帝“对酒当歌”篇,通篇四言体式,从魏到晋代,曹丕、曹叡、傅玄、陆机所拟也都为四言体。也有革新的,即语体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魏文帝曹丕《燕歌行》二首,均七言,陆机、谢灵运拟作,亦皆七言句式且句句押韵,篇幅不超过15句;从南北朝开始,则有创新。第一,篇幅大增,梁元帝同题诗歌22句,萧子显24句,王褒26句;第二,重视了声韵的变化,换韵而非前期一韵到底形式;最后,句式也有变化,不再是通篇七言句,如萧子显《燕歌行》就在末尾加入五言句式“吴刀郑绵络,寒闺夜被薄”。正是文人自觉地对古乐府诗歌不断地模仿和突破,并积累五、七言诗歌艺术,才有日后唐代成熟的歌行体诗。
以上是六朝以前行体诗的文体形态研究,主要针对文体意义、文体形态特征及发展变化的角度论述,当然,行体诗还有很多方面有待研究,比如与相和曲其它文体对比、与“××歌”诗的对比、韵律等诸多问题,将在日后研究中逐一论述。
[1]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27.
[2](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96.
[4]徐爽.汉魏晋南北朝行体诗歌的叙事性[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1).
Stylistic Formation of“Xing”Poetry from Han Dynasty to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U Shu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2,China)
According to Lu Qinli's The Poetry from Qin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0“xing”poetries.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Xing”poetry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nalyzing its literary forms,music forms and narrative styles.
“xing”poetry;literary forms;stylistic formation
I206
A
2095-3763(2015)04-0061-04
2015-04-02
徐爽(1988-),女,河北承德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