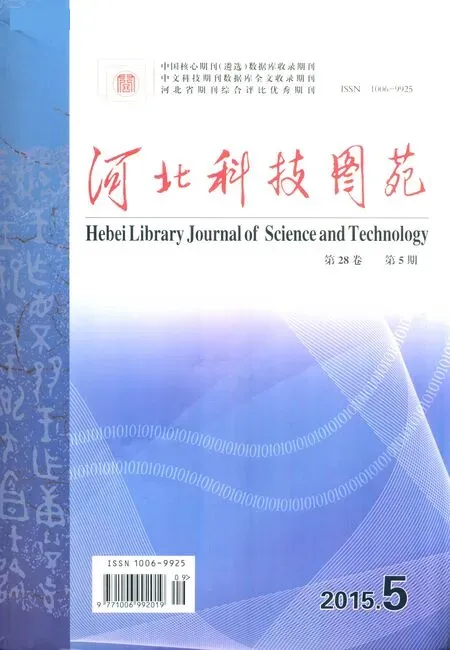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特点及其整理利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特点及其整理利用★
郑玉娟
(许昌学院图书馆河南 许昌461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的流行,寺院藏书日益兴盛,并呈现出了新特点。藏书数量迅速增长,藏书形式出现新变化,涌现出了一批藏书宏富的寺院,高僧云集,佛典日众,并对其藏书进行了校刊编目、撰著等整理利用活动,对我国佛教典籍的保存和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寺院藏书;佛教;整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G259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201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及其整理利用研究”(2015-gh-3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8-06 责任编辑:刘丽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佛教的教义思想和人们苦难的心灵相契合,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希望,佛教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大发展,得到了统治者和贫民百姓的普遍尊崇和信奉。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佛教译经的大量涌现,寺院藏书日渐兴起,并逐渐发展为我国古代社会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并存的一大藏书系统。
1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的发展与特点
1.1 寺院藏书的数量迅速增长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早流行于上层统治者,史载东汉时期汉明帝刘庄、楚王刘英、汉桓帝刘志都崇信佛法,京都洛阳成为汉译佛经的中心,尤其是明帝下诏修建的白马寺,成为我国汉传佛教的第一所寺院,相传佛典《四十二章经》就是在此译出的。佛教经典是佛教三宝中法宝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佛教界的共同财产,除了供僧人记诵、抄录进行日常修行外,从西域传入的原始佛典与新译出的佛典自然需要统一珍藏,共同敬奉,寺院藏书便随之而生。据史书记载,东汉后期的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相笮融曾“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檗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1]这则材料中笮融能够大造佛寺,广聚僧徒,诵经布道,寺院自然藏有经书,这也足以表明东汉末年寺院已有藏书形态出现,藏书数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2]。
到了曹魏时期,史书中虽未见魏武帝、魏文帝信佛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寺院藏书的停滞不前。据《出三藏记集》卷七《般若三昧经记》载,此经为竺朔佛、支谶等人在洛阳译出,又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校订[3],既然在曹魏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和许昌有译经、校经之举,当时的寺院就当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到曹魏中后期,自魏明帝对佛教的认识有所改观,寺院藏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齐王曹芳嘉平年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康僧铠先后在洛阳白马寺译经;高贵乡公正元年间,安息僧人昙无谛也在此译经。据《开元释教录》统计,曹魏共译佛经十二部十八卷[4]27。据有关史料记载,曹魏政权还修建了一些寺庙,如无迁寺、建官寺等以供印度及西域僧人居住和传经等,虽然其藏书具体情况不详,但有部分藏书则是无疑的。江东孙吴政权与曹魏不同,一开始就对佛教采取宽容和尊重态度,许多僧人奔赴东吴,如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还为康僧会建寺礼佛,成为有记载以来江南的第一座佛寺,故名“建初寺”。康僧会此后一直在此从事译经和佛教活动,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去世,此寺必有相应的藏经和藏书。除建初寺外,孙吴时当还有其他寺院,如支谶曾在吴地译经三十六种四十八卷,也必有译经和藏经之所。据《开元释教录》统计,孙吴时期,共译佛经一百八十九部四百一十七卷[4]29。
西晋前期,晋武帝司马炎对佛教并不扶植,佛教发展不大。至西晋后期,晋惠帝信佛,在洛阳建寺;晋愍帝在长安相继建寺,以供养僧人。洛阳、长安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两大中心,共有佛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人。西晋译经大师主要有竺法护、竺叔兰、法立、法炬、支法度、无罗叉等人,共译佛经三百三十三部五百九十卷[4]43。永嘉南渡之后,北方不少佛教僧侣也南渡避难,据王青先生统计,“公元4世纪时,江左信奉弥陀佛的大多数是北人南渡者”[5]。东晋时期,上至皇帝、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信奉佛教者颇多,佛教随之获得了较大发展。整个东晋一朝共有寺院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共译佛经一百六十八部四百六十八卷[4]68。
北方政权十六国中的后赵、前秦、后秦、北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大力倡导佛教。后赵石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并颁诏准许民人奉佛出家。据《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载:“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6]石虎统治时期,后赵有寺院八百九十三所。前秦苻坚频频加惠于僧尼,后请得名僧释道安,对佛教更加尊崇。这一时期,以释道安为首的译经僧人共译出佛教典籍十五部一百九十七卷。后秦姚兴尊儒敬佛,特建逍遥园以供养僧侣,长安成为佛教圣地。这一时期,在高僧鸠摩罗什主持下,共译经九十四部六百二十四卷。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凉州作为天竺、西域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名僧汇聚,塔寺众多。中印度高僧昙无谶到北凉后,受到沮渠蒙逊的厚待。在慧嵩、道朗的协助下,译出佛经十一部一百一十七卷。北方十六国时期,共译经二百五十一部一千二百四十八卷。由于译经事业的发展,这个阶段的寺院藏书理应比三国时期有较大发展,然由于文献无征,具体情况已无从考察,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最起码道安在襄阳居住的檀溪寺,在长安居住的五重寺,鸠摩罗什在长安居住的中寺、大寺,慧远的庐山东林寺等,均藏有大量佛经与其他图书[2]517。
南北朝时期,在封建帝王的带领和扶持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崇佛狂潮,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佛教发展达到了繁盛,佛典繁富,佛教藏书也随之达到鼎盛。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宿僧译经。这一时期著名的藏经寺院为牛头山佛窟寺。据《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一《法融传》记载,此寺位于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城南,因有辟支佛窟而得名,为刘宋初刘司空所建,藏有佛经、道书、佛经史等七藏经书[7]280-281。刘宋一朝共有佛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译经高僧可考者二十二人,其中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智严、宝云和释昙无竭等最为知名。刘宋为南朝译经之冠,共译四百六十五部七百一十七卷[4]119。萧齐时期,齐高帝、武帝都尊崇佛教,武帝临死时在《遗诏》中还嘱咐其子孙尽心礼佛,供养玉像。其诸子中以竟陵王萧子良最崇佛教,他“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并亲抄佛经十七部,自号“净住子”,“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8]698-700。萧齐虽立国较短,但佛教有较大发展,共有佛寺二千零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所译佛经十二部三十三卷[4]151。至梁朝,梁武帝萧衍曾“四次舍身入寺”,亲自讲经、注经,并组织译经。佛教在其大力扶植下,在南朝达到了鼎盛。梁朝共有佛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梁武帝还特批华林园,庋藏佛典,并命僧绍整理编辑了《华林佛殿众经目录》。梁朝位于建康东北钟山的定林寺,藏经四千余卷,著称于江南。另外,建初寺、长沙寺,也是当时富藏佛经的著名寺院。梁释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共十五卷,计著录佛籍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卷,这足以想象当时寺院藏经之盛。遗憾的是,梁末侯景之乱,京师佛寺七百余所焚烧殆尽,各地寺院藏书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至陈朝,陈文帝、陈宣帝等均信奉佛教,努力恢复寺院藏书,但全国仅有佛寺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译经仅有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4]175。据统计,南朝共译各种佛经五百五十六部,一千零八十四卷[9]。
梁启超先生曾云“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10]。在统治者的重视和引领之下,这一时期国内寺院及译经数量快速增多,寺院藏书数量随之获得迅速增长,藏书多达四五千卷的寺院已不鲜见。
1.2 寺院藏书形式多样化
随着人们对书籍保存认识的深入,这一时期的寺院藏书形式除以手写佛经为主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藏书形式——石刻佛经,即将相关经文刻在石窟中摩崖上。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就认为,无论是缣缃皮纸,还是简策之书,都容易受到水火的毁坏,然而金蝶难求,佛教经典难以长久保存。于是,佛教徒就把佛经刻在佛窟石壁上或镌在石版存放在窟中,从而开创了石刻佛经,并成为保留经本、防备法灭的一种新的藏书形式[11]。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甚多,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主要有北魏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北齐开凿的天龙山、响堂山石窟等。其中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北响堂山石窟包括刻经洞、释迦洞和大佛洞三大窟。刻经洞历时四年完工,窟内外的壁面山镌刻有《维摩经》、《胜曼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和儒家石经异曲同工,是北朝佛藏的一个类型。在历代石经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北齐南岳慧思大师发愿倡议,由弟子静琬开始实施,历时千余年才完成的房山石经。
2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的主要寺院藏书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有寺院僧徒的地方当有藏书,只是藏书多少不同而已。遗憾的是许多寺院藏书多被历史所湮灭,现只能将见于史料记载经过考证藏书较丰富的寺院介绍如下:
2.1 建业建初寺
孙吴时期孙权于建业城内为康僧会建造的,这是有记载以来江南的第一座佛寺。据《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解释其名称由来:“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7]5康僧会一生以建初寺为基地,从事译经和佛教活动,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去世为止。另外,僧佑曾在建初寺造立经藏,搜校佛教典籍,直到梁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圆寂于此,这都证明此寺拥有丰富的藏经和藏书。
2.2 襄阳檀溪寺
东晋道安在湖北襄阳的主要驻锡地。兴宁三年(365年),道安因避战乱率弟子来到襄阳,先据襄阳白马寺,后因寺院狭小而另建檀溪寺,起塔5层,有屋400间,道安及其信徒在此居住15年,建立僧团,明确戒规,讲经传教,整理佛经,还编制了《综理众经目录》。如果没有充实的藏书、藏经作参考,编制目录是完全不可能,因此,檀溪寺必有大量藏书是毫无疑问的。
2.3 庐山东林寺
庐山东林寺为江州刺史桓伊为道安高弟慧远所建。公元378年,前秦大军压境,道安为东晋守将朱序所拘,无法离开,就命弟子分遣四方,慧远东下到达庐山,先居西林寺,东林寺建成后,迁居于此,修行、传教、著述,直至去世。慧远作为东晋后期南方佛教界最有影响的人物,秉承道安传统,在东林寺收藏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与教外图书。史载东林寺曾编有藏经目录《庐山录》一卷;慧远弟子释道流曾依据东林寺藏经编有《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等四部目录,目录未成因病去世,由同学竺道祖补编而成,这些书目早已亡佚,今人已无法知晓慧远时期东林寺藏书数目,但却足以证明东林寺的藏书之盛。
2.4 建康道场寺
东晋时南方重要的译经、藏经中心。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和西行求经回来的法显在宝云的协助下,于此寺共同译出法显带回的经书六部六十三卷,此外,佛驮跋陀罗还曾在此寺单独译出经书多部,求那跋陀罗等也曾在道场寺译经。因此,此寺亦当有丰富的藏书。
2.5 会稽嘉祥寺
东晋孝武帝时郡守王荟起造。据《高僧传序》载,作者慧皎在此寺编著《高僧传》时,曾“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资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7]3,此足以证明嘉祥寺藏书之丰富。
2.6 长安五重寺
长安五重寺是释道安在长安的居住地。公元379年,前秦派兵攻下襄阳时,道安受到苻坚的无尚尊崇,被请入长安,成为前秦佛教界的最高领袖。道安在五重寺期间,除继续佛学著述外,还组织中外学僧译经、译律。道安在此共生活了六年,成就和影响都很大。从苻坚对道安的礼遇以及道安在长安的佛教活动来看,道安北上时很可能已将襄阳檀溪寺藏书大部分带走,并在五重寺建立了新的藏书体系[2]517。
2.7 钟山定林寺
钟山定林寺也叫钟山定林上寺,是南朝著名寺院。据《高僧传》卷十一记载,僧祐建康人,“初受业于沙门法颖。……祐乃竭思钻求,遂大精律部”。后受到齐竟陵文宣王、梁武帝的尊崇,遂集合众力,更广其事,“凡获信施,系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建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7]81。先后在钟山定林寺和建业城内的建初寺建立经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经藏的人。在僧祐主持期间,定林寺收藏经书最多时达四千余卷。文学家刘勰也曾经在此帮助编制过经藏目录。
2.8 洛阳永宁寺
洛阳永宁寺是北魏时洛阳城中著名寺庙。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寺中有僧房一千余间,外国所贡献的佛经和造像,都保存于此。由此推断,此寺是专门收藏外国进献的佛经、佛像的,其藏书当不在少数。还有菩提流支来华后,也曾由北魏宣武帝安置于此译经。
2.9 邺城天平寺
邺城天平寺是菩提流支随东魏迁都后的居住地。据《续高僧传》引李廓《元魏众经目录》载,二十余年内,共译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所藏佛典丰富,并编成《译众经论目录》行世。又据《续高僧传》记载,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来到邺城,被安置在天平寺,文宣帝下诏将千余夹梵本,送给流支并请他译经。这些资料亦可见天平寺藏经之丰富。
此外,这一时期藏书颇为丰富的寺院还有长安大寺、中寺,丹阳牛头山佛窟寺,会稽龙华寺,荆州长沙寺,陕州五张寺,郢州头陀寺,招提寺,陈留郡仓垣的水南寺、水北寺等等。
3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的整理和利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藏书的整理与利用不仅表现在供僧侣诵经译经修行之用,更表现在对佛教藏书的整理编目和对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初步建立。
3.1 供佛教徒及信众诵经修行和译经撰著之用
在汉传佛教中,寺院不仅是僧侣及其信教徒聚集、生活修行的地方,更是他们集体诵经、译经、做法事等活动的场所,其修行教育功能远远大于其生活功能。寺院藏书种类丰富,不仅有大藏经、单本译经、中国僧人撰著,还包含有宣教通俗文书、寺院活动文书等,为僧侣们进行一切文事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说,僧侣们的诵经、讲经、译经、撰著等活动是对寺院藏书的最直接利用。第一,念诵、抄录佛经是僧侣们最主要的日常活动。按照佛教教义规定,佛教经书、戒律是每一位修行者所必须随身携带的十八种物品之一,随时随地都可以念诵修行。第二,讲经。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讲经高僧,据《高僧传》记载,释僧佑“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7]81;释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7]40等等,由此可见,讲经作为一项普教性的活动,听讲的人甚多,不仅有普通信众、寺内僧徒,还有当时学养甚高的佛教徒。第三,译经、撰著。在功德心的驱使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极其兴盛,逐渐由私人译经发展为由官府组织在皇帝为译经专门开辟的译场集体译经。这一时期,不仅僧侣译经兴盛,还出现了中国僧人撰著的佛学著作。如晋释支道林著有《圣石辩之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佛学著作,史称其文“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12];梁释僧祐编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佛教论著总集《弘明集》等。此外,还出现了经序、史传等。《出三藏记集》载经序(包括译经后记)一百二十篇,记录了经本的来源,译经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类似后代的目录提要。史传是指僧人传记,最著名的是梁代慧皎撰写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僧人传记——《高僧传》,记载了后汉至梁初257人(附见者又200余人)的史实。据唐代释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凡六百六十四载,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4]3
另外,寺院藏书不仅供寺内佛教徒诵读修行、译经撰著之用,还常为信众阅读研习佛经提供便利。据《广弘明集》卷二十七记载,东晋时期,“(刘遗民)于西林涧北,别立禅坊养志,闲处安贫,不营货利。是时闲退之士轻举而集者,若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之徒,咸在会焉。遗民与群贤游处,研精玄理,以此永日”[13]。刘遗民诸人均系士人,他们在一起研究佛理,必定要阅读东西二林的藏经,才能贯通佛学理论[14]。
3.2 寺院藏书的整理与佛教目录的编撰
随着寺院藏书的勃兴与发展,佛教典籍的数量和品种日益增加,对其进行去伪存真,校订整理已经势在必行,佛教界开始对其藏书进行系统整理,编制佛教目录,使之规范化、体系化。佛教目录大多记录了一寺、一地或一时所藏佛典,是对佛教藏书进行整理的最重要成果,也是我国目录学史上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姚明达《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统计,这一时期产生的佛经目录有近四十部,但留存至今的甚少[15]。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晋释道安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编制的《综理众经目录》和梁释祐于梁武帝天监四年历时六年撰成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是我国较早的佛经目录书,著录东汉光武以来,迄晋宁康二年(374年)所出的佛典,是对当时中国佛教典籍的一次大梳理和总结。全书共分六类:一为“经论本录”,收录自汉至晋十七家二百四十七部完整而质优的译经;二为“失译经录”,共收失缺译者姓名的译经一百三十四部;三为“异经录”,指收录各地区不同版本的译经;四为“古异经录”,收录古代翻译的佛经九十二部;五为“疑经录”,共收真伪存疑的经书二十六部三十六卷;六为“注经杂经录”,收道安自己所注佛经共十八部二十七卷。梁释僧祐曾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绎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3]22这足以说明《综理众经目录》在我国佛教目录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作用。梁释僧祐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经录》,对经藏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细致的考订、校雠。同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也相从进行了整治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经过僧祐和刘勰等人的历年辛苦整理,编撰了我国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此书全录十五卷,著录佛经凡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全书共分为四部分:一是“撰缘记”,记载佛教三藏和译经的起源;二是“铨名录”,记从东汉以来译经目录,其中又分十二录;三是“总经序”,记各经的前序和后记一百二十篇;四是“述列传”,记译经人的传记。前二卷记录外国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十人,共三十二人。录内又有《集三藏录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出入藏记》三篇文字,详细叙述了佛经结藏的过程,成为研究南北朝佛藏发展的重要文献。
3.3 初步建立了汉文佛教大藏经
大藏经,为汉朝佛教所独有,通常被称作“众经”、“一切经”、“经藏”、“藏经”、“大藏”等,是一切佛教典籍的总汇。这个名词的出现,约在南朝末年或隋朝初年,但组织、编定藏经的尝试,却远早于此时[2]510。大藏经有手写与雕版两种形式,唐五代雕版印刷出现之前处于手写大藏时期。而手写大藏的萌芽,约产生于道安(314-385年)时期。道安在其所编《综理众经目录》中提出了疑、伪经的问题,为佛教典籍的鉴别和收藏提供了一个理论判断标准,实际上已涉及大藏的取舍问题。之后,鸠摩罗什的弟子慧观提出了“五时判教”的观点,为佛教大藏经体系化的形成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再者,这一时期佛典目录的大量出现,客观上为一定地区各个寺院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客观规范,同时又推动了各种自行设定的大藏经组成标准的出现。另外,佛教三宝思潮的影响、社会信众功德心理的强化等都大大推动了手写大藏的出现。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各类手写大藏的雏形不断出现,(南)齐高宗明帝曾写一切经,陈高祖武帝、世祖文帝、高宗宣帝又各曾写一切经十二藏,(北)魏太祖道武皇帝写一切经,(北)齐肃宗孝昭帝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藏。这些不同类型大藏经的出现,是对寺院藏书整理利用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又为寺院藏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标准和规范,对佛教寺院藏书的更好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4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藏书虽然处于勃兴阶段,但在寺院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保存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和其他典籍,而且非常注重藏书的整理和利用,开始了佛教目录的编纂和大藏经的形成进程,为后世的佛学研究留下了大量宝贵翔实的史料,更为隋唐及其以后历代寺院藏书的兴盛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1185.
[2]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32-34.
[3](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268.
[4](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M]//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第10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7.
[6](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87.
[7](梁)释慧皎.高僧传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9]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5.
[1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陈士强,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68.
[11]王子舟.六朝隋唐佛教藏书考[J].图书情报知识,1989,(1):43.
[12](宋)王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120.
[13](唐)释道宣.广弘明集[Z]//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304.
[14]滑红彬,刘佳佳.庐山佛教藏书在文化史上的贡献[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5-27,34.
[15]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8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