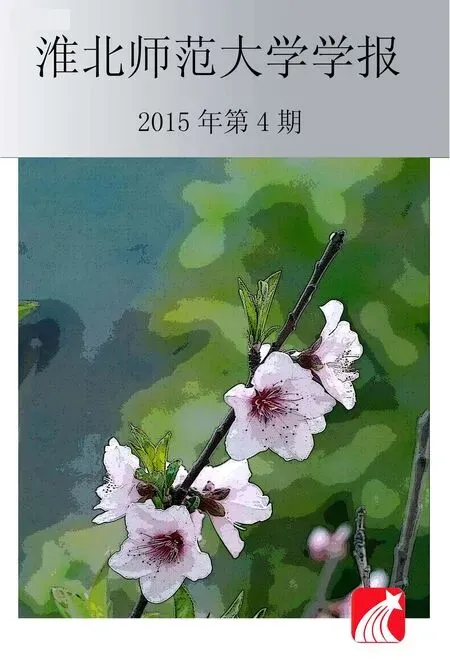顾颉刚爱国思想形成之探究
彭龙富
(中共娄底市委党校 马列教研室,湖南 娄底 417000)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逾两千万言的文稿,是给后人留下的一份丰厚而珍贵的学术遗产。
上世纪20年代初,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引发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古史辨伪运动,受到胡适、傅斯年、蔡元培、郭沫若等学界名流的称赞;他“邃于经学”,矢志不渝地沉浸在经学的命题里,将“破坏”与“建设”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他还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不但摇旗鼓呼、身先士卒,而且联结学人、识拔才俊,学识之宏富,胸襟之广阔,堪称士林的一面旗帜。
作为学界大师的同时,顾颉刚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醉心民众文化,自觉而大胆地将自古以来均以“圣贤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史扩张到包括“民众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或历史研究,体现了一位学者浓郁的民众情结;他致力历史教育,倡导历史教育、通史教育不仅是科学的、全面的历史知识的传授,还应是发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途径,反映了一位学者独特的教育追求;他重视边史问题,三番五次实地考察,不遗余力编撰刊物,四处奔走发表演说,据理力争参与辩论,目的只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彰显了一位学者拳拳的报国之心;他投身社会活动,或组织学术团体,或建立科研机构,或干预时事政治,教授、编辑、出版人、社会活动家等角色一身兼具并多维转换的担当,透出了一位学者“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入世情怀。完全可以说,顾颉刚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目前,学界关于顾颉刚的史学建树已作广泛研究,且成果丰硕,但关于顾颉刚爱国思想的成因关注甚少。本文将顾颉刚定位为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分析、例证分析,对顾颉刚爱国思想的成因作一番探究。
一、传统文化的浸染是顾颉刚爱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
顾颉刚在上小学之前,接受的是传统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家庭和私塾这两个地方,是顾颉刚爱国观念启蒙和萌芽的土壤。
(一)家庭教育的训导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所有的教育中,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和基点。家人的性格、品质、生活态度、社会地位等,家庭的知识架构、经济状况、和睦程度、社会背景等,对孩子的成长、成才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顾颉刚一生勤勉,至真至善,积极进取,经世致用,与他的家庭出身关联密切。顾颉刚的童年,受父亲、祖父和祖母三人影响最大,而三者中,又数祖母为最。
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是秀才而优贡,经过殿试后,做了安徽候补知县。正准备踏上仕宦之途,却遭遇辛亥革命,知时势已变,便退休乡里。迫于生计,又先后到南京、杭州等地谋职,最终告老还乡。关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顾颉刚并无详细说明。从零零散散的记录里可知,顾柏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言行举止基本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准则。顾颉刚能够顺顺畅畅读书求学,本本分分为人处世,必然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而且,从顾柏年允许顾颉刚接触《新民丛报》《国粹学报》等新潮刊物,也可见他是一位相对开明的父亲。
与父亲相比,祖父在顾颉刚心中更有分量。在《祖父的故事》一文中,顾颉刚称祖父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1]32祖父也是一个秀才,是在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且受过丁日昌赏识。平日里,他给顾颉刚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为国雪耻的故事,讲伍子胥忠心劝谏自尽身死的故事,讲范仲淹贫而力学断齑画粥的故事……这类溯源穷委传神尽情的故事,一方面诱发了顾颉刚对历史的喜爱,另一方面强化了顾颉刚对家国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也好,祖父也罢,他们四处游历,见多识广,奋发图强,人尽其才,“这与普遍的惮于奔波而好享受定居生涯的故乡人性格截然不同……虽不必引以为荣,确在族中算得是一特点”。[1]8也就是说,祖辈、父辈的敢作敢为、敢闯敢拼,激发了他的斗志,玉成了他的信念,是他日后胸怀壮志、施展抱负的一股动力。
当然,对顾颉刚影响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在《我的祖母》的回忆中,顾颉刚开篇就袒露心迹:“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1]14顾颉刚8岁丧母,之后跟随祖母十余年。祖母不是一般的妇道人家,而是明事理、通人情、有识见的妇人。她除了照顾顾颉刚的饮食起居,给他以无限的慈爱和庇护外,还严格要求他的学业,同时又极其注意他的品行。祖母盼望孙子由读书而科名,时时告诫孙子读书要好好用功,“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1]24祖母希望孙子做个知难而进、不畏困苦的人,便斩钉截铁地教训,“就是落铁也得去”;[1]24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祖母疼爱孙子,却不以把孙子放在身边为满足,相反她鼓励并支持孙子四海为家,“男孩子是该让他出出远门”。[1]24可想而知,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富有见地的祖母作引路人,顾颉刚是非常幸运的。成年以后,顾颉刚围绕开发民智、振兴民族,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他忧国忧民、劳心劳力,有这样的高风亮节和社会关怀,实在不足为怪。
(二)儒家思想的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家思想更是长时间占据着中国思想领域的的主导地位。作为宣扬儒家学说的重要载体——私塾,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培养启蒙儿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受过私塾教育的人,基本上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
顾颉刚幼时接受的也是私塾教育。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祖父等人的影响下,读了《诗品》《三字经》《千字文》《天文歌诀》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在记诵经典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自然有了初步的感知。进入私塾后,顾颉刚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礼记》等经典,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有了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虽然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严厉而压抑,但顾颉刚是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自小就喜欢读书。在谈到读书时,他自己表示:“我的翻看书籍,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长者的赞许,只觉得书籍的世界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2]13可见,顾颉刚不仅接受了正宗的儒家教育,而且带有自觉性、主动性和探究性。
习读的过程中,“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高尚节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拯救使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华夏民族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象征、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让顾颉刚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激发了他的爱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平常年代,不见其显、藏而不露。一旦遭逢乱世、礼崩乐坏,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深厚而浓重的对国家命运的挂念关怀之情。儒家所提倡的“入世”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促使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把国家整体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勇于担当“平治天下”“济世安民”的重责。
从提抱之时到读完私塾,十余年的时间,顾颉刚深深浸染在传统文化当中。这是他爱国观念得到启蒙和灌输的重要时期。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固然有一定的局限,却是成就一个人忠诚、热爱、报效国家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丰富营养。成年后的顾颉刚勤劳奋发、轻利重义、自强不息、诚信谦和、爱国恤民、胸怀博大,所有品质、性格的形成与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显然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换言之,传统文化的浸染是顾颉刚爱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
二、革新图强的裹挟是顾颉刚爱国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906年,14岁的顾颉刚进入小学阶段。两年后,入苏州公立第一学堂。1913年4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一阶段,顾颉刚的爱国思想处于萌芽状态。虽然心智没有完全成熟,对人事是非还无法作理性而深入的思考。但新旧时代的变迁,各种运动的裹挟,让顾颉刚有了爱国方面的最初的体验和锤炼。
(一)学校环境的影响
学校环境是个人发展的重要依托。一个人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对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顾颉刚14岁进入的是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这是苏州开办的第一所高等小学,也是一所新式学校。从私塾到小学的过渡,“如同踏入了一个新世界”。[2]16在小学,顾颉刚接触到了《时报》《国粹学报》《新民丛报》等革命派书刊。革命派人士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对顾颉刚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在作文时,甚至涉及到“革命立宪辨”一类的敏感话题。顾颉刚还学唱了《中国男儿》等爱国歌曲,歌中唱道:“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2]18从歌词可知,这是悲壮高昂的革命曲、爱国曲,令歌者心潮澎湃,拳头紧握,拿顾颉刚自己的话说便是“真觉得自己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2]18
在中学,顾颉刚吸收了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在他上三年级时,还遇到了同盟会会员的校长袁希洛。袁希洛是个爱国志士,面对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欺压,他忿恨不已,挺身而出。出任校长后,仿照秋瑾在大通学校的做法,把学生训练为革命军队。辛亥革命后,他还号召学生剪除鞭子,参加学团。顾颉刚是积极的响应者,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1912年春,顾颉刚还与叶圣陶、王伯祥、王彦龙等同学,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入党后,顾颉刚任文书干事,激烈地宣传社会主义。为了公务,他常常废寝忘食,深夜不眠,遭到家庭的斥责、朋友的讥笑,也全然不顾。顾颉刚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直可以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2]25此时,顾颉刚的爱国思想已在师长、同学的陶冶下有了长足发展。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学校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顾颉刚从1893年出生到1913年中学毕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年。血气方刚的顾颉刚写过一篇《恨不能》,里面提到“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等。[2]16关于为什么有第一个人生志向,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有这样的解释:“那是因为他生于离乱之际,两岁时便逢甲午之战,六岁时便逢戊戌变法失败,八岁时便逢八国联军攻破京、津,十二岁又逢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他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见到日俄两国军官的照片,知道他们竟然在我国境内如此耀武扬威,在战争中杀了无数中国无辜百姓,为此而气愤至极,总想长大后为救国做一番事业。”[2]16顾潮女士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顾颉刚萌生这样的志向,同鲁迅弃医从文、济世救国可谓如出一辙。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国男儿,在巨大的国耻、深重的国难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反,意气更高涨,感情更浓烈,也更容易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抵抗外侮的坚决性。
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并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70余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历史巨变,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顾颉刚也不例外,他说:“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2]24当时的顾颉刚已经对国学有了一定的爱好,但受革命潮流的涌荡,还是想投身其中,并作诗言志:“嗟尔经与史,存之有空椟;宁乖俗士心,勿污精灵目。”[2]p24可见顾颉刚当时革命热情之高,以至于连一向浸淫的古书也可以束之高阁、冷落一旁。
众所周知,近代的中国中西文化大交汇,国内的变乱和外来的祸患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巨痛。革新图强是整个民族的呼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爱国具体体现为忧国、卫国和强国。顾颉刚受过多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又见证和体验了民族的阵痛,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振兴,也许一时还未上升到责任感、使命感的高度,但他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爱已经深深融入血液,渗到骨髓,一旦时代呼唤、社会需求时,他必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相结合,将自己的事业投进时代的洪流之中。
三、空前深重的危机是顾颉刚爱国思想形成的直接诱因
1913年4月底,顾颉刚到京,正式开始了他的北大生活。之后,求学,结婚,谋业,治学,成名等,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期间,顾颉刚基本上是“出世”的。谈到个中缘由时,顾潮女士有这样的文字:“父亲说自己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深知世界形势的复杂和一己知识的短浅,觉得自己这一生只配研究学问,而毫无‘用世’之心,就是对于政治社会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但总以为自有人能担当责任,不必自己不适合的才能投入其中,弄得于世无益,于己有害。”[2]145顾潮的说法很有可信度。我们知道,从古至今,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阶级,在经济上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甚至可以说,除了谋生手段的特别,知识分子与一般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并无二样。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将他们推向道德的审判台,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加以界定。
然而,随着顾颉刚西北之行的考察,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随着对“亡国”与“灭种”的切身感受,顾颉刚受爱国心的驱使,毅然走上了书生救国的道路,竭尽全力地去呐喊,去行动。
1931年春,顾颉刚与燕京大学同仁一起到河南、河北等地考察,惨淡的民生状况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和痛苦,“从此以后,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元,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做些事了。”[2]146可见,这次考察直接动摇了顾颉刚“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宗旨,让他走出书斋,将研究学问的精神化作报效国家的热忱。后来的事实证明,顾颉刚不是做了些事,而是做了很多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民间去,到西北去,利用自己的名望与威信,极力宣扬国家的需求,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开展了大量与抗日救亡密切相连的活动,实乃忧国之切,以救国自任。完全可以说,西北等地的考察之后,顾颉刚“不再满足于从书本上获得知识,而是深切地感到,实地考察对解决学术问题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西北考察活动,他自觉意识到史学家的社会职责,这使他在处理学术研究和社会责任、求真和致用的关系方面,做到了高度的统一”。[3]106
“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认识到解决民族危机的一个有效办法便是加强民族史的研究。于是,他又抽出时间、精力作民族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满腔热情,勇往直前。他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注和成就,既包括纯学术的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考释,也包括深入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的论说和实践,这都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1938年,顾颉刚在《边疆》发刊词中这样写道:“要使一般人对自己的边疆得到些知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4]27这段话全面地阐明了他的研究动机,也让我们见证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之际的果断担当。
抗战时期,顾颉刚更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在“致世”中,顾颉刚的一个重要作为是组织人力编写各种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顾颉刚认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必须唤起民众一齐上阵。但书生气十足的刊物不受民众欢迎,以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笔触编写的通俗读物,才能收到灌输抗建精神、鼓舞民众斗志、传播时事新闻、开阔民众视野的效果。“新的历史环境也使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带有更突出的为民众服务的特点。他自五四以来所有的民众情绪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5]4历史也有力证明,顾颉刚的通俗读物出版活动,对传播历史知识、发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抵御外辱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开展民众教育,注重边史研究,出版通俗刊物,发表爱国演说,参与社会团体……一系列的举动透出顾颉刚炽热的爱国情感,体现了他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的殷切期盼。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顾颉刚的爱国思想在说与做的高度统一中逐渐形成。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积淀在顾颉刚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日益膨胀并最终如火山式迸发。
应该说,顾颉刚爱国思想的形成与深化,是民族危机煎迫下酝酿陶铸的结晶。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大历史背景下作的必然抉择。
综上所说,顾颉刚的爱国思想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诞生于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救亡图存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主题。尽管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顾颉刚有过彷徨,饱受煎熬,但他热爱学术,又能将学术与爱国结合起来,“在动乱中经受了考验,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立身学术、忠心报国的近代知识分子范本”。[6]46顾颉刚的学术径路,对当今知识分子也不无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1]顾颉刚.顾颉刚自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周励恒.西北民族考察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J].民族研究,2013(6):103—112.
[4]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在云南[J].史学史研究,1994(2):27—28.
[5]刘俐娜.顾颉刚学术研究中的民众情结[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5.
[6]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