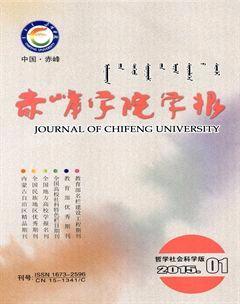巴尔扎克在中国
曹文刚
摘 要:中国翻译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显现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特点,先是译介他的短篇,后来译介中短篇,数量由少到多,在选择作品时有实用取向,新时期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部作品的翻译,注重译本序文的写作是中国译者的一大特色。中国批评界对巴尔扎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缩短了他和中国读者的距离,由于左倾因素的干扰,加之一些批评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受到了误解和曲解,中国读者与他无法靠得更近。新时期,中国批评界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观照的格局,排除了非文学因素,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使中国接受者得以重新走近巴尔扎克。
关键词:巴尔扎克;译介;中国批评家;中国读者;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49-02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马克思十分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1];恩格斯称赞他作品中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2]。他创作的《人间喜剧》共90多部小说,写了2000多个人物,有法国社会“百科全书”之称,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大厦,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愈显巍峨壮观。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说:“巴尔扎克是一座富矿,是说不尽的,他提供了对文学具有永恒意义的经验。”[3]
一、翻译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
1915年,林纾和陈家麟合作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哀吹录》短篇集,收录了四个短篇小说。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廋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收入了巴尔扎克另一个短篇小说《男儿死耳》。这些译介虽然不能使国人了解巴尔扎克的全貌,但对他的东渐具有开拓意义。1919年到1930年这段期间,巴尔扎克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的很少。三十年代巴氏作品的译介数量有所增加,但远逊于同期译介到中国的其他法国作家,如仲马父子、雨果、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接受者的审美取向、作品的风格特点、译介者的才力等。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蒋怀青译),收入巴尔扎克8个短篇小说。1945年重庆出版的《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受录20篇小说。这两部译文集都附有巴尔扎克的介绍,前者附有作家王任叔写的《序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一文,后者附有译者自己写的序。王任叔在文章中对巴尔扎克的生平和创作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作了总体分析,颇有见解,是对巴尔扎克作品作总体评价最早最有分量的文字:
《人间喜剧》……从横面看,是19世纪法国全土的Panorama。从纵面看,是那时期的政治经济史,极详细的风俗史、思潮史。论年代,则为自大革命直至二月革命前——這50余年之活历史。大革命后王党的暴动,帝政时代秘密警察的活跃,波尔滂王家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权力渐渐增高、集纳主义的跋扈,以及其他酿成二月革命的一切事象,都在此描画殆尽。从阶级的见地看,则勃兴布尔乔亚之旺盛的奋斗力,与贵族阶级传统的没落,以及普罗利太利亚(即“无产阶级”一词的法文音译)未来任务的预言,也都在此有所描写。在有如此纵横累叠的骨骼的《人间喜剧》里,实有二千余人物,散在于巴黎之街,布尔谷尼的山奥,鲁尔之河畔。上至拿破仑,下至乡间乞食女,这些显示一切阶级与身分的人物,或泣或笑,或叫或嗫,熙熙攘攘,尽皆往来于这不可思议的世界中。这就是《人间喜剧》之名得与《神曲》并举的原因[4]。
陈原的序分析了巴尔扎克讽刺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历史价值,他把这些脍炙人口的短篇翻译成中文,是出于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使我吃惊的是,白鲁因、路易十一、希贡、魔鬼的化身、沙瓦西(按,皆巴尔扎克讽刺小说中的人物)这些西方的魔影,竟穿了中国的民族服装时常在这里的大街显灵。正所谓,地无分东西,时不论古今,凡是有人的地方,总会有假道学家、伪善者、吝啬鬼以及杀人而致肥、谄媚以兴家的人在。巴尔扎克的‘趣闻轶事,可不就是我们蝼蚁众生之已积压在心头的恨与笑爆鸣么!”[5]
这种选择巴尔扎克的实用取向在中国译者中是很有代表性的。1936年穆木天翻译了《欧贞尼·葛郎代》(今译《欧也妮·葛朗台》),标志着中国译介者开始挺近巴尔扎克这座富矿的中心,从而把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译介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穆木天外,还有傅雷、高名凯、陈占元、黎烈文等,他们把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的一些重要中长篇作品都先后翻译成中文。这些译作在中国的流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都曾试图将《人间喜剧》整体译介到中国来,都曾付出过艰苦的努力,但终因力不从心而未能如愿。他们的遗愿在新时期得以实现。70年代启动了《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程,这个近代以来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由法国文学学者夏玫主持。《巴尔扎克全集》和十卷《巴尔扎克选集》,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巴尔扎克原著,富有远见卓识的主持人组织了编者、译者在每部译文篇首写出序文,使中国的巴尔扎克介绍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些序才气盎然、情文并茂,对一个未涉足巴尔扎克这座富矿的人是一份诱人的“导游”;对读巴尔扎克小说的读者来说是很好的“导读”,对巴尔扎克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国新时期的巴尔扎克学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批评界对巴尔扎克的接受
巴尔扎克一进入中国批评家的视野,就给中国人留下了相当稳固的映象,即他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是资产阶级意识的深刻的表现者,是伟大现实主义艺术家。此后中国研究者对巴尔扎克所作的一切思想和艺术的思索,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基本观点。中国学者所接受的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如世界和社会那样丰富广博、那样复杂矛盾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个映象的形成,除了归因于中国学者对巴氏作品的深刻透视,也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尔扎克的深刻论断。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深刻阐发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家能以如此的深刻性和准确性对巴尔扎克作如此深刻的剖析,如此独到的透视,如此科学的阐发。这些科学论断被视为理解巴尔扎克世界的一把钥匙,中国的研究者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索巴尔扎克的思想和艺术的,中国的巴尔扎克学也正是沿着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不计其数的研究巴尔扎克的文章,归根到底就是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阐发的阐发。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论断,曾引起了中国批评家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特色的讨论。瞿秋白首次论述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的一致性,并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应该在巴尔扎克等所开创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这种诠释得到了批评界的肯定。在这之后,随着巴氏作品越来越广泛的传播,随着对现实主义的反复讨论,巴尔扎克世界观与创作问题又被批评界屡屡提及,许多人从不同角度作出了不同的阐释。60年代初,批评界出现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讨论,一些批评家提出了理解巴尔扎克的途径和方法。比如陈伯海从巴尔扎克具体作品的分析入手,从其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双重态度来观照其世界观的矛盾性又从塑造人物的得失来考察其世界观与创作的一致性[7]。李健吾则从巴尔扎克的论文、书信、和言论来探究他的信仰。这些研究客观性较强,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巴尔扎克,因而缩短他和中国读者的距离。
但是,由于复杂政治背景下左倾因素的干扰,加之一些批评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受到了误解和曲解,导致了对巴尔扎克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判,称巴氏的世界观和作品是反动的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未能理解巴尔扎克,也无法接近他的复杂世界。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上半期盛行于中国批判界的这股风气,也使一般读者无法与这个西方巨人靠得更近。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勤于思考和挖掘的研究者给出现危机的中国巴尔扎克研究带来复苏的希望,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又将离中国读者很远的巴尔扎克拉近了,使中国接受者得以重新走近这座富矿。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胜利”的特点以及有关他的创作和世界观关系的讨论,一直是中国批评家的热门话题,新时期批评家又围绕它撰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多从巴尔扎克实际出发,排除非文学因素,因而也多有创见。他们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观照的格局,显示了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0.
〔2〕恩格斯.致劳·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7.
〔3〕柳鸣九.他提供了对文学具有永恒意义的艺术经验[N].文艺报,1989-7-1.
〔4〕王任叔.序巴尔扎克短篇小说.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陈原.《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第一卷译序.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5.
〔6〕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2-463.
〔7〕陈伯海.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J].文学评论,1960(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