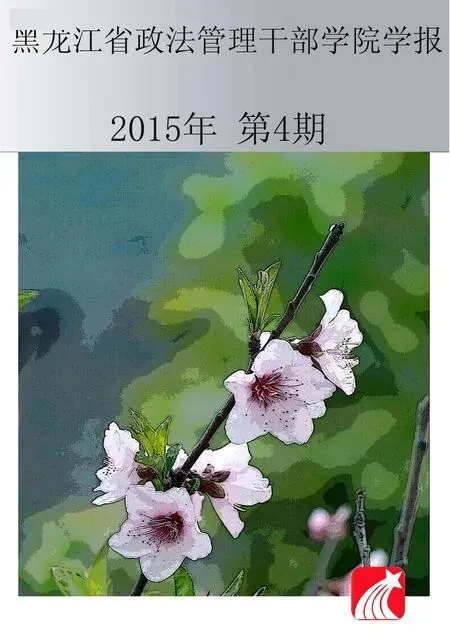论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袁祥境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论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袁祥境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要:恢复性司法理念已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广泛认可,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协商程序充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该理念在我国大陆地区表现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制度程序。两岸历史文化同宗同源,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的借鉴,以期完善我国大陆地区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刑事协商制度;刑事和解;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志码:志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7966(2015)04-0106-04
收稿日期:2015-04-11
作者简介:袁祥境(1994-),男,新疆阿克苏人,2014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前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之斗争。这是关于“犯罪”概念的经典表述。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破坏了社会关系的稳定,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刑事法律因而应受处罚。国家作为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民生命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根据社会契约的观点,人民让渡部分权利给予国家,国家据此享有权力而制定刑罚来惩戒犯罪。强大的国家机器启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罪犯得到审判,刑罚得以实施,正义得到伸张,犯罪人承担了其因为犯罪行为而应该承担的责任。随着时代变迁,在国家确立了依法治国理念的今天,“犯罪”这一概念有了多元化发展,其实质方面不再以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为主要内容,而把对国家、社会、公民利益的侵害作为犯罪概念的实质方面[1]。被害人作为遭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与刑诉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被害人不仅希望能得到经济赔偿或补偿,更要求法律谴责、惩罚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判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2]。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不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还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因此任何忽视、忽略被害人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也在不断显现。刑事司法领域体现为:犯罪率快速增长、刑事案件数量激增与法律资源极其有限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为实现二者间的平衡,我们需要设计一种制度既可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能够及时消弭犯罪带来的损害,实现程序分流。即对部分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案件或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追诉人有犯罪行为的案件都不再进入正式审判程序,进而终止诉讼,或是对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采取快速、简便的简易程序[3]。如日本的微罪处分制度、英国警察警告制度、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等,这些制度都体现了“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的理念。在这些制度中,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协商制度极具特色,其不仅体现了程序分流的思想,更展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的确立
(一)刑事协商程序的具体内容
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其中增加了10个条文从而确立了刑事协商程序,一经实施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台湾地区的刑事协商程序,是指检察官提起公诉(包括声请简易判决处刑)的非重罪案件,当事人在经法院同意后,开启协商程序,在审判外进行求刑和相关事项的协商,于当事人达成合意且被告认罪之前提下,检察官向法院声请依协商内容而为协商判决之程序[4]。
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2第(一)项的规定,刑事协商程序的启动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案件范围仅限于“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的其他非重罪案件。重罪案件或属高等法院管辖的内乱、外患及妨害国交之一审案件不在刑事协商案件范围内。第二,适用刑事协商程序,必须经管辖法院同意。这项规定给予了法院对刑事协商程序的司法控制权,也起到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作用。检察官欲启动协商程序还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但被害人的意见并不能左右协商程序的启动,其意见只是征求、参考性质的,检察官才是申请开始协商程序的唯一主体。第三,启动协商程序的时机仅限于审判阶段,“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或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后,在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或者简易判决处刑前,才可以进行协商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障法院审判的公正客观,也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要求。
台湾地区刑诉法对协商的内容也进行了规定:(1)被告愿意接受科刑的范围或愿意接受缓刑的宣告。即检察官与被告人进行协商时,罪名是不纳入协商范围的,双方仅就量刑轻重进行讨论。(2)被告向被害人道歉。要求被告道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精神层次的关注,目的在于治疗被害人所遭受到的精神创伤,从而抚慰被害人因犯罪而受伤的心灵。(3)被告支付相当数额的赔偿金。赔偿金是对被害人物质补偿的直接表现,在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很难恢复原状,使用金钱进行弥补是通常做法。(4)被告向公库或指定的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支付一定的金额。恢复性司法理念认为,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侵犯,更是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因此才有矫正的责任。司法意味着犯罪人、被害人、犯罪人周边的人、社区共同寻求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修复、和解以及重新确信[5]。对于上述四项内容的协商,检察官应在法官同意进行协商程序后的三十日内与被告达成协议。其中,检察官就第(3)、第(4)事项与被告进行协商时,还应得到被害人的同意方可实行。
(二)刑事协商程序的精神内涵
1.恢复性司法理念
在刑事司法领域,恢复性司法是与报复性司法相对应的一种理念,其着眼点在于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的恢复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具体而言,恢复性司法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来实现恢复性结果的司法方案。其中,恢复性过程是指被害人、犯罪人和其他受犯罪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解决犯罪产生的问题的过程。恢复性结果则是指进行恢复性过程后的结果,通常表现为达成的协议,如赔偿、社区服务和其他用来实现社会关系修复的方案或反应[6]。以恢复性司法理念看待犯罪,则犯罪不仅是违反刑法的行为,而且它还给被害人、被害人周边的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造成伤害和损失的行为。修复性司法通过组织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间的沟通协商,反映和传达出受犯罪影响的主体的需求,主张采取一种纠纷解决的方法来取代传统的刑罚手段。
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内容的第(2)项、第(4)项分别为:“被告向被害人道歉”和“被告向公库或指定的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支付一定的金额”。被告人向被害人道歉,关注点在于对被害人的精神慰藉,改变被害人被边缘化的趋势,增加被害人的安全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被告向被害人发自内心的道歉,对于恢复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有积极作用。被告向公库、公益组织、自治团体支付一定金钱,从恢复性司法视角出发,公库、自治团体可以看作是社区的代表,而社区在恢复性司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双方交流和制定恢复协议的“桥梁”性参与人,也是实际执行恢复协议的监督人。和谐良性的社区更有利于被告人的回归,社区的运转需要各项资源的支撑,被告向社区支付一定的金额,既可以用以维护社区的运转,又能够起到担保被告遵守恢复性司法协议的保证作用。这两项规定都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要求。
2.刑事诉讼效益理念
效益是经济学领域的词汇,简单讲就是效果和利益。该概念最初出现于微观经济学中,用来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成本与收入之比例。将其作用于法学领域,司法的效益通常表现为“好”与“快”:“好”是指司法结果令人满意,即当事人满意,与当事人相关的周边社会关系也处于满意状态;“快”要求的是诉讼效率,在投入一定的司法资源的基础上力争处理尽可能多的案件,单位案件的处理时间在保障公正的基础上应尽量压缩。具体至刑事诉讼,我们应该关注刑事诉讼效益的两个方面,第一是结果效益方面,刑事诉讼的进行必定会产生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处理结果是否被当事人认可、信赖,是否被社会公众支持、理解以及其程度是考量结果效益的标准。如果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被各方及群众完全认同,司法权威、司法文明能够得到完全彰显,该案就体现出了最好的结果效益。第二是经济效益方面,刑诉效益理念要求刑事诉讼成本的最小化,这些成本既包括个人为进行诉讼而支出的各项费用,又包括国家为进行刑事诉讼而消耗的各种资源。这些都是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而付出的设施、人力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消耗。
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协商程序只能依检察官的声请,具体为检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诉后一审言词论终结前,或检察官申请简易判决处刑以后法院作出简易判决处刑前。这体现了程序分流的思想,分流机制将大部分刑事犯罪分流到普通程序之外,使用更合适的处理办法,从而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有效地矫正犯罪人并修复社会关系。经过分流后,协商程序处理部分非重罪案件,蕴含有与美国控辩交易制度相类似的内涵,从个案角度看,它不需要经历繁杂的普通程序,且协商结果来自控辩双方,增加了被告对审判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避免了上诉等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益。从司法整体角度看,它减轻了法官、检察官的工作压力,使得他们可以集中更多精力在重大疑难案件上,从而提升司法运行的整体效益。
三、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体现
恢复性司法已成为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部分,2002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该决议为各国恢复性司法实践设立了基本的参考标准,帮助各国实施相关恢复性司法。如同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有恢复性司法制度与程序。恢复性司法与我国传统“无讼”价值观念、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社区矫正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1)恢复性正义对传统“无讼”价值观念之修正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的是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犷。”无讼,即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通过包容忍让以协商解决冲突与摩擦,而非诉诸官府、通过法律来强制解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儒家“无讼”思想影响着汉朝以后的漫长封建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根基。
我国古代法虽以刑为主,但注重礼法结合,而非单纯适用刑罚。《周礼》所期望的是“刑期无刑,辟以止辟”的社会状态,法家主张“以刑去刑”,实质上是借助刑的手段去实现和谐的无讼世界[7]。统治者为巩固统治不仅要依靠严刑峻法,更要重德崇礼,主张息诉、止讼。诉讼是法治社会最常见的法律行为,但古代无讼思想将大量矛盾排除在讼诉的领域以外,这片广泛的领域就纳入了人治的范畴,会带来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的风险,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且无讼价值观隐含有法律虚无倾向,易使人们产生轻法贱讼的心理。
现代恢复性司法也追求通过协商、和解、调解来解决矛盾与冲突,从而定纷止争。然而与传统“无讼”价值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恢复性司法并不排斥诉讼程序。以美国“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为例,恢复性司法项目案件来源,主要是由法官、检察官、警察、缓刑官从各自案件中移送出去的。这些案件或多或少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亦是如此,协商程序必须经过法院的同意,这是在刑诉程序进行中开展的协商,不可能回避诉讼。但中国古人却视诉讼为“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肖”的卑劣行为。与“无讼”的传统观念相比,恢复性司法实践更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与精神。
(2)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修复性司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主要表现为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受我国传统“无讼”思想与恢复性正义思想的影响,加之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我国需要适合自己国情的恢复性司法程序以满足实践要求。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曾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277条规定了和解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①《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第278条是对和解协议书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而第279条是对和解不起诉从宽处罚的规定。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目标是一致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结合是传统刑事司法所强调的理念。刑事和解也秉持这些价值基础,但追求对传统刑事司法目标的发展。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忽略了被害人、社区的权益,不能满足被害人的精神层次的需求,罪犯改造效果不理想等。刑事和解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力求完善传统刑事司法目标的实践效果,进而追求刑事案件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价值目标。我国大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与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一样,都要求被告对被害人赔礼道歉,被告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两种程序都追求这种“修复关系”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不是对传统刑事司法价值的背离,而是进一步的升华。
(3)社区矫正制度中体现的修复性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8]。根据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力求达到以下效果:“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这些效果与修复性司法追求的“帮助犯罪人重返社会”、“促使犯罪人承担责任”的目标高度契合。
(4)恶性事件中“政府补偿”体现的修复性思想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暴力事件,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2009年7月10日,民政部门为每名无辜死难者发放20万元特殊抚恤金和1万元丧葬补助金。这类特殊的政府补偿虽没着眼于帮助犯罪人重返社会,促使犯罪人承担其因为犯罪而应该承担起的责任,但强调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满足了被害人的要求。恶性事件中的“政府补偿”说明,如若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从犯罪人的角度对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则应该及时调整思路,至少应当修复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创伤。犯罪人固然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主体,但在犯罪人不能到案或犯罪人无力进行社会关系修复活动时,国家理应出面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毕竟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与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这种政府补偿机制虽然没有犯罪人和社区的参与,但国家作为社会方方面面力量的集合体,其对被害人的补偿体现了修复性正义的要求。
四、刑事协商程序对大陆恢复性司法的借鉴意义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与大陆文化同宗、历史同源,通过对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的研究学习,我国大陆可以借鉴其宝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完善发展我们自己的恢复性司法措施。
(一)完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激发了学界对刑事和解程序这一热点问题更加热烈地讨论,许多学者提出了对完善刑事和解程序的思考,他们的观点集中于:应扩大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建议将重罪案件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延伸刑事和解适用阶段,台湾刑事协商制度明确为在审判中协商的制度,即在审判阶段才能启动,刑事和解制度虽未规定具体的启动时间,但大多学者都建议刑事和解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应增加刑事和解参与主体,刑事和解程序的主体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公检法三机关是和解协议的主持人,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建议将一些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民间团体也纳入主持人的范围;大多数学者还强调在和解程序中要注意保障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除以上完善建议外,笔者认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要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刑事和解程序具有自己的特点,适用该程序应只要求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可,对于不影响定罪和开展和解的部分事实细节,不必苛求一清二楚。但对于影响案件定性的事实和证据必须查清,需知“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更要防止公安司法机关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违法处理事实不清的案件。
(二)强化社区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
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犯罪人、社区积极参与、解决犯罪产生的问题。社区是实现恢复性司法的重要组织,是开展恢复性司法的载体平台,同时也是对恢复性司法过程进行监督的主体。台湾地区刑事协商制度规定,被告要向公库、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等广义的社区代表支付一定的费用,表明社区确实参与在协商程序中,符合恢复性司法的要求。
我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一样要求凸显社区的作用。社区矫正的实施成效与社区的发育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区矫正是社会化的刑罚模式,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仅仅有发达的经济作支撑是不够的,社区矫正的施行还要求该社区是一个整体和谐、邻里和睦、交流频繁的集体,该社区成员构成一个小小的“熟人”社会。而当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人们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加速,人际关系冷漠,甚至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不熟悉,这种状态的社区是不可能完成对犯罪人的矫正任务的。恢复性司法本身就强调多元化参与,而多元主体间良好畅通的沟通是实现恢复性的基础。为实现社区矫正制度的设计初衷,应强化社区建设,突出精神文明层次的社区建设,而不是仅关注物质层面上的。
从狭义上理解社区,社区仅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9]。而着眼于恢复性司法,笔者认为,我们理应关注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区的组织或团体。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中规定,被告要向公库、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支付一定金钱,这些公库、公益团体、自治组织就是社区的代表,甚至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社区。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等极端恶性犯罪,我国大陆地区应建立赔偿金公库或抚恤基金,当发生恶性事件后由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公库资金来源可多样化,包括对犯罪人的罚金、政府补助、社会捐助等。
(三)坚持程序法定原则
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之所以引来诸多争议,主要是因为其难以回答“如何保障刑事诉讼追求法治程序之目的”、“如何处理刑事诉讼发现实体真实之目的”的问题[10]。我国恢复性司法实践起步较晚,劣势是实践基础薄弱,但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借鉴已有经验,避免走弯路。不论是刑事和解、社区矫正还是其他的恢复性司法制度、措施,都不能脱离刑事法律的轨道,不能突破法定程序,以行恢复性司法之名,做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之实。恢复性司法注重沟通,关注被害人的感受,但绝不意味着一味迁就被害人,实际司法过程中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高铭暄刑法思想述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9.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78.
[3]宋英辉.刑事和解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1.
[4]林俊益.审判中之协商程序[J].月旦法学教室,2004,(20).
[5]Marry Ellen Reimund,Is Restorative Justice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Constitution?3 Appalachian L.M.1,4(2004).
[6]宋英辉.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J].现代法学,2004,(6).
[7]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7.
[8]社区矫正[EB/OL].百度百科,(2014-06-30)[2015-02-08]. http://baike.baidu.com.
[9]姜振华,胡鸿保.社区概念发展的历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7).
[10]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9.
[责任编辑:王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