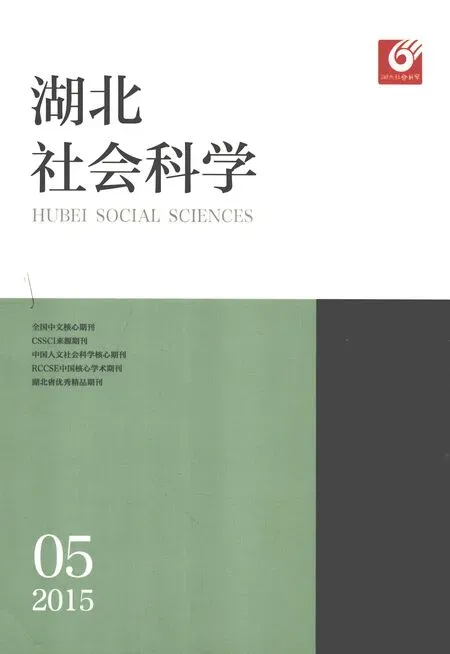对外传播中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建构研究——以《中国日报》2012年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日报》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了较为全面、丰富的中国农民工形象,尤其采取特定的叙事策略着重突出其“幸福”形象,以积极回应国际舆论、服务对外宣传目的。本质上《中国日报》的农民工报道是对国内不同属性媒体报道的贯通与综合,农民工仍然是沉默的被代言群体、并作为新闻背景存在。后续传播中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切实提升传播效果。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5)05-0187-04
作者简介:刘旻(1979—),女,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博士。路淼(1990—),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正在中国形成,并持续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外媒的报道采取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或从经济视角叙述中国廉价劳动力拯救世界经济,或从人权视角指责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缺乏人权保障。这些报道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农民工的认知与想象。在该议题的话语竞争中,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农民工形象,能否起到舆论引领的作用成为本研究关注的议题。
一、文献与理论探讨
(一)身份建构与叙事理论。
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事实。媒体是协助社会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工具。叙事是新闻业务的核心,根据后现代叙事理论,叙事是制造身份和意识形态主体的方法之一。人们修改故事,使其适合自己的“身份”,反过来,他们剪裁“现实”,使其适合自己的故事。在叙事研究中,经典叙事理论将叙事分为两个部分——“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前者指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指该故事被如何讲述。 [1](p47)新闻学引入该理论后认为,新闻报道不仅是真实事件的呈现,更是“故事的述说”。媒体通过叙事“讲述”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世界。为了使叙事更加简捷高效,媒体倾向于采取模式化的表达方式。这是媒体塑造群体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特定群体的形象建构。
特定群体的媒介形象是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议题。农民工媒介形象塑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当前研究多以国内传播中的农民工报道为主,针对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农民工形象建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农民工媒介形象始终随着政策话语的变化不断变动。 [2](p175)20世纪80年代,他们被塑造成被城市拒之门外的“盲流”;90年代媒介以“打工仔”、“打工妹”指代他们,并将其建构为居于城市边缘的越轨群体;进入21世纪,农民工群体摆脱了污名化的桎梏,但媒介又以高度类型化的叙事将其建构成一个权益受损的“弱势群体”。 [3](p6)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随着社会学研究转向,开始涉及这一群体的公民身份定位等问题。
此外,学界开始零星涉及国外媒体上的中国农民工形象建构。徐保华发现国外媒体对中国农民工的报道寄托了西方中心话语的想象, [4](p64)不是将其塑造成拯救世界经济的英雄,就是指责农民工缺乏人权保障,进而为宣扬西方神话价值体系服务。这使得我国对外传播中农民工形象塑造的研究显得更为紧迫。
一、研究问题与方法
(一)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研究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建构,用以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媒体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向世界报道农民工?它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农民工形象?2.在农民工议题上,中国对外传播与国内新闻报道是否有差别?3.在国际舆论较量中,面对外媒在农民工议题上的指责,中国对外传播是否做到了及时反应、有力回击?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改进对外传播、提升我国传媒的国际影响力。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日报》(China Daily)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日报》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份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并被国外主流媒体转载最多的报纸,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2010年,《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中国工人力量的崛起》。自此,中国工人群体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报道中。2012年,中国召开“十八大”,对于诸多涉及农民工政策的调整国际社会相当关注和期待,例如,26名农民工党员进入十八大代表行列、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出现在中共全国党代会上。 [5]并且,2012年中国发生了多起与农民工相关的典型事件,如毕节农村留守儿童垃圾箱取暖死亡事件等。这都使得2012年的相关报道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日报》2012年全年有关农民工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的分析单位为有关农民工的单篇新闻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新闻照片。判断农民工新闻的标准是,首先新闻报道中有migrant worker(s),或者存在一些具体描述可以判断出指代农民工;其次,新闻的主题应该是围绕着“农民工”的,而非其他人群。
(三)编码。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编码变量分别是:
1.对农民工的叙事类型。从一定程度看,有关某一特定群体的新闻报道就是在讲故事,讲故事就会有一定的叙述类型,并显示出媒介的建构偏好。本研究的叙事类型主要包括四种:赋权叙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政策、制度或社会行动,把各种权利、帮助赋予农民工的报道;身份争议叙事——包含所有议题指向农民工究竟退回乡村或融入城市的报道;苦难叙事——讲述农民工个体的不幸遭遇,包括天灾人祸、工伤事故、维权困境、精神空虚等;经济符号叙事——从经济角度探讨农民工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价值;以及无法归类的其他类型。
2.报道主角。指报道所涉及的主要新闻人物或组织,它体现了报道的视角和出发点,主要包括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普通市民及其他。
3.消息来源。指新闻信息的提供者,部分报道在文中明确交代新闻来源,如“记者从某政府部门获悉”,而未明确标明新闻来源的报道也可从新闻叙述中推知其消息来源。根据研究者阅读的前期研究文献和相关新闻报道,本研究建构了六个类别:农民工、政府/官员、记者/编辑、社会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以及群众/网友。
两位经过训练的编码员进行编码,抽出含有2012年migrant worker(s)的报道共378篇,符合筛选标准的共有182篇,并对其进行叙事学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丰富但侧重点明显的中国农民工形象。
总体而言,“赋权”叙事是《中国日报》农民工报道的第一大叙事类型(占35%),其次是身份争议叙事(29%)、苦难叙事(20%)、经济符号叙事(12%)。另有8篇无法归入以上四种类型,列入其它。
这些叙事类型建构了农民工形象的不同侧面。赋权叙事塑造了一个沐浴在各方关爱中的“幸福群体”;身份争议叙事中农民工成了回不去、更融不入的“无根群体”;苦难叙事中农民工回归了传统的“悲情群体”形象;而在经济符号叙事中,鲜活的农民工个体或群体形象隐没,被整体异化为抽象的劳动力要素。
显然单个叙事类型并无新意,在国内不同属性的媒体各有侧重,而《中国日报》的农民工报道正是对国内不同属性媒体报道的贯通与综合,涵盖了这一群体大部分影像侧面,塑造了一个较为真实、丰富的农民工形象——即作为经济建设主力军的农民工,其身份归属问题及面临的权利侵害已经引起各方关注,国家与社会正采取措施给予其帮助和改善。总体而言,他们是一个沐浴关爱的“幸福”群体。
(二)回应国际舆论基础上的对外宣传。
尽管贯通了四种叙事类型,但《中国日报》并未平均用力,而是采取了特殊的叙事策略突出农民工形象的某一个侧面,在这个过程中回应国际舆论、实现对外宣传。
首先,浓墨重彩突出赋权叙事。除了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消息展示各种关爱措施外,“两会期间”《中国日报》连续发表7篇通讯报道农民工人大代表,并大量运用叙事与修辞策略。具体包括:其一,今昔对比——标题大量使用数量词more及高频句式from…to…,二者分别出现了3次、2次,以展示其选举权、被选举权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正面回应国际舆论中的相关人权指责;其二,直接引用农民工的感恩话语;其三,挑选欢乐、喜庆的新闻照片,如拿到工资后开怀大笑的民工;其四,多用隐喻,如以“情同父子”(Father and sons)指代农民工与城市民警的关系,以此隐喻其对国家体制的认同。
其次,通过话语竞争呈现“身份争议”。身份争议叙事正面回应了农民工的身份归属问题,但与国内新锐媒体为农民工“大声疾呼”不同,《中国日报》并未体现出明显的观点倾向,主张“融入”、“回去”或持“中立”态度的报道各占三分之一。在制度走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为规避风险,《中国日报》选择并呈各方观点、客观反映在户籍议题上激烈的话语博弈。
最后,淡化处理其他叙事类型。苦难叙事中的新闻时效性较差,一般是被动跟进已被炒成热点的新闻,同时在数量与体裁选择上尽量弱化处理,尤其善于引用政府消息来源将事件定性为“意外工伤”。
因此,赋权叙事在与其它叙事类型的竞争中胜出,农民工形象的一个侧面——沐浴关爱的“幸福群体”得到强调与放大,不仅回应了国际舆论,更通过明示或暗示了农民工对政府的感激,建构了“官民一家亲”的媒介镜像,进而实现了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宣传。
(三)农民工:不是主角,是新闻背景。
从报道主角分析的角度分析,总体而言,农民工作为新闻主角的报道只占43%,还不到一半。将报道主角简化为“农民工”和“非农民工”两类,并将其与叙事模式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四种叙事类型中,只有苦难叙事中农民工才是新闻主角,比例超过50%,这印证了“伤痛展览”是农民工获得媒介近用权的捷径。
在其他三种叙事类型中,农民工通常作为新闻背景存在,起到作证与衬托的作用。“赋权”叙事中“非农民工”是主要的新闻主角,其中又以政府为最多,农民工以感激与幸福来衬托政府的工作业绩。而“经济符号”叙事中,中国经济是叙述的主角,农民工的出场只是作为谈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劳动力要素而出现。作为新闻背景的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非常被动。
(四)“被他人言说”的农民工。
从消息来源的角度看,农民工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只占总体报道的23%,即总体上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总是被他人代言。而政府/官员是最主要的代言人,作为消息来源比例达到31%。
将消息来源与叙事类型进行交叉分析发现,苦难叙事中农民工作为消息来源比例最高,达到44%。这是源于伤痛展览无法代替的缘故。而作为最大的代言人,政府/官员消息来源在赋权叙事中比例最高,达到56%,与之相比农民工仅占12%。这再次印证了新闻报道中农民工并没有主动言说的话语权,他们只是被动的、沉默的。
此外,“身份争议”叙事中消息来源涉及最广,分布也较均衡,记者/编辑、农民工、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在25%上下;专家学者、群众及其他所占比例稍低,约为15%。这种平衡是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它使得在农民工身份争议的问题上,各方意见——“融入”、“回去”或持“中立”的报道各占三分之一,保持着一种话语竞争、没有定论的态势,也使《中国日报》保持中立、巧妙规避了政策风险。“经济—劳动力”叙事中农民工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最低,只占9%,主要是让其现身说法讲述招工难问题。因此,农民工在此模式中是典型的“被提及”的背景群体。
四、研究讨论与局限
(一)公民权视野下“幸福”形象说服力不强。
农民工问题是现行户籍制度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从公民权视野来看,其实质是现代公民权问题。美国学者莱恩·特纳认为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前者决定后者,是现代公民权的核心。 [6](p3)
从此角度看,《中国日报》的叙事类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农民工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要素”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身份争议”使其成为体制边缘人,无法享受相应的市民权利与资源,经常处于“苦难”状态。但是社会各界正设法通过“赋权”为其提供福利性的帮助。这是现实中农民工的“故事”。
显然,《中国日报》淡化了“故事”本身的逻辑——即“身份争议”—“苦难”—“赋权”之间的先后关联。并通过突出“赋权”、弱化“苦难”、在“身份争议”中保持中立,重置了不同叙事之间的关联,建构起了一个沐浴在关爱中的幸福群体形象。这固然是服务于对外传播目的的叙事策略,但是这种被建构的“幸福”在外媒的指责面前多少有些不够自信。
在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日报》侧重“赋权”叙事建构“幸福”,但作为支撑的却是边缘性福利、农民工人大代表等个案,即目前的“赋权”停留于资源配置的福利层面,而非关键性的公民身份。因此,被人代言时他们是“幸福的”,而自己言说时仍充满悲情,不同叙事类型间巨大的矛盾张力使“幸福”打上了强烈的宣传意味。
归根结底,农民工要改善自身境遇,需要其公民身份的重塑,这样“承认的障碍”才能被扫除。这也是《中国日报》在今后的国际传播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对后续传播的建议以及本研究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中国日报》的农民工形象建构较为全面、客观,但对于后续传播而言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尤其报道如何更契合国际传播特性值得思考。一方面,《中国日报》的报道大多是对国内热点的跟进,对农民工议题的积极开发度不够;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表达和抗争已引起了外媒的关注,但《中国日报》的关注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故事讲述与消息来源引用等叙事模式与国内媒体区别不大,国外受众更青睐的民间视角、小人物故事还有待加强。
此外本文存在诸多不足,尤其选择了2012年报道进行全样本分析,样本量有限,后续研究可以进行年度跨越更大的历时性分析。此外,如果有条件可进行读者访谈,将内容分析与受众调查结合,也可为改进传播效果提出更有实践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