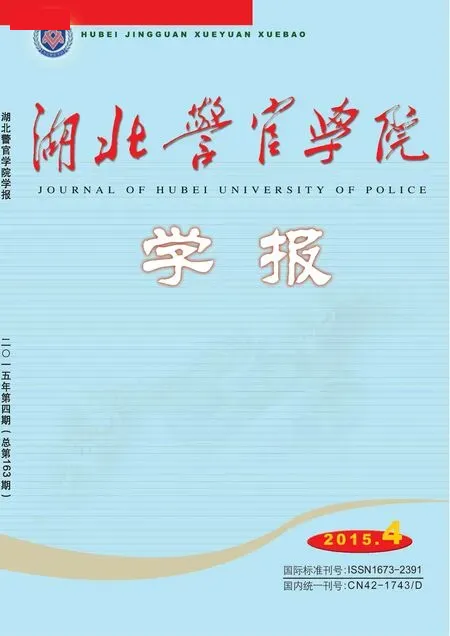法律推理在现代司法中的转向
印大双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法学界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表现为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司法实践中可供适用的大前提常常有多个,而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也可能与大前提并不完全一致,因而需选择最妥当的大前提,并实现大小前提之间的涵摄。抽象的概念无法运用于具体案件之中,需要考量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有效链接,使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个找法和解释的过程本身并不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的范畴,但须在三段论的框架中进行。
法律推理基本框架必须紧紧围绕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展开,除了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并对其进行妥当解释,还需按照命题推理的要求,大小前提间需形成有效的链接,以得出法律裁判结论。无论是大前提还是小前提,都要保持对应与耦合,并将此宗旨贯穿法律推理过程的始终。司法过程的源初形式就是对话或理性交往,每一个法律规范都假定了一种事实状态,使得客观事实成为法律事实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确定用于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过程中,法官需要在事实和法律之间进行交互流转。
一、普遍永恒的正义标准与法律规范的存在根基
法的形成过程,总是基于某种动因和进路,以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制度性配置。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问题是批判法学针对自然法学、规范主义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内的传统自由主义法学关于侧重价值、形式、事实等方面进行质疑的基本问题。然而法律推理的结果反映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又使法律推理变成具有确定性的活动。所以,仅就法的确定性问题而言,批判法学远不如现实主义法学那样能够保持观点的逻辑一贯性。法律推理是建立在法律条文与具体事实的这种既相关又不完全对应的关系基础上。在制定法律时,所考虑的往往是比较典型的情况,不可能给予边缘性的问题足够、全面、周到的安排。况且,语言本身的表现力就是有限的。法律推理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上并不在于将确定的法律适用于相应的事实,而是因为作为法律推理前提的法律和事实本身的相对不确定,[1]法律推理往往具有明显的循环性特征,即法律推理在前提与结论之间、已知与未知之间来回地反复或摆动,在每个环节上呈现多层次、连环性和全息性的特征。法官在查找裁判规范时,可能不是一个规范,而是多个规范的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全法条。不完全法条与其他法条结合,才能适用。对相应法律规范的抽象化和概括化,使法律更具普遍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实现法律的高覆盖率,能够将法律的内在矛盾和漏洞降到合理限度之内,使人们事先遵循并且使法律规范容易实现较高的保真度,在适用上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和确定性。①在法律规范运作中,法律规范要件(T)通常由诸要件特征(M)组成。其公式如下:T=M1+M2+M3→R;S=M1+M2+M3;S→R
法律推理以法律事实为载体、以法律规范为中心,在法理意义上存在同一性,构筑了以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世界。然而大前提的寻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建立科学的方法论,按照一致性、不矛盾性和体系化的要求,为具体的个案寻找到最佳的裁判规则。从结构上看,法律推理由大前提、小前提以及大前提对小前提的涵摄三个部分组成,就逻辑推理而言,这三个命题或步骤是分阶段进行的。在法学方法论上,小前提的确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是一个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确定法律事实的问题。大前提的确定不是简单地对照法条,而要根据法律事实来确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必须以法律事实为起点,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据事实寻找法律规范。在此意义上,大前提的确定也是一个链接事实和规范的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大小前提的链接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反复检验才能完成最佳的链接。法官在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时,需要对小前提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性质。一般性规范适用于个别性事实时只有在逻辑上一致、贯通,才具有正当性,其实质在于寻求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对接。从动态过程来看,现代主流学说倾向于认为法律适用是一个在规范与法律事实间往返来回的思维过程或对向交流的过程,由此来缓和或调和规范的普遍性与个案的特殊性之间的距离。”[2]
法律规范设别首先应当从既有的法律规范中查找,只有在既有的法律规范中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大前提时,才应当进行漏洞填补。大前提必须是与个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具体裁判规则。①在内容极为复杂的法律体系中寻找大前提,必须首先确立找法的基本路径。但找法的过程,是以小前提即案件的事实确定为基础的,大前提的确定本身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和补充,进而确定出规定中所需要的构成要件。在英美法系国家,在寻找大前提的过程中,主要以法官为中心展开,裁判中注重遵循法官解释的经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解释法律时比较注重学者的理论阐释,关注法典解释背后所蕴含的学理。黄茂荣教授认为:“大前提之寻找及其内容与意义之确定系法律规定之萃取(rechtsgewinnung),这属于法律解释与法律补充的活动”。[3]由于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逻辑体系,某一具体个案可能涉及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的适用。因此,大前提必须是与个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具体裁判规则。
法律文本隐含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运用它建立的秩序,自然也就是法律秩序。寻找规范看起来是寻找某个适合于事实的规范,实则涉及全体法律制度。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在裁判的过程中发挥了证成裁判者价值判断结论正当性的作用。作为大前提存在的法律规范,事实上成为了裁判者说服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传统上的司法三段论主要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一般不以价值判断作为法律论证的内容。但事实上,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裁判者在作出价值判断时,要从法律共同体所具有的价值共识出发,采用被司法审判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各种司法技术来作出价值判断。从逻辑学上看,大前提包括大项和中项。在司法三段论中,大项对应法律效果,中项对应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小前提包括中项和小项,小项即事实要件。三段论推理需要通过中项的媒介作用,推导出大项与小项之间因链接所产生的结论,只要大小前提是真实的,结论也必然是真实的。法律哲学认识论认为,法律规范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意义,纯粹抽象地讨论法律规范的内涵是徒劳的。任何法律规范的解释,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中。[4]
二、法律事实的裁剪与整理
法律事实贯穿于整个法制运转过程,法律事实是法的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性概念。在立法过程中,要对事实世界及其规律有一个比较清晰而理性的认识,另外需要考量法律事实的形式以及法律事实的归类。在司法过程中,裁判者始终要为自己的法律主张提供事实基础。③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依据,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联系的中介。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一方面,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等原因,对法律事实的看法、角度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争议的焦点往往是法律事实。另一方面,确定小前提的基础实际上就是确定法律事实,但并非所有的法律事实都可以作为小前提。确定小前提不仅要通过证据规则确定事实的法律真实性,而且还要确定与大前提相符合的事实构成要件。[5]法律事实本身是非常繁杂的,小前提所包含的内容是由大前提所包含的构成要件所决定的,就法律事实本身来说,其中有大量的内容在法律上并没有意义,并不能成为司法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必须是经过法律程序最终得到确认的事实才能成为法律事实。
在法律推理中,法律事实作为小前提是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法律事实的确定是找法的基石要件,只有确定了事实才可能确定将要适用的法律规范。在成文法体系中,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通常适用于规范某一类事实。只有适用具体的法律事实,才能使该抽象的法律规范在具体个案中实现裁判的结果。法律事实的确认能保证结论的可靠,司法审判结果有赖于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任务不是将整个法律事实笼统地与某个规范相链接,而是从法律事实中抽象出要件事实,并确定其与大前提的规范要件的对应性。在立法过程中,为了实现法的规范性,立法者将各种事实加以整合、归类,实现对其系统性的过滤,而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法律事实。通常来说,一个成文法条文所要调整的是一个事实类型,包括了一组具体情形,各个具体情形之间具有实质相似性,应当同等对待。在制定成文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将各具体情形中的那些非实质性因素予以过滤,并通过各具体情形的实质相似性,将其归入一个事实类型之中,体现了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但是,法律适用则是一个与立法相反的过程,表现为从一般到具体,是一个将一般化的规则还原到具体情形的过程。法律事实认定意味着将生活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运用法律概念和术语对生活事实予以界定,使其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项。没有经过事实的识别,就无法进入事实的筛选、整理等过程。法律事实与适用是紧密而又不可分的。事实的发现过程常常涉及法律的定性问题。[6]在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的裁剪过程中,法官应当将无关的生活事实予以剔除。法官需要说明一般化的事实类型到底包括哪些情形,尤其是否包括诉争法律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事实的判断,主要就是确定要件事实与规范要件的对应性。通过法律关系的判断、事实的整理,最终寻找到要件事实,从而与大前提链接。①在法律推理中,法律关系的一端链接的是法律事实,另一端链接的是法律规范。由此得出法律裁判结果。对法律关系的识别,也是判断小前提的基础。就链接过程而言,需要不断探索最合理的裁判结论,通过链接寻找到具有密切联系的规则,选择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中,法律事实应当表现为大前提中所预设的事实类型,这是对两个前提进行合理链接的先决条件,而确保小前提与大前提中预设的事实类型相符合本身就是一个对接过程。成文法是一种命题性知识,但在命题性知识与针对某一法律事实的裁判结论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地带(Interspace)。填补该中间地带的就是逻辑三段论的运用。如果我们把中间地带这个链接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其不仅包含了三段论的形式逻辑,还包括了确定两个前提的论证过程。[7]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会根据当事人提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初步选择大前提,并且依据这个大前提判断在具体个案中哪些事实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同时要求双方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则,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从证据证明的事实构成到特定案件的要件事实,这一步骤需要从生活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并且要通过证据来作为中介,使得法律事实得到证明。如果法律事实(即小前提)中的具体特征与一般规范(即大前提)中的构成要件相符合,那么,抽象规定的法律后果就可以适用于具体个案。[8]对此,需要考量事实构成的每一个环节,尤其要对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进行判断,所以,这个过程不是单纯地将事实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而是要涉及法律价值判断。大前提的确定是为了寻求规范要件,小前提的确定是为了确认法律事实,最终促使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形成最佳的契合,这既是一个动态、往复的过程,也是司法三段论追求的直接目的。
三、实然命题与应然命题之间的勾连与耦合
在大小前提确定之后,必然进入链接阶段,以确定与法律事实之间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将普遍、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法律事实相链接,实现法律规范对预设事实的调整。立法实际上就是预设人类未来的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法律规范通常预设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事实或者事实类型,以实现人们有序地安排和组织生活。链接所要做的,就是在一个真实的事实发生之后,保证其受到预设该事实的法律规范的准确调整。
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联系越密切,司法审判就越有效。建构大小前提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合理的对接活动来实现,由此确保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准确对应性。否则,即便两个前提本身是真实准确的,但如果两个前提之间并不存在合情的对接关系,即小前提并不是大前提所要直接调整的法律事实,则三段论推理结果也可能是无效的。在表明法律规范的结构由法定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构成之后,魏德士强调了在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之间的链接的重要性,指出法官的活动就是“将有争议的某个事实涵摄(归纳、吸纳)到事实构成之下”。[9]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某个事实之时,如果事实满足规范中的法定事实构成,生活事实被涵摄于该规范之下,就可以得出该规范的法律后果。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处于法律推理的两个不同层面,法律规范为抽象、普遍的应然层面,法律事实则为具体、特殊的实然层面,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必须通过一个积极的创立性行为被等置。①考夫曼曾提出将“事物本质”的概念作为架接规范与事实的桥梁,实现两者的同一与等置。
在确定用于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过程中,法官需要在事实和法律之间往返流转。对小前提的准确认识有助于法官对大前提的选择,而对大前提的选择,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对小前提性质的判断②尤其是当法官存在着过度重视价值判断而轻视司法三段论运用倾向时,容易造成脱离三段论分析框架的基本形态。。建立法律大前提和小前提的链接,就是要形成在规范和叙事上具有一致性的方式,将事实纳入规范之中,从而构建一个完整性的叙事。[10]链接虽然从大小前提的确定就已经开始,但这一结合的过程往往需要循环往复的考察。事实上,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的联系,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一次就能完成,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往往需要通过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反复的考察才能够实现链接。
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是直接涉及价值的概念和现实,根据其含义,它们是服务于正义的;法律生活和法律事实是间接涉及价值的概念和现实,根据其含义,它们只能来源于那些被引向正义理念的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法律规则的本质就在于它无所不包,在没有通过人们之间关系的已规定部分之选择来对未规定部分——也就是通过对法律效果的排除——加以表态的情况下,法律不可能是一个部分规定。它不是一个法律上未作规定的事实范围,而是在消极意义上,通过对所有法律后果的否定在法律上有所规定的事实范围。法律规则在所谓的法律虚空的空间中有时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形,只有根据一个法律规则的立场,另一个法律规则才是有效的,因为是那个空间满足了这个法律规则,另外的那个法律规则也从自己这方面提出了要求,需要根据自己规则的有效性出发,使其他的法律规则有可能获得有效性。德沃金认为:“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则可用来处理手边的案件,某一方仍然可以享有一种胜诉权。即使在疑难案件中,发现各方的权利究竟是什么而不是溯及既往地创设新的权利仍然是法官的责任”。[11]
在法官寻找到规范以后,可能需要重新来认定事实,尤其是要补充新的事实。在事实和规范之间来回穿梭,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在链接过程中,不断补充事实。只有在循环往复的考察过程中,才能够使得作为适用法律的大前提和法律事实的小前提相互匹配,并最终能够相互链接,使得司法三段论能够在符合客观事实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③考夫曼认为,第一,必须考虑法律事实中的规范因素,使其与规范产生关系,注意发现事实对规范意义的影响。第二,应在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用规范思考事实的法律意义。
四、法律推理从自然法理念下的纯粹理性走向现代司法中的实践理性
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等一系列矛盾。法律推理促动法律规范由普遍规则到个案规则的适用,建立规范与事实、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同盟,法律推理以逻辑的方式控制权力的运作,以价值回溯确立法治运作。法律推理涉及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追寻,涉及推理主体关于知识论与实践理性的思考,法律推理的重心由立法领域到司法领域、由法律本体论到方法论、由法律移植到制度理性整合、由宏观论证到微观分析的转向。法律推理呈现内部逻辑强制与外部言说理性互动的特征,已经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形成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的交互流转。
近代以来,法治的社会基础、哲学基础已发生改变,特别是长久以来建立的规范与事实、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同盟关系已经被打破。此时,再简单地将法律适用等同于将既定的法律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形式逻辑推理模式,将不断地受到来自自由法学、法律现实主义和形式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的各种批评和质疑。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在现代司法理念上产生猛烈碰撞,司法活动不再仅仅是在形式逻辑的宰制下,单纯在法律规范层面上寻求裁判大前提的活动,而是考虑将法律事实纳入到法律解释的视野,将传统的逻辑涵摄模式扩展为从规范到裁判的一般性思考过程,表达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设别以及在规范中对事实再认识的思维过程。
法官在循环往复的思维考察过程中,既需要借助于实务经验和逻辑推理,也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技术,还需要作出价值判断。这种往返流转必须以客观的法律事实与实体法上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和前提,法官通常不得突破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而必须在可能的文义范围之内进行价值判断,不能随意进行所谓的自由裁量。在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在司法三段论中加入价值判断的因素,这也是寻求最密切联系规则的需要。有时可以将制定法等同于推理的大前提,但也不能否定三段论对法治的建设性意义。虽然制定法并不能直接作为三段论推理的前提,依据考夫曼的认识,法律三段论应该是类推的过程,而这一类推中的法律不等同于制定法,而是“在法律与具体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过程”中产生的。[12]试图用法律方法论拯救法律推理的前提,以便解决判决的合法性问题,这意味着作为法治三段论大前提的法律具有整合性,是对各种法律方法综合应用的结果。
从司法三段论结构考察中可以看出,其中蕴含了大前提的确定以及小前提的整理过程。司法三段论并非是三个独立的过程,无论是大前提的确定、小前提的整理,还是大小前提之间的对应并得到最终的结论,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这些显然都是逻辑三段论所不具有的。司法三段论既是一种操作方式,更是一种法律思维方式。比德林斯基认为:“法律事实被作为小前提而被涵摄到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之上,最终得出结论”。[13]规范所确定的法律效果可能是较为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并不是单纯地确定大前提含义或小前提内容的问题,更多地在于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对应性的确认。司法三段论的思维方式能够确保法官对于案件的审理符合逻辑思维的规律性、科学性,所具有的功能也是逻辑三段论所不具有的。
[1]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J].法学研究,1997(5):82.
[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3.
[3]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22.
[4]Manning,John F.What Divides Textualists from Purposivists,70 Columbia Law Review 106,2006:106.
[5][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 06:12.
[6]Bernard S.Jackson.Law,Fact and Narrative Coherence,Deborah Charles Publications,1988:93.
[7]Geoffrey Samuel.The Found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ntwerp:Maklu.Uitgevers,1994:142.
[8]Franz Bydlinski.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Wien/New York,Springer-1ag,1982:395.
[9][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3-64.
[10]James A.Holland&JulianS.Webb.Learning Legal Rul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24.
[11][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18.
[12][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M].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97.
[13]Franz Bydlinski.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Wien/New York,Springer-1ag,1982:41.
——中项消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