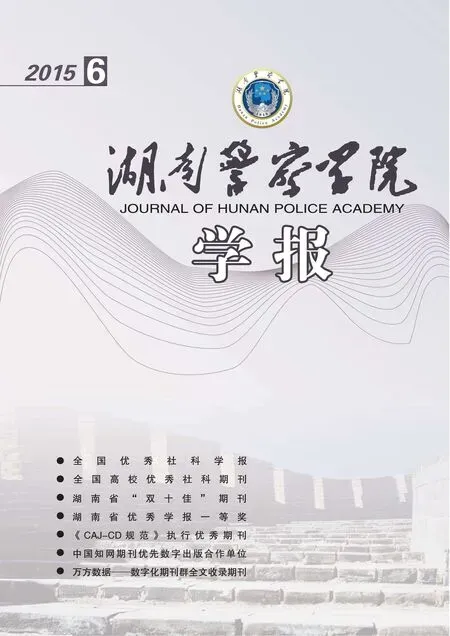转化型抢劫之转化“四要件”新释
安鹏鸣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8)
转化型抢劫之转化“四要件”新释
安鹏鸣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8)
作为一种拟制型抢劫类型,法理上习惯将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称为转化型抢劫。要实现抢劫的转化,必须满足主体、主观目的、时空和行为四个方面的要素。基于对现有观点的分析,比较合理的结论是,主体要素上应通过违法性和有责性二层次对是否转化为抢劫进行界定;从严格法条主义的立场,必须严格解释第二百六十九条项下规定的行为人主观目的;时空要素方面要摆脱时间与空间分离讨论的误区,将二者统一,宜认为“当场”只受时间上不间断性的约束;在判断特殊类行为是否可以转化为抢劫时,应当以与转化型抢劫的基础行为有法益侵害同质性与否作为界分点。
主体;法条主义;时间唯一;法益同质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当前,学界对该条中的诸多问题解释不一,对于转化条件的认定存在分歧。笔者主要围绕转化主体、主观目的、时空、行为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对该四要件做不同视角的解读。
一、转化主体:以违法性和有责性为解读视角
刑法中的犯罪,是行为人的犯罪。脱离行为主体,不牵涉刑法的适用。刑法理论对行为主体的论述,主要围绕身份和责任年龄两个要素展开。相应地,在转化型抢劫的主体的研究中,也涉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转化型抢劫是否为身份犯辨析
例1:甲实施盗窃行为后逃跑,在甲逃跑过程中,乙经甲的求救,与甲一同使用暴力将追赶之人打伤,帮助甲顺利逃脱,事后甲将销赃所得分给乙,表示感谢。该案中乙是否构成事后抢劫罪?
1.身份犯肯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人,才能转化为事后抢劫罪。行为人没有达到这种特殊构成要件要素的要求,难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主体。在承继共犯的场合,“后续加入的行为人没有与前罪行为人进行共同犯意的联络,那么按照身份犯的观点,帮助行为人不能继承身份犯的身份,不构成共犯关系,其自身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独立定罪。”[1]因此,案例1中,乙在甲实施盗窃行为时并没有与甲有意思联络,其后加入并不能承继甲作为盗窃犯的身份,那么乙就不能与甲构成共犯关系,乙也就不能转化成抢劫罪。
2.身份犯否定说
该说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一般认为,构成转化型抢劫,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人,后续帮助者也可以转化为事后抢劫罪。其逻辑为:转化型抢劫也是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基础行为是转化型抢劫实行行为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人整个行为过程中,加入的第三者行为也就成为共犯行为。根据该说,例1中乙的帮助行为与甲最终取得财物具有因果性,乙的“后行为并不是单纯的暴力与暴力威胁,而是同时具有使盗窃等前行为成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机能。”[2]因此,可以发生转化。
笔者赞同身份犯否定说的观点,但是对于该说的解释方法存在质疑。否定身份犯说的理由在于:一、身份犯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具有特殊的内涵,如把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理解为一特殊身份,会泛化身份犯概念,进而失去实质内涵;二、会产生割裂转化型抢劫基础行为和后续行为的不当结果。该观点将基础行为当成转化型抢劫的身份确认条件,忽视了其作为实行行为一部分的重要意义。转化型抢劫侵犯的是财产和人身双重法益。后续暴力行为侵犯的人身法益,前行为仅是身份要素的话,很难说明哪一行为是对财产法益的侵害。三、如果基础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那么转化型抢劫的身份要素消失,后行为便不可能转化成抢劫。显然,这种结果是不合理的。
(二)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可否转化辨析
案例2:甲(十五周岁)深夜携刀窜至被害人乙家中,实施偷盗时惊醒了乙。为抗拒乙的抓捕,甲从口袋里拿出刀与乙纠缠。在拉扯中,甲刀刺伤乙的脸部致流血受伤。经鉴定,乙的伤情为轻伤。该案中的甲可否转化为抢劫?
1.肯定说
该说肯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转化为抢劫。认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观上具有盗窃、诈骗、抢夺的故意,在该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侵犯三种罪名法益的行为,就具备了构成事后抢劫的基础。“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如果因为其不能成立刑法意义上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就不成立抢劫罪的主体,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3]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肯定了此种观点。该《答复》第二条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可根据刑法第十三条条的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案例2中甲的行为完全符合转化型抢劫的要件。
2.否定说
否定论者的判断理由大致为,要构成转化型抢劫,必须至少能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符合转化型抢劫的基础行为。由于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可能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转化型犯罪的基础条件便不复存在。而且,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家庭和社会对其应当负相应的责任,因此“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行为不按转化型抢劫罪处理,而是按照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处理,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罪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4]这种观点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认可。该解释中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因此案例2中的甲无论如何也不会转化成抢劫罪。
笔者赞同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转化成抢劫罪。之所以反对否定说,在于该观点虽然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观点目的性过于明显,却没有其他足够的理由支撑观点本身。实际上,刑法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有条件地转化为抢劫罪,关键在于在行为人为了窝赃、抗捕、毁灭伪造证据而实施暴力行为时,相对于普通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此时的危险性更高,具有更重处罚必要。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处罚也应当坚持罪责刑均衡原则。同时,即使是承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构成转化型抢劫,也不会出现不利于保护未成人观点的担心。因为,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依然可以在该年龄范围的人构成转化型抢劫时实现轻缓量刑。另外,否定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依据在于;首先,刑法已经有转化型抢劫的规定,即使不存在这样的解释,照样可以对此种情形进行违法规制。其次,将此情形规定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与转化型抢劫的定罪量刑在实际的量刑处理上并不会存在较大差距;最后,该解释只肯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定故意伤害或杀人罪,排除了轻伤害的情形。而同样情况下,成年人只要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就构成抢劫,会造成量刑不均,破坏刑法裁量体系的内在协调性。总言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转化型抢劫情况下没有必要特殊对待。
(三)违法性与有责性层次区分对转化主体的界定意义
根据两阶层犯罪论体系,犯罪的实体或者基本特征是违法性和有责性,犯罪构成是违法构成要件和责任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类型。而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标准①参现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22、123。。根据该构成要件理论,一个行为要构成犯罪,需要从客观到主观的进行判断。违法性是客观判断而有责性是主观判断。对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评价,按照以下顺序展开:“正向违法性+逆向违法阻却事由”是第一个阶层的判断,“正向有责性+逆向责任阻却事由”为第二个阶层的判断。根据违法性和有责性层次的理论,违法性是客观的判断,不具有违法性则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但是具有违法性并不是说行为就构成了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只完成判断的第一个层次。
对转化型抢劫的主体的判断,同样可以在二层次犯罪论体系下进行。
对于例1,乙属于承继的共犯类型。承继的共犯是否能够转化,如果依照违法性和有责性两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因为,根据该理论,共犯的从属应当是一种违法的从属。行为人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阻止抓捕。对于新加入的行为来说,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其行为的违法性从属于先前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而不仅仅是后行为自身具有违法性,或者仅仅能处罚的只是后面的帮助行为。由于加入行为的违法性从属与前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在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后加入者也应当为整个犯罪过程承担刑事责任。申言之,在盗窃、诈骗、抢夺构成的转化型抢劫中,后加入者只参与后续暴力行为依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例2中,按照违法性与有责任两层次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转化型抢劫的基础行为,违法是客观的。是否承担责任,则是主观的第二层次判断。在违法行为的支撑下,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伪造证据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人身权益,具有侵犯双重法益的性质,惩罚必要性升高,可以构成转化。据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转化成抢劫罪并不会违背罪行法定原则。
二、转化目的:以严格法条主义进行限制的说明
转化型抢劫,要求实施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时,主观上为窝赃、抗捕、毁灭伪造证据的目的。窝藏赃物,是指将已经取得的赃物予以掩藏,以防失去控制。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拘留、逮捕和一般公民的扭送”[5]。毁灭伪造证据,是指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销毁,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偏离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的目的,是否转化成抢劫罪,是需要进一步判断的问题,如:
例3:行为人甲偷偷将超市的数码相机转入方便面盒,企图以买方便面的名义将数码相机偷走,在收银时被超市人员发现将相机扣下。甲甚为愤怒,对超市收银小姐拳打脚踢后将相机取走。
例4:行为人乙翻墙入室盗窃被发现,与被害人家中男主人纠缠不过无奈逃出门时,刚好遇见自己的好兄弟丙某,告知实情后,乙与甲旋即回到被害人家中将男主人殴打致重伤。
对于盗窃、诈骗、抢夺,刑法将行为在随后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为抢劫罪,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同时侵犯了财产法益与人身法益,而基础行为与后续的暴力行为发生的关系上具有通常性,恰好抢劫罪的法益又能够囊括行为人两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但是,当行为人主观上并未为继续获得财物或者行为人并非因为先前财物犯罪的因素而直接实施暴力行为,财产法益与人身因素就不具有相关性,此时不能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为转化型抢劫。
根据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窝赃、抗捕、毁灭伪造证据的目的。在对这种目的进行解释时,应当坚持严格的法条主义原则,不得进行扩大解释。司法能动的前提,首先,必须是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的情况出现;其次,在刑法的体现上应当在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内,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以维护法律权威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为原则。不具备上述条件,司法裁判就应当严守在法律的边界内。即使适用当前法律会造成极端不公正,也只能依据有解释权或者立法权的机关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能让司法机关才裁判中肆意做“违法”的裁决。据此,例3的情形下,行为人甲的前行为已经被识破而无法实施,而甲又采用其他方式试图继续获得财物,该行为直接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刑,而不宜用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转化型抢劫的规定。该结论的合理性在于,适用抢劫与转化型抢劫所产生的刑罚效果一致,直接适用抢劫罪的规定也是基于对法条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逻辑前提之下的。例4的情形下,行为人在犯罪未遂后,又返回被害人家中实施暴力行为,此第二个行为与前行为同样不需要做统一评价。后行为构成故意伤害或者其他犯罪的,直接依据相应的规定与前行为实行并罚。据此,如为了报复、灭口等而使用暴力;在未取得财物情况下,为了单纯报复、情绪泄愤而杀害被害人,均不转化成抢劫。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特殊问题是,转化型抢劫是否要求前行为已经取得财物。窝藏赃物内在要求行为人已经取得赃物是显而可知的。但是抗拒抓捕和毁灭伪造证据是否要求前基础行为已经获得财物,则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要使关于事后抢劫主观方面的规定真正反映事后抢劫与一般抢劫的同质性,就必须将“行为人通过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作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条件。”[6]实际上,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并没有对前行为是否已经取得财物做出限定。首先,行为人实施基础行为后没有取得财物(中止或者未遂),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情形不是不可能出现。例如,惯犯甲深夜进入A家实施盗窃,突然听到警笛声,以为警察来抓捕自己,遂准备离开。这时警笛声也惊醒了熟睡的A。甲被A发现后,为逃离对A实施暴打。此案中,甲虽为达到获得财物的要求,但是其行为亦完全符合转化型抢劫的要件。应当按照转化型抢劫论处。其次,就毁灭伪造证据而言,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已经获得了财物。但是如前例所述,行为人在基础行为未遂或者中止后,在掩盖罪证的过程中对他人实施暴力也存在转化成抢劫的可能。对此,应当肯定行为人在未取得财物的情况下亦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实质上,判断的关键在于,其一,行为人后续行为与基础行为是否有关联性,是否都是为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服务。如果行为人后续行为与基础行为高度关联,且为财物犯罪服务,则可以转化成抢劫罪;其二,行为人后续行为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如果情节严重,存在转化的余地;如果情节轻微,则不宜转化。
三、转化时空:时间要素解释“当场”具有唯一性
(一)“当场”与现场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后续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必须发生在“当场”,而“当场”的界定与现场有关。
这里可能出现的现场有:实施基础行为的现场,实施暴力行为的现场,实施窝赃、抗捕、毁灭伪造证据的现场。在基础行为的现场和后续行为现场相同时,现场也就是“当场”;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发生偏离时,“当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场。想要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不可能窝藏、抗捕、毁灭伪造证据和暴力行为单独、分别存在的情况。要么行为人为了窝藏、抗捕、毁灭伪造证据而实施了暴力行为,要么行为人实施的窝赃、抗捕、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具有暴力因素。因为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的场所可能不具有一致性,案件会产生两个现场,而这两个现场是否属于“当场”,则要从时间要素上进行分析。例如:
例5:行为人甲电动车行至商场外,见有一名包放在旁边的电动车座位上,甲趁被害人A弯腰开锁之际,一把抓住该包驱车就跑。A立刻骑车追赶,并大声呼叫抢劫。甲飞车行驶经过两个拐弯路口时,被闻讯的交警制服。例6:行为人乙于某地采用撬锁手段试图将被害人B的小轿车开走,得手后为逃跑一路高速狂奔,逃至某路口时被早已掌握其行为的并进行追踪的公安人员设卡抓住。
上述两个案例中行为人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取决于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当场”的理解。通说认为“当场”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同时,行为人刚一离开现场就被发觉而被追捕的过程,是其犯罪现场的延伸,也应理解为这里所说的当场。“当场”是一个时空概念,要在时间上进行要求,亦需空间上的限制[7]。根据这种观点,案例5中的甲始终没有脱离抓捕过程,此时的犯罪现场发生延伸,应当认为符合“当场”的规定,因此,甲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案例6同样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另外,也有学者论及“有关说”、“控制说”等等。由于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时间、空间两个要素进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早期的观点仅仅将“当场”限于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由于过于界定过于狭隘,不利于法益的保护而始终未被学界所提倡①。
总结当前学界大多数的观点,均将此处的”当场“理解为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的结合。实际上,如果时间上发生间隔,犯罪场所必然发生转移,此时就要判断所谓的现场如何延伸。如果行为人没有被”追捕“、“追赶”、“监控”、“监视”的情况下,如果时间间隔已久,则不能再转化为抢劫。
(二)时间要素判断“当场”具有唯一性
学界无论采取何种学说,都没有脱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那就是时间的不间断性。现场说也即指明行为发生的时间与暴力行为的时间没有分离,有关说、控制说以及通说中也突出整个过程的不间断性和整体性,实质上也就是指时间未间隔。因此,只要时间要素始终保持延续性,就可以断定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的“当场”的规定。申言之,“当场”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一个空间问题,界定“当场”的核心应在于时间而非空间因素。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基础行为的场所和后续行为的场所为同一场所,两行为发生时间具有高度密接性;此时行为人符合转化成抢劫罪的要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其次,时间发生间断的情况下,考虑时间要素也足以判断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这里存在两种情况:第一,时间发生间断,基础行为实施场所与后续行为的场所分离,行为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例如;行为人盗窃完成刚出被害人家门,就被被害人邻居发现,行为人为抗拒抓捕而实施暴力。此时基础行为现场和后续行为现场发生分离,但是时间上具有密接性,符合“当场”的规定,则可以肯定转化型抢劫的成立。再如,追捕过程中断、或者作案一段时间后才被发觉,由于时间不具有连续性,不符合“当场”的内在含义,不能再转化成抢劫罪;第二,时间发生间断,即使现场不分离,但是不能再认定为符合“当场”的情况,也可排出转化成抢劫罪构成的可能性。例如,被害人人外出,家里没人,行为人盗得财物后,熟睡在被害人家里,第二天被害人回来。此时现场尚未发生分离,如果按照现场说的处理,则要转化为抢劫。然而时间间断已很久,即使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也不应再以转化型抢劫论处,而应当单独定罪处罚。原因在于前基础行为与后续暴力行为已经失去了直接的因果性。除此类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时间的间断必将伴随着场所的转移。
再次,只要时间不发生间断,场所的因素就无需考虑。前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在时间上保持连续性,不发生间断,则不用考虑场所因素,可以直接对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进行评价。质言之,现场并不是影响“当场”与否判断的因素。因为时间不间断,就赋予了转化成抢劫的最大可能性。时间连续的情况下,场所的意义微乎其微。如追捕过程中,时间不间断,场所发生变化,依然不排斥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综上,笔者主张,对于“当场”的理解,不应当聚焦于对概念解释的角度。而应当在具体判断过程中,用时间的不间断性作为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的连接点,进而对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进行判断。只要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在时间上具有不间断性,就可以认定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当场”,在符合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转化为抢劫。时间要素唯一性的合理性在于,首先因为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其次是即使基础行为与后续行为发生在不同场所,只要时间具有不间断性就可以判断属于“当场”。况且,通常情况下时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四、转化行为:法益同质性为判断根据能以逻辑证成
例7:行为人甲与朋友手持钳子等作案工具,骑车至所在村某处,将正在使用的高灌铝线用钳子剪下。正要逃离现场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甲与朋友捡起石头将该村民打倒在地后骑车逃离现场。经鉴定,该村民伤情为轻伤。
例8:村民乙与丙素来不合,双发多次发生纠葛乙均吃了亏。某日,丙的父亲因病去世,乙认为终于有了对丙进行报复的机会。于是在丙父未下葬前悄悄潜入丙家,想将丙父的尸体偷走,好让丙丢丑。盗窃过程中被丙的儿子发现,乙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丙子刺伤后逃离了现场。经鉴定,丙子伤情为轻伤。
转化型抢劫中,有两个行为,基础行为也即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续行为也即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对于基础行为是否限定在法律规定的盗窃、诈骗、抢夺范围,学界不同的解读会影响上述两个案件的结论。
(一)特殊类犯罪可否转化的观点阐释
对于除《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二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盗窃、诈骗、抢夺罪以外的行为是否可以构成转化型抢劫。有学者认为,应该严格格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即转化型抢劫中的基础行为必须是盗窃、诈骗、抢夺罪①赵秉志.侵犯财产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10。。如对于实施的基础行为是合同诈骗、金融诈骗,以及针对枪支、弹药的盗窃、抢夺等行为时,不能转化为抢劫罪①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9。。因此,以上案例7和案例8均不能构成抢劫罪。然而,如例7中,行为人实施的基础行为与后续的暴力行为均与转化型抢劫中的行为相当,行为侵害的法益也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要保护的目的相同,完全可以适用转化型抢劫予以惩罚。
另有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实施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符合第二百六十四条、二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七条的犯罪构成,就可以将该行为评价基础犯罪,进而取得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承认盗伐林木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抢劫(即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条),并不意味、也不需要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盗窃罪”扩大解释为(或类推到)“盗伐林木罪”,而是说盗伐林木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可以将其评价为盗窃罪;在盗伐林木的行为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伪造证据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应当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论处。”[5]854该观点不能解释的是,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该罪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证明作用。”[5]760而事后抢劫中,基础行为属于侵犯财产安全的犯罪。将该种盗窃行为与伤害行为结合拟制为抢劫,超出了用语的一般含义,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还有观点认为需要区别对待,首先,以特定财物为犯罪对象犯其他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罪发生牵连的,符合牵连犯的特征而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如例7中的情况即是如此;其次,以特定财物为犯罪对象犯其他罪,而该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罪发生竞合关系,表现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时,如果抢劫的处罚较重,则可以转化②参见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1043、1044。。这种观点面临的质疑是,该观点并没有分析究竟何谓法条竞合,是否就一定会竞合,由于刑法理论中的法条竞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其含义如何至今尚无统一界定,其适用原则也是众说纷纭,因此,用法条竞合阐释转化型抢劫的问题恐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③参见金泽刚,张正新.抢劫罪详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429、430。。牵连犯同样也面临这一困境。
(二)以法益同质性界定转化基础行为的可行性论证
鉴于上述观点的分析,首先,不应当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局限于基础的盗窃、诈骗、抢夺罪,这种观点将许多与转化型抢劫具有相同本质属性的犯罪排除在外,显得过于机械;同时,也不宜将所有特殊类盗窃、诈骗、抢夺罪都包含进转化型抢劫罪里来。简单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则会不当扩大第二百六十九条的适用范围,超出可预测性,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应当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是否具有同质性来判断其他特殊类行为可否转化为抢劫。
第一,作为基础行为来源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二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七条,其保护的法益是财产利益。又由于刑法规定的抢劫罪中财产法益与人身法益并重,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行为拟制为抢劫罪才获得合理性依据。因此,想要转化为财产犯罪,行为人所侵犯的基础行为必须具有财产法益。转化型抢劫罪是刑法侵犯财产罪章节的内容,与盗窃、诈骗、抢夺罪是侵犯的对象具有同质性,立法上将这些犯罪规定在同一章节是因为他们具有本质上相同的法益侵害性。同样,之所以转化型抢劫罪与这些犯罪被规定在同一章节,也说明是为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需要。
第二,笔者所称的财产法益并不是单纯的指所侵害的对象具有财物属性。而是指财物身上更多的是具有经济属性,而不是指其他诸如公共安全、精神心理等方面的价值属性。比如“在以盗窃、抢夺的方式获取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国有档案等的场合,因为上述物质主要是体现在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上,而更多地存在于对公共安全所具有的潜在威胁或者对公共秩序管理所必要的手段价值上,不能将其看做普通财物,”[8]因此,基础行为是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国有档案时,不转化成抢劫罪。
第三,如果基础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具有财产属性和其他属性,此时行为既符合转化型抢劫罪,也符合所侵犯的特殊罪名,由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重,则适用从一重处罚的原则加以处理。比如以盗窃、抢夺的方式获取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同时符合其他条件的情况,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又由于该法条同时也保护公共安全,因此适用从一重处罚的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获得结论是,在行为人实施的基础行为所侵犯的法条所要保护的是或者主要是公私财物时,则存在转化为抢劫的余地。实质言之,即行为人实施的基础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基础行为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同质性,在符合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则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因此,如例7中的情况,行为人盗窃的是正在使用的电线,侵犯的是公共安全的法益,同时,所侵犯的对象“电线”具有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基础行为侵犯法益的共同本质,财物属性,因此,行为可以转化为抢劫罪,最终从一重处罚。而案例8中,由于基础行为侵犯的是尸体,不具有一般意义的财产属性,与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基础行为保护的对象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不发生转化。
[1]竹莹莹.论转化型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法律适用[J]. 2005,(8).
[2]张明楷.事后抢劫的共犯[J].政法论坛,2008,(1).
[3]李希慧,徐光华.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为视角[J].法学杂志,2009,(6).
[4]刘艳红.刑法学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6.100.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13.
[6]吴天昊.事后抢劫主观要件浅析[J].法制与经济,2010,(5).
[7]肖中华.论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J].法律科学,1998,(5).
[8]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25.
New Interpretations About Four Elements of Transformed Robbery
AN Peng-ming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00)
As a type of special robbery,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used to be called the Article 269 of Criminal law as transformed robbery.ln order to realize this transform,there are four elements are needed: subject,time,space,and behaviors.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views,some new opinions are reasonable.Firstly,illegal and responsibil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judging the subject.Then,the purpose of subject must be restricted strictly.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get rid of a traditional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ime and space,because time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analysis of transformed robbery than space.Lastly,ln judging whether some special kinds of behaviors will be transformed or not,the standard should be based on this factor,compared with the theft,fraud and robbery,that the previous behavior must has already violated the homogeneous benefits of criminal law.
subject;legalism;time;homogeneous interest of law
D914.34
A
2095-1140(2015)06-0075-08
(责任编辑:天下溪)
2015-09-07
安鹏鸣(1990- ),男,贵州毕节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