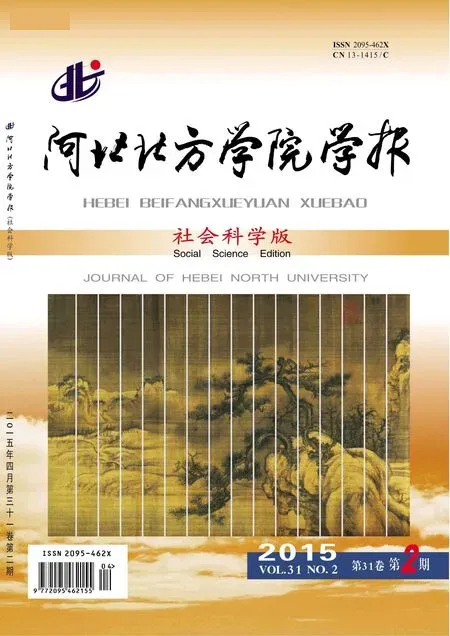燕人蒯通略论
严 可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411105)
蒯通,范阳(今河北徐水北固镇)人,约生活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其人其事散见于《史记》的《乐毅列传》《淮阴侯列传》《张耳陈馀列传》等记载以及《汉书》的《蒯伍江息夫传》中。在《史记》和《汉书》里,蒯通作为纵横家即策士的形象出现。如《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载,蒯通的专长就是纵横家权变之说:“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之说,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1]2167对于这一身份及相关行为,古代学者历来评价不高,如茅坤认为:“武涉之说,为楚也,而蒯通何为哉?其言甚工,假令韩信听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内矢石之斗何日而已乎?大略通特倾危之士,徒以口舌纵横当世耳,非深识者。”[2]339他认为蒯通是逞口舌之争,不是“深识者”。蒯通是否没有“深识”?通过蒯通在反秦、楚汉战争和汉初局面等几个关键时期的表现重做评论。
一、择主而事,劝降范阳令
蒯通生于战国末年,秦时已成年,但秦王朝建立后他并没入仕,而是选择规避闲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秦朝的深刻认识。他认为秦朝的统治策略包括对士人的态度与六国之时迥异,必然不会长治久安。秦始皇去世后,国家便开始动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8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地起义军的势力风起云涌。陈胜、吴广派武臣率领一支部队进攻蒯通的老家范阳。此时的蒯通正在家乡,通晓时局的他果断加入反秦队伍,成为武臣麾下的重要谋士。而且蒯通觅得了发挥个人才能的绝好时机,孤身一人游说范阳令归降。这段劝降过程展示了蒯通的口才和胆识。《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蒯通眼光老到,从秦法的苛重入手,将秦朝的气数与秦法融为一体,具体描述了秦朝的危机。同时又向范阳令晓以利害:“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将范阳令的危机展现在他自己面前,让他清楚自己处境的危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蒯通很快取得范阳令的信任。尔后,他又回见武臣,献上“传檄而千里定”之计,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使燕赵边城之地相率而降:“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曰:‘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下城,臣窃以为殆矣。用臣之计,毋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如通策焉。”[3]2575
蒯通凭借高超的口才双边游说,深刻地指出秦王朝即将灭亡的社会原因,使范阳令认识到自己的危险所在;同时蒯通还让武臣意识到双方共同的敌人都是秦王朝,说服武臣放弃了屠城政策,实施优待降者的方针,避免了不必要的残杀。不伤一兵一卒便下燕赵30余城,蒯通功不可没。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却不见蒯通参与其它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从活跃到沉寂,似乎过于突兀。笔者认为不是他不参与,而是明主难遇。太史公曾在《史记·乐毅列传》中言:“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3]2436可见蒯通敏而好学,胸怀大志,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不遇明主赏识的心态。《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中载:“初,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1]2167由此可知,他确实投奔过主人,只是得不到重视。此时的项羽势力最盛,而且“欲封”他与安其生,最后蒯通还是选择离开,表明蒯通遇事冷静、洞悉世事。因为他认准项羽并非托身之主,宁愿闲处不仕。
二、劝韩不成,明哲保身
随着楚汉战争的发展,天下形势更加复杂,除刘邦和项羽势力之外,还有韩信、英布、彭越等割据力量。公元前203年,韩信率汉军虏魏王,破赵军,下燕,逐渐扭转了汉的劣势,成为黄河以北一股重要势力。于是蒯通看准时机,投入韩信帐下,成为韩信麾下的重要谋士,并决定游说韩信三分天下。
首先,他协助韩信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韩信正准备率军进攻齐国,却得到齐国已被郦食其劝降的消息,韩信欲止。此时蒯通决定劝韩信继续进军,以武力占据齐国:“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2]331蒯通的话坚定了韩信以武力攻克齐国的决心。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不仅壮大了韩信的声势,也拥有了一块根据地。
其次,劝韩信自立山头,破燕协赵,争衡天下。韩信自平齐后,实力大增,成为刘、项之外另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因此,刘、项争相拉拢他,但韩信刚为齐王,对刘邦心怀感恩,拒绝背汉。蒯通分析当时的形势,果断劝韩信独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蒯通借算命入手,为韩信剖析天下大势:“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3]2623-2624
听了蒯通深入的分析,韩信犹豫不决,不忍背汉。他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3]2624面对韩信的犹豫不决,蒯通又拿出“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道理督促韩信下定决心: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3]2625
从这段话不难发现蒯通对人事和社会走向的洞察力,对残酷政治斗争认识的敏锐。韩信虽一度动摇,但却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至此蒯通明白韩信难以说服,于是为明哲保身起见,他毅然脱离韩信集团,“佯狂为巫”[3]2626。
三、洞察时局,优于辞令
后来时局的发展果不出蒯通所料,公元前201年刘邦将韩信诬以“谋反”罪名,削去王位,降为淮阴侯。再后来,韩信被吕后诛杀。临刑前还叹息:“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3]2628韩信这句话再次反映出蒯通的独到之处。
然而,后世学者如茅坤、王夫之等对蒯通与韩信的关系以及蒯通的献计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的做法既害了韩信,又不利于天下。茅坤的言论已见开头所引,王夫之则认为:“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4]15不过也有辩驳者,如清人赵翼认为韩信是死于愚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文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曰之巫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2]339从赵翼的话可以看出,茅坤、王夫之等人只是从结果出发评价蒯通,不免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没有讨论蒯通对时局的分析是否正确,掩盖了蒯通的智慧与眼光。
蒯通的智慧还可从他在汉初的经历窥知一二。西汉初年,因劝说韩信背汉,高祖下令逮捕蒯通。蒯通揣摩刘邦心理,巧妙为自己脱罪。面对刘邦“若教淮阴侯反乎”的责问,蒯通坦然应对,并指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再以“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3]2629之言,平息了刘邦怒气,最后逃过一死。因谋反而得“不烹”,实在难得,所以清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称蒯通“奇谋雄辩”,“足与《国策》同传”。
不仅如此,蒯通还迅速适应新环境,选择入仕曹参幕府,利用优于辞令的特点,将东郭先生与梁石君等人推荐给曹参,事见《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乃见相国(曹参)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一个积极游说的策士,为何向曹相国推荐东郭先生、梁石君等隐士?这正是蒯通的过人之处。当时国家休养生息,重用黄老学说,曹参本人更是如此,譬如他做官,常常“不事事”、“饮以醇酒”[1]2048。那么向曹参推荐与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的隐士,无疑合乎时宜。
综前所述,在战国至西汉初年的社会巨变期,蒯通对社会局势以及自身的进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的几次重大选择充满了智慧;他利用辩才使得燕赵之地“降者三十余城”,避免了流血与伤亡,更值得肯定。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明)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