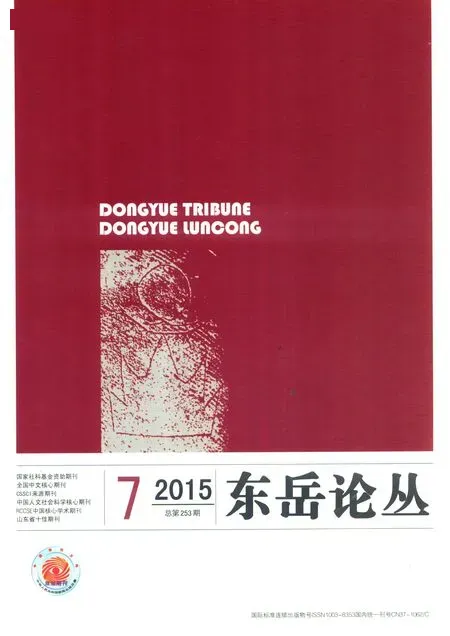佛典、话本与《西游记》关系揭橥
——以白龙马形象为例
刘冠君,车 瑞
(1.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2.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成果选萃
佛典、话本与《西游记》关系揭橥
——以白龙马形象为例
刘冠君1,车 瑞2
(1.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2.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西游记》中“白龙马”是作者在结合前代文化原型基础上经过宗教互文、神话互文、文本互文再加工创造的人物形象。其先后经历了犯法受戮的孽龙、佐佑唐僧取经的神驹、修成正果封为八部天龙马的过程。白龙马是外来血统与中华图腾结合的成功典范,具有中国民间信仰火神和印度佛教护法神的神格。吴本《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形象绝非凭空臆造,而是源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结合神话、宗教、文化原型加工再创造的结果。上古神话、印度佛教中龙、马、火神有关的原始意象,以及宋元话本赋予这一形象以无限生成的可能性。
白龙马;《西游记》;佛典;话本;神话原型
佛教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不言而喻。根据佛经故事改写的变文,不仅作用于唐传奇、宋元话本,而且对明清小说、鼓词、评话等说唱文学影响深远。陈寅恪曾说:“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①随着佛教、话本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大胆提出中国小说的真正源头不是神话和传说而是天竺史诗,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应该是“天竺史诗——佛本生故事——五朝小说(志怪、志人)——唐变文、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②。吴本《西游记》成书之前,西游故事大量存在于佛典、变文、诗话、平话、杂剧、话本中,这表明这部“世代累积型”小说采用了之前的一些西游故事。吴本《西游记》在从前佛教典籍、俗讲变文、宋元话本、图册壁画以及勾栏瓦舍里不断流传、演变的西游故事基础上形成:伴随俗讲的流布古代印度史诗、佛典中的故事逐渐引介东土而与玄奘取经故事合流;会同宋元说话艺术对西游故事的衍变和扩充而趋于完备丰盈;又由元代初具规模的西游平话、杂剧,加上明代文人在西游文化接受史上综合诸多神话、文化、宗教因素以“集撰”方式累积成书。其间,唐代俗讲和宋元话本对于西游故事的生成和发展贡献巨大,书中的白龙马形象即是明证。白龙马是吴承恩《西游记》中一个特殊的形象,他是作者在结合先前的神话、宗教、文化原型基础再加工创造的结果,在佛教典籍、宋元话本、图册壁画以及明代同期作品中均能发现他的身影。白龙马在吴本《西游记》中虽所占比重不大,但与其他取经三徒相同之处在于都经历了犯法→受罚→取经→成佛的过程。
一、犯法受戮的孽龙
西游叙事模式的特点在于取经与成佛同步。取经五众(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龙马)在完成取经任务的同时也圆满自己的修行,尤其是后四人都经历了“犯法受戮”到“脱胎换骨”或“改邪归正”最后“加封正果”的过程。吴本《西游记》第十五回中玉龙与孙悟空斗法时如此描述:“那个是迷爷娘的业子,这个是欺天将的妖精。他两个都因有难遭磨折,今要成功各显能。”③只是孙悟空因猴性闹天宫、猪八戒因思凡辱月仙、沙僧因失手打破琉璃盏,如果说前三者是因冒犯天庭而遭贬的话,白龙马则因忤逆父王而受诛。在吴本《西游记》第八回中,菩萨与木叉辞了悟能前往长安城途中,听见一条玉龙求救,打探之余得知此龙是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父王以忤逆之罪表奏天庭,玉帝将其吊打三百,不日遭诛。菩萨慈悲奏请玉帝赦免玉龙之罪,命其化为白马为取经人做个脚力以将功赎过。《西游记》中白龙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三太子,而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的白龙马则是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他的遭诛并非因忤逆王道,而是因渎职受罚。第七出“木叉售马”中,南海火龙因为行雨差迟,要被玉帝斩龙台上处斩。观音慈悲,上九天朝奏玉帝,救下火龙,着他化为白马随唐僧西天驮经。然后复归南海为龙。正所谓“火龙护法西天去,白马驮经东土来”④。唐人小说《李靖》中卫国公李靖乘青骢马升天替龙行雨,龙因失误降雨过多而受罚的情节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孽龙因行雨当斩的情节十分相似,但到了吴本《西游记》中则衍化为泾河龙王与袁守诚赌赛而违犯天条在剐龙台遭戮的故事,只是泾河龙王终被魏征梦中斩首,而南海火龙终因菩萨度脱得救。
吴本《西游记》中鹰愁涧吞食唐僧坐骑的孽龙在宋代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已有雏形,只是鹰愁涧一龙作孽,而九龙池则是九龙肆虐。“入九龙池处第七”中猴行者曰:“我师看此是九条馗头鼍龙,常会作孽,损人性命。……只见馗龙哮吼,火鬣毫光,喊动前来。……被猴行者骑定馗龙,要抽背脊筋一條,与我法师结條子。九龙咸伏,被抽背脊筋了,更被脊铁棒八百下。”⑤《诗话》中损人性命的馗龙与吴本《西游记》中鹰愁涧吞食唐僧白马及鞍辔的孽龙无二,与猴行者斗法的馗头鼍龙和小说中与孙悟空鏖战的龙太子相同。只是小说中龙猿相斗最终冰释前嫌,玉龙纳入西行队伍。《诗话》中悟空抽取龙筋作法师的腰带,并未如小说中化龙为马,但“法师才系,行步如飞,跳回有难之处。盖龙脊筋极有神通,变现无穷。三藏后回东土,其条化上天宫”⑥。这里龙筋和白马一样起到了助力唐僧取经方便脚力的作用,最终都获得了飞升成正果的结局。
此外,元代王振鹏所绘《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4]题签为“佛影国降瞿波罗龙”。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灯光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波罗龙王所住之窟,如来昔日降伏此龙。”⑦《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东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罗龙之所居也。……供养受记窣堵波,愿为恶龙,破国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为大龙王,便欲出穴,成本恶愿。适起此心,如来已鉴,愍此国人为龙所害,运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龙见如来,毒心遂止,受不杀戒,愿护正法。因请如来:‘常居此窟,诸圣弟子,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将寂灭,为汝留影。遣五罗汉常受汝供。正法隐没,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奋怒,当观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当止。’”⑧孽龙发恶愿涂炭生灵,如来悯恤民众,降服毒龙,最终瞿波罗龙受佛祖感化守护正法。
《正法念处经卷第十八》将龙分为两种,一种法行龙,一种非法行龙,前者护世界,后者坏世间。非法龙王包括恼乱龙王、奋迅龙王、黑色龙王、多声龙王等,云中现身,眼如车轮,颈上三头,形如马相或作蛇身。非法行龙所到之处地崩山摧、常雨热沙、焚烧宫殿、淫人妻女。《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龙变为人,与妇交会生龙种的故事。初时大龙池中诸龙易形交合牝马生龙驹,后“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⑨。金花王不堪戾龙作乱,于是戮尽城中不听王命为非作歹的龙种,可以算作较早孽龙遭戮的传说。吴本《西游记》中玉龙受菩萨度化锯角退鳞变白马,第三十回“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中白马得知唐僧被黄袍怪变为虎精,登时顿绝缰绳,抖松鞍辔,化为人形前去与黄袍怪斗法,这可以算作玄奘西行所记龙/马/人互相置换的意项在《西游记》中的互文性延续。
从晚唐五代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经过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到王振鹏绘《唐僧取经图册》,最后到吴承恩的《西游记》,西游取经被逐渐发展和完善,白龙马也从最初戾龙难驯危害一方、到受如来感化皈依佛法、到受观音度脱护法唐僧的转变。《大唐西域记》中孽龙淫乱民间而被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瞿波罗龙贻害四方被降;《西游记》杂剧中南海火龙行雨差池而遭戮;吴本《西游记》中西海龙太子忤逆父王而受罚。凡此,说明在取经故事的发展和演化过程,西游故事虽以唐僧师徒(包括白龙马)历尽艰险取经为主题,但副部主题则是负罪的取经团队四徒通过取经获得自我救赎,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祸害无穷的恶龙逐渐走上西行护法之途,完成了孽龙向神龙的飞升。
二、佐佑唐僧西行的神驹
没有孙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没有白龙马,唐僧西行寸步难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唐僧坐骑不堪脚力,幸有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此马健硕通人性,法师遂与老翁易马西驰。这里健而识途力堪远涉的赤马已然具备吴本《西游记》中白龙马日行千里的神驹功能。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木叉对龙马的描述“大宛国天产才,渥洼水龙媒种。带轻云一块雪。走落日四蹄风。玉尾银骔。驮双将无嫌重。出群驽立大功。胜普贤白象身高。赛师利青狮性勇。……非伯乐谁知良马。有刘累方豢真龙。奉天佛牒玉帝敕将君送。且休言九逸还宫。更休论八骏腾空。这马跳青溪曾救蜀王。到紫陌还归塞翁。至乌江曾弃重瞳。离了普陀寺中。云行千里乘飞鞚。这马你看一丈长头至尾。八尺高蹄至骔。但一嘶凡马皆空。比豹月乌别样精神。比忽雷驳争些徒勇。”⑩“渥洼水龙”典出《史记》。《史记卷二十四·书第二》云:“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李斐注:“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傍。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应劭注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此马奔则汗血沾濡,流沫如赭。
“豹月乌”和“忽雷驳”均为骏马名。豹月乌见明王志坚《表异録·毛虫》:“张飞有马名玉追,又曰豹月乌。”“忽雷驳”又作忽雷駮,唐初秦叔宝所乘名马。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记载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駮”,常饮以酒,每于月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对于白龙马的脚力木叉无不溢美之词,说“他曾到三足金乌窟。四蹄玉兔宫。他有吃天河水草神通。晋支遁性命也似看承,周姬满心肝一般敬重。”金乌窟譬日,玉兔宫喻月,足见其上天入地之能。支遁为东晋名僧,好鹤爱马,《吴地记》记载晋支遁尝隐于支硎山,后得道,乘白马升云而去。据传,白马涧是支公放马处,他有匹神驹名频伽,曾在苏州城卧龙街桥边饮水,马溲处忽生千叶莲花,人异之,故称此地为“饮马桥”。吴本《西游记》第六十九回悟空为朱紫国国王配制丸药,需要白龙马的尿,只见那马跳将起来,厉声激辩道:“师兄,你岂不知?我本是西海飞龙,……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味,变作灵芝,仙童采去长寿;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白马本非凡畜,马溺亦为圣物,得者即可飞升成道。周姬指周穆王姬满,《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用八骏之乘,御以西巡,越过漳水,行程九万里,以观四荒,北绝流沙,游于昆仑之丘,见西王母,与之唱和,乐而忘归。传说穆天子之马能日走千里,胜人猛兽。木叉将白龙马与张飞的豹月乌、秦叔宝的忽雷駮、支遁的神驹、姬满的八骏并举,更突出其性情温驯和脚力惊人,木叉将此龙马送给唐僧,安慰他说:“吾兄从今后不必把眉头纵。骑着龙马。引着部从。到前途。莫惊恐。有山精。有大虫。有猿猴。有马熊。见放着龙君将老师奉。到花果山乱峰。相遇着悟空。取经卷回来受恩宠”。可见,在吴本《西游记》中毫不起眼的小白龙在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不仅上天入地、护法唐僧、翻江倒海、显耀神通,而且比孙悟空入师门为早,比孙、猪、沙三人辅佐唐僧时间都长,杨本《西游记》杂剧中三个徒弟功德圆满后均辞了师父圆寂,唯独白龙马驮经随唐僧回东土。按杨本杂剧的顺序,木叉售马在第七出,唐僧收孙悟空为弟子在第十出,收沙和尚在第十一出,收猪八戒在第十六出,所以白龙马应为唐僧的大弟子,或至少排位应在沙和尚、猪八戒之前。
根据最早创作于西夏的甘肃安西榆林石窟关于唐僧取经壁画《普贤变》中,带着光环的法师向普贤菩萨施礼,他的左边有一只猴子一只马,马背驮着莲花座,莲花座上供奉着散发祥瑞的经书,这应该是取经成功后的场景,可见在早期的取经队伍中只有一僧一猴一马。而第二、第三、第二九窟三处《唐僧取经图》壁画均可以发现只有唐僧、孙行者和白马,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
《杂阿含经》将世间良马概括出八中品德,一生於良马之乡、二体性温良不惊恐人、三不择饮食、四厌恶不净择地而卧、五马师调习速舍其态、六随其轻重能尽其力、七常随正路不随非道、八勉力驾乘不厌不倦。此八德白龙马可谓样样兼备,而且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王振鹏所绘《唐僧取经图册》中有唐僧得火龙马,包括图[上4]、[上6]。[上4]题签为“遇观音得火龙马”,与上述杨本《西游记》杂剧“木叉售马”相类。[上6]题签为“石盘陀盗马”,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在玉门关收得徒弟石槃陀,后至玉门关与第一烽之间,石槃陀欲害玄奘,玄奘察觉,给予石槃陀马一匹,劳谢而别。此图内容当为石盘陀欲盗火龙马,马化为龙飞上天空。石盘陀见此马灵异,终于放弃杂念决心随玄奘西天取经。另[下10]题签为“悬空寺遇阿罗律师”,内容为火妖狐吐火欲加害昏迷中的唐僧师徒,龙马现原形在空中大战火妖狐,火妖狐口吐火焰喷向神龙,而神龙则怒目圆睁,张牙舞爪,气势凌厉。[下4] “东同国捉狮子精”,图中持斧大将为毘沙门或观音手下大将。大概火龙斗败火妖狐之后,唐僧与石槃陀依然昏迷不醒,故来向毘沙门天王或观音求救,遇持斧神将而诉说原由。[下5]“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当为持斧神将向天王或菩萨报告之后,持斧神同火龙前去搭救唐僧师徒。图册中火龙马不仅承担驮载唐僧的重任,而且担负起护法师父的功能,堪比吴本小说中孙悟空的职责。
显然,对比以往诸形象,白龙马在吴承恩笔下由显而隐。在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和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白龙马,在吴本《西游记》中的形象却被大大弱化了。但这一处理却并不代表作者对白龙马的刻意忽略,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个形象上依然倾注了心血。吴本《西游记》第二十三回,孙悟空曾说:“他不是凡马,本事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唤名龙马三太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父亲告了忤逆,身犯,天条,多亏观音菩萨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鹰愁陡涧,久等师父,又幸得菩萨亲临,却将他退鳞去角,摘了项下珠,才变做这匹马,愿驮师父往西天拜佛。这个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这实际上对白龙马与其他人的平等身份作了交代。在最后一回“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中,白龙马与唐僧等人同受如来加封,列入五圣之一,也说明这一形象绝非可有可无。白龙马由显而隐,究其原因,一方面大概是随着小说情节的丰富和人物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结果。根据明代流行的三种《西游记》,除了吴本外,还有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三种西游小说都强化了孙悟空的形象,将唐代开始单纯的玄奘西行事迹敷演成“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条线索的西游故事。随着孙悟空形象的浓墨重彩,白龙马自然退居配角,以白龙马的“意马收缰”映衬出“归正”的“心猿”孙悟空。由此便可以理解白龙马在取经过程中,除了第三十回勇战黄袍怪之外再无更多笔墨。另一方面安静沉稳的白龙马也寄托了吴承恩的理想精神。曾有学人联系吴承恩所处的时代作出分析,认为吴承恩把孙悟空刻画为有着自由平等观念“童心”的“真人”,把白龙马塑造成稳重质朴有着“常心”的正统形象是联系自身时代作出的选择。在新兴市民阶层兴起的背景下,吴承恩受时代精神的感染欣赏“童心”,却又不得不承认封建正统思想和制度的合理性,认为“童心”应受“常心”制约。
三、火龙与八部天龙马
吴本《西游记》第十五回白龙马在蛇盘山鹰愁涧是一条深谙水性的孽龙,第一百回因“驮负圣僧来西,驮负圣经去东”加升正果,封为“八部天龙马”。但在小说定型前的文本中此马是以“火龙马”的形象出现的。从唐至元至明,此形象经历了“火龙马”到“白龙马”到“天龙马”的淬炼与形变,带有中国民间信仰和印度宗教神格。
王振鹏所绘《唐僧取经图册》中保护唐僧的是“火龙马”,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七出“木叉售马”中龙君自云:“偃甲钱塘万万春。祝融齐驾紫金轮。只因误发烧空火。险化骊山顶上尘”。第八出“华光署保”中,观音为唐僧西游,奏过玉帝,差十方神圣保护唐僧沿路相安无事,其中第九个保官是火龙太子。前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引述唐僧坐骑为一匹老赤瘦马,这里的“赤色”马、王振鹏图册中的火龙马以及杨本杂剧中的祝融、火龙均为吴本《西游记》中白龙马承担的五行“火”的角色奠定基础。
上古时期《山海经》中多次出现龙形火神,《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烛龙与烛阴系为同物,郭璞注“烛阴”云:“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关于烛龙之形象,《大荒北经》谓其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海外北经》谓其身形绵长千里有余,人面蛇身呈赤色。在早期典籍中,除《山海经》外,烛龙神话亦见于《楚辞·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
关于烛龙之原型,姜亮夫认为“烛龙”即“祝融”之音转,烛龙传说是“祝融传说之分化”,“古人依声托事,遂使祝融之音,分化为烛龙,南方炎神遂化为北方寒神。古人束草木为烛,修然而长,以光为热,远谢日力,而形则有似于龙。龙者,古之神物,名曰神,曰烛龙。”作为太阳神炎帝后裔的属神祝融原本为火神,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献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郭注:“祝融,高辛氏火正号。”《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郭注:“火神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火正曰祝融”。《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孙诒让《墨子间诂》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从《山海经》、《左传》、《墨子》等的记载来看,祝融为高辛氏的火正,也就是管理火的神,由此可见祝融的火神神格。无论是蛇身而赤的烛龙或乘两龙的火神祝融均为中华文化与龙图腾原始崇拜的表征,而龙形火神作为集体无意识代际相延,为后来白龙马的成形奠定了神话基因。
除了龙形火神的神话原型,西游故事的流衍与佛教声息相通。小说一百回白龙马因“驮负圣僧来西,驮负圣经去东”加升正果,封为八部天龙马。“天龙八部”是佛教中常见护法神,又名“龙神八部”、“八部鬼神”、“八部众”等,“天龙八部”是为佛护法的八类鬼神,具体名称为:天、龙神、夜叉、乾祗婆、阿修罗、迦娄罗、紧那罗、摩祗罗伽神。《月灯三昧经》记载月光童子天龙八部诸鬼神等,出王舍城向耆阇崛山拜谒如来的场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六》:“今在道场。无量菩萨大众围绕。彼佛众会一切天龙八部鬼神。乃至无量净居诸天。地神。风神。海神。火神。山神。树神。丛林药草城郭等神。皆悉云集。奉觐世尊听受正法。”佛教中的“天龙八部”常以诸鬼神的形式为世尊护法。此外,《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第八》、《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八十》、《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等均有天龙八部与众比丘、菩萨、鬼神静听佛法信受奉行的记载。
《宣室志·法喜寺》记云:“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祗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谓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视之,果白龙也。”作为护法神的白龙“天龙八部”至迟到中唐已经渐趋深入民心,带有祈祀求雨应验的功能,因此无论在民间或文人笔下受到业已翻译过来的印度佛经或中国高僧撰写的各种典籍的影响或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季羡林认为“八部众”中的龙,佛教称之为“那伽”,其实在印度指“蛇”而非龙,前文所述“非法行龙”即马头蛇身。印度人相信蛇有神力,因此便来做佛教的八部护法。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龙与中国龙结合在一起,几经民间敷衍、文人加工、读者想象逐渐融合,使“白龙马”分别具有了中国民间信仰祝融火神和印度佛教护法神的神格,既有腾云吐火的功能又有行云播雨的职责。以此观察吴本《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形象,固然要承认其中蕴涵着作者卓越的独创之功,但也不容否认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创作这一形象中的价值和作用。正如陈寅恪所言:“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说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不得不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故有原为一故事,而歧为二者,亦有原为二故事,而混为一者。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为丁事。”由于原始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和马这种较早驯化动物的偏爱,加之佛教的渗透,投射到文学中便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反复出现在各个时代的文本中,并潜移默化地渗进人们心理结构的深处和民族文化的肌质。
总之,《西游记》中白龙马的形象并非平空产生,它源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古神话与印度佛教中与龙、蛇、马、火神有关的原始意象代代相传给这一形象的问世提供了可能性。从犯法受戮的孽龙到护佐唐僧取经的龙马到修成正果的八部天龙马,从白龙马形象的变迁可窥见变文、俗讲、话本影响《西游记》演变之一斑。荣格曾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清代的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也说了类似的话:“则学问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长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过假长春之笔墨以为之耳。”印度有释迦牟尼骑马朱骔遁世修行,中国有玄奘乘白马西行求取佛法,白马成了人类在苦寻真理的荆棘之途上由俗入圣不可或缺的坐骑。白龙马形象虽然在吴本《西游记》中所占比重不多,但仍以众多的神话原型、宗教元素、文化功能为基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吴承恩“尤未学佛”,但吴本《西游记》的出现,证明作者不仅对旧有的神话原型、宗教元素、文学功能、意义单元进行移花接木,而且将其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从而在妙笔生花中产生出不同寻常的新意,生成新的审美境界。
[注释]
②普慧:《佛教故事——中国五朝志怪小说的一个叙事源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页。
③吴承恩:《西游记》,黄永年,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下同。
⑤⑥(宋)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页,第2页。
⑦(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堂,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页。
⑧⑨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5页,第58页。
[责任编辑:王 源]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书坊对戏曲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CB088)、浙江省社科联课题“江浙宝卷与《西游记》交互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5N046)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冠君(1982-),女,中共中央党校助理研究员;车瑞(1979-),女,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博士后。
I207.414
A
1003-8353(2015)07-01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