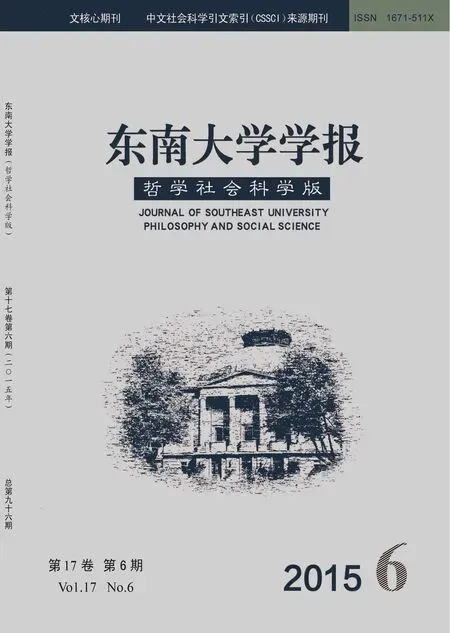自尊、尊重与伦理共同体——“尊严慈善”实现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分析
王银春(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当代美国慈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迈克尔·P.穆迪在《慈善的意义与使命》的中文版序言中满怀信心地说道:“中国将会是21世纪慈善事业发展创新最令人期待和兴奋的地方之一。”中国慈善事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即从个体化慈善模式向社会化慈善模式转型,因之,慈善伦理从传统的“个体美德”范畴向现代“社会伦理”范畴转换已经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卢德之博士在华民慈善基金会内部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现代慈善的三大愿景:“纯粹慈善、尊严慈善、诚信慈善”[1],清晰地勾勒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关于“纯粹慈善”与“诚信慈善”的讨论已非常充分,且已基本达成共识,本文不再赘述,但“尊严慈善”尚未展开过具体阐述与有效论证,本文将就此问题作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一、尊严如何进入慈善伦理
近年来,尊严作为非常重要的伦理概念,在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等领域广泛地被讨论。为什么要讨论尊严问题呢?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一般而言,当人的生理、安全、社交需求满足之后,就开始产生了尊严和自我实现需要。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的生理、安全与社交需要已经逐步得到满足,个体对尊严的需求就愈发重要,因之,关于尊严问题的讨论也愈来愈广泛。然而,脱离具体情境抽象地讨论尊严问题容易陷入空洞形式,而应当将尊严问题置于具体事件、具体情境中加以讨论。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对尊严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安乐死、克隆人以及养老等现实问题上,而慈善伦理中的尊严问题的探讨则少之又少。
慈善本质上是“善”的,但慈善总是“善”的吗?现实生活中,不乏做慈善伤害受助者尊严的情况,比如将“成捆现金摆放在杨柳床头”的照片;在美国纽约街头撒现钞的高调慈善行为;首届在慈展会上展出的受助小女孩只伸出一只小指头的“牵手”照片;学生接受资助之后签订“道德协议”的感恩门事件等等。这些一做慈善就“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的急于索取回报的“作秀”和花钱获取社会评价的“买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受助者尊严最大的伤害。因之,公共舆论中强烈呼吁“尊严是最大的慈善”、“扶贫莫伤弱者尊严”、“捐赠也要考虑受助者的尊严”等。在荷兰郁金香基金会(荷兰最大的慈善机构)总部的院子里,竖立着一座纪念该国慈善家费尔南德的塑像,其底座刻着“一手给予帮助、一手给予尊重”。可见,“尊严”理念对于慈善事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慈善伤害受助者尊严的洞见。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批判慈善“不以劳动为中介,违背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伤害了受助者的尊严”[2] 24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论著中,认为资产阶级的慈善使“被蹂躏的人遭受更大的欺凌”。因为它要求“那些失去尊严、受社会排挤的贱民”放弃对人的尊严要求,还要“去乞求它的恩赐”[3] 43-55;当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一书中认为,“私人慈善产生了依赖性,进而形成人们的恶习,一方面是顺从、被动和谦卑,另一方面是傲慢”[4] 119,不一而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慈善有可能伤害受助者的尊严进行了初步讨论,但尚未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基于慈善是一种非对等的施与关系,受助者的尊严问题更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尤其在当代尊严价值不断凸显的社会语境中,构建“尊严慈善”现代慈善理念意义尤为重要。那么,何谓“尊严慈善”?易言之,“尊严慈善”的内涵是什么?
为准确而充分地探讨相关问题,需要对“尊严”观念在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稍作梳理。“人格尊严”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其内涵在西方世俗与宗教传统的交互演进中不断深化与拓展,主要包括两种范式:首先是外在尊严范式。其一,尊严来源于上帝。在西方思想史上,“尊严”具有深厚的宗教渊源。西方宗教传统始终主张“人格尊严”建立在神学命题之上,即上帝按自己的映像创造了人类。“尊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典中出现的次数较少。希伯来文“尊严”通常指其高贵的品质或是在共同体中的特殊地位。其二,身份或地位尊严。在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与神学家阿奎那的《神学概论》(Summa Theologiae)中,尊严意指身份或地位尊严(the merits dignity),即你的出身、地位、官位决定了你配享某个层级的尊严,属于大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特权尊严[6] 136-147。霍布斯则将尊严与力量联系起来,认为力量大小与财富多寡决定是否配享尊严[7] 63-64。事实上,无论“尊严来源于上帝说”,还是“身份或地位尊严说”都属于外在尊严范式,且其中身份与地位尊严的明显缺陷在于将普通人尤其弱势群体排除在尊严范畴之外。
其次是内在尊严范式。(1)理性尊严,主张人的尊严是独立于直接的自然规定,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具有正确运用理性的能力与义务。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理性是灵魂中最高尚的部分,是神赐予的物质[8] 228-252。亚里士多德在《优台谟伦理学》中将尊严界定为一种美德,他认为人因为理性获得了尊严,因为理性为个人和社会生活带来了秩序。[9] 17总体看来与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相去甚远。(2)价值尊严。“人之为人”的普遍内在尊严范式。文艺复兴时期,皮科在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的《论人的尊严》一文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格尊严”的概念,并将“个体自由”视为人的尊严的核心[10] 25。康德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可视为对霍布斯尊严概念的一种回应,认为人是道德自主与立法主体,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人是无条件的内在价值,是尊严的来源,是西方人格尊严理论中的不可动摇的基石[11] 53。二战期间,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为了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找到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安全之所,转向了人类意识的内心世界,认为人格尊严等同于人选择和创造自我的自由,不受限制的极端自由成为所有价值的唯一基础,成为极端主观主义的人格尊严理论[12] 1-27。尊严是关系中的尊严,具有主体间性,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出发,个体尊严的实在性将会受到质疑。(3)权利尊严。关于尊严与权利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迈尔与帕伦特为代表,认为尊严是人的一项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详尽地讨论了尊严与自由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国内伦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甘绍平也持此观点[13] 85-92。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格尊严是权利的基础”,并认为人格尊严概念同时包括外在经验与内在逻辑两个方面[13] 85-92。目前,学界主导性的观点还是倾向于认为“尊严是人的一项权利”。20世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都明确了人格尊严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开篇指出:“对所有人类家庭成员的内在尊严和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承认,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第一款则肯定了“所有人类存在者生而自由,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社会中因各种不同缘故而导致的对人的歧视总是伤害着人的人格尊严或普遍尊严。[14]受助者尊严的守护与实现要求我们拒斥以财富多寡与权力大小为衡量标准的身份或地位尊严。而理性尊严、价值尊严与权利尊严等内在尊严观念都是受助者尊严的多种思想来源。宗教中的尊严观念虽然有赖于上帝,但其衍生而来的每个个体生而具备平等的尊严是“尊严慈善”的重要理论根据。
从以上对尊严在思想史的追溯不难发现,“尊严”或“人格尊严”的主体是人,即人的尊严,离开了人,尊严则无从谈起。国内学者王泽应教授认为人的尊严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由此所形成的道德主体意识、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的总和,它意味着人是不能任意处置和被当作工具器物来对待的,它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值得尊重的目的性意义,必须而且应当得到来自人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尊重和善待”[15] 71-76。他从“人性尊严、人道尊严、人品尊严、人格尊严和人权尊严”五个维度完整而系统地考察和把握人的尊严。社会心理学领域将“尊严”阐释为“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具有的、应该被自己、他人所尊重、且不容侵犯的属性,尊严的属性参与人际互动,并在其中彰显出来,即表现为尊重对方的主动行为和接受对方尊重的被动结果”[16] 1136-1140。有学者认为“自尊、受尊重与尊重”体现了尊严内涵的三个重要维度,其中“尊重”和“受尊重”将尊严规定在人际互动的情境之中[16] 1136-1140。此种尊严概念主要在主体间性或关系性维度中进行阐发,体现了尊严的人际互动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主体性权利的超越,更具社会意义。
上述对尊严内涵的阐释都存在合理之处,只是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学者们要么从历史维度对尊严内涵理解的范式做了历时性的梳理;要么基于当代尊严的内涵的诸种要素,从横向维度出发完整系统地考察了尊严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本质;要么突出“尊严”的心理与关系的维度。这些都为本文把握与考察“尊严慈善”理念提供了有益视角与概念性框架。我们认为,“尊严慈善”首先要坚决摒弃古代政治尊严范式,即以权力与财富作为衡量标准的地位或身份尊严,而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人的普遍性尊严,即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是人类存在者,他或她就应当得到应有的人格尊重,其人格不得被侵犯。每一个有着自主能力的人类个体都具有他的不可侵犯、不可凌辱的(人格)尊严,它要求得到社会和他人最基本的尊重。[17] 17-20“尊严慈善”主要指慈善主体尤其是受助者不能被任意处置或当作工具器物来对待,它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值得尊重的目的性意义,必须而且应当得到自己、施助者以及社会的尊重和善待,同时,在慈善关系中的参与主体之间应当相互尊重。但是,如何实现有尊严的慈善呢?易言之,“尊严慈善”的现实性、实在性何在呢?
二、自尊与尊重:受助者尊严实现的主体间性
在如何实现“尊严慈善”问题当中,受助者尊严的实现无疑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受助方往往是由极度贫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精神病人、重大或长期病患者、灾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社会流浪人员等组成的弱势群体。社会中漠视甚至践踏弱势群体人格尊严的现象时有发生。慈善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即为人与人之间在财富或者是能力上的差异,而财富或能力的不平等就容易导致人格的不平等。同时慈善作为一种财富或者劳动能力的单向度施与行为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时代业已普遍确立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正义”,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施助方容易产生地位的优越感,导致傲慢与偏见,歧视或蔑视受助方,致使受助方的“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受到侵害。受助者的尊严是根植于人的族类特性、人的理性与人的道德能力而自在生成的显著属性,它是超越种族、性别、天资、财富、社会地位之上的人普遍具有的属性。受助者与施助者同样作为人之为人的类存在者,同样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理性与道德能力,因此在人格上享有平等地位,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格尊严,它不因受助者的财富、天资、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原因而有所区别。关于人的歧视问题的核心都是围绕权力大小与财富多寡展开的,在慈善关系中张扬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尊严,则意味着拒斥以不平等为核心的身份地位尊严。在慈善领域“保持受助者的尊严”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原则。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在健康、学业与工作等方面遇到困难时,普遍具有寻求社会救助体系帮助的意愿。但是大多不愿牺牲个体尊严以换取他人救助。慈善若使受助者心灵受到伤害,同时受到伤害的也会是慈善救助事业本身[18]。总之,受助者的尊严内在地要求“给予”的同时要做到“不伤害”,而这需要在受助者与施助者的关系互动中完成。
受助者尊严问题的前提在于受助者自身具有自觉的自尊意识。自尊与自尊意识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日常生活与学术意义上的自尊概念不同。在现代汉语中,自尊是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节,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19] 1671,这属于日常生活意义上自尊概念,主要描述一种防御机制或防御方式。说某人拥有很强的自尊,意味着他/她将无法忍受任何可能会羞辱他或她的言行。西方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尊”是指个体内部的尊重,是一个人希望自己在不同的情景中具有实力、能够胜任、充满信心、独立自主[16] 1136-1140,简而言之,是行为主体的自我总体的积极评价,包括情感与信念两个维度。可见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尊”概念,是一种自信的力量。受助者的“自尊”概念应该包含“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对实现自我意图能力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对自我不容侵犯与不被侮辱的要求。只有当受助者具有自尊意识之时,才会产生自尊需要,反之,则不会有自尊需要,且也无法获得受侮辱或伤害的情感体验。在米德看来,“意识”有多种用法,既可用来表示某些内容的可接近性的“意识”,也可表示某些内容本身的同义词的“意识”[20] 29。不言自明,受助者的“自尊意识”主要是作为自尊本身同义词的“意识”,是由个体经验决定的内容。自尊意识或自尊感由“自信”与“自爱”两个相互交织的部分组成。自尊国际协会的理事长布兰登博士在《自尊的六大支柱》一书中认为在实践中应从六个方面培育自尊意识:其一,有意识的生活或积极地生活;其二,自我接受;其三,自我负责;其四,自我维护;其五,有目的的生活;其六,个人诚实,且这六大方面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21] 242-243,221其中自我接受、自我负责、自我维护与积极生活对受助者自尊意识的培育至关重要。贝蒂·B.杨斯在《自我尊重的六个关键要素》一书中认为,依赖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个体经验,自尊可被加强,也可被腐蚀[21] 242-243,221,可见,受助者特殊的情感体验会对自尊意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自尊感愈强,对侮辱与伤害的情感体验更为敏感,当施助者在眼神、表情、语言或行为中表现出“蔑视”的姿态①冯特分离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姿态(gesture)”观念,在某种情境中,存在一系列态度和运动,而“姿态”可等同于这些社会活动的开端,作为某种刺激会导致其他活动者做出反应。在达尔文看来,姿态具有表达情绪的功能。冯特则认为姿态并不发挥表达情绪的功能,而是刺激另一些生物做出反应的工具。姿态既是社会活动的组织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这种组织的非常重要的成分。[20] 45-48时,受助者就会感到自尊的情感受到了某种伤害。自尊感弱的受助者对“侮辱”或“伤害”的情感体验相对就比较迟钝。受助者的自尊意识受自身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的制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与文化素质愈高的受助者,自尊意识愈强,而受教育程度与文化素质愈低的受助者,自尊意识愈弱,甚至会陷入自尊的无意识状态。
受助者内在的“耻感”意识与自尊呈现出某种互动关联。由于人既是主体性存在,又是对象性存在。当“我”(受助者)在他人面前展现了那样一种存在状态会感到羞愧难当。在慈善关系中,将自身的缺陷展现在他人面前之时,就会产生羞耻之感,进而感觉到个体尊严受到了伤害。“羞耻感是对我们自己的感觉的一种形式,因此属于自我感觉的范围,这是羞耻感的实质。”[22] 544羞耻是一种自我承认,它是“意向性的,它是对某物的羞耻的领会,而且这某物就是我。我对我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22] 282比如近年来,诸多爱心助学活动,大多采取大张旗鼓地将受助对象的贫困境况与困顿遭遇通过影像资料等方式在公众中予以传播,然后再举行一个“展”贫穷“显”爱心的现场仪式[24],当捐赠者进行轰轰烈烈慈善捐赠活动的同时,受助者的隐私也一览无余,赤裸裸地袒露在公众面前,这无疑会使受助者产生羞耻感,对其尊严是一种伤害甚至是羞辱,违背了慈善活动的本真意义。所谓“予人者骄,受人者畏”,讲的就是此理[24]。受助者对自身的存在状态,对“我所是”体验到羞耻感,而这种羞耻感的体验是通过他人(施助者、慈善活动的相关参与者或者旁观者)之境所呈现的,因为“我通过我的经验经常追求的,是他人的感觉,他人的观念,他人的意愿,他人的个性。”[23] 282当受助者“转回自我”之时,在施助者等他人那里,因为展示了“我”弱小、无能较为阴暗的一面而感到羞耻,因为“我”总想展现给他人是“我”的美好生存状态:伟岸、强大、自信、有能力,然而“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且人又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受助者所追求的他人的“承认”瞬间坍塌,耻感油然而生。“我……在他人面前的自我呈现,我对我的真实处境,仅仅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作为人的尊严无法得到认肯。”[25] 87-92“耻感”指向人的尊严,并且要维护人之存在的尊严。一般而言,个体的自尊心与耻感意识呈正相关关系,即自尊心愈强者,耻感意识愈强,反之亦然。“耻”是对一个人自尊的揭示。只有当个体具有耻感意识时,才会在意尊严及其对人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耻感的强烈程度标志着一个人对尊严的理解程度[25] 87-92。可见,受助者如果在慈善活动中因“我”之“弱小、无能”的呈现,耻感意识愈强,其自尊心愈强,反之亦然。
受助者的尊严要求来自与受助者发生关系的他者的尊重。尊严具有关系性、主体间性特征,受助者的尊严获得与实现有赖于与受助者发生关系主体的尊重。康德认为一个人类存在者作为一个人格,即作为道德实践理性的主体具有尊严,并据此要求从世界上的其他理性存在者对自己尊重[11] 211。尊重是对尊严的回应,尊重主要表现在:首先,承认我们自己对道德共同体平等成员负有平等的责任,并提出要求的主张与权威;其次,其提出的要求是关于彼此如何的相互对待方式[26] 125。在慈善道德共同体中,与受助者直接发生关系的主体主要有施助者、慈善机构等,间接发生关系的有政府、公共舆论以及具体情境中的旁观者等。事实上,与受助者直接发生关系的主体——施助者——的尊重对受助者尊严的获得具有决定作用。达尔沃将尊重区分为评价尊重与承认尊重,评价尊重意味着人们应得或获得尊重的理由在于其行为或品格,承认尊重的对象不是优点和功绩,而是“人之为人”的绝对价值与内在尊严,是在关系中彼此承认并如何相互对待的方式[26] 125,当然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在慈善活动关系中,对受助者的尊重显然属于承认尊重,我们尊重受助者,诚然不是因为他/她的优点和功绩,而是因为他/她是一个人,这里起作用的不是评价而是承认。尊重关注态度与行为,尊重受助者时,倾向于调节与受助者关系中的态度与行为,倾向于去做受助者尊严要求做的事。“好的礼节”或者“礼貌”的核心功能是表达尊重[26] 150,谦卑而不自大,平和而不傲慢地为受助者提供帮助,如,富人对向他求助的流浪汉友善拥抱;或者保护受助者的隐私;甚至巧妙地采取特殊的方式维护受助者的尊严,如南非开普敦流行的流浪汉可以“购买”慈善性质物品的“街边店”等[27] 50。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尊严是自我给予的,受助者的尊严获得还需要受助者接受慈善捐助而不依赖慈善捐助,更不能任意挥霍慈善物资,而是应该借助他人的援助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真正尊重。
尊严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人们彼此对待的可允许性方式,即我们必须以某些方式对待人们,而绝不能以另外的某些方式对待人们。受助者尊严的真正获得意味着不受“伤害”与“侮辱”,“伤害”或“羞辱”与蔑视形式也就是拒绝承认的形式紧密关联。在“身份或地位尊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物欲社会中,受助者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尤其施助者态度、语言或行为上的“轻视”或“羞辱”。比如在《孟子·告子上》中的“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等,都是蔑视的表现形式。霍耐特认为关于自我未受到善待的描述中主要表现为蔑视形式,其所含的意义就是“人的特殊脆弱性”。他将蔑视区分为“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深深扎根于“肉体虐待”的经验中;第二种形式主要指因个体遭遇社会权利排斥导致的道德自尊削弱;第三种形式表现为对个体或集体的生活方式的贬黜,其中与慈善相关的主要是“侮辱”形式。蔑视经验使个体遭遇伤害体验,具有将个体同一性带向崩溃边缘的可能性,正如传染病危及人的肉体生命一样。[28] 140事实上,相对于物质援助而言,精神鼓励更为重要。物质援助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救助,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贫困者生活的困顿。在物质援助的过程中,如何给受助者自信、温暖与阳光的力量,尤为重要。因为困顿者最为恐惧的,往往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匮乏,更是他人的嘲弄[29]。根据康德尊严学说的要求,施助者应当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把受助者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来对待,而且应当将不得蔑视和伤害他人作为自身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30] 473-474黑格尔和米德都认为蔑视的经验隐含在人类主体的情感生活中,而且成为社会对抗和社会冲突,即“为承认而斗争”的动力之源[31] 140-146。事实上,慈善是一种社会进化、促进公益的基本方式,还是全世界人们尝试当事情向谬误方向发展,集众人之力使其良善的媒介[31] 1。如果因为施助者对受助者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进行否认,对其基本人权进行公然的贬低,使受助者经历某种受“蔑视”的经验,那么慈善就不再是“善”,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反而成为可能引发社会对抗与冲突的动力之源。但是社会蔑视经验激发主体进入实际斗争与冲突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对于此类问题黑格尔和米德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霍耐特认为根源在于缺少“引导功能”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即由社会蔑视经验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而感到愤恨引导主体进入实际斗争或冲突[31] 140-146。那么,当受助者的社会蔑视体验带来消极的情感反应,以致他们感到愤恨的时候,就会促使慈善主体之间进入实际斗争或冲突。当然,在慈善关系中,不公正的蔑视及其引发的斗争与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仅仅具有可能性,所以慈善主体之间的实际斗争属于极端情况。
三、慈善机构:受助者尊严实现的伦理共同体
受助者尊严的获得,无论是要求受助者如何具有自尊意识,或者施助者以及社会公众如何不蔑视、不伤害、尊重受助者,都是基于慈善主体的内部道德自律,具有不确定性与脆弱性。因此,我们不仅要从慈善主体内部寻求受助者尊严获得的主观条件,也要从外部寻求其现实性的客观条件。然而,受助者尊严真正获得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易言之,受助者尊严实现的外部可能条件是什么呢?共同体是人的存在方式,任何人都是生活的共同体之中,没有人是不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黑格尔认为共同体是高于个体的存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被视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且认为个体只能在共同体中存在,关系生存是人的本质生存。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32] 60。慈善活动显然属于一种关系性活动,慈善主体,无论是受助者还是施助者,只能在共同体或社会中生存。根据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标准,共同需要或相互依存的结合是共同体的标志,而相互分离甚至对立是社会的标志。共同体的结合,既指利益的结合,也指情感的结合,而社会形态的分离其根源在于利益的分离,而结合是通过契约将利益冲突或利益对立的双方或各方的一种结合,正如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结合。[33] 67-68一般而言,受助者是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竞争性“社会”中,根据“优胜劣汰”法则淘汰下来的“边缘的、孤独的、弱势的”单个个体,因此他们要想获得力量与尊严,只有基于共同的利益与情感需要,相互依存、相互联合成为一个群体。可见,受助者是存在于共同体而不是社会中。那么,受助者尊严实现的外部可能条件只能从共同体中寻找,然而抽象共同体的实在性需要通过某种具体形式予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慈善机构则是慈善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合理性可以通过回顾共同体概念发展的历史窥见一斑。
“共同体”概念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希腊城邦被现代学者视为共同体思想的原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古希腊的城邦就是某种共同体[34] 3,当城邦的所有成员都在追求某种共同的善,就可称之为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是实现善的手段。柏拉图则认为城邦起源于满足个体能够“自足”的生活需要。因之,个体之间相互协作,为整体利益而与他人分享利益成为城邦的立法原则。[8] 58可见,共同的“善”与城邦的“自足”是古希腊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与最高目的。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与“社会”相对的,在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35] 53,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是公民社会。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张力,“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35] 54。但是在本质意义上却存在某种同一性,即“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关系之中”[35] 52,此种社会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36] 52。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的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该称为‘共同体’。”[36] 65-66反之,“社会”则意指以价值或目的理性为驱动的利益平衡或联系的社会行为[37] 29-34。可见,情感与精神上的归属感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所强调的。当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主要指发端于北美的“共同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思潮,虽然在源头上与希腊哲学和现代社会学两个共同体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此时,“社会”不再是“共同体”的对立面,已转化为“个人”和“自由”[37] 29-34,其核心主张为“共同善先于个体权利”。
通过回顾“共同体”概念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慈善机构符合伦理共同体的诸多特征:(1)慈善机构的使命与意义是追求共同的“善”,即为了其成员所过的好生活;(2)受助者为了“自我持存”,只有融入于慈善机构之中才能“自足”;(3)慈善主体尤其受助者在慈善机构中能感受到成员感或归属感;(4)施助者与受助者物质与精神共享的情感联结,以及受助者、施助者与慈善机构物质与精神共享的情感联结;(5)慈善机构相对于慈善主体尤其受助者具有共同性与整体性。伦理共同体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甚至人类共同体等。而慈善机构是伦理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同时,慈善机构亦是黑格尔意义上具有伦理性的同业公会。开放性的同业公会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黑格尔看来,同业公会中出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普遍性内在于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本身将普遍性作为其意志与活动的对象,因此,“伦理性的东西作为内在的东西就回到了市民社会中,这便是同业公会的规定”[2] 248。根据这一规定,同业公会在公共权力监督之下享有以下权利:(1)照顾内部成员的切身利益;(2)接纳会员的标准在于个体是否具有某种技能与正直等客观特质;(3)关心会员,防止特殊偶然性,并负责给予给养,使获得必要的能力。[2] 249黑格尔认为同业公会与个体及其特殊需要密切相关,是“作为成员的第二个家庭出现的”形式[2] 249,因而以情感为纽带的伦理关怀是同业公会的本质规定。在黑格尔看来,同业公会可以把原子式的市民组织起来在其中培养伦理道德精神。他在谈到同业公会的时候,不仅指经济组织,还想到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和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城镇委员会[2] 274,310,易言之,黑格尔意义上的同业公会主要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无疑属于社会组织范畴,它作为联结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中间环节,从组织特征来看具备上述同业公会的“三项权利”,且其伦理属性更为明显,因为它诞生与存在的使命与意义就在于救助与关怀其共同体的成员(受助者),因此,慈善机构无疑是同业公会概念客观化的一种现实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慈善机构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同业公会,是伦理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形式。
但是,黑格尔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对抗是市民社会的根本缺陷,通过慈善方式解决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祸害只是越来越大”,且与个体独立自尊的感情相违背,“如果由富有者阶级直接负担起来,或直接运用其他公共财产(富足的医院、财团、寺院)中的资金,来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他们通常生活方式的水平上,那末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以保证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2] 245。并以英国慈善活动的结果为例加以证明,他认为慈善是“对付贫困”、“对付丧失廉耻和自尊心”以及“对付懒惰和浪费”等等的最直接的手段,其结果是“使穷人们听天由命,并依靠行乞为生”。[2] 245黑格尔对慈善自身局限性的批判主要在于:(1)不以“劳动为中介”,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对贫困问题解决的非彻底性;(2)主观领域还容易滋生“懒惰”、对个体的独立与自尊造成伤害。显然,黑格尔对慈善的批判是深刻且有力的。但是黑格尔批判的是前现代社会的慈善模式,而现代社会慈善模式正是要克服这样的缺陷。当然“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在市民社会内部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克服的。因为“物质需求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市民社会的根本矛盾。因为“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2] 245。笔者认为,希求慈善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其他方式彻底解决市民社会的贫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僭越。但容易滋生“懒惰”或对个体尊严造成伤害,则是现代慈善模式需极力予以克服的,而且这是慈善模式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克服这两大缺陷的根本方法就是慈善也要以“劳动为中介”或者在施助方与受助方间产生中间环节,那么,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慈善模式,尤其是致力于实现社会与经济双重目标的“社会企业”①目前,社会企业还没有被官方或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但通行的看法是社会企业具有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特性的新的实体企业,经济特性或企业特性主要表现在:(1)可持续地生产商品和/或销售服务的活动;(2)高度自治;(3)有显著的经济风险;(4)最少数量的带薪雇员。社会特性主要体现在:(1)让某个共同体受益的明确目的;(2)由一群公民发起行动;(3)拥有不是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4)具有参与性质,要求受到活动影响的所有人都参与;(5)有限的利润分配。[38] 112-120形式是一剂良方。
自由主义者则走得更远,试图将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之外,成为社会极力想要抛弃的“无用的、过剩的多余者”。马尔萨斯认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匮乏、贫困、贫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从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阶级中有的比较富裕、受过教育、有道德,而另一些阶级则比较穷苦、贫困、愚昧和不道德”[39] 484,所以,他认为穷人即为“过剩人口”,是“多余的”,并引用某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其原因在于穷人“在出生前没有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纳他”,所以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不在于使“多余的”、“过剩人口”变为“有用人口”,而在于采取办法限制过剩人口。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尔萨斯认为“慈善事业和济贫金是无意义的”,“济贫机构给穷人工作同样是毫无意义的”[39] 484-485。但是,《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开篇指出:“对所有人类家庭成员的内在尊严和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承认,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且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显然,自由主义的上述主张与人类基本的人权精神相违背的。
共同体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则认为:一般而言,个体遭遇匮乏具有某种普遍性,即“每个人在他的一生的自然循环中都要遭到匮乏”,而遭遇匮乏的原因有主观上的“任性”,即“挥霍成性,从而毁灭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的安全”,还有“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②黑格尔认为造成个体匮乏的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主要指:“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人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2] 211,都可以使个人陷于贫困”[2] 242-243,是客观原因。而遭遇匮乏的众多个体的联合就会形成弱势群体,即弱者共同体。当然,弱势群体属于相对意义上的概念。慈善机构存在的意义与使命就在于使受助者免于成为“孤独的、弱势的、多余的”个体,而是成为对人类共同体起着基础性作用或构成性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成员的家园。在慈善机构中,受助者已经产生一种“伦理情绪”,即对个体权利、自由与共同体整体利益一致性的感受与体验,而这种感受与体验会使受助者对慈善机构产生归属感,从中获得在其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竞争性组织中所不能获得的力量与尊严。黑格尔认为同业公会的成员属于一个整体,而同业公会(即这个整体)本身属于普遍社会的一个环节,且其成员的意志与活动都致力于促进整体的无私目的,并获得外部的承认,因此同业公会的成员在他所在的等级中享有他应有的尊严[2] 249。而且,同业公会是除家庭以外,构成国家的基于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根源[2] 251。“公会精神”具有转变为“国家精神”的潜能。慈善机构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同业公会表现形式,与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中介”[2] 197,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主观为己,客观为他”的不自觉的必然性相区别,是一种自觉的和伦理的必然性[2] 251。因此,慈善机构将慈善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其中的成员都获得了力量与尊严,尤为重要的是,受助者尊严实现的同一性获得了可能的外部条件。
总之,慈善机构作为受助者尊严实现的伦理共同体的理由在于:首先,受助者只有在慈善共同体中才能感受到与他者否定性环节中的力量。共同体本身包含着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中弱者或“孤独者”只有融入某个共同体当中才能获得某种力量,才有获得尊严的可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力量都存在个体之中,而不在抽象的共同体之中。个体一旦加入某个共同体,其自身就成了共同体的力量来源之一,尽管力量或大或小。其次,共同体是个体尊严与价值的来源,黑格尔通过对古希腊伦理共同体通过战争、劳动、生殖这些环节,帮助个体战胜了人与超越性的神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从而得以取代神成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来源。因为在共同体之中,自然生命个体被赋予了区别于动物的另外一种超越自然生命、灵性的或精神性的自我,使其具有自然生命所不能给予的价值、尊严、权利。正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说,共同体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相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宗教上的神圣性,并使人成为人而非动物。共同体规定了个体的价值、尊严、权利与本质。当然,个体的尊严不可能来源于抽象的共同体之中,尊重个体的共同体才能让个体获得尊严。在慈善机构之中形成慈善主体相互尊重的氛围也是受助者尊严实现的重要条件。关于这一点,文中第二部分已作过充分阐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慈善机构只是受助者尊严的真正获得或实现的外部可能条件。
[1] 卢德之.2011年9月4日在华民慈善基金会内部工作会议的讲话[R] .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揚,张企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 潘乾.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4]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褚松燕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 Pope Leo XIII.Rerum Novarum:On Capital and Labor Encyclical[EB/OL] .15 May 1891,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Leo13/l13rerum.html.
[6] Charles Trinkaus.The Renaissance Idea of the Dignity of Man[M].Philip P.Weiner,ed.,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IV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1973.
[7] Thomas Hobbes.Leviathan,X.,Richard Tuck,e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8]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9] Aristotle.Eudemian Ethics[M].2nd edn.,1221a.8,trans.Michael Woo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0] 皮科.论人的尊严[M].顾超一,樊虹谷 译.吴功青 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 Sartre.The necessity of freedo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3] 甘绍平.作为一项权利的人的尊严[J] .哲学研究,2008(6).
[14] 世界人权宣言[R/O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udhr/index.shtml#ap.
[15] 王泽应.论人的尊严的五重内涵及意义关联[J] .哲学动态,2012(3).
[16] 黄飞.自尊、受尊重与尊重[J] .心理科学进展,2010(7).
[17] 龚群.论人的尊严[J] .天津社会科学,2011(2).
[18] 许小峰.扶贫莫伤弱者尊严[N] .人民日报,2014-10-31.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0] 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M].霍桂桓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1] 马前锋,蒋华明.自尊研究的进展与意义[J] .心理科学,2002(2).
[22] 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上)[M].刘小枫 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3]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24] 呵护受助者的尊严是献爱心的最高境界[EB/OL] .http://hlj.rednet.cn/c/2012/07/19/2682744.htm.
[25] 王峰.耻感与尊严[J] .道德与文明,2010(4).
[26] 斯蒂芬·达尔沃.第二人称观点:道德、尊重与责任[M].章晟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7] 南非“街边慈善店”,让流浪者有尊严地受助[J] .中国社会组织,2014(4).
[28]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9] 受助者的尊严[N] .工人日报,2012-07-15.
[30]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李秋零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1] 佩顿,穆迪.慈善的意义与使命[M].郭烁 译.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2013.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龚群.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5]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6] 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7] 陈越华.伦理共同体何以可能——试论其理论维度上的演变及其现代困境[J] .道德与文明,2012(1).
[38] 雅克·迪夫尼.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概念与方法[J] .丁开杰,徐天详 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12-120.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