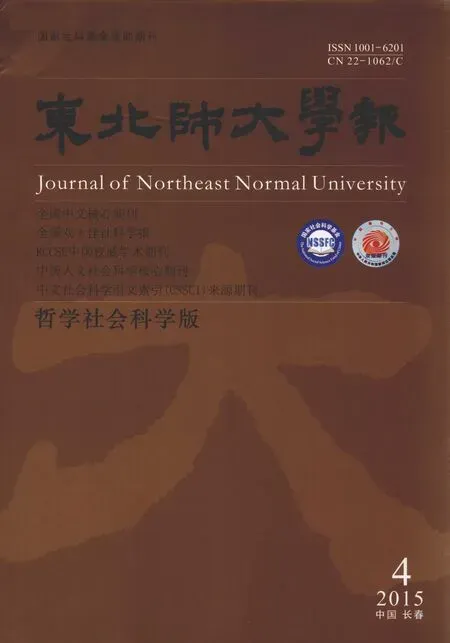伦敦意象的女性主义书写
——《伊芙琳娜:少女涉世录》中的都市想象体系探究
杨 岸 青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伦敦意象的女性主义书写
——《伊芙琳娜:少女涉世录》中的都市想象体系探究
杨 岸 青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弗朗西斯·伯尼的《伊芙琳娜:少女涉世录》常作为讲述女性成长话题的社会风俗小说受到关注,却很少被视为女性都市文本加以研究。本文拟将《伊芙琳娜》置于城市文学和女性主义交叉视阈之下,探讨女小说家如何作为话语主体通过女主人公的伦敦奇缘批判和解构都市中的男权话语,进而建构女性主义的都市意象体系。
弗朗西斯·伯尼;都市想象;女性主义书写
一、引 言
18世纪英国女小说家弗朗西斯·伯尼 (Frances Burney,1752—1840) 的成名作《伊芙琳娜:少女涉世录》(Evelin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sEntranceintotheWorld)于1778年1月出版并轰动一时,这部书信体小说惟妙惟肖地叙述了乡下孤女伊芙琳娜·安维尔来到大都会伦敦并在尴尬、羞辱等磨难中成长的经历。《伊芙琳娜》常作为早期社会风俗小说受到关注,批评界对该书议论较多的是女性在社会成长的话题。然而,这样一部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却很少被当作城市文学的样本加以研究。在西方,文学与城市的渊源关系虽然久远,反映城市生活的城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虽然早在11世纪就已存在[1],将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进行交叉和渗透并形成城市文学批评则迟至20世纪初,因此小说未被纳入城市文学研究也情有可原。在尝试对该小说进行城市文学解读时,还要兼顾女小说家伯尼作为话语主体直接参与都市文本创作的事实。威廉·黑兹利特 (William Hazlitt) 认为“伯尼在观察人物时总是带有强烈的性别意识”[2]。雷金纳德·约翰逊 (Reginald Johnson) 也认为《伊芙琳娜》虽然师法理查逊等前辈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却“另辟蹊径——表达了女性主义人生观”,显然是“由一个女子写给女人们看的”[3]。的确,伯尼以女主人公伊芙琳娜为视角,透过其书信表达自身对女人与都市关系的女性主义认识。鉴于此,本文拟将《伊芙琳娜》作为一部女性都市文本进行研究,从女小说家的性别视角出发,探讨伯尼如何通过女主人公都市生存体验,暗中消解男权话语支配的都市意象,分析作者如何隐晦阐释都市文化并进而构建赋有女性主义内涵的都市想象。
二、批判与解构男权话语主导的都市意象
伊芙琳娜对伦敦的第一印象充满惊喜和欢快,刚到伦敦的那个周末通过乡下少女轻快俏皮的笔端显得五光十色、热闹非凡。伦敦的绚丽街景和新鲜、时髦的文化生活令人目不暇接,自己“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4]20。然而,女主人公走马观花看到的只是伦敦光鲜浮华的外表,少女在都市中浮光掠影般的畅游也并不代表伦敦已经接纳了她。伊芙琳娜真正介入都市生活并遭遇挫折始于斯坦利夫人举办的私人晚会。在晚会上,伊芙琳娜断然拒绝了奇丑无比、行为猥琐的拉威尔的跳舞请求,转而接受了相貌英俊、温文尔雅的奥威尔伯爵的邀请,结果因违反舞会游戏规则受到轻视。在伦敦社交圈糟糕的首秀之后,女主人公逐渐深入到大都市生活的内在肌理,城市的阴暗面也一点点暴露出来。
都市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劳拉·布朗(Laura Brown)在其《现代性的寓言》(FablesofModernity) 中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指出现代性和都市化发展的必然联系。谈到现代性,自然离不开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政治经济和公共空间。但首要的是,现代性是“一个专属男性的领域”[5]。因此,作为现代化产物的都市理所当然处于男权话语权威的统治之下,女性则被边缘化,沦为都市中的弱势群体。在18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中,伦敦往往扮演邪恶角色,是吞噬人的地方,单纯的老实人常常成为牺牲品。而在这部女性小说中,伯尼则利用伊芙琳娜的视角凸显伦敦是女性地狱的意象。这是一个充斥雄性荷尔蒙的丛林,是男人猎艳寻芳之所,到处闪烁着对女性虎视眈眈、不怀好意的眼睛,处处都是女性的陷阱。在男性代表的都市之中,女性变成男性欲望的消费对象;在伦敦的欲望景观中,女性成为被审视与观照的他者和客体。自始至终,除了伊芙琳娜心上人奥威尔伯爵之外,伦敦城里几乎没有什么好男人。活跃在她周围的是丑陋的公子哥儿拉威尔、死缠烂打的纨绔子弟克莱蒙特·威洛比爵士、虐待狂米尔文上校、伪绅士史密斯先生以及俗气势利、言行粗鄙的中产阶级代表布朗顿等等。上流社会的品味堕落低俗,对女性的歧视和亵渎比比皆是,甚至充满暴虐色彩。为戏弄伊芙琳娜的外祖母杜瓦尔太太,威洛比爵士纠结同伙大搞恶作剧,假装拦路抢劫并将老太太摔倒沟里。又比如,上院议员莫顿伯爵和下院议员卡沃里先生为了打赌,竟让两个80高龄的老太太赛跑以从中取乐。这就是女主人公视野中男权话语权威治下的都市生活和都市情趣。
为强化都市中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挤压和排斥,伯尼有意将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来自乡下、没有私产、没有家庭支持的孤女。当这样一个身份暧昧的少女到达伦敦踏入雄性丛林之后,陷入了形形色色的花花公子和浪荡子们的调戏和骚扰之中,几乎不设防,简直是步步惊心。一次,伊芙琳娜随外祖母和娘家亲戚布朗顿一家去公共游乐园沃克斯豪尔花园游玩时,被布朗顿姐妹撇入一条黑暗小巷,遭到一群醉鬼纠缠,摆脱醉鬼后又被一帮公子哥儿调戏。最后总算遇到威洛比爵士解了围,结果不怀好意的爵士以保护为借口又把她带到另一个更黑的巷子里进行骚扰。这个“才出狼窝又入虎穴”的情节让伦敦彻底变成女性地狱的都市符号。拖维·芬斯特 (Tovi Fenster)认为,即使在今天,在男权文化构建的城市空间中,女性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住家这样的私人空间,而公共空间则为男性所专属。这就意味着女人“不可以独自在街道、花园和公共场所闲逛”[6]。艾伦·鲁宾逊 (Alan Robinson) 经考证指出18世纪伦敦的规矩要求“未婚女子在外出时必须由一位女伴或一位男伴陪同”,否则轻者招致“言语或身体的骚扰”,重则被视为娼妓[7]31。换句话说,街头的独行女子肯定不是良家妇女,会遭到男权话语的鄙视和排斥。伊芙琳娜在马里乐伯恩公园看烟火后的遭遇正好为此做生动脚注。女主人公受烟火惊吓后和其他人走散,在受到纨绔子弟骚扰时慌忙向两个过路女子求救,后来发现这两名女子实为妓女,在并肩行走时又偶遇奥威尔伯爵,伊芙琳娜感到非常尴尬与羞辱。在伯爵第二天登门拜访时她迫不及待地向他澄清自己与那些妓女毫无瓜葛,而后者也委婉地告诫她交友小心。街头游荡的妓女、伊芙琳娜的尴尬以及伯爵的告诫等情节将男权主义都市话语体系对女性空间归属的规约和挤压揭示得淋漓尽致。
《伊芙琳娜》是一部“风俗喜剧”小说,但女主人公的伦敦街头遭遇读来却触目惊心,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具备哥特小说元素,大可以称之为准哥特小说。只不过在这部小说里,伯尼没有像其他哥特小说那样把对女性的威胁放到某个恐怖阴郁的地牢里,而是放在了“街头、马车上、舞厅里以及写实小说的生活场景之中”[8]。由于是书信体小说,从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不难体味她穿行都市之中所经历的恐惧。伯尼笔下的女性惊恐在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社交场合,伊芙琳娜时时刻刻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在过去,男性评论家们总认为女作家此举未免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是小女子的聒噪。黑兹利特就断定伊芙琳娜所遭遇的那些“女性磨难”是“无中生有”[9]。约翰·克罗克(John Croker)也认为伯尼动不动就把女主人公塑造成“琐碎的烦恼和虚构的磨难”的受害者是其小说的“一个主要错误”[10]。但是今天从女性主义和都市再现这个角度来看,伯尼正是通过伊芙琳娜的焦虑和畏惧隐晦表达出女性对男权主义主导的所谓都市文化的批判和解构,揭示女性在城市空间所遭遇的社会归属以及性别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困境和束缚。
三、女性主义都市意象体系的建构
伯尼揭露伦敦阴暗面时,她所批判的并非是伦敦都市文化,而是都市文化中的男权话语。批判和解构男权主义都市文化的终极目是通过自己的书写构建女性都市意象体系。虽然伊芙琳娜在书信中不断诉说和抱怨自己在伦敦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委屈,但是字里行间难掩乡下少女对城市生活的羡慕以及对跻身上流社会的憧憬和渴望。当伊芙琳娜获知霍华德夫人邀请自己去伦敦并有机会进入大都市社交圈时大喜过望,在征求看护人乡下牧师维拉斯先生许可的信中抑制不住内心对到大城市开开眼界的渴望:“她们告诉我说此时的伦敦最是热闹繁华。两大剧院都开了,……歌剧院也开了,……拉内拉赫娱乐园也开了,……还有万神殿娱乐园。”[4]18在后来给维拉斯先生的信中,伊芙琳娜“狂喜”地汇报了她在特鲁里巷剧院欣赏当红演员大卫·加里克出神入化的表演、去波特兰教堂、圣·詹姆斯公园购物市场和肯辛顿花园以及为出席舞会把自己“打扮成伦敦人”而购置衣物等畅快经历[4]20。在伦敦的6个多月中,“令人愉快的泰晤士河”、漂亮的花园、如繁星闪烁的灯光、欢快的人群、精彩绝伦的音乐会和游园会以及鳞次栉比的店铺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她流连忘返[4]160。她盼望融入热闹的都市生活中去,更渴望自己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获得关注。当行走在圣·詹姆斯公园购物中心时,她也期望像同行的米尔文小姐一样碰上个把熟人,结果“连一个自己认识的人都没有看见,真是太怪异了”[4]21。
这部小说甫一出版便造成轰动,不到一年便刊印4版之多。一个女小说家写的以女主人公为视角的小说能够被一个男权社会认可和接受堪称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伯尼主动顺应男权统治秩序中的社会规范和都市文化。但是这种顺应其实是一颗包裹着女性诉求的糖衣炮弹。在叙事层面之下、涌动在暗流之中的是女主人公乃至女小说家伸张女性主义的努力。在顺应和妥协之中隐含着作者利用社会规范为己所用的算计。尽管小说叙述的是乡下少女在都市的成长故事,但女主人公并没有被动地和全盘地接受男权主义的洗礼。评论家们常常把女主人公在伦敦舞场的那次挫折评价为其踏入社会接受教育和接受社会规范的开始,但实质上是她藉此对都市文化中的男权话语体系进行的第一次挑战。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时髦场所的一个主要功能“不过是充当女人被视为商品进行展示的流通市场而已”[7]41。从一进舞场,女主人公就对舞场的游戏规则表达不满。那些绅士一幅漫不经心和懒散的样子来来回回、转转悠悠地挑选舞伴,而女子只能被动地任人挑选。伊芙琳娜认为这个规矩“相当气人”,自己“绝不助长此风”[4]23,宁可不跳舞,也绝不接受第一个邀请人。表面上,伊芙琳娜因为懵懵懂懂和无知拒绝了拉威尔,又好似无奈地接受了奥威尔伯爵的请求,但实际上是她不惧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而自主做出的选择。后来,她又因为“不懂事”而就亲戚们的失礼给奥威尔写道歉信,结果触犯了淑女不可以主动给男人写信的天条。尽管这些统统可以被理解为女性成长所必需的磨炼,但兴许也是女小说家故意利用乡下少女没有涉世经验而暗中挑战男权话语的底线。
伊芙琳娜一直无名无分、身份成疑,在伦敦这个讲究名分的大都市难免遭到歧视和边缘化。在各种社交场合,她只得知趣地站在边缘旁观并用自己的笔去记录。女主人公的这种姿态看似被动,她书信中的描写也貌似客观,但是由于叙事主要出自于她的视角,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她或者说是女小说家的女性主义态度。隐藏在伊芙琳娜的那些所谓懵懂和不懂事背后的是很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是以对上流社会进行品评的姿态出现。伊芙琳娜生活在乡下,但是因为母亲有法国血统,父亲又是贵族,她的骨子里自有上流社会的品味和旨趣,对都市文化有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标准。这从她对娘家亲戚、身处中产阶级的布朗顿一家和伪绅士史密斯先生的无情嘲讽可见一斑。女主人公二次进伦敦不得不住到布朗顿家,还要时时应付对她穷追不舍的假绅士史密斯先生。布朗顿一家和史密斯先生的庸俗和粗鄙让伊芙琳娜深以为耻,甚至羞于让自己的心上人奥威尔伯爵知道她和这些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女主人公的上流社会品味和意识归根结底又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其意图在于揭露和解构上流社会的堕落和粗俗,旨在消解都市文化中的男权话语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女性主义的都市话语体系。她所构建的女性主义城市文化显然有别于父权制主导的城市文化。在这个充满女性主义想象的都市空间里,女性能够获得尊严、平等、独立和自由,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尽管这样的女性都市意象体系在当时的社会难以构建,伯尼依然委婉曲折地对都市意象进行了女性主义书写。尽管在男权话语垄断的都市的夹缝中生存,伊芙琳娜依然不事声张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她处事低调,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她的个性和主体意识便尽情释放。房客麦卡特尼(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兄弟)自杀时,她毫不犹豫地上前相救,勇敢地夺下自杀者手中的双枪。在塞尔文太太的帮助下,她用纯真、善良和宽容感化生父贝尔蒙特,让他为当年的放荡不羁进行忏悔。最终,就像她在舞场上主动挑选了自己的舞伴,她又如愿以偿地和自己心仪的奥威尔伯爵步入婚姻殿堂。
都市是男、女两性共有和共处的空间。在伯尼书写的女性主义的都市想象中,女性与男性平等相处、和谐共存,并受到男性的尊重和呵护。小说中这种都市想象的实现有赖于伯尼对男主人公奥威尔伯爵的着意刻画。奥威尔几乎是在见到伊芙琳娜的那一刻就“成为她的奴隶”[11]。他被塑造成一个具有正能量的“伦敦好男人”,相貌英俊、谈吐高贵、举止优雅,是一个对伊芙琳娜有求必应的无私爱仆。伯尼不断利用这个伦敦好男人推动叙事,让他成为伊芙琳娜到达大都会的开路先锋,以备女主人公遭遇险境时充当护花使者。当女主人公在舞会上遭到拉威尔纠缠时,他主动上前解围;当她被两个妓女胁迫时他前来化险为夷;当她受到威洛比死缠烂打之时是他帮她摆脱纠缠[4]285;最终还是他护卫着未婚妻前去和她的父亲相认。对此,他解释道:“她太年轻,又非常没有经验,…… 她看不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我非常想给她指出这些危险。”[4]286
伯尼塑造的这个男性形象更像一面镜子,反衬着伦敦上流社会腐败、堕落的丑恶习气,一再消解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都市意象体系。因为没有社会地位,伊芙琳娜遭到讲究名分的上流社会的歧视,受到都市中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当邀舞被拒的拉威尔后来意识到女主人公身份可疑时立刻满脸不屑:“就这么一个没名没份的人还装什么清高,——我得说我可压不住火儿。”[4]29而那个信誓旦旦要娶女主人公为妻的威洛比爵士则对奥威尔伯爵坦承伊芙琳娜什么都好,只可惜“身份不明,唯一的嫁妆就是美貌,一看就是寄人篱下。”[4]287然而伯尼笔下的伦敦好男人在女主人公自以为认父无望、万念俱灰之际竟然向这个乡下少女求婚,仅仅就因为后者纯真、明智和有见地。奥威尔伯爵的举动无疑颠覆了讲究身份和家世的男权话语体系。而这在当时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只能理解为伯尼一厢情愿的女性主义诉求。
正是通过这个“爱的奴隶”的一路开道和步步呵护,才使得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乡下姑娘成功跻身伦敦上流社会,让乡下灰姑娘逆袭大都会的童话故事成为可能。伯尼在女性都市意象系统中以话语主体和审美主体的身份审视和塑造了体现女性审美价值的奥威尔伯爵,在这个男性形象身上寄托了女性主义者的都市幻想。这个男主人公摆脱了男性主导的、既定的文学传统,有别于同时代男性小说家们所塑造的体现父权思想的男性形象。他既不是亨利·菲尔丁笔下的那个曾经寻花问柳、后来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汤姆·琼斯,也不是塞缪尔·理查逊塑造的那种动不动就为女性指引人生且左右女性命运的理想绅士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伯尼心目中的城市英雄是那种和女性平等相待,随时可以为女性排忧解难的充满正能量的爱仆。
四、结 语
从伯尼对伦敦意象的女性主义书写可以看出,当都市文化主导权被男权主义霸占时,女性争夺话语权的最佳途径就是拿起笔杆,通过成为写作主体争得女性主义的文学表达。伯尼在小说前言大胆宣称自己不想追随男性前辈走寻常之路。在向约翰逊、卢梭、理查逊、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等男性文学前辈们致敬之后她依然表示要和他们分道扬镳。她解释道:“虽然他们可能已经清除了野草,但同时也割掉了鲜花;虽然他们已经扫清了道路,但是同时也让道路变得荒芜。”[4]7这番表述虽然不是伯尼对男性巨擘们的公然叫板,但至少流露出女性小说家另辟蹊径、摆脱男权菲勒斯中心的企图。这种企图始于这部处女作并贯穿女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到她第4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漫游者》时则已经昭然若揭,直接“在文化景观中为某种女性主体性创出一番天地”[12]。尽管伦敦那吞噬人的阴暗面触目惊心,尽管乡下少女在男权话语统治的都市里举步维艰,伯尼仍执意要述说一个喜剧故事。正是小说家的女性主义意志让伊芙琳娜的罗曼司花好月圆;正是小说家的女性主义“私语”,让灰姑娘童话一举冲破笼罩在伦敦上空的男权话语阴霾,彰显身为写作主体的伯尼对构建女性都市意象体系美好明天的乐观心态。
[1] 刘士林. 都市文化原理[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213.
[2] Hazlitt,William.“OntheEnglishNovelists”[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Hazlitt,vol. 8 [C]. Ed. A.R. Waller and Arnold Glover. London: Dent,1903:123.
[3] Johnson,Reginald.“TheFirstWomanNovelist”[A]. The Women Novelists[C].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7:12.
[4] Burney,Frances.Evelin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sEntranceintotheWorld[M]. Ed. Stewart J. Cooke.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INC.,1998.
[5] Brown,Laura.FablesofModernit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10.
[6] Fenster,Tovi.“GenderandtheCity:TheDifferentFormationsofBelonging”[A].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C]. Ed. Lise Nelson and Joni Seager.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246.
[7] Robinson,Alan.ImagingLondon,1770—1900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8] Fraiman,Susan.UnbecomingWomen:BritishWomenWritersandtheNovelofDevelopment[M]. New York: Columbia UP,1993: 32.
[9] Hazlitt,William.“StandardNovelsandRomance” [J]. The Edinburgh Review,Vol. XXIV,No. XLVIII,February,1815: 336.
[10] Croker,John.MadameD’Arblay’s“DiaryandLetters” [J]. The Quarterly Review,Vol. LXX,No. CXXXIX,June,1842: 255.
[11] 李维屏. 英国女性小说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57.
[12] Cook,Elizabeth H.Crownforestsandfemalegeorgic:FrancesBurneyandthereconstructionofBritishness[C].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Revisited: Eng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155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99: 198.
Images of London in Feminist Writing —Study of City Image System inEvelin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sEntranceintotheWorld
YANG An-qi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College of Normal Education,Beijing Un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11)
Frances Burney’sEvelin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sEntranceintotheWorldis widely viewed as an important work of novel of manners because it touches upon the theme of female initiation. However,it is rarely studied as the text of urban female imag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Evelina not only as urban literature but also as feminist writing and discuss how female novelists as discourse subject build feminist city image system by criticizing the heroine’s experience and deconstructing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in London.
Frances Burney;City Image;Feminist Writing
2015-05-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WW022)。
杨岸青(1967-),男,辽宁大连人,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语言文化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I106
A
1001-6201(2015)04-0163-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30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