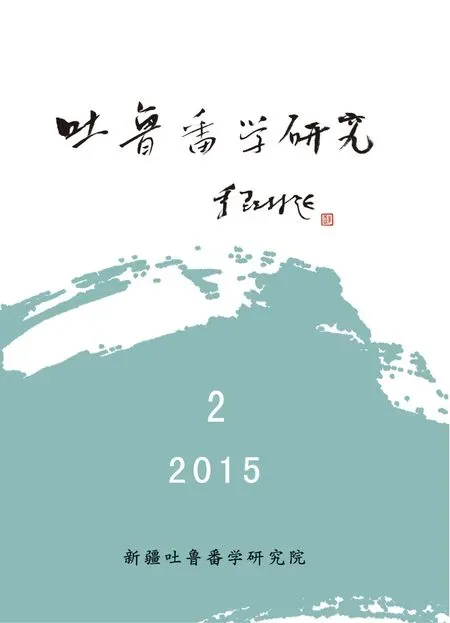古代双陆游戏小考*
——兼论敦煌、吐鲁番的双陆游戏
丛 振
古代双陆游戏小考*
——兼论敦煌、吐鲁番的双陆游戏
丛 振
双陆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项博弈类游戏,因其胜负的偶然性而使参与者倍感刺激,乐此不疲。利用敦煌、吐鲁番的文献、图像资料及其他史料,对双陆游戏的起源和游戏规则进行讨论,有助于加深对双陆的形象认识,还原双陆在丝绸之路各民族盛行的场景。
敦煌 吐鲁番 双陆 游戏规则
古代博戏中风行一种叫双陆的盘局游戏。“双陆”一词,因其对局双方各有6枚棋子而得名,《资治通鉴》卷207《神龙元年二月》云:“双陆者,投琼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棋,故谓之双陆。”*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587页。双陆流行于曹魏时期,在隋唐达到高峰,因其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可操作性而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陆走向衰落的南宋时期,这种游戏“在与南宋同时及其前后的辽金元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汉人中却得到广泛的传播”*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这说明双陆不仅有广泛的流传范围,亦能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融合。
一、双陆的起源
双陆自清代便已失传,传世史籍对其记载也都有出入,使得双陆的起源问题尚不甚明了。因此,一直以来,致力于社会史、民俗学、体育史等研究的学者纷纷撰文就双陆的起源、名称等问题进行讨论*有关双陆的代表性文章参见:陈增弼:《双陆》,《文物》1982年第4期,第78~82页;罗时铭:《古代棋戏——双陆》,《体育文史》1986年第5期,第19页;胡德生:《双陆棋》,《紫禁城》1990年第3期,第18—19页;马建春:《大食双陆棋弈的传入及其影响》,《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59~62页;杜朝晖:《“双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第113~118页;刘欣:《我国古代双陆传播考述》,《体育文化导刊》2010年第7期,第121~124页。。总体说来,对于双陆起源观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本土说和外来说两个方面。支持本土说的观点认为双陆纯属于土生土长的中原游戏,由三国时曹植所创。此种观点的史料来源为《事物纪原》卷9引《续事始》云:“陈思王曹植建制双陆,置投子二。”*高承:《事物纪原》,《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48页。支持外来说的观点则宣称双陆为胡戏,源自于天竺*马建春曾撰文提出双陆源自天竺为误传,实应来自大食,参见马建春:《大食双陆棋弈的传入及其影响》,《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60页。。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说法见南宋人洪遵《谱双序》中的记载:“双陆最近古,号雅戏。以传记考之,获四名:曰‘握槊’,曰‘长行’,曰‘波罗塞戏’,曰‘双陆’。盖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陈、魏、齐、隋、唐之间。”*洪遵:《谱双》,《说郛三种》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59页。谢肇淛《五杂俎》卷6亦云:“双陆一名握槊,本胡戏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双陆者,子随骰行,若得双六则无不胜也。又名‘长行’,又名‘波罗塞戏’。”*谢肇淛撰,郭熙途校点:《五杂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在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说法,意即双陆源自天竺,后由曹植引入,并加以改造后流传于中国。如洪遵《谱双》卷5中记载:“双陆,刘存、冯鉴皆云魏曹植始制。考之《北史》胡王之弟为握槊之戏,近入中国。又考之竺贝双陆出天竺,名为波罗塞戏。然则外国有此戏久矣。其流入中国则曹植始之也。”*洪遵:《谱双》,《说郛三种》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69~4670页。《山樵暇语》卷8亦记载:“双陆出天竺,名为波罗塞戏,然则外国有此戏久矣,其流入中国则自曹植始之也。”*俞弁撰:《山樵暇语》,《丛书集成续编》第9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869页。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双陆为外来游戏,其源自天竺*对此种观点的支持者,参见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7~38页;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前提,即是双陆与波罗塞戏、握槊以及长行为同一个游戏,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然而,部分学者对双陆等同于长行、波罗塞戏、握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主要代表性文章参见王赛时:《古代的握槊与双陆》,《体育文史》1991年第5期,第29~32页;王俊奇:《长行是双陆之异名吗》,《体育文史》1997年第2期,第57~64页;王永平:《唐代的双陆与握槊、长行考辩》,《唐史论丛》2007年,第297~311页。。其实早在唐代,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就曾提出:“(长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8页。明人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卷40中则进一步说道:“李肇所言,则唐之长行正与今双六合,而李以为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则唐之双六或反与今不同,而洪氏《谱双》合而为一,尚似未妥。总之,三者亦小在异同之间,非必相悬绝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胡氏在此文已经点明了双陆与长行、握槊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而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其《书影》卷5中则更直接指出:“予按李易安《打马图序》云:‘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焉。若云双陆即长行,则易安之时,已无传矣。岂双陆行于当时,易安独未之见;或不行于当时,反盛于今日耶!则长行非双陆□矣。”*周亮工:《书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37页。文中李易安即李清照,如若按照周氏的推测,李清照所处的南宋时期,长行是不被称为双陆的。因此,前文中把双陆等同于长行、握槊、波罗塞戏的提法有一定的风险,而以其为论据推断出的双陆来自天竺说也应谨慎使用。不过,从史籍中的记载及出土的双陆文物来看,笔者认为其同樗蒲一样,也是外来之戏,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二、双陆的游戏规则
双陆是一种典型的棋盘类游戏,玩家以所投掷骰子点数的多少来决定棋子移动的步数,王昆吾对此颇有研究:“按掷骰所得之彩行马;各自棋盘一方行至另一方,以叠行之马打对方单行之马,据到达目的地的先后和打落敌马的多少决定胜负。”*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第15页。也就是游戏者每次投掷骰子后,都要从多种方案中选择出最佳的走法,尽量把棋子移动及移离棋盘,并伺机打落敌马。
传统史籍中也有较多对双陆游戏规则的记载,唐代张读《宣室志》中的一则志怪故事,记述了唐代双陆棋子、骰子的情况:“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居肄业……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其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割然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丁如明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0页。由此则故事可知,道士、和尚各15人,实为双陆的30枚棋子,2个怪物则是骰子,每当一人单行时,很容易被对方的人众击倒而离开。
“奈良时代,双陆传入日本”*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故而日本保存下来的双陆资料多能反映唐代双陆的面貌,日本《日用百科全书》第25编《围棋与将棋》中有大原芳藏菊雄撰《双陆锦囊》一文,其记载:“棋盘上下各十二道,棋子黑白各十五枚。黑棋自上左向右行,复由下右向左行;白棋自下左向右行,复由上右向左行。入局时布子如图。二人对坐,交互掷骰行棋。骰子二枚,如掷得二与三,掷者任择自己之棋内,一子行二,一子行三。同色之棋,一道中可任重数子。已有同色之棋二子在一道中,则敌棋不得入;已入者取除;取除之棋,于敌方下次掷骰时入局。黑棋自上左一道起,白棋自下左一道起,依点行棋。如取除之棋,不得入局;则他棋皆不得行。一方不能行棋时,即由对方掷骰。至一方之棋,均人最高之六道内(黑为下内六道,自为上内六道),即为胜利。若最高六道内,每道各有二棋(右方五星之右三道内各有一棋及二棋),则为大胜。”*转引自王赛时:《古代的握槊与双陆》,《体育文史》1991年第5期,第31页。这则文字记载同《宣室志》中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更为详尽。
由上述两则材料,结合《事林广记》中的相关内容*陈元靓编,耿纪朋译:《事林广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我们大体可以推知双陆大都是以六为限,其方法是左右各有十二路,白、黑各十五马,且白、黑相偶,用骰子二个,各按照所投掷骰子的数字行走。白马自右向左动,黑马自左向右动,马先出尽者为胜。游戏之初,两位玩家各投掷两枚骰子,点数大者先走,先走者再投掷两枚骰子,可以一马走两枚骰子数字之和的步数,也可以二马分别行二骰子之数。如果一方的马落单或单行,对方的马就可以伺机将它打掉。被打掉的马仍然可以回到棋盘中复活,但必须要等到它开局时的位置上没有其他的马之后,才能重新放到棋局中。一般以马先出尽为胜,但如果对方有其他马未归梁,或者已经归梁但无一马出局则胜出双筹,赏罚由游戏者自行提前约定,并无定数。
宋词中亦有与双陆游戏规则相对应的内容,《西江月打双陆例》载:“幺六把门已定,二四、三五成梁。须知四六做烟梁,五六单行无障。掷得么三采出,填胲此处高强。到家先起妙无双,号日全赢取赏。”*唐圭璋:《全宋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02页。文中“幺六”、“二四”、“三五”、“四六”、“五六”、“幺三”等点数需要精妙地配合,先能到达方可获胜。如能掷得重色、浑花,则都呼为“双”,称之为“如双”,属于比较高超的技巧。
三、敦煌、吐鲁番的双陆游戏
同樗蒲流行于古代西域地区一样,双陆也深受丝绸之路沿线各族人民的喜爱,西域各地出土的双陆文物也能说明这一现象。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唐代墓葬中出土有一件镶嵌螺钿的双陆局(图1),此双陆局“长20.8厘米、宽10厘米、高75厘米。棋盘带壶门底座,棋盘的盘面分成三个大小相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内都镶嵌骨片、绿松石组成飞乌和花卉图案。另外,棋盘盘面的两条长边正中处,各用象牙镶嵌出一月牙形,彼此相对。以月牙图案为中心,两侧饰六朵花瓣纹。棋盘制作精美,工艺水平较高。”*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自新疆向东,1980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南营乡青嘴湾弘化公主墓出土了21枚唐代双陆棋子(图2),“这些棋子为象牙质,底径约1.6厘米,高约1.7厘米,重约80克;形状为半球体,底部圆平,顶部另嵌圆球形短柄,状如截柿;表面浅雕各色花朵、飞鸟、蝴蝶等图案,部分棋面涂红彩。”*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游戏》,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这两件文物使我们对唐代的双陆形象有了直接的感官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皆出自于墓葬中,是当时贵族阶层的陪葬品,寓意着他们死后能继续享受这种游戏所带来的乐趣。

图1 唐代双陆棋盘 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 图2 唐代双陆棋子武威弘化公主墓出土
敦煌文献中亦存在有对双陆游戏的叙述,P.2999《太子成道经一卷》中记载:
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明日[即]问大臣是何意志(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第1页;录文见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87页。
这则变文故事中大臣巧妙地借双陆棋子来纳谏大王应立太子,无独有偶,《新唐书·狄仁杰传》中也记载有类似的故事:“久之,召谓曰:‘朕(武则天)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5,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2页。这就历史上著名的“狄仁杰智保皇嗣”的故事,狄仁杰凭着其智勇,利用双陆为媒介,终于说服了武则天立李氏子孙为嗣。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唐墓壁画六屏式人物的第二幅中,树下站立一名宫廷侍者,另有一侍者半跪,手中捧着一双陆棋盘,二人旁边坐有一位贵族,手握棋子,正在指画陈说(图3)。常任侠认为:“就画面看起来,表情和人物与狄梁公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相合。”*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3页。不过,常氏此处显然把握槊和双陆等同视之,考前文《新唐书·狄仁杰传》中的记载,改为狄梁公双陆进谏武后应更为合适。

图3 双陆图 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唐墓壁画六屏式人物摹本
P.2718《王梵志诗一卷》把双陆作为智者的游戏:
双陆智人戏,围棋出专能。
解时终不恶,久后与仙通。*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
此诗将双陆称赞为益智的游戏,持褒义色彩。除此之外,洪遵在《谱双》中亦把双陆称为“雅戏”,因此,双陆也受到古代女性的欢迎,王建《宫词》中即有:“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02,中华书局,1960年,第3444页。由此可见双陆在宫中,尤其是在仕女阶层也是很盛行的。
双陆作为博戏的一种,在古代也曾被作为不务正业的代表,同样是敦煌文献中的记载,P.3883《孔子项托相问书》中云:
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答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此则变文中假借项托之口,痛斥双陆的危害,令人深思。古代也确实有对双陆游戏着迷之人,《朝野佥载》记载:“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船风吹,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01,中华书局,1961年,第1515页。为了保住双陆局连性命都可以舍弃,足以说明潘彦是个棋迷及其对双陆的喜爱之深。
四、结语
以双陆为代表的博弈类游艺活动,充满着益智雅趣的内涵,娱乐着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人士,使他们在枰声局影中,能够忘却世俗的烦恼,神游于尘世之外。敦煌、吐鲁番文献和壁画中对双陆游艺活动的记载图文并存,能使我们对其娱乐性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当然,通过释读古代双陆游戏资料,也可以看到此类游艺活动带有很强的赌博性质,令人沉迷其中,甚至家破人亡,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亦有对此的劝诫,值得反思。
A Study on Ancient Backgammon ——Also a discussion on Backgammon in Dunhuang and Turfan
Cong Zhen
Backgammon which was popular in ancient China is a kind of gambling games,and often made players excited and obsessed with it because of its occasionality of defeating the rival.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rule of the gam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s,picture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ssociated with Dunhuang and Turfan, so as to make the game impressed in people's mind and reproduce the game's prevailing scene among various nationalities living along the silk road.
Dunhuang;Turfan;Backgammon;Game rules.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汉唐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研究”(15DLSJ01)。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