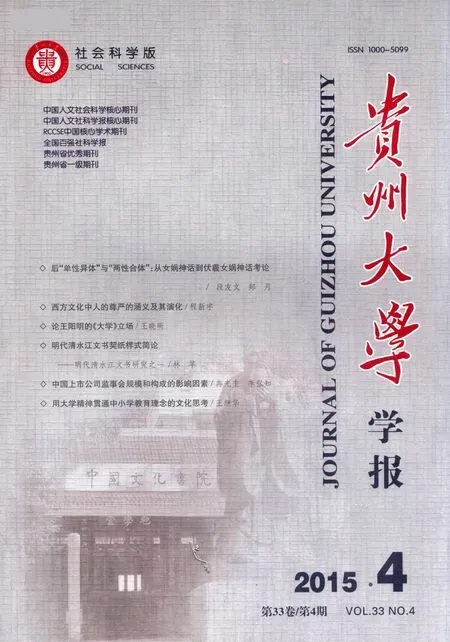苗族古经中的哲理探析
杨曾辉
(1.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2.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
和很多民族一样,自然发生论往往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初始哲理,对此苗族也不例外。不过,这样的传统哲理至今在苗族社会中仍有所延续,以至于不仅对我们去理解苗族古经大有帮助,而且也能够为我们去窥探,甚至是复原苗族的传统哲理,提供一种路径。
当下,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关创世神话的文本却并非如此。这样的文本,要么是宣扬神创论,要么是宣传英雄创造世界。显然,这些文本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后世文献整理者的规制化产物,但当我们在阅读苗族古经文本时却发现,其间所体现出来的苗族古老哲学理念却是与很多远古民族一样,都属于自然发生论范畴。这是一种透视着先民对世界初始认识的哲学理念。在此,仅就所见的苗族古经文本,尤其是《苗族古歌》为引子,对自然发生论做一番初步地探析,以飨读者,并求教于海内方家。
一、自然观:自然生成说
苗族的自然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自然自我不断发展的产物,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一切既不是神的创造,也不是上帝所赐,而是客观存在的,是早就有了的。比如,在张明所收集整理的古歌文本《创造宇宙·开天辟地》就唱到,“悠悠太初头年份,最初最初古时期;草草巴茅还不长,花花野菜还没生。天上还没有造就,地上还没有造成;没打银柱来撑天,没造日月来造明;什么都还没有造,不知生些什么好!干活的人还没生,只生出些和尚们,他们一批老公公,连续不断跟着生。这么多公懒得数,只问四个来最初:第一个公叫什么?第二公叫什么?第三个公叫什么?第四个公叫什么?第一个公叫友央,友央公公老人家;第二公劳栋养,尖鼻子的劳栋尹;第三个公叫甫方,甫方公公老人家;第四个公叫修妞。他们四位来最早……”[1]3-4从最初的古老时期,逐步生成了人类,而他们的始祖“友央”“劳栋养”“甫方”“修妞”不是别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整个演变的历史过程,缓缓推进。
再如,在龙炳文等人整理的苗族古歌文本中,苗族先民关于人类起源的认识和表述是这样的:“开天立地 濮都娘柔 从前天上灰蒙蒙,古时地下黑沉沉,从前天地相近,古时天地相连;里水没有路船路筏,地下没有路驴路马;天上没有鸟飞,里水没有鱼游。盘古才来开天,南火才来立地,地下才开始有土有岩,天上啊才开始有日有月。”[2]1-11
在这一古歌表述中,天地之初其实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世间没有一切,既没有虫鱼鸟兽,也没有日月星辰,更是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推进,“濮都娘柔”出来了,它创造了人世间的一切,被苗族先民认为是人类的第一对男女祖先。从此,混沌的天地发生了变化。一个叫“盘古”的先人将天撑了起来,而一个叫做“南火”的先人则是塑造了大地的一切。在这一简单明了的古歌中,苗族先民表达出了自己对世界本源的一个基本认识。
与苗族先民的自然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民族的自然观则是典型的神创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圣经》中所记载的关于耶和华创造世界的故事。《圣经·创世纪》载,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地,但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深渊上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就这样,天主在水上行走了七天七夜,将世间的山川形胜创造完毕,然后接下去就创造人,创造婚姻等。世间的一切都为这个“天主”所主宰,天主是生命的源泉,是万物的根。苗族古歌文本反映出来的创世过程,恰好表现为是在混沌中,自然孕育和发生了人类的始祖,但这样的始祖既不是神,也不是英雄,而仅仅是人类的源头,人类就是从这个源头发展而来。因此,不管是对这个源头冠以什么样的称呼,但他都不是“神”,也不是父母所生的“英雄”,而仅仅是自然演化中某一特定阶段的“总汇”而已。
生息在我国境内的古代壮族先民认为,自然界的最原始状态乃是“一团气”。据《壮族百科辞典》载,天地分家之前,宇宙中旋转着一团大气,越转越急,最后变成一个大圆蛋。这个圆蛋有三个蛋黄。后来,这个蛋爆开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了天空;一片飞到地底成为海洋;留中间的一片,则成为中界的大地。于是,自然界分成了天、地、海洋三界,然后才出现人类和万物。人类的始祖就是布罗陀和女米六甲[3]325。
在布依族古歌《赛胡细妹造人烟》中则唱道:“很古很古那时候,世间只有青青气,凡尘只有浊浊气,青气浊气混沌沌,不见树木和野草,不见走兽和飞禽。”[4]11
与此相似的还有,彝族先民同样认为,世间万物的起源乃是“气”。《西南彝志选·创世志》载:“哎哺未现时,只有啥和呃,啥清与呃浊,出现哎与哺。”[5]1这里的“哎”和“哺”,其内涵就是指汉语文本中的“影”和“形”之意。
古代汉族一些学者在论及事物的本初时,也有坚持“气说”的。比如,汉代的王充就认为,“万物之生,皆禀之气”[6]349。宋人张载亦持“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学”[7]5之观点。
总而言之,苗族先民在认识事物本源和世间生命产生的过程中,坚持的是一种自然生成说,即他们对于世界的自然认知,认为世界的一切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演进的过程并非突兀,而是循序渐进的。这一切既不是神创造的产物,也不是上帝所赐,因为我们从这些古歌当中看不出有哪些神或上帝的存在,而他们一出现的身份就是人类的老祖宗,如壮族古歌所提及的“布罗陀”和“女米六甲”就是指代父亲和母亲,而不是神或英雄。如此一来,世间的本质在于自然产生的,是客观早就存在了的。
二、生命观:自然演化说
纵观苗族古歌文本不难发现,苗族先民的生命观体现为自然演化说,即人间的生命是自然演化而来的,而不是神的创造,同样也不是英雄所产。
众所周知,枫香树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实际生活功能和符号意义,甚至他们将枫树认为是本民族的“母亲树”,因为枫香树是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产物,而不是“冒然”生出来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生命起源,一样有孕育它们的“母亲”,因而被苗族先民视为是生命诞生的寄托。在《苗族古歌》之《枫香树种》中唱到,“我们来赞枫树种,最远古时枫树种,哪一对妈妈来生的?一对妞赏妈妈生,才有远古枫香树。”[8]395在这里,枫香树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同样是“妈妈”所生的,是一个名叫“妞赏”的妈妈生的,而且它们都是极富生育能力的“原种树”。“我们来赞枫树种,树子生在野山坡。我俩看看现在吧,树子多得数不完,树种多得数不清……”对枫树赋予如此超强的生命能力,当然是与苗族远古时期的生命观相互嵌套的,因为这些枫树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茂盛,随处都有,也是经历了一个生长的阶段,经历了种群规模自然扩大的自然演替过程,当然也就自然象征着世间生命的不断延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了。一些学人曾将苗族之所以有枫树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枫树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是保村护寨的守护神;枫香树集中生长的区域,也是他们青年男女进行游方的好去处;以及他们认为枫树是世间一切生命体的始祖,因而对枫树的崇拜,就是对生命的尊敬,对世间万物平等的一种心态。从这一古歌所表述的内容来看,这样的结论确实是得到了验证和回应的。
在田兵等人整理的《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唱道:“远古那时候,山坡光秃秃,只有一根树,生在天角角,洪水淹不到,野火烧不着;那是什么树,那是白枫树;枫树在天家,枝桠满天涯,结出千样种,开出百样花。各色花相映,天边飞彩霞,千样百样种,挂满树枝桠。枫树砍倒了,变作千百样。树根变泥鳅,树桩变铜鼓,树干生疙瘩,变成猫头鹰,树叶变燕子,树梢变鹡宇,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这个妹榜留,古时老妈妈。”[9]118,182
在文本中,“妹榜”“妹留”“妹榜留”等称呼皆为苗语音译,“妹”即“母亲”之意,而“榜留”则意为“蝴蝶”,因而“妹榜留”等,即被喻指为“蝴蝶妈妈”[10]469-476。在这里,人世间的生命本源体便在枫树的树心中产生了——妹榜留,她是人类的始祖。显然,在这里,苗族先民的哲学理念已经认识到了生命产生的本质乃是物质,而并非是一种超神力的产物,而是由物质世界本身自然演化出来的产物。
蝴蝶妈妈的诞生无疑为生命的创造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可能,因为生命的诞生必然需要母体的孕育,而在具备了“母亲”这一角色之后,当然还得需要“父亲”这一角色的出现,那么“父亲”又是谁呢?应当去哪儿找呢?回答这一问题,在古歌当中表述得十分自然、明理,十分符合逻辑推演。古歌唱到……“才告诉它怀胎:去跟清水交友,去和泡沫交配,你就身怀有孕,你会下蛋生子……去跟泡沫相交,去同泡沫相配,去了身子怀孕,肚子慢慢鼓起来,裙带成了捆鼓带,衣带成为鼓社巾。转回嘎养曲的地方,来找地方生崽,来找村寨下蛋。生蛋生在河沙坝,产卵产在河沙滩……去蹲十二天,生十二个蛋,十二个黑蛋。去孵十二月,生十二个蛋,十二个花蛋……”[11]114-119
“妹榜”“妹留”通过“游方”的形式找到了“水沫”(“父亲”),结合后生下了十二枚蛋,而这十二枚蛋就继续生出了十二个生命体。在这里,蝴蝶的样态被喻为是女性的外阴,而水沫当然也就被指代为是男性的精液了。这样一来,就否定了是神或上帝创造世界的观念,强调生命是在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产物,而且又是自然界中,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两性结合演化物。经历了一个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历史过程,那就是鹡鸠鸟帮忙孵蛋的过程。从此,动物生命就出现了,而不再是植物的生命。在古歌当中,生命的产生自然而然,并不显得突兀和有反逻辑。就这一意义而言,不得不说苗族先民早期的哲学理念所蕴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逊色于当下的哲学。
当然,关于苗族早期的生命观,我们除了从枫香树游方的故事中获得理解和认识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苗族先民早期的生命观,那就是他们的“灵魂循环论”。
在苗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灵魂循环论”,亦即“灵魂不灭论”。他们认为,人死后,肉体与灵魂将会分离,而且更看重的是灵魂,因为灵魂并不是随着肉体机能失去生命而死亡。相反,灵魂不但不会随着肉体机能的死亡而死亡,而是沿着祖祖辈辈们的灵魂所归属之路,去到祖宗那里去,而所谓的“祖宗那里”,即是祖宗灵魂的归宿。在那里,死者的灵魂不仅能够与祖宗团聚,而且还能够继续投胎做人。灵魂回归祖宗那里,与死者生前的一切为人处世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灵魂都能够回归到祖宗那里去。这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证据,那就是苗族社区十分流行的“仙娘”。仙娘是苗族社会中,从事宗教活动人员的一种专用称呼,而且大多为女性所担任,男性担任仙娘角色的很少见。仙娘的身份不是别的,正是介于阴、阳两界之间,作为儿孙代表与已逝祖宗灵魂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半神人”,而她们的职责内容大抵不过是子孙询问祖宗在那边的情况,抑或是祖宗询问自己儿孙的生活现状,并指导其如何趋吉避凶,祈求保佑等内容[10]469-476。从仙娘的这一角色不难看出,在苗族的观念当中,灵魂是不死的,祖宗的灵魂永远存在,因而仙娘才得以进行活着的人与逝去的祖宗的灵魂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
苗族先民的这一认识,与佛教中所认为的投胎转世是有别的。佛教认为,人是有善恶之分的,恶人投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极恶之人死后甚至是直接立刻下地狱而不是直接投胎,但极善之人死后却能立即通往天界完成投胎。在这里,人是有善恶之分的,而生前被“善”和“恶”所贴了标签的逝者,在投胎转世时的路径却完全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他们的灵魂归属充满了诸多不测的因素,而这些不测之因素基本上是生前所种下的,而且他们的灵魂并非是前往自己的祖宗那里,要么是地狱,要么是天堂,但就是没有去祖宗那里。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苗族先民的灵魂不死观却将所有的逝者的灵魂视为同等去对待,没有善恶之分,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罪”,更是没有神灵来审判,而是直接前往祖宗那里,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灵魂循环。
与此相似的还有,根据《旧约圣书·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出亚当与夏娃之后,由于二人在伊甸园内,被蛇所蛊惑,因而偷吃禁果,进而被上帝所惩罚,并诅咒其“归于尘土”。于是,将违抗上帝旨意的行为和人被认定为是“永生的罪恶”,上帝是有罪与无罪的最终的“裁决者”。人死去后,必须得经过上帝的裁决,要么入地狱,要么永生天国。
从上述不难看出,苗族先民的生命观同样体现出了自然演化的逻辑,他们认为,世间的生命并非是突兀的出现,而是自然自身不断演化的产物,而由此形成的灵魂观念也体现为是自然而然的循环状态,灵魂最终的归宿在祖宗那里,而又自然而然的去投胎转世,完成生命的轮回,是不分罪与无罪的,因为“灵魂无罪”。当然,灵魂不死的观点并非苗族先民所独有,很多沿袭着自然发生论的民族,都具有与苗族相似的灵魂观和生命观。
三、价值观:生命等值说
由上文所述可知,苗族先民认为,世间的生命乃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即学界所说的“自然发生说”。因此,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生命的本质在于等值,而不是具有高低贵贱之别。也就是说,既然是自然发生论,那么无论是虫鱼鸟兽也好,还是山川草木也罢,其价值,尤其是生命价值,都与人类生命体一样,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着谁领导谁的问题。当然,需要着重申明的一点是,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古代都曾有过自然发生说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世界上的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每个民族的自然发生说的着生点却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苗族古歌》中所记载的,在蝴蝶与水沫游方过程后相结合,生成了十二枚蛋。在这里,古歌中并没有给蝴蝶的性别定性,她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而水沫同样也没有。但我们却可以从蝴蝶和水沫的外形,去推测出蝴蝶所代表的女性角色和水沫所代表的男性角色。
在众多民族的生命价值体系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和重点领域,因为人类生命,乃至社会体系的存在、发展和延续,都无法绕开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命体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因而对自然界生命的尊敬、崇拜,乃至是将其神秘化,也就变得十分合情合理了。同样的,苗族先民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既然世间生命是平等的,那么一切事物也应当是平等的。可是,生命延续的源泉在于物质和能量的有序摄入和不断获取,直到生命体生命特征的结束,因而出现物质和能量的竞争也就很正常了。因此,在这样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他们对世间一切生命的处理原则是,获取任何自然资源都是可行的,同样也是合理的,但前提必须要节制人们自己的欲念,对自然资源理当进行有节制的获取,有量度的获取,不能够进行超额获取和使用,更是反对那种将资源获取了,但却将其搁置而不用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同样是在浪费生命。
在燕宝等人编的《苗族古歌·打柱撑天》中唱道:“天上三次垮下来,三次把它修整好;天下三次遭毁坏,三次造成山坡垴,千万山坡都造好……先前五棓柱撑天,先前蒿枝柱撑地,天上看去圆溜溜,天上不会矮下来。哪个手脚真灵巧,天上它也能去到,爬到天上去试摇,摇了外来又摇内,摇了东来又摇西,看看天上稳不稳?地神手脚真灵巧,天上他能爬得到,他爬上天去试摇,摇了外来又摇内,摇了东来又摇西,看看天上稳不稳,看看地上稳不稳……甫方是个聪明人……拿银子柱来撑天,拿金子柱来撑地,天上这才稳笃笃,地上这才笃笃稳……第一根柱撑抬拱……还留下来四根柱,需把它砍去六尺,一根拿去撑东边,一根拿去撑西边,一根拿去撑左边,最后还有一只角,就拿这根去撑住。十二根柱都撑完,天上圆圆平整整,地上坚固稳笃笃……东边一角有缺陷,有个地方出漏洞,天上才是不牢固。有个什么老大人,朝朝都在熔岩石,暮暮都在熔岩石,熔化岩浆来焊补,粘补东边天一角……”[12]299-321,314-315
在整个歌词当中,不仅表现出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一种尊敬和敬畏,同时也将人们的思维方式用以去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匹配关系和比例进行调整。天地本已存在,但由于天地之间的高度太矮,不方便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担心着天会塌下来,而地则将要垮下去,因而需要建构柱子去将天地撑住,确保一个稳定的活动空间。从开始利用五棓柱和蒿枝柱撑天,但却感觉到这样撑起来的天和地,其空间并不稳定,因而才是去寻找金银来建构十二根银柱子去撑天,用去了八根银柱,还剩下四根,“需把它砍去六尺,一根拿去撑东边,一根拿去撑西边,一根拿去撑左边,最后还有一只角,就拿这根去撑住。”这样一来,十二根柱子就得到了完整的利用,丝毫没有浪费。在唱到当天地还有漏洞需要填补的时候,他们还将岩浆进行填补。如此一来,天地万物几乎都得到了合理而完美的利用,既不过度浪费,又能取得预期的改造自然的目的,实现了对资源的节制利用,最终确保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而世间的其它生命又能得到生息和繁衍。
四、余论
《苗族古歌》是苗族先民早期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类社会认知的一个历史缩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歌文本的整理免不了会参混附会之物,而且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古歌时必须要加以剔除出来,方能把握《苗族古歌》的实质。比如,当用12根银柱子来撑天的时候唱道:“一柱撑台拱,二柱撑方西,三柱撑翁仰,四柱撑都匀,五柱撑幸宁,六柱撑排纠,七柱撑排勒,八柱撑大海……”[12]非常明显的是,“台拱”“方西”“都匀”“幸宁”等地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而这些地名却进入了他们的古歌文本中,显然是后世之人在整理古歌文本时所混入的产物。
总而言之,当我们将古歌中的后人附会之物逐步剔除之后,我们就能够对《苗族古歌》的本来面貌进行逐步的复原和解读。仅就本文的探讨而言,从中不难看到,苗族先民早期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对世间万物生命的认知,乃至是对价值观的评判,都体现出了他们对自然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是一个突兀的历史过程。它们既不是西方民族所认定的主的创造物,也不是我国其他民族,如汉族所认定的神或英雄的杰作,而是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物,然后从物开始逐步演化出生命,而生命又是从生命体演化而来,先是植物有了生命,然后蝴蝶妈妈和水沫游方过后产下了十二枚蛋,从而动物生命也诞生了。一切体现为合情合理、自然而然。因此,《苗族古歌》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苗族先民的哲学理念,也有助于我们探讨人类社会早期的思想观和认识观。
[1]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2]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古老话[M].龙炳文,龙秀祥,等,译注.长沙:岳麓书社,1990.
[3]〈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民间文学资料:四十五集[M].1980.
[5]贵州民族研究所.西南彝志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6](汉)王充:.论衡·言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7]张载撰,王夫之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M].上海:世界书局,1981.
[8]燕宝.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9]田兵.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
[10]〈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编审委员会.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11]吴德坤,吴德杰.苗族理辞[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12]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苗族古歌[M].贵阳: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