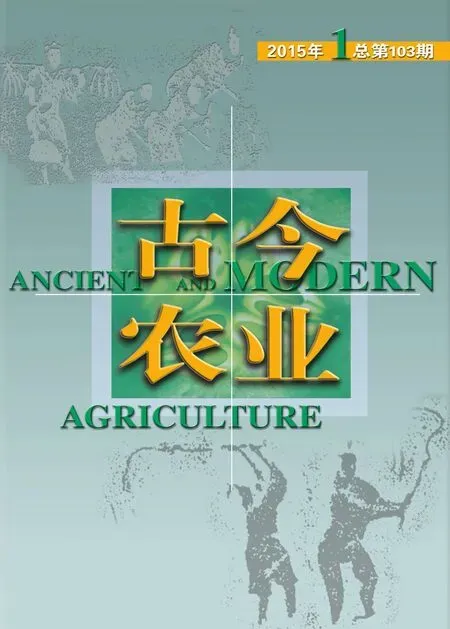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分析
贾廷灿
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分析
贾廷灿
(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北京100122)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耕文化是其主体文化,在漫长的农耕文化传承过程中,基于各种目的,统治者是农耕文化传承的主导者,而知识阶层则是农耕文化传承的总结与推广者,而底层劳动人民则是农耕文化的直接参与与实践者,三者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耕文化;传承;角色分析
钱穆先生曾说:“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和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自古代到今天,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中国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农耕文化的发展,这一过程就是农耕文化的传承过程。那么,在传承农耕文明的过程中,主要由什么角色来完成?其中又是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前学者们很少有专文探讨,本文旨在缕述有关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不同角色的作用。
笔者认为,从事农业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取得大量的税收,所以统治阶级倡导与宣扬“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被历朝历代作为国策,统治者是传承农耕文化的主导者;而处于国家与底层农民之间的知识阶层,利用其知识分子的天然角色,主要从撰写农书的角度传承农耕文明;而中国古代的农民,出于自身家族传宗接代,血脉延续的需要,养家糊口,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试图发明创造,以便更好地养活更多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农耕文明的实践者与传承者,千百年来,是他们的实践延续了农耕文明有进程。
一、封建统治者是传承农耕文明的主导者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依靠,特别是在一个农耕立国的国度,农业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重农一直被视为国策,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民以食为天,有时还有时毫无道理地不惜抑制商业发展,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地位,使政权长治久安。农业的发展与传承自然也是国家之政策之首。在重农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帝王处在封建制的国家政权金字塔的顶端,下面是郡、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由他们组成统治阶层,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农业政策,并将农业生产、土地开垦等与农业有关的事项纳入考核地方官的标准。皇帝亲自主持祭社神、稷神,亲自扶犁,为的是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还有的亲自撰写《劝农诏》来鼓励农业生产,有时还亲自参与农业的育种工作。清朝康熙帝在丰泽园发现一个长得很大的早熟稻穗。他将该穗单独收藏,次年单独种植。经过几年的单收单种,培育出了高产早熟良种——“御稻”。为了推广御稻,康熙帝派员将稻种送往江南。地方官员亲自抓试种,各阶段的长势都要按时写成奏折送到北京。可以说,从上到下对御稻的重视,其对农业和农耕文明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水稻良种本身。统治阶段在农耕文化方面传承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农与劝农
早在西周初年,王室大臣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农的重要性。他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教庞纯固于是乎成”。这就是说,农业是百姓的大事,因为祭神所需的祭品出于农业,人民的繁殖基于农业,事物的供应来自农业,社会的和谐赖于农业,财货的增殖始于农业,国家的强固成于农业。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思想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农业是强国之本,对西周虢文公的思想有所发挥和发展,他们大都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农业能解决民食和农副产品的供应问题,是人类社会和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先秦管仲说:“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墨翟也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古人把是否“足食”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志,如果“足食”,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国家就会强固。反之,就是“饥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寄生之君”就可能地位不稳固,甚至被推翻,“国非其国也”。
第二,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先秦荀况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命仓库者财之末也”。他的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如果农业发展了,社会财富才会增加,才能“演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国库才有可靠的财富来源,国家才会强固。第三,农业的发展能养民和富民,才能“富安天下”。稳定社会,强固国家。西汉贾谊说:“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才能“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北宋范仲淹在他提出革新时政的建议中,阐述了重农才能富民,富民才能社会稳定的思想。他说: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深刻阐述了“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的思想,只有发展农业,才是养民之政,富国强国之本.第四,农业的发展能众人口,使国家繁荣与昌盛。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社会里,战胜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需要人口“庶”。因此,古代许多思想家都把“庶”与“富”作为施政的目标。
于是历代政府经常性亲耕耤田,并祭祀炎帝神农,昭告天下。这一习俗源于原始社会,春初部落长带头耕种,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的古俗。它是“祈年”(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又称“亲耕”。寓有重视农耕之意,自周、汉以下,各代多行之。届晨,以太牢祀先农神,在国都南面近郊天子执耒(后代执犁)三推三反(返),群臣以次耕,王公诸侯王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然后籍田令率其属耕播毕,礼成,命天下州县及时春耕。唐玄宗时,载其仪于《开元礼》。《诗经.周颂.载芟》:“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颜师古注引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通典.礼六》:“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纮,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远古的神话传说,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找出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总结农业经验,传授天下百姓,让人民种植五谷,得以解决温饱,告别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因而炎帝神农氏与后世的黄帝轩辕氏一并被公推为中华民族的先祖。
经过漫长岁月积淀的远古神话,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以史书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西汉中期以前,又正逢汉代黄老无为思想盛行,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国策,统治者大力提倡趋本舍末,即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经济,因而对炎帝神农氏——农业神的崇拜得以提倡,皇帝不仅亲自举行亲耕典礼——亲耕耤田,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并举行祭祀神农的仪式。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因而得以正式确定。经过了神话定型时期,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大为丰富,他的农业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历代都为统治者大加提倡并加以肯定。几乎历朝都要立坛、立庙、立祠予以祭祀,并大行皇帝亲耕耤田之礼,借以祭奠神农。由民间至官方还逐渐明确了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及安葬地,即今湖北随州历山(古称厉山或烈山)的神农洞,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今湖南株州炎陵县(酃县),是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亡的安葬地。到了北宋,统治者大事建造了炎帝陵(今湖南株州炎陵县),元、明、清历朝都不断修缮,并于皇帝登基等日举行国家祀典。炎帝神农氏不仅是神明,而且已演化为稳固封建时代统治秩序的政治载体之一。
炎帝神农氏的国家祀典分为两个部分:亲耕耤田与祭奠典礼。西汉以前,只出现过亲耕耤田。西汉开始,在弘扬亲耕典礼的同时,又逐渐将后来的祭祀神农与亲耕典礼合二为一,即以亲耕耤田享祀神农(先农),统称“亲耕享先农”或“耤田享先农”,并沿袭至清亡。一耕一祀,耕是形而下,祀是形而上,恰如其分地涵盖了炎帝神农祭祀内涵的两个层面。
周代,天子、诸侯都有耤田。春天,天子、诸侯“以车载耒耜”,到耤田行亲耕耤田之礼,以此劝天下务农。进入汉代,皇帝不仅行亲耕礼,还仿效祭祀社稷的礼仪祭祀神农,设神农祠。东汉沿袭西汉之制,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典章制度上的变化逐渐完成。自此,耕即是祭,祭为了耕,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一做法至明清达到完善。唐、宋时期,“耤田千亩之甸”,神农耕祭已形成较大规模,作为郊祀的一项重要内容,行礼的等级及次数虽不比祭天等项,但先农坛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神农祭祀礼仪的物质载体却已大体定形。宋代“绍兴16年春亲耕耤田”(《宋会要辑稿》卷11854)。到了元代,为了安抚汉民族知识官僚阶层的情绪,蒙古统治者居然引经据典,于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元史》,卷76),后在大都东郊选地千亩作为耤田;至大三年(1311年),建先农坛,“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元史》,卷76)。明代建国伊始,便在都城南京设先农坛,内有耤田,“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耤田北。亲祭先农,以后稷配。祀毕行耕耤礼”(《明会要》),定神农耕祭之礼为大祀,后改中祀。明永乐18年(1420年)仿照南京先农坛,在北京建造先农坛,“悉仿南京旧制”,在洪武时期制订的祭仪基础上,再行补充。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耕耤田。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耕耤田,1531年更定耤田仪。
北京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亲自耕祭先农(炎帝神农氏)的祭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炎帝神农氏祭祀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坐落于北京城西南,与天坛东西相望,分布于京城南中轴线西侧。它原样照搬了明洪武帝时在南京建造的先农坛式样,不仅祭祀神农,还祭祀其他间接或直接与农业有关的众多神祇,如太岁神、十二月将神、江河湖海神、风云雷雨神等。为了达到祭祀的目的,从明永乐18年(1420年)始,至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明清两代统治者不断增加先农坛的建筑数目,赋予它们不同的功用;完善并严格执行先农(炎帝神农氏)的耕祭礼仪规章,借以表明重农从本的治国纲领,达到佑护政权稳固的政治目的。它的建筑功能完整,有先农神的拜台(先农神坛),有清帝观看大臣耕作的观耕台,有供奉神农神龛的神库,有储存耤田收获粮食的神仓(仓房和圆廪),有亲耕耤田前更换服装的具服殿,有亲耕耤田成功后举行庆贺的庆成宫,甚至有为祈祷和报答风调雨顺、地力肥沃而建的神耤坛。
(二)防灾救灾
灾害是农业生产经常遇到的问题,自古代至今天莫不如此。通过防灾救灾,起到传承农耕文化的作用。在数千年的古代农耕历史中,早在先秦,思想家们不断地以谨慎的态度提出农业技术革命的思想,为后世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供了认识上的武器。自然灾害从反面作用于人类的农业生产,从某种意义说,起到了促进农业科技,尤其是思想认识领域的发展的客观作用。
报灾、勘灾,是中国传统救灾体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是朝廷救灾的前提和依据。正如朱熹所说,“救荒之务,检放为先”。明清两朝对此要求尤其严格,若迟报逾限或报灾不实,各级官吏都将受到处罚。严重匿灾不报,更要严惩,直至杀头。
灾情发生后,灾民最需要救助。朝廷的救灾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赈济、减免赋税、调粟平粜、转移灾民、抚恤安置、劝奖社会助赈等。
自然灾害难以避免,但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可以减轻危害,避免重大损失。中国古代防灾减灾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兴修水利和海塘工程,治理河患,防范水旱潮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兴修了一批预防、减轻水旱灾害的著名水利工程。宋以后历代政府都重视河防管理,元朝工部尚书贾鲁、明朝河道总督潘季驯,在治理黄河方面还取得了突出成就。康熙皇帝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政事,书写在纸,悬挂在宫中柱子上,每天都想着。平定“三藩”之乱后,他把治河放在最重要位置,六次南巡,调查研究,亲自制定治河方略。康熙和乾隆年间,黄淮流域水灾因此明显减轻。
(2)加强气象、灾情监测,建立雨雪禾麦收成分数和粮价呈报制度
中国历代朝廷一直重视天文、气象观测,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代表。秦朝把上报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泽及受灾程度作为一项法令,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汉朝建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制度,以后历朝相沿不废。宋代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报汛制度。金朝规定,沿河州县在汛期随时奏报洪水险情。明朝开始建立黄河飞马报汛制度。清代沿袭这一做法,还建立有用羊皮筏传递汛情的“羊报”制度,在黄河支流沁水下游和长江、淮河、永定河上先后设立水志桩,在汛期及时驰报水情。清代更建立了雨雪、禾麦收成分数、粮价奏报制度和晴雨录。晴雨录是扬州、苏州等地有关每天晴、阴、雷、雪、雾和风等气象情况的记载,最早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来清廷将晴雨录和奏报制度推广到全国。每逢下雨降雪或缺少雨雪,地方都要向皇帝报告雨水入土深度和积雪厚度及起讫日期。这类奏折称为雨雪分寸。清廷还要求各省军政大员呈报禾麦收成分数和当地粮价。清朝通过建立各省气象观测及晴雨录与雨雪、收成分数、粮价奏报制度,及时掌握全国天气变化和粮价走势,对预测可能发生的农业气象灾害并采取相应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3)推广防灾技术、抗旱涝高产粮食作物,开展多种经营
著名的《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都提出了许多防涝抗旱,保墒,防低温、病虫害、盐碱化及治蝗等对策。历代封建政府大力推广防治农业灾害的技术和知识,不断刊印各种救荒书,特别是明清时期,让官民掌握相关防灾知识技能,借鉴前人救灾经验。先秦以来著名思想家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水土山林的相互关系作了有益探讨,闪烁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火花。秦汉以来,国家在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不断颁布法令,鼓励植树造林、禁止滥伐森林,特别是把发展抗旱耐涝高产粮食作物,作为防灾备荒的重要措施。宋真宗曾亲自推广耐旱的占城稻,乾隆皇帝大力推广过番薯种植。
(三)官修农书
唐朝武则天时期,由武则天删订《兆人本业》,是为中国最早的官修农书。元代《农桑辑要》问世,是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清朝大型农书《钦定授时通考》由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纂成。书前冠有乾隆皇帝御制序文。全书约98万字,24册4函。乾隆二年(1737年)高宗敕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40余人纂修《钦定授时通考》。该书汇辑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搜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事的记载达427种之多,并配插图512幅。共分8门:一为“天时”,论述农家四季活计;二为“土宜”,分六子目,论述地势高下、土壤燥湿、田制水利;三为“谷种”,记载各种农作物的性质;四为“功作”,记述从垦耕到收藏各生产环节所需工具和操作方法;五为“劝课”,是有关历朝重农的政令;六为“蓄聚”,论述备荒的各种制度;七为“农余”,记述大田以外的蔬菜、果木、畜牧等种种副业;八为“蚕桑”,记载养蚕缫丝等各项事宜。全书结构严谨,征引周详,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见,堪称是一部古代农学的百科全书。
还有一些古代的官员,写有农业方面的著作,留传后世,北魏贾思勰编著有《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编著有《农书》、元代鲁明善编著有《农桑衣食撮要》、明代徐光启编著有《农政全书》,为农耕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落榜知识阶层是农耕文明的总结与推广者
尽管中国的古代知识阶层标榜“耕读传家”,但是封建知识分子一般很少参加农业劳动。其主要原因来自孔子,他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区别明显,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好官,不必了解农业生产。由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有文化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参加农业生产,而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民又没文化,这就是明代马一龙总结的“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现象。因此,多数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农业,但是,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关心农业,他们中间有很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一些并不醉心于科举的士人,除了读书,就是从事农业,所谓耕读传家是也。知识阶层往往不像现在居住在城市,与农村不计成本联系,身边的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创造或培育出的良种,由知识分子记录下来,写进农书,留给后人。宋代农学家陈旉撰写了《农书》,这是一部专门讲述南方水田农业的农书;明代文学家黄省曾写有《稻品》、《养鱼经》等农书;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著有《农蚕经》、《农桑经》、《农经》等。关于中国传统耕作技术和传统的优良品种,能够有人留下文字的东西供我们今天来研究和参考,知识分子们所写的古农书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农书数量是与医书并列的,许多农书就是一些未能进入官场或者辞官的知识分子所撰写。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很多读书人因考试落榜,便在乡村从事生产劳动,通过观察实践,撰写农书。唐代陆龟蒙,出身官宦世家,进士考试中以落榜告终。他写作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诗歌和小品文,其中在农学上最有影响的当属留下的《耒耜经》。宋代的陈翥,自称“铜陵逸民”,早年曾闭门苦读,但都名落孙山,四十岁时感到仕途无望,于是“退为治生”,于庆历八年(1048年)在村后西山南面植桐种竹,并在此基础之上,写就了《桐谱》一书,以“补农家说”。清代写出了人所共知的《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多次考试落榜以后,专门志怪的同时,还从事农书的写作,著有《农桑经》,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农学家。清代刘应棠也是这样的一位农学家。因为应试不得意,就打断了功名的念头,隐居在梭山务农,同时集徒讲学,写作完成《梭山农谱》。《农圃便览》一书作者丁宜曾,因为早年没有养成种地的习惯,所以务农后尽心学习访问,随时记录心得,又参考前代的农书,长期居住在山东日照县西石梁乡间务农,写成的写成《农圃便览》一书。马一龙在明嘉靖26年(1547年)考中进士,被选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后因母年老多病,他辞官回到故里江苏溧阳,招募农民垦荒种地,他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往来于阡陌之间。他发现,农民所做的虽然是农活,却不懂得农事的道理,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农事经验写下了《农说》一书,成为农学史一篇不可多得的农学理论著作。清代的杨秀元写成了《农言著实》一书。书中“言岁时占验,早晚种植与一切锄耕获之事特详,老于农者,或不能知也”,“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以故丰种茂,有相之道,乡之老于陇亩者,咸愧叹弗如,帖然心服。”杨双山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有见于关中地区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他曾试种棉花和苎麻,但“殚思竭虑,未得其善”。其后读《诗·豳风·七月》认为陕西可以种桑养蚕,于是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找出了一条在陕西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积累了13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他还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基地。
知识阶层,特别是与官不相关的知识分子作为农书的作者,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实际,他们编写的农书中很少能看到象官修农书那样连篇累牍地照抄前人的著作,而更多是自己生产经验的总结。明代的张履祥选择了隐居躬耕之后,就开始搜集一些农业技术参考书,他得到了一本《沈氏农书》,并与家人共同研读。张自己如是说:“予学稼数年,谘访得失,颇识其端;而幼不习耕,筋骨弗任,雇人代作,厥功已疏,自非讲求精审,与石田等耳。因手是编,与家之人,共明斯义,校之言说,益为有征。”
三、广大农民是传承农耕文明的实践与直接创造者
农民是亲自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发现和培育的良种,对农耕文明来说,是直接的贡献。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没文化,他们的发明创造有可能无法写下来,得不到广泛传播。但是,他们的经验是第一手的,他们的经验则主要由知识阶层间接传承下来,另外则是由父子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继承下来。
作为地方官员的贾思勰在写《齐民要术》时,方法之一是“询之老农”,说明农业生产者的实践对于古代农书的撰写起了决定作用,而农书作者不过只是记载这些经验而已。
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些经验并不一定写进古代文献,有时成为歌谣的一部分,代代相传,成为今天的农谚。农谚也成为普通劳动人民对古代农耕文化贡献的重要方面。游修龄教授在“论农谚”一文中认为,农谚的起源是与农业起源一致的。农谚实在是农业劳动中从歌谣分化出来的一支重要分支,主要描写劳动人民与自然斗争,即着重生产方面的。不少古书上有有关农谚的记载。
无法运用文字的记载,但是农民对于一些长期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依然有传下来。劳动人民因为穷困,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他们的生产经验主要靠“父诏其子,兄诏其弟”的口头相传方式流传和继承下来。在还没有今天的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的朝代,农民就拿多年生树木的生长状态作为预告农事季节的依据,因为多年生树木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客观气候条件,于是产生了“要知五谷,先看五木”的农谚。在指导播种期方面,有许多反映物候学的谚语,如“梨花白,种大豆”;“樟树落叶桃花红,白豆种子好出瓮”;以及“青蛙叫,落谷子”等等。更多的是根据二十四节气指出各种作物的适宜播种时期:如“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草子正当时”;“白露白,正好种荞麦”等。农民有了这些农谚就能掌握适时播种。另外如“立冬蚕豆小雪麦,一生一世赶勿着”;“十月种油,不够老婆搽头”等谚语,却是失败教训的总结,提醒人们要抓紧季节,不误农时。
民国时期,费洁心编有《中国农谚》,分为时令、气象、作物、饲养、箴言等五大部分共5953条,这些农谚的内容涉及生产与收获过程的许多方面,是农民对古代农耕文化的贡献所在。新中国时期,农业出版社以吕平为主,进行了有计划的全国农谚收集工作,经过归并整理分类,收集31 400余条,编成《中国农谚》,于1987年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是农作物部分,包括大田作物、棉麻、果蔬、蚕桑、豆类、油料直至花卉为止,据笔者统计,共约16200余条;下册为总论及畜牧、渔业、林业等部分,总论包括土、肥、种、田间管理、水利及气象等,共约15200余条。这些农谚有的是1949年的总结,但是多数是之前数千年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智慧结晶,是农耕文化传承的象征。
四、小结
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经过统治者的主导,农民的实践与口传心授,知识阶层的提炼与记载,三者缺一不可,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遗产。
传统的农耕文化遗产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特别是在现代农业产生诸多问题的时候,传统的生产方式能够在今天解决一些环境与食品安全问题。
[1][罗马]P.加图.农业志[M].商务印书馆,1986.2.
[2]吕氏春秋集释[M].卷2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4月北京第1版,1955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1170页.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1994,2.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M].中华书局,1976.
[5]李根蟠.精耕细作、天人关系和农业现代化[J].古今农业,2004(3).
[6]李根蟠.农业实践与“三才”理论的形成[J].农业考古,1997(1):92.
[7]吴十洲.先秦荒政思想研究[J].农业考古,1999(1).
[8]曾雄生.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1).
[9]郝治清.我国古代救灾防灾的经验教训[J].求实,2008(13).
[10]董绍鹏.先农文化与先农坛[J].北京文博,2004(3).
[11]吴运生.论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J].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4(1).
[12]游修龄.论农谚[J].农业考古,1995 (3).
Analysis of theRole of the Inheritor of Ancient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Jia Tingcan
(Rural Social Undertakings Development Cent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122)
Ancien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and farming culture is the main culture.In the long process of farming culture inheritance,based on a variety of purposes,the rulers are the leaders of the inheritance of farming culture,and the intelligentsia is the explainers and promoters of the inheritance of farming culture,and the lower working people are the direct participa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farming culture,all of the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arming Culture,Inheritance,Role Analysis
贾廷灿(1963—),男,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