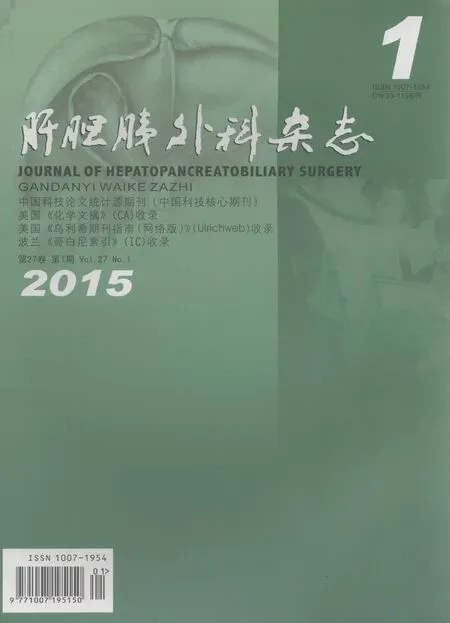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诊治中的应用
倪其泓,张赟和,陈炜,王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胆胰外科,上海 200127)
肝门部胆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HCC)是胆道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胆道恶性肿瘤中,肝门部胆管癌占其中的60%~70%,且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1]。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晚期仅表现为腹痛、黄疸等非特异性症状及体征,所以诊断尤其是早期诊断较为困难;肿瘤所在的解剖位置特殊,与肝动脉、门静脉相邻,所以术前的可切除性评估存在一定偏差;患者术前多存在梗阻性黄疸,影响了肝脏凝血因子与蛋白合成,使得出现术后出血、肝功能衰竭等并发症与病死的风险增高。因此,肝门部胆管癌的诊治一直是近年来肝胆外科的一大焦点与难题。
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自从出现以来,一直被作为腹部疾病的主要检查手段之一。传统CT与早期单排螺旋CT对胆道肿瘤的诊断及术前评估价值较低[2],随着技术的发展,多排螺旋CT的出现,CT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清晰地显示肿瘤的位置、扩张的胆管、周围血管的受累、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的情况,还可以测定需要切除的肝脏体积与残肝体积。所以多排螺旋CT可以作为肿瘤定性定位、分型分期、术前可切除性评估、手术安全性评估与手术规划的主要依据[3]。
三维重建(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技术是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CT、MRI等检查的二维图像进行分割重建导出三维模型[4]。随着数字医学概念与精准肝胆外科理念的提出,三维重建模型相比二维图像具有更加直观、精确的特点,近年来逐渐被运用到肝门部胆管癌的诊断与评估中。本文就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1 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诊断中的应用
肝门部胆管癌早期常无明显症状,中晚期也仅表现为腹痛、黄疸等非特异性症状,所以影像学检查是其诊断的主要依据。多排螺旋CT对于胆道梗阻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定位准确率>90%、定性准确率>95%,是肝门部胆管癌诊断的最常用手段之一[5]。
在CT图像上,肝门部胆管癌表现为肿瘤的直接征象和周围胆管、肝脏的间接征象。肿瘤在CT平扫图像上的特点为密度低于肝脏的软组织影,在增强图像上的特点为缓慢持续的强化。根据病灶大体类型的不同,其直接征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肿块型表现为软组织包块,肿瘤大者可侵犯整个肝门区域;浸润型表现为胆管壁增厚、管腔狭窄甚至完全闭塞;管内乳头型表现为管壁内结节或息肉[6]。肿瘤间接征象主要是病灶近端胆管的扩张与局部肝叶的萎缩[7]。
应用三维重建技术,可提高肝门部胆管癌的早期诊断率。由于病变早期肿瘤可局限于胆管壁,应用三维重建技术,更有利于早期病灶的发现[6]。计算机将多平面二维图像转换为三维立体图像,在一张图像上即可以显示肿瘤的软组织影、近端扩张的胆管、萎缩的肝脏等所有直接与间接征象,在减少漏诊的同时,肿瘤的定位也更加精确。
将影像学检查与肿瘤标记物结合,可进一步提高早期诊断率。通过肿瘤标记物CA19-9和B超进行筛查,再利用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对肝门部胆管癌作出定性定位的诊断方法,已达成了共识[3]。
2 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可切除性评估中的应用
根治性手术是目前公认的肝门部胆管癌的最佳治疗方法[8]。术前准确的可切除性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有根治性手术可能的病例,应尽量达到根治性切除,不要错失手术机会,而对于无法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应减轻痛苦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和盲目的探查[9]。
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可切除性评估主要包括肿瘤对二级以上胆管的侵犯、对肝动脉与门静脉的侵犯、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是否合并肝叶萎缩等。目前公认的肝门部胆管癌不可切除标准包括:肿瘤侵犯双侧肝内胆管并超出胆管切离的极限点、门静脉主干广泛浸润或包裹、肿瘤超出一侧胆管切离极限点合并对侧门静脉或肝动脉浸润或包裹、肿瘤超出一侧胆管切离极限点合并对侧肝叶萎缩、一侧肝叶萎缩合并对侧门静脉或肝动脉浸润或包裹、超出肝十二指肠韧带的淋巴转移或远处转移。多排螺旋CT可以对以上各项做出全面的评估。根据Ruys等[10]报道的Meta分析显示,多排螺旋CT对于判断肝内胆管侵犯程度的准确率为86%,对于判断肝动脉侵犯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3%和93%,对于判断门静脉侵犯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9%和92%,在以上三个方面均有较高的价值,而对于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的灵敏度略低。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客观、全面、清晰、立体的显示肿瘤与周围血管的位置关系,避免了医生仅凭二维图像在脑海中想象肿瘤能否切除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于预测手术切缘阴性的准确率高达94.4%[11],可以术前规划手术方案,为根治性切除提供重要依据。
虽然磁共振对胆道系统和软组织的显影更佳,但与磁共振相比,多排螺旋CT层距更小,对血管的显示更加清晰,两者各有优势,联合应用于复杂病例,能进一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虽然肝门部胆管癌可切除性评估的准确性已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仍存在误差,常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由于肿瘤沿胆管壁黏膜扩展,故对于胆管侵犯的程度易被低估。从图像上有时难以区分炎性粘连与肿瘤性侵犯,尤其是肿瘤与血管间脂肪间隙消失,但血管外形尚清晰时,对于血管侵犯的评估易过度。对于较小的孤立淋巴结转移和腹膜粟粒样播散,图像上常难以发现。
3 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安全性评估中的应用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前常存在梗阻性黄疸,胆汁淤积影响了肝功能,使多数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肝酶升高,而仅除少数BismuthI型患者外,大部分的手术方式都包括了联合肝叶的切除,对于肝功能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所以术后肝功能衰竭是容易发生且后果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由此可见,手术安全性评估,尤其是肝功能与残肝体积的评估显得极为重要。
残肝体积需要结合胆红素水平、肝脏基础疾病及吲哚氰绿(ICG)清除试验等综合评价,一般对于梗阻性黄疸患者,残肝的功能性肝体积应至少大于全肝体积的40%[12]。多排螺旋CT联合三维重建技术,能够准确的评估切除的肝脏体积与残肝体积,误差仅在5%左右[13],通过术前虚拟手术,在保证根治性切除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更多的正常肝组织,对于预防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通过术前在三维图像上制定手术方案,预先了解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避免手术的盲目性,进一步降低手术风险[14],模拟的手术方案与实际的手术方式符合率可高达90%[15]。
此外,肝胆系统解剖变异并不少见,对于存在解剖变异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前通过三维图像及时发现变异,能够大幅度降低术中血管的损伤概率,减少术中出血量[16],同时通过三维重建预判肝脏切缘胆管开口的数量和位置,可避免术后持续性胆瘘等并发症的发生[17],提高手术安全性,符合近年来提出的精准外科的理念,也是未来肝胆外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多排螺旋CT及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的诊断、可切除性和安全性评估中都有较高的价值,可作为术前手术规划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临床上仍需结合患者的年龄、全身状况、血液指标、术者的手术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对于不同患者个体化治疗,才能进一步改善肝门部胆管癌的预后。
[1] Aljiffry M, Walsh M J, Molinari M. Advances in diagnosis,treatment and palli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1990-2009[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9, 15(34): 4240-4262.
[2] Choi JY, Kim MJ, Lee JM, et al.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role of preoperative imaging with sonography, MDCT, MRI,and direct cholangiography [J]. Am J Roentgenol, 2008, 191(5): 1448-1457.
[3]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 解放军全军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 肝门部胆管癌诊断和治疗指南(2013版) [J]. 中华外科杂志, 2013, 51(10): 865-871.
[4] 方驰华, 陈建新. 数字医学技术在肝胆管结石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2, 11(2): 104-107.
[5] 陈敏蓉, 丰川. 胆道梗阻病变的多排螺旋CT诊疗价值探讨 [J].实用医学影像杂志, 2012, 13(3): 146-147.
[6] 杨立, 董家鸿. 肝门部胆管癌的CT诊断 [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0, 9(3): 230-231.
[7] Marsh Rde W, Alonzo M, Bajaj S, et al.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tract cancer 2012.Part I: diagnosis-clinical staging and pathology [J]. J Surg Oncol,2012, 106(3): 332-338.
[8] Nagino M, Ebata T, Yokoyama Y, et al. Evolution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ingle-center 34-year review of 574 consecutive resections [J]. Ann Surg,2013, 258(1): 129-140.
[9] 倪其泓, 陈涛, 王坚. 肝门部胆管癌的分型分期与可切除性评估 [J].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13, 19(6): 477-480.
[10]Ruys AT, Van Beem BE, Engelbrecht MR, et al. Radiological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Br J Radiol, 2012, 85(1017):1255-1262.
[11]Sasaki R, Kondo T, Oda T, et al. Impact of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ultidetector row computed tomography cholangioportography in operative planning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J]. Am J Surg, 2011, 202(4): 441-448.
[12] 王健东, 沈军, 周学平, 等. 提高Bismuth-Corlette Ⅲ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率及安全性的综合措施 [J]. 中华外科杂志,2013, 51(7): 596-599.
[13] 汤地, 匡铭, 梁力建, 等. 64排CT检查及软件辅助系统在肝门部胆管癌术前评估和手术规划中的应用 [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0, 9(3): 186-189.
[14] 方驰华, 李晓锋, 鲁朝敏, 等. 数字化三维重建及解剖性肝切除治疗Bismuth-CorletteⅢ型肝门部胆管癌 [J]. 中华外科杂志,2009, 47(17): 1353-1354.
[15] 苏昭杰, 段朋, 刘昌华, 等. 三维可视化系统在肝门部胆管癌治疗中的应用 [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3, 12(3): 213-216.
[16]Endo I, Matsuyama R, Mori R, et al. Imaging and surgical planning for 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 2014, 21(8): 525-532.
[17]Endo I, Shimada H, Sugita M, et al. Role of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in operative planning for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J]. Surgery, 2007, 142(5): 66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