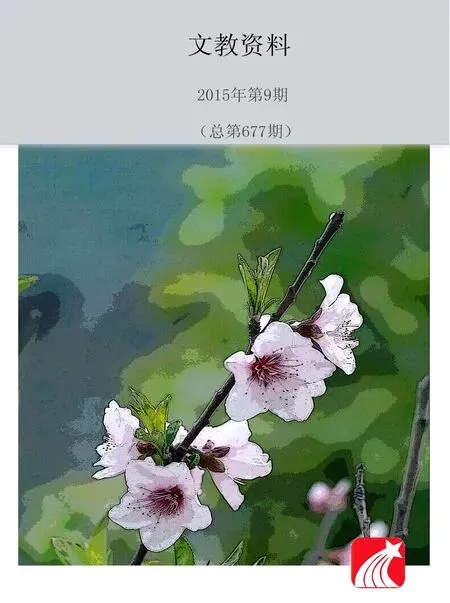以尼采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说解读作品《明智的孩子》
赵雪媛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江苏 南京210000)
以尼采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说解读作品《明智的孩子》
赵雪媛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江苏 南京210000)
被誉为“白人女巫”的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她的作品被称为“一片异教神纵欲狂欢的沃土”,其中盛行的酒神文化风格在她的作品中重获了古希腊式的狂欢。在《明智的孩子》中,安吉拉·卡特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混合在文本中,不平均地分配在人物身上,通过一种魔幻的方式,将被抛弃的欠思姐妹的悲剧人生幻化成一场讽刺喜剧的盛宴。
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 《明智的孩子》
尼采认为,理性的出现消灭了神话,而神话的消失使得诗歌无所适从,诗歌的困惑则衍发了人们对艺术的美和生活的真理之间深刻的思考。当尼采提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时候,他向古希腊遥望致敬,并且试图寻找这二者的区别和共鸣。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都是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者恰恰相反却相依而生。周国平先生在序言中极为精炼地总结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特点:
日神精神沉眠与外观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自是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著人生,后者超脱人生。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更具形而上学性质,且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①。
在尼采的想法中,酒神精神比日神精神更加具有悲剧的色彩,然而无论是酒神精神还是日神精神,都和科学理性是相对的、相反的,并且是难以融合的。二十世纪的末期,“白人女巫”安吉拉·卡特综合了伊壁鸠鲁主义、酒神狂欢精神和魔幻色彩的一位传奇女作家,她的作品被称为“一片异教神纵欲狂欢的沃土”②,在她的作品《明智的孩子》中,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不平均地分配在人物身上,让他们形成了相反或者相似、相对或者相容的不同关系。在《明智的孩子》里,没有什么人是清白的,私生子、神秘的阿嬷、轮椅上的第一任妻子、疯狂的梅齐尔、与兄弟行为恰恰相反的佩瑞格林……有些人对着人生的痛苦转过头去装作看不见,用金钱和虚幻的美与庄严来遮羞;有些人却正面临着人生的悲剧,对它发出大声的嘲讽和欢笑。
在《明智的孩子》里,安吉拉·卡特将女性主义和酒神精神结合了起来,实际上突破了从伍尔夫开始的“女性生态主义”的简单区分法:在女性生态主义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亲和的、趋向自然的、原始的(一如母系氏族),而男性通常被认为是工业的、强力的、现代的、城市的。然而安吉拉·卡特并没有这样简单区分。诚然,在阿嬷的身上,有着天体主义(裸身)、素食、不能接受有人摘花等诸多自然的原始的典型特征,但是在欠思姐妹身上,更多的是一种狂欢式的酒神精神和古希腊式的日神精神;另外,与沉迷于虚幻荣耀的梅齐尔相反——从梅齐尔的身上,可以看出割裂了酒神精神的日神精神的存在——他的兄弟佩瑞格林身上,闪耀着酒神精神的超然和日神精神的执著。“西方文学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矛盾与融合,体现了其文化内质上的矛盾与互补两重性,也体现了人自身的矛盾性和文化之悖谬。”③这句话在《明智的孩子》中有很明确的体现。
一、《明智的孩子》中的狂欢与酒神精神
快乐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我们从滑稽可笑变得至高无上,然后心碎④。
西勒诺斯对国王说:“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⑤
“生存的恐怖和可怕”(《悲剧的哲学》,第11页),对于每一个人都敞开自己的怀抱。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它们:叔本华选择了悲观的态度,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行动是有意义的,因而整个人生都是没有意义的,唯有死亡是真实的结局。然而与叔本华的悲观不同,酒神的信徒们正视生存的苦难,却从狂欢中宣泄了苦痛,嘲讽了粉饰。
欠思姐妹是梅齐尔·罕泽的私生子,根据她们的说法:“我们的私生女身份没什么狗屁浪漫可言,最好也只是个闹剧,最糟是个悲剧,其他时间则是长期的不便与困扰。”(《明智的孩子》,18页)但是欠思姐妹在提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却采取的是一种嘲讽的、超然的态度。她们不乏戏谑地提到自己在遇到佩瑞格林叔叔之前幼年时候的艰苦生活,也将自己一次一次得不到亲生父亲承认的失望与痛苦转化成了对生活更加坚强的态度。在接到并不真诚的梅齐尔·罕泽爵士百岁寿诞宴会的邀请函时,诺拉·欠思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紧张或者尴尬而退却,反而嘲讽道:“天知道,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也该喝点泡泡香槟了!”(《明智的孩子》,第9页)
《明智的孩子》里,充满了戏剧性的狂欢气氛。欠思姐妹从小就被训练成一对歌舞女郎,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世代更替和际遇不幸而逐渐堕落为最末流的歌舞女郎。但是欠思姐妹从来没有乖乖服老,也从来没有对生活的苦难低头,相反,她们自称“两个疯癫的老太婆”,并且嘲笑起自己现在困窘的境遇:“买杯酒请我们,我们就唱支歌儿给你听,如果场合特殊,甚至还可能抬腿跳个舞。”她们总结道:“唱歌跳舞是多么开心的事!”(《明智的孩子》,第10页)这种态度和酒神信徒面对生活的痛苦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时的狂欢与放纵是多么相似。
理性的人是难以面对酒神的狂欢的。他们以洞察人生的真理为最终目的,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为生命的意义。然而酒神的信徒恰恰相反:
酒神状态的迷狂,它对人生日常界限和规则的毁坏……个人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淹没在其中了……在这个意义上,酒神的人与哈姆雷特相像,他们彻悟了,他们厌弃行动;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尼采,第28页)
当然,酒神的信徒和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还有很大区别,否则,酒神精神就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要混为一谈。但是最重要的是,酒神状态带来了一种迷狂,类似酒精作用于中枢神经引起的麻痹和混乱效果。它让人们做出疯癫的举动,然而这能够怪罪于酒精吗?它破坏了日常的界限,破坏了理性的规则,因为真理和艺术、美、爱,其实并没有很大关系,在有些时候还有可能会是相对立的。在欠思姐妹的面前,人生已经走进了最低谷:她们年老了,八十岁的歌舞女郎,听来就是令人伤心的一个身份。她们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承认,并且不断地被罕泽家的姐妹夺去风头,事业一再下坡。她们住在阿嬷留下的房子里,古老的房子,在“错误的一边”,贫民区和富人区隔着一条河流。生存毫不留情地向欠思姐妹展示着痛苦、贫穷、无可奈何,然而当欠思姐妹去参加父亲的百岁寿诞的时候,她们“浓妆足有一寸,衣服比人年轻了六十岁,丝袜上满是星星,又短又小的裙子勉强盖住屁股”。在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之后,欠思姐妹开心地相对一笑,“大胆招摇地跨进宴会厅。”她认为,“我们还是很有看头的,即使他们受不了看见我们”。(《明智的孩子》,第274页)
他们——理性的人们,或者说自以为理性的人们,当然受不了看见她们。“这些可怜虫当然料想不到,当酒神歌队的炙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愰如幽灵”。(《悲剧的诞生》,第5页)欠思姐妹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早已不是歌舞女郎取悦于别人的目的。她们已经八十岁了,一切打扮都是为了自己愉快。在她们心里,她们还是美丽的、迷人的,虽然打扮得过火了些,却在这过火的放纵中找到了灵魂的慰藉。她们不惮于惊愕了他人——而他们却必然被她们惊愕。“日神式的希腊人看到他们(酒神的信徒)必定多么惊愕!……也许这一切对他来说原非如此陌生,甚至他的日神信仰也不过是用来遮隔面前这酒神世界的一层面纱罢了”。(《悲剧的诞生》,第9页)看着欠思姐妹的行头,人们感到惊愕的同时感到了畏惧。人生其实不过是一场悲剧,区别仅仅是用狂欢来抵抗,还是用欺骗来遮掩。当欠思姐妹如同酒神狂欢的队伍一般走过的时候,梅齐尔被从神座上拉下来变成了凡人,轮椅变回了艾夫人,佩瑞格林回到了原来的模样。人生的痛苦在酒神狂欢的队伍面前黯然失色。
与欠思姐妹相似,同样具有典型的酒神精神的还有阿嬷。阿嬷出于一种简单的爱,收养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私生女。她是个素食主义者,远离肉铺和屠宰场,并且远离一切花店,因为她无法忍受花朵被摘下、被夺去生命时的尖叫。阿嬷是个敏感而聪明的人,她对生存和生活的理解如同哲人。她对战争的理解独有特色:“每二十年,这种事总要发生一次。这是代与代之间的问题。老男人受不了竞争,就把找得到的年轻男人全杀掉。”(《明智的孩子》,第43页),她的座右铭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阿嬷平日总是一副正派人的模样,但就连小小的欠思姐妹也感觉到“阿嬷看来有点古里古怪,跟她出门时总抱着一种叛逆全世界的感觉。”(《明智的孩子》,第48页)
阿嬷从来没有为任何人,任何事情或者任何环境妥协过。按照欠思姐妹的说法,就连法西斯也没办法阻止阿嬷去酒馆打酒。尽管阿嬷死在空袭的炸弹中,死在去酒馆的路上,但是她并没有什么意外,也没什么后悔的。她的一生之中都有这种超然的态度,她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不是一种酒神的迷狂,而是酒神精神的另一个体现,一种“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译序》,第3页)阿嬷即使年老,依旧不曾羞于自己残破的身体,坚持天体主义的裸体行为,这里面包含的回归自然与复归世界本体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二、《明智的孩子》中的幻觉与日神精神
他悲叹道:“我父亲扮演李尔王时曾戴过的王冠——历经那么多死亡,那么多心碎,那么多辗转奔波……你可知道,你可猜想得到,它对我有多重要?重要得超过财富、名声、女人、小孩……”(《明智的孩子》,第147页)
回顾古希腊的神话,在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中,希腊人铸造出生活辉煌的幻象:“在日神阶段,“意志”如此热切地要求这种生存……以致悲叹本身化作了生存的颂歌。”(《悲剧的诞生》,第12页)古希腊人是多么聪明,早已看透了生存中的不幸和痛苦,所以他们的神祇不再为他们增加罪过,而是如此欢愉,用一切美的和愉快的事物构建出一个神圣的奥林匹斯山——唯一一个美与幻觉的神祇的乐土。
梅齐尔的一生并非十分顺利。他继承了父亲对莎士比亚戏剧狂热的喜爱,和戏剧与现实无法区分的特点。梅齐尔和佩瑞格林共同的父亲,老罕泽,在两个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便自杀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佩瑞格林逃跑了,而梅齐尔被困住了,这句话不只是说他们的姑姑,那个痛恨自己哥哥的女人,也是说那顶纸做的金王冠,那个虚幻的高贵、权利、荣耀的象征。佩瑞格林逃走了,而梅齐尔被困住了,一生一世都没有走出这顶金王冠的世界。
有一些人认为,既然酒神精神象征的是迷狂的非理性状态,那么与酒神精神相对的日神精神应当就是理性的代表。其实这一点周国平先生在开头就特意提出过:“日神冲动既为制造幻觉的强迫性冲动,就具有非理性性质。有人认为日神象征理性,乃是一种误解。”(《译序》,第2页)日神精神其实也是非理性的,它阻止人们理性地看待世界的真相,取而代之的是用美的东西和艺术的东西自我麻痹。梅齐尔的一生显然充满了日神精神的特质,不幸的是,他割裂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不可分裂的联系,从而沉溺在了辉煌和荣耀的假面之下,欺人又自欺。
在日神状态中,艺术“作为趋向幻觉之迫力”支配着人,不管它是否愿意⑥。金王冠和莎剧对于梅齐尔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梅齐尔不是在追求着荣耀和经典,相反的是,荣耀和经典朝着他扑面而来,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就像他和佩瑞格林刚失去父母的时候“那些在饭店大厅做生意的、胸部下垂头戴羽毛帽的可爱女士”用糖果、热狗、冰淇淋派和泛滥的同情心几乎淹死这两个幼小的孩子。梅齐尔被困住了。他继承了父亲的金王冠和莎剧,至死都没有放弃。他带着金王冠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美国,并且将莎剧也带了过去;在火灾现场,他对自己的兄弟、妻子、孩子(不论是私生子还是亲生孩子)都没有关心,唯一在乎的是他的金王冠,佩瑞格林将他的金王冠和私生女救出来的时候,他扑上去抢金王冠,丑态百出;直到他百岁寿诞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金王冠,从佩瑞格林手上接了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金王冠所象征的东西,不仅仅是《李尔王》,或者《麦克白》,或者《哈姆雷特》,或者莎士比亚的其他什么悲剧。梅齐尔被艺术的“趋向幻觉之迫力”支配着,从来没有逃脱出来。他没有到达过酒神精神的境界。他满足于这种支配,并没有揭开面纱的勇气与力量。他和佩瑞格林,和阿嬷,和欠思姐妹比起来,都太过懦弱。他害怕生活的残酷和生存的悲剧,所以背过脸去,宁愿沉浸在幻觉中。
沉溺于幻觉是日神精神的特征。“日神精神教人停留在外观,不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译序》,第4页)希腊人构筑起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时候,就是在试图通过一个辉煌壮丽的神话来阻碍自己透彻地看清生活的真相。对于有死的众生而言,看清生存不过是为了死亡这一真相并没有太大好处,如果没有酒神精神的拯救,就会很容易走入悲观主义的歧途。而梅齐尔割裂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联系,他失去了看清生活真相并嘲笑它的勇气。他看见自己的私生女的时候,竟然大言不惭地对自己的弟弟说:“佩瑞格林,真高兴你来看我……还把你的可爱女儿也带来了!”(《明智的孩子》,第102页)
明智的孩子认的爹,明智的爹更应该认得自己的孩子。而梅齐尔拒绝了,他不愿认亲生女儿,而是让自己的弟弟为他认下。(却因为第一任妻子的出轨阴差阳错将弟弟的女儿认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多么讽刺。)尼采从未认可过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割裂,如果硬要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割裂开来,则我们只会收获过度的疯癫野蛮和虚假的美好与幻境。梅齐尔换过三任妻子,有过数个儿女,却从来没有学会爱的真正意义,因为爱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在生存的痛苦面前的从容和镇定,来自于在生活的苦难和真实面前的不离不弃。梅齐尔将日神精神的蒙蔽性发挥到了极致,当他在百岁寿诞的时候看到私生女带着酒神狂欢的面具招摇而过的时候,他的荣耀和幻境花容失色,而他也第一次伸出双手,呼唤“女儿”,得到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和解。
三、《明智的孩子》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统一
喜剧与悲剧面具并挂,一个嘴角往上,一个嘴角往下,它们是守护神——在人生中亦然。戏如人生,不是吗?(《明智的孩子》,第81页)
尼采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区分开,并且反复强调二者正好相反的作用力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两种精神是不相容的。恰恰相反,很多艺术形式正是日神精神的外表和酒神精神本质的结合体,例如诗歌和神话。在审美的国度中,伦理道德、善恶是非不再是唯一的标准。“重估一切价值……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译序》,第6页)这使得审美的狂欢获得了可能。无论是酒神的迷狂还是日神的自持都只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不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在《明智的孩子》里,虽然诸多人物身上都有酒神和日神的结合,但是作为最完美和最有趣的结合,佩瑞格林确实是一个典范。
日神状态的鲜明特征是适度,酒神状态的鲜明特征是过度⑦。这两点看似不相容的特征在佩瑞格林的身上很好地融合起来,他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却又具有温馨的爱和包容的情怀。让我们再回顾这段话:
日神精神沉眠与外观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自是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著人生,后者超脱人生。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更具形而上学性质,且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译序》,第4页)
佩瑞格林给欠思姐妹塑造了一个温馨的 “父亲”的形象,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个“父亲”其实是叔叔;他试图用零食和魔术来逗欠思姐妹开心,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这是对别人而言的。对他自己,他从来不放弃正视人生,无论是欢乐还是苦难,他将欠思姐妹带进舞台后台,进入梅齐尔的化妆室,让她们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并且在梅齐尔拒绝与女儿相认的时候愤然而去。佩瑞格林是一个决不放弃人生欢乐的人,他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略带喜剧性的、爱好美食和自然的胖子。但他也不曾回避人生的痛苦,虽然他的事业数次起伏,他也曾经数次在欠思姐妹视线中消失 (有一次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在异国他乡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从生活中消失,每次卷土重来都是一场新的成功盛宴。欠思姐妹说他“单单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太容易觉得无聊”。(《明智的孩子》,第87页)无聊是人生的本质,佩瑞格林是如此聪明的人,不会看不清生命的本质,有时候不过是短暂的爱恨纠葛之后永恒的沉寂。在他的眼中,石油大亨也好,钻石财富也罢,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那只不过是生存的一点必需品而已,而生存本身就不等于生活。
佩瑞格林身上的酒神与日神的二元色彩在一次聚餐中完美地体现了出来。他为两个亲生女儿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两个盒子各装着小小的草叶窝,窝里是一只毛毛虫。”(《明智的孩子》,第243页)
他用两个女儿的名字命名了全雨林最美的两种蝴蝶。只要人们依然热爱美丽,热爱蝴蝶,就会记得她们的名字。他带给她们“美丽的永恒”,美丽而能永久流传的东西,因为这两个女孩子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最珍贵的宝物,他试图给她们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两件东西:美丽和永恒。这是日神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美丽和永恒的不懈追求,一如希腊人塑造奥利匹斯山上的神祇。
然而两个女儿对蝴蝶的反应不仅冷淡而且嘲讽,她们希望得到钻石镯子或者一点石油财富。生活的现实和冷酷像一记嘲讽的耳光打醒了佩瑞格林,撕开了日神蒙在生活上面的美丽面纱。佩瑞格林终于发现,“经过这番家庭团聚,我会很高兴与鳄鱼为伴”。生活的美丽假象荡然无存,丑陋和冷酷赤裸裸地显露出来。然而这不是一切的终结。就在他独自离去之后的数年,众人都认为他死在雨林之中的时候,他再次在哥哥的(也是他自己的)百岁寿诞归来,带来了雨林中无数美丽的蝴蝶。他告诉哥哥:“我们的每一个女儿,都各有一种以她们命名的蝴蝶。我还把这一种以你命名,你这没用的糟老头。”(《明智的孩子》,第288页)
这一次佩瑞格林的蝴蝶和魔术与过去不同。他不再是一个日神的信仰者,单纯地相信生活外表美丽的外衣。他看到生活的丑恶,他离开过,可是他又回来了,以一种狂欢的嘉年华式的姿态。他不仅仅是酒神的信徒,也不仅仅是日神的信徒,成了二元艺术的混合体。西方文学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矛盾与融合,恰恰正是体现了其文化内质上的矛盾与互补两重性,也体现了人自身的矛盾性和文化之悖谬。“文学因其具有酒神精神而使人性以艺术的方式获得一种自由进而拥有美感;文学也因其具有日神精神而使人性以艺术的方式表达理性意志、捍卫人之为人的高贵理性、提升人之精神与灵魂品位,从而也拥有美感。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运载着文学所不可或缺的人性意蕴”⑧。这段话正是对佩瑞格林这个人物和《明智的孩子》这本书最好的概括。
注释:
①包慧怡.胶片之影,杂剧之光:赏析《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凤凰网读书,2012年05月31日.
②周国平.《悲剧的哲学》译序.悲剧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4.本文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③赵国春,刘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酒神与日神之悲剧.求索,2012.
④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0.本文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⑤尼采.悲剧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11.本文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⑥周国平.《悲剧的哲学》译序.悲剧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3.引《强力意志》第798节.
⑦周国平.日神和酒神:尼采的二元艺术冲动学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卷(4).
⑧赵国春,刘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酒神与日神之悲剧,求索,2012.
[1]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哲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2]安吉拉·卡特.严韵译.明智的孩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伊莱恩·肖瓦尔特.韩敏中译.她们自己的文学.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周国平.日神和酒神:尼采的二元艺术冲动学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卷,第四期.
[5]赵国春,刘进.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酒神与日神之悲剧.求索,2012.
[6]杜雪琴,余静.论《聪明的孩子》的叙事.大众文.
[7]张永慧.欠思“阿嬷”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大众文艺.
[8]李凤.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论——论《悲剧的诞生》中的美学思想.安徽文学,2009.
[9]蒋承勇.酒神与日神:西方文学的双重文化内质——兼谈文学的人性意蕴.江西社会科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