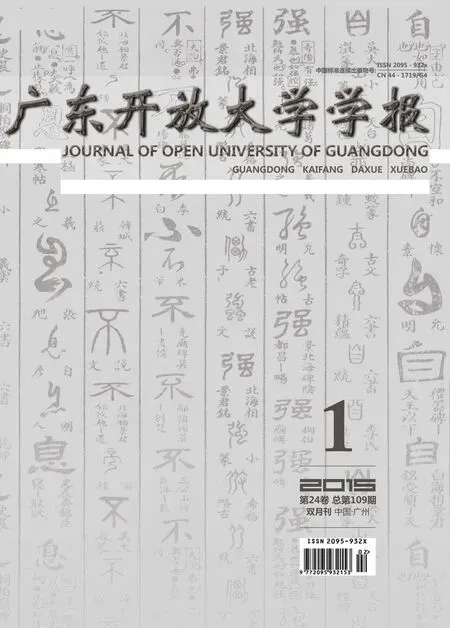西山会议派研究述论
姚江鸿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是民国史上一个特殊又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发端于国共合作,但却没有终止于国共的分裂,并且在后来的国民党各种派系斗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正面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二十年代,这段历史的关键在西山会议。”[1]所以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民国政治史和国民党党史的相关一环,同样也是全面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而旁窥早期中共党史的重要一幕。
然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早期的“西山会议派”研究存着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大陆地区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偏重于对其“反革命”的定性与叙述,港台地区出于维护国民党的“正统性”,在对“西山会议派”进行研究时往往立足于其反共的正当性,对中共有所贬低。但是,随着大陆和港台各地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紧密,学术领域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变得越来越弱,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文即是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成果作一定的梳理,探讨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热点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对“西山会议派”研究浅见。
一、早期基础性的研究
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冒充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2]。“西山会议派”因反对联共而被当时的中共和国民党一批激进党员称为“右派”。
早在1924年4月,陈独秀就发表了《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首次公开宣称“国民党内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分化”[3]。西山会议召开期间,陈独秀又对“左右派”概念作出了界定,实质是对“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身份的界定[4]。后来,毛泽东又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打破反革命宣传,对抗西山会议及“右派”之言论,把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是腐败懒惰分子,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方法之一,“西山会议派”的所作所为,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背叛[5]。
中共当时以《向导》和《政治周报》作为攻击“西山会议派”的重要阵营和基地,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主要撰稿人,他们将“西山会议派”视为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的,反对国共合作和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从此,这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便一直被扣在参加西山会议的一批国民党元老身上。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大陆史学界对“西山会议派”的研究也长期沿用和继承这一说法,在不客观的定性之下而力图弄清楚基本史实和进行学术探讨研究,这是长期以来大陆对“西山会议派”研究的基本模式①用这一模式来进行研究的著作有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等人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系列;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宗华《中国大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贺贵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上台又下台》,载于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的一鳞半爪》,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集》第12期。论文方面有高福德《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光远《西山会议派概述》,《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董江爱《西山会议派反共纪实》,《历史教学》1999年第4期;赵德教《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李正华《西山会议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周自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两次反动会议》,《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卷;王光远《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文史精华》1996年第3期;王光远《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民国春秋》1996年第1期。
“西山会议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他们的日记和言论资料如文集、自述、年谱,以及第一次国共合时期两党重要成员的自述和回忆录,也都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史料②代表作有汪仰清等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持日记》(未刊);《戴季陶先生文存》,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59年版;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另有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居正、邹鲁《清党实录》,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编》,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85年版;《叶楚伦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1987年版;《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2年版;谢幼田《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西山会议派”成员所留下的东西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弄清楚基本的史实之外,也作出了一定的评述和价值判断。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讲,并不具有很强的学术作用,它们的史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此外,大陆和港台的一些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人物传记也具有此功能③大陆代表作有林有华《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林济《居正评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小林《覃振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台湾有许继峰《邹鲁与中国革命》,中正书局1981年版;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海外有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从早期的研究成果看来,大陆方面对“西山会议派”研究的成果稍有欠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中共先前反攻“西山会议派”时所提出的主张。港台方面则大多利用“西山会议派”人物所遗留的史料,基于事实和基本史实的还原,如西山会议的召开、上海“二大”、中央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等历史内容的梳理,无论是港台还是大陆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
二、研究之突破与进展
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关注多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中港台方面是主要阵地,研究成果较为显著,虽然数量不多,以专著和学位论文为代表,但对问题的研究都很深入,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第一个正面谈及“西山会议派”的是台湾学者沈云龙,他曾发表《西山会议派反共之经过》一文。由于资料的限制,这篇文章基本是叙事性的,也没有作相关的学术性评论。后来他又发表了《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从武汉分共到广州暴动》、《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大会的合作》等与“西山会议派”活动有关的文章[6]。沈氏的文章一向只标注书名,没有明确注释,上述四篇文章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其文与后人的研究成果相较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但对于帮助我们了解西山会议的来龙去脉仍有很大价值。与此同时,台湾传记文学三十二卷第三期也发表了桂崇基、黄季陆、唐德刚等人的关于专论“西山会议派”的文章④该期的文章主要有桂崇基《西山会议之形成与经过》,黄季陆《访黄季陆先生谈西山会议》,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均载于台湾《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其中尤以唐德刚的《论西山会议派》值得注意,他认为“西山会议派”不仅反共而且反集权[7]。从反集权的角度开启了“西山会议派”研究的另一扇门。
接下来要算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史的知名学者李云汉,他于1967出版了《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专章讨论了西山会议。文中视戴季陶主义为西山会议反共运动的理论先导[8],开“西山会议派”理论思想来源之先河。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国民党内反共风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也曾参与过西山会议的召集,大陆学者王奇生同样持这种观点[9]。虽然该书有关“西山会议派”的论述的篇幅不是很多,但影响非常大,常常被两岸各地学者竞相引用,而且书中诸多的一手资料和原始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李云汉也算是早期对“西山会议派”研究造诣颇深的一位学者。不久以后,他又发表《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一文,如果说《从容共到清党》对西山会议的探讨是李氏研究“西山会议派”的第一步,那么《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一文可以说是第二步,因为这是一篇专论“西山会议派”的文章。此文详细叙述了“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中央的组织与人事,地方党务中的反共活动,上海中央在北伐清党中的立场等问题,且也为我们了解国共之间在各地党部的斗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0]。
谢持是“西山会议派”元老之一,他的孙子谢幼田作为“近水楼台”式的人物来研究其爷爷辈自然有不可多得的优势。2001年,在胡佛研究所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西山会议派”元老之一谢持之孙谢幼田年在香港出版了专著《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大有为“西山会议派”的“叛党集团”罪名平反之意,他在书中说:“将所谓七十五年来一直被当权者刻意隐瞒和歪曲的这一段事实真相展示于世人之前。”[11]作者认为在中国高举反对共产主义的大旗和反对苏俄红色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就是西山会议,国民党以后的一切反共运动,都是西山会议在政治上的延续,蒋介石在思想上继承了西山会议的道路,但在组织方面,对西山会议始终是打击[12]。该书运用了独家资料《谢持日记》,对整个西山会议的发轫、兴衰进行了全面细微的考察,揭露了先前大量未知的事实,最为明显的是对蒋介石的崛起、蒋对联俄容共的态度,及其与西山会议的利益交换和妥协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述。段干木在书评中也称该书为一部勘误求是拨乱反正的力作[13]。然而由于立场的原因,作者的观点难免有失偏颇。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该书的评价则相对公允。他认为谢君之作,终究不失为西山会议派传统的反俄反左的一家之言,也不脱当事人后裔著书,辩冤谤白,难免于隐恶而扬善,但作为谢持的孙子,难免笔端常带有感情[14]。
这个时期的台湾,除著作外,以博硕学位论文来研究“西山会议派”也算是一大特色。韩剑华在1980年撰写的硕士论文《西山会议之研究》开始以西山会议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并应用新的理论方法。作者以政治学者Dentin之政策分析法(policy Analysis)及系统论为框架讨论西山会议,他将联俄容共政策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列为“输出项”,即没有联俄容共政策,便不会发生西山会议[15]。时隔17年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金永信则以“西山会议派”为研究对象,于199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这是一篇真正以史学角度对“西山会议派”进行研究的高水准学术论文。该文运用了多种史料,结合当时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西山会议人物的具体活动以及“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组织的运作进行了甚为细致的介绍,文中对“西山会议派”参与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的叙述可算是填补空白之举⑤参见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一1931》,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台湾地区汉学学位论文汇目:http://ccs.ncl.edu.tw/theses_83/theses_83_index.htm.。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最后论及了“西山会议派”的失败,并将其原因归结于本身无实际力量,不懂得运用群众,只有一个响亮的反共口号等。这种超越历史本身的历史分析法与大陆地区在分析近代革命失败的原因上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大陆地区关于“西山会议派”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但在台湾地区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以博硕士论文和专著为代表。在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基本史实梳理的同时,也对其思想理论先导和来源,以及形成和失败的原因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与分析。与此同时还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其研究的学术性可谓空前。
三、繁荣和多元化的研究
21世纪前后,由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大为减弱,大陆地区的史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民国史由曾经的“险学”一跃而成为当今的“显学”。因此这也同样影响着作为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重要一环的“西山会议派”的研究,其主要表现为突破了过去传统的“西山会议派”反革命的说法,研究不再单一而显得相对多元,对“西山会议派”评价也大体客观,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三部分展开。
(一)“西山会议派”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共产党的态度
按照先前大陆地区的说法,“西山会议派”的产生是“反共”、“反苏”的结果。2000年前后出现的相关论文,首先开始将“西山会议派”的具体环节或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并提出“反叛性”观点的是杨奎松的《容共还是分共》一文,他打破了传统的“西山会议派”“反共”一说,首次指出西山会议决议中的“分共”主张。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反共”的角度考察这段历史,他主张从深入了解国民党分裂者当年如何看待“容共”问题入手,以此分析说明他们逐渐走向“分共”道路的主客观因素乃至心理情感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16]。杨奎松所展现的这一视角为考察西山会议的发起缘由打开了更广泛的理路。同时他还认为“西山会议派”是为“分共”而不是“反共”才聚集在一起。在他接下来的一系列关于研究国共关系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中都持这种观点⑥如《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大革命前期国共关系与及共产国际》,《文史哲》1990年第6期;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容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与此持不同但又相似的观点的学者有王奇生等。王奇生在他的名著《党员党权和党争》以及他参与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均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产生不是因为“反共”和“反苏”,而是出于对汪精卫排挤党国元老的不满。他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容共’政策的不满,二是共同对汪精卫的不满”[17]。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也认为“西山会议派”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基本主张是“分共”,尚非“反共”。复旦大学尚红娟在其博士论文《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中同样持此观点,稍有差异的是作者认为西山会议之缘起的“反鲍(鲍罗廷)”色彩远浓于“反共”,“西山会议派”的形成重点是“反鲍”,不是“反共”或者反“汪”。
(二)“西山会议派”与“三大政策”及俄国的关系
长期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三大政策”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陆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般是持否定立场的,即“西山会议派”向来是“反俄”、反“三大政策”的。杨天石首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是现今学术界研究“三大政策”的最权威代表,该文在解决海峡两岸对“三大政策”来源分歧的同时,也将“西山会议派”与“三大政策”形成的关系真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其认为“三大政策”是在中共反对“西山会议派”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而提出的[18]。也就是说,“西山会议派”是“三大政策”这一概念提出的“中间”客体。台湾学者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如蒋永敬的《三大政策探源》、《海峡两岸对三大政策解释的比较》。他们认为“西山会议派”在早期也是赞成三大政策的,包括后来也是赞同的,“西山会议派”反对的只是“三大政策”的这个提法[19]。
此外,陈均在《试论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对联俄容共的态度演变》一文中,则就“西山会议派”对“联俄”、“容共”的态度分别进行了分阶段考察。作者将“西山会议派”对苏俄的态度演变大致划分为“联俄”、“疑俄”、“反俄”,对共产党的态度则分为“一般反对”,“友谊解决”,“彻底清共”,并由此态度的演变分析了“西山会议派”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影响[20]。复旦大学尚红娟的博士论文《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对此同样有所研究。该文主要通过对鲍罗廷在“联俄容共”中扮演的角色分析,尤其是对他分化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的政治言论的梳理,得出西山会议之缘起是因为“反鲍”。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她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形成是“反鲍”,重点不是“反共”或者反“汪”,而“反鲍”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反俄”的[21]。
(三)“西山会议派”和蒋、汪的关系
早期大陆的研究基本上是把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视为一伙人,认为他们勾结起来“反共”、“反革命”,同是“一丘之貉”。而现今学术界的观点是蒋、汪和“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的三大派系和三股政治势力,三方对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瓜分和争夺是其关系的本质。其中代表作为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他在该书中运用大量未刊档案和史料对这三方的相互斗争、角逐以及合作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同时,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大陆地区还有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罗敏的《邹鲁与蒋介石的关系(1923—1931)》。因为“西山会议派”的主张多以邹鲁、谢持、居正等领导人物的意旨为代表,故他说邹鲁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西山会议的代言者,通过邹鲁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考察整个“西山会议派”与蒋的关系。该文指出1923年至1931年蒋与“西山会议派”活动发生演变,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为“容共”、“限共”与“清党”的争论,一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邹、蒋围绕“容共”、“限共”与“清党”问题的争论不是要不要“反共”的政策性分歧,而是采取何种方式的策略性分歧。正因为如此,邹鲁在反共伊始时,采取“薄汪厚蒋”的策略,直至“整理党务案”后,邹鲁因对蒋的“限共”策略表示失望,转而公开攻击蒋,邹、蒋矛盾由此表面化。由于双方的分歧仅是方式和方法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因此双方在“清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一度和解[22]。这对我们探讨“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另一篇则为复旦大学尚红娟的博士论文《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作者认为“西山会议派”普遍存着这一个转型和蜕变的过程。同时,他们的蜕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固守三民主义,执着地反对联俄容共到因为个人恩怨,毫无原则地反蒋,再到因对现实的无奈,最终苟存于蒋中央异化的“党国体制”之中从开国元勋沦为在野政客,而最后被中央闲置。“西山会议派”之所以有这种蜕变,这是他们在跟将、汪的各种政治斗争是分不开的。通过研究,作者得出如下结论:“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史上的四次大分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山会议派”的发展与主导民国政局的蒋、汪两大集团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23]。该文结合“西山会议派”所有的政治活动给“西山会议派”的成立和消失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线索,使“西山会议派”研究更具有理论高度和实际内涵。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大陆史学界对“西山会议派”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成见和限制,研究的成果则相对比较客观和全面,既有对其进行总体性的概述,又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抽象概括,无论是研究方法抑或是切入角度,都显得多元而有层次,关于“西山会议派”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了繁荣的局面。
四、关于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唐德刚在新世纪开端的时候曾说:“21世纪中叶将是中国文艺复兴,更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在这一新的史学潮流里,西山会议派这个史学题目,必然也是将来博士生选择的重要对象之一,这是无可置疑的。”[24]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大陆与港台地区都出现了好几篇关于“西山会议派”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这不仅从侧面反映和印证了“西山会议派”在民国史乃至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它在研究成果上的繁荣。当今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研究日趋客观和公正,但在对这一重要选题进行研究时我们仍需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后期的“西山会议派”还是不是一个政治派别。黎安友曾给“派系”一词定义道: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⑦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pp.32.转自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按照黎先生的定义,我们恐怕很难再称后期的“西山会议派”是一个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是在一定目标、目的(主要为反共)下集结的,当目标消失、目的达到之后,即失去原先集结的纽带,并随着政局之变迁而与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发生复杂剧烈的分合变化。所谓后期“西山会议派”,往往因此而很难界定言说。人们之所以把后期的一个个“西山会议派”分子重新组合再称为“西山会议派”,乃是由于舆论的惯性。
再从后来所谓“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活动来看,1930年的扩大会议、1931年非常会议乃至如1933年“闽变”,这些所谓的“西山会议派”的政治立场与主张实在很难再说他们还是一个“派”。甚至,作为“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人物和元老的邹鲁,其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并谈论到“西山会议派”的时候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山会议派”是个政治派别。他在自己的回顾录中说道:“西山会议只有主张,没有派别,特别委员会成立,主张已达,西山会议即不存在。”[25]
“西山会议派”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或政治派别是我们在研究当中约定俗成的定性和前提,前期的“西山会议派”勉强符合这一定性,但是后期的“西山会议派”恐怕很难再称为一个政治派别。因此,要不要对后期的“西山会议派”客观地评价我们暂且不论,但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不得不注意这点。
二是要在发现新史料的基础上注意研究方法和切入角度,应注意结合国共史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要在国共关系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同时还应避免个人主观意志情感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正如前文所述,西山会议派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它发端于国共合作,但却并没有终止于国共的分裂。因此,以国共关系为切入点和大背景,以“西山会议派”为微观视角,进而考察国共两党的宏观历史,可能是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就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关于国共两党的史学知识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意识以及高瞻远瞩的发现问题的能力。
[1]邹达.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M].香港: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15.
[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340.
[3]陈独秀.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N].向导,1924-04-23.
[4]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右派[N].向导,1925-12-03.
[5]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N].政治周报,1925-12-20.
[6]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86.
[7]唐德刚.论西山会议派[J].台湾传记文学,1978,(3).
[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M].台北:台北及人书局影印,1987:412.
[9]王琦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98-105.
[10]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J].近代中国,1988,(66).
[11][12]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M].香港: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3.
[13]段干木.一部勘误求是拨乱反正的力作——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J].传记文学,1981,(6).
[14][24]唐德刚.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M].香港: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8-12
[15]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D].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
[16]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J].近代史研究,2002,(4).
[17]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99-211.
[18]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J].近代史研究,2000,(l).
[19]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248-277.
[20]陈均.试论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对“联俄容共”的态度演变[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21][23]尚红娟.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22]罗敏.邹鲁与蒋介石的关系1923-1931年[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1999.
[25]邹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