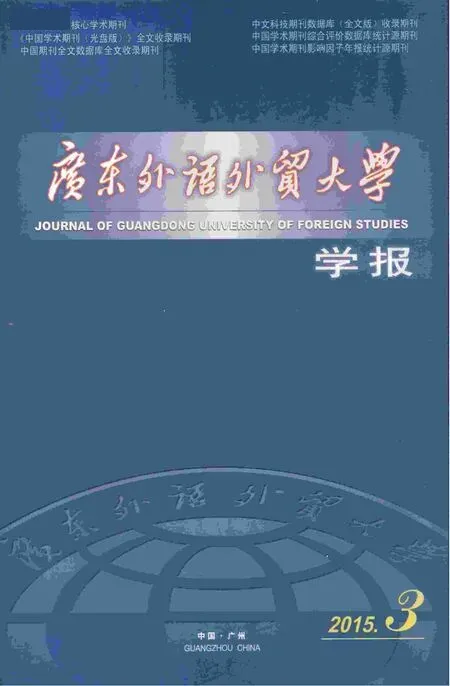日本汉诗对“谪仙”李白的接受
徐 臻
(西南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31)
一、引言
李白诗名重天下,身前不仅与日本、新罗等国诗人有诗赋酬唱,还曾赋诗“东风日本至,白雉越裳来”,颂扬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千百年后,他的“谪仙”形象也如东风化雨般播撒东瀛。特别是自江户时代以来,李白在日本汉诗坛始终占据重要的一席。然而,近几十年来日本学界对李白的关注度远低于同时代的白居易、杜甫等唐代诗人。笔者统计,1949年以来,被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收录的李白相关论文仅300余篇,而白居易为600余篇、杜甫为400余篇,均高于李白。这些李白研究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从微观出发,择取某个诗语、素材,通过考察其在诗中的运用来弄清李白诗歌风格、创作态度以及李白诗作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另一方面,与李白相关的日文出版物虽数量逾百,但多数为李白诗选集、精选。关于“谪仙”李白的接受史研究尚未引发关注。基于此,本文以梳理“谪仙”李白东渡扶桑的历史轨迹为基础,聚焦日本各时期汉诗中对李白的接受情况,探讨李白在日本被接受的背景、历程与特点。
二、平安时代:道教神仙形象的受容与李白的初传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思想使中国诗人的想象力受到禁锢,而道家飞天成仙之说却促使李白这一仙想大师的诞生。同样,老庄的神仙思想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浸润。《日本书纪》所载创世神话、《万叶集》的和歌直至近世小说、俳句中均有受到神仙思想的影响。笔者统计,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共有18处提及“仙”。随后,平安时期的汉诗集《凌云集》有10处、《文华秀丽集》有12处、《经国集》有27处提及神仙。这一时期汉诗中的“仙”多指道教仙人或与仙人相关的事物,营造的仙境意象一味模仿中国汉诗对道教仙境的想象。如《怀风藻》有诗:“姑射遁太宾,崆巌索神仙”(《春日应诏》)、“神仙非存意,广济是攸同”(《三月三日应诏》)、“灵仙驾鹤去,星客乘查逡”(《游吉野》)(与谢野宽,1926:10-70),这些诗句里的“神仙”、“灵仙”均是诗人想象中的天宫仙人,与李白并无关联。
平安中后期的日本汉诗中才开始出现“诗仙”一词,道教的神仙形象与日本汉诗、诗人、文人形象逐渐重叠。《本朝丽藻》所收中书王《和户部尚书同赋寒林暮鸟归》的第三联“唯应草圣妙飞墨,本自诗仙何用丹” (与谢野宽,1926:136)将唐代书法名家草圣张旭称为“诗仙”,认为“诗仙”即擅长丹青的人。《法性寺关白御集》所收藤原忠通的《运转左时至龄》诗序:“往日宴席,诗仙济济。年去年来,或无所残,统两三。”《江吏部集》所载大江匡衡的《九月尽日于秘芸阁同赋秋唯残一日》亦云“已到诗仙心事定,侍郎佳兴过潘郎”。①文中的“诗仙”均指擅长吟诗的人。江户汉学家林鹅峰的《本朝一人一首》卷十亦云大江匡房:“求王勃杜少陵集,且谈及李谪仙事。”(富士川英郎,1983:17-18)根据这一史料,平安中期的日本文人不仅称李白为“谪仙”,且谈论李白,熟悉他谪仙称号的由来。
关于李白诗作的最早记录则是藤原佐世 (847~897)《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李白歌行集三卷”的记载。(矢岛玄亮,1987:36)卷首题“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佐世奉敕撰”。藤原佐世任陆奥守是在891~897年间,故目录应该编撰于此一时期前后,李白诗作的传日也可推定为九世纪以前。但在平安时代 (时间相当于唐代),李白被接受的程度却远逊于后辈白居易等人。大江匡房(1041~1111)撰《诗境记》,历数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诗人,未提及李白。成书于1013年的《和汉朗咏集》中也未收录李白诗作。大江维时 (888~963)的《千载佳句》收录白居易诗507联、元稹诗65联、许浑诗34联、章孝标诗30联等。对于李白却仅仅收录了2联,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李白诗作。其诗如下:
天象部·雪 玉阶一夜留明月,金殿三春满落花。(《瑞雪》)
地理部·山水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题凤台亭子》)(金子彦二郎,1995:671-674.)
所选上述两联语言华丽、明快,但远称不上上乘佳作。编选者明显追随平安诗坛炽盛的“乐天之风”,以白居易淡泊平和的闲适诗风为尺度,甄选出以上两联。编选者并未真正理解李白天马行空、热情奔放的浪漫诗风,飘逸狂放的“谪仙”形象也尚未被日本文人解读。
三、五山时代:李白诗作传播与受容的扩大
其后的五山时代,称李白往往依中国惯例“李杜”并举。较之平安时代,李白在五山禅林中已有一定影响力。五山禅僧虎关师炼 (1278~1346)曾在《济北诗话》中有关于李白的四段记载,引用如下:
①《玉屑集》 “句豪畔理”者,以石敏若“冰柱悬檐一千丈”与李白“白发三千丈”之句并按,予谓不然。李诗曰:“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盖白发生愁里,人有愁也,天地不能容之者有矣,若许缘愁,三千丈犹为短焉。翰林措意极其妙也,岂比敏若之无当玉卮乎!
②李白《送贺宾客》诗云: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又,《王右军》云:“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按,《右军传》写《道德经》换鹅,不写《黄庭经》也。白虽能记事,先时偶忘耶?
③李白进《清平调》三诗,眷遇尤渥,而高力士以靴怨谮妃子,依之见黜。嗟乎,玄宗之不养才者多矣!昏于知人乎?
④杨诚斋曰:“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坏者非也。夫人有上才焉,有下才焉。李杜者上才也,李杜若有和韵,其诗又必善矣。李杜世无和韵,故赓和之美恶不见矣。元白下才也,始作和韵,不必和韵而诗坏矣,只其下才之所为也,故其集中虽兴感之作皆不及李杜,何特至赓和责之乎!(池田四郎次郎,1920~1922)
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关于李白的诗论。第一段诗话点评李白的名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赞李白“措意极其妙”,已然了解李白浪漫夸张的诗风。第二段诗话举出李白两首诗中自相矛盾的用典,评论李白“虽能记事,先时偶忘耶”。作者指出李白的偶尔失考之处,正说明对他已有相当了解。第三段是李白被黜离京的故事,发出“玄宗之不养才者多矣!昏于知人乎?”的感叹,为李白的际遇鸣不平。第四段议论“李杜”与“元白”的上下之分,作者认为李杜上才也。这与平安文人推崇白乐天的风气大相径庭,肯定了李白在五山诗坛上的地位。
然而,翻检五山文学全集,五山禅僧的创作往往诗偈并作,整体诗风带有浓郁的蔬筍气息,并未明显表现出对李白诗作的整体受容,多数还只是对李白个别诗句的踏袭。五山禅林中与李白的诗风较为接近,对李白较为喜爱的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元代日本禅僧雪村友梅。友梅的《岷峨集》中有不少豪迈之作,浪漫飘逸的诗风颇似李白。如《失题》诗开篇:“西南足元气,融结川与山。大峨势不群,渥洼出天闲。奔腾六合表,一目穷海寰。”(玉村竹二,1967~1981:866)起笔豪放,气势非凡。还有《平羌》诗:“天澹澹,云闲闲,扁舟夜泊平差湾。水声骤雨杂松籁,峨眉月冷冰轮环。”(玉村竹二,1967~1981:873)明显受容李白《峨眉山月歌》。长篇《送开先腴知客游峨眉》:“乾坤阔日月幹,蜀江急峩山岌。峩山岌哉界天,壁立千万丈。大鹏侧翅飞不上,尘埃野马何苍苍。呼吸风霆俯星象,饤馔群峰如核盘。雪岷银色冰阑珊,五月行人冻如蚁。”(玉村竹二,1967~1981:883)描摹巴山蜀水想象奇异夸张,语言富于变化,诗语和意境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
友梅还以李白自比。如《寄别李公叔二首》之一:“冰檗声名记昔年,追随鹰隼雪岷天。笔扛龙鼎台衡表,书抱鸿钧造化边。行乐人生能几几,羁縻世事动连连。嘉阳幕府江山好,今着诗仙与酒仙。”(玉村竹二,1967~1981:876)追忆西蜀流放生活,赞美巴山蜀水的壮美,自比诗仙与酒仙,抒发了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另一首《赠李以正·李元夫归乡》:“谪仙才调欠一官,诗酒风流转豪气。浪游万里天一陬,笑谈自可轻王侯。”(玉村竹二,1967~1981:894)刻画了狂放傲世、任侠使气、诗酒逍遥、视名利如敝屣的“谪仙”李白。
尽管五山禅林中出现了喜爱白诗及李白“谪仙”形象的倾向,但镰仓和京都的五山禅院的实质是受幕府庇护的官寺,禅僧与幕府关系紧密。他们更加推崇杜甫诗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喜爱琐细平淡、追求理趣的宋诗。李白的狂放超逸难以符合人格方正、崇尚幽玄的五山僧侣的审美取向。正如马东歌先生所言:“在日本,对于李杜,一开始就是并称的,且并之为“李杜”,一开始就是作为“元白”——其诗风在王朝时期曾盛行三百余年之久——的对立面而提出的。”(马东歌,2004:49)
四、江户时代:李白诗作流行的高潮期
(一)李白被广为接受的历史背景
江户初期,日本积年战乱、道德沦丧,长期主导文化的僧侣不足以承担力挽狂澜的历史重任。德川幕府开始重视儒学和儒生,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但朱子学的伦理道德规范却成为禁锢文士思想的枷锁。江户中期,伊藤仁斋的“古义学”与荻生徂徕的“古文辞派”相继而起挑战朱子学,提倡人性的解放。此时,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也流波东被日本,汉诗理论也由幕府初期的“劝惩论”转向“人情论”,倡导气象高华、诗风昂扬的盛唐诗。托名李攀龙的《唐诗选》盛行加速了盛唐诗在日本庶民阶层中的普及。
首先鼓吹盛唐诗风的是被朝鲜使臣权菊轩称为“日东李杜”的石川丈山。1642年,丈山在叡山山麓筑诗仙堂,请林罗山代为选出屈原、杜甫、陶潜、陈之昂、杜审言、李白、王维、孟浩然等36位中国诗人的画像挂于墙上。丈山自号六六山人,潜心诗作。丈山之诗多仿杜甫,讲究声韵格律及文字巧拙。然而,诗仙堂的设置亦尊崇李白,于李白诗作也有倡导之功。松永尺五盛赞石川丈山“昼坐诗仙堂,摘李杜之精华而入毫端;暮登啸月楼,漱陶谢之芳润而充绣肠”,批评五山禅僧“不贵杜甫之神圣,何仰谪仙之高格”(《凹凸窠先生诗集序》)。江户晚期的石克子复亦赞丈山之功云:“本朝之学者久效元白之轻俗,而未闻有闯李杜樊篱者,以至于今泯泯也。先生首倡唐诗,开元大历之体制遂明于一时。”(富士川英郎,1987:51)
自石川丈山倡导李杜诗以来,李白的“诗仙”之名日隆。江户诗人兼评论家江村北海的《青莲榭》 (《北海诗钞》二编卷四)云:“采石沉明月,浮云遗恨长。谁知东海外,复此仰清光。”将传说于采石矶醉后捉月影而沉水的李白比作明月,将李白诗才比作清光,表达了对李白“谪仙”地位的敬仰。冈本黄石的《半谪仙人歌赠古梅》赞李白“万古奇才李青莲”;伊藤东涯的《南山词伯抱病退隐于洛市顷和拙韵见寄再和谢之》亦言“豪情应似青莲李”;室鸠巢的《用前韵叠和君美见酬》 “李白文才倾宠贵,井丹经术倒王侯”。(转引自马东歌,2004:57)还有尾藤孝肇的《读<白长庆集>》 “自从知读书,触兴辄吟诗。渊明与太白,所慕曾在兹。”(李寅生,2009:188)都表达了对李白的推崇以及学习李白诗作的激情。
(二)“东瀛诗仙”祗园南海与李白
祗园南海 (1676~1751)名瑜,字伯玉,别号蓬莱、南海等,江户中期著名汉诗人。自幼颖悟,16岁入木下顺庵门下。父亡后继承纪州藩儒一职,后因行迹放荡遭流放,谪居长原村。获敕后,以汉诗文应对朝鲜通信使李东郭,大展诗才。南海性格狂傲豪放,与李白相契。曾自拟李白,作《偶作》诗:“千里依剑去,十年抱玉归。若逢知己问,山东一布衣。”诗后自注: “以为慷慨之气,可以拮抗盛唐。”(富士川英郎,1987:405)此处的“盛唐”代指李白,诗末句则是化用李白的《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顾余不及仕,学剑东山来”之句。诗风率直雄浑,颇似李白。
南海与李白的相似还体现在好仙与嗜酒上。李白诗多言“仙”,花房英树 (1957)的《李白诗歌索引》中所录李白的1049首汉诗中,言“仙”字共110次。这些想象多取自道教的神仙思想与道家的老庄思想。南海亦好仙,他描写李白的仙姿:“君不见青莲骑鲸天随仙,六如之外先生耳。”(《赠乌石处士》)(多纪仁之助,1928:12)他在《贺白石60岁寿诞》中刻画飘逸脱尘的仙人姿态:“白石先生天上仙,身骑麒麟下九天。三十六帝留不得,天风吹衣飒翩翩。夕憩扶桑倚东壁,夜炼白石餐紫烟。往往吐出天上语,人间听者耳茫然。”(富士川英郎,1987:374)表面吟咏白石,字里行间描绘的却是口吐“天上语”的李白形象。他还以“仙”奉人,对访日的朝鲜使君李东郭赋诗《敬呈东郭李君案下》:“由来学士登瀛客,先见仙才御大风。”李东郭和诗一首《敬次南海诗仙韵》,诗题亦将南海比拟为仙。(转引自蔡毅,2007:31)
李白还是以咏月名垂诗史的谪仙,在言“仙”的同时喜好在诗中营造月的意象。南海也注重将言仙与咏月结合,模仿李白舞影戏月的仙想情怀。可以说对月意象的承继是南海描摹“谪仙”李白的重要方式。他的《秋日游明光浦》:“吾今傲云月,斗酒搜枯肠。安得李太白,百篇共商量。”又有七古长篇《丁未中秋与诸子泛明光浦》:“兴逐星槎凌霄汉,身生羽翼度瀛洲。浩歌酣饮出尘埃,岸上人言李郭儔。啣杯向天仰大笑,明月落杯河影浮。”(转引自蔡毅,2007:39-40),在一片月色朦胧中营造出飞天的仙人形象。
李白有以酒沃诗,“斗酒诗百篇”之说,南海也有立地成诗,一气呵成之风。南海作诗不事推敲,鄙夷雕琢,私淑于天马行空的李白。17岁时,曾于十二小时内作五言律诗一百首,新井白石亦记载此事“亟呼酒沃之。夜未半,竟成百篇。才思若沸,俊语叠出”,“不烦师训,日弄翰墨,洒洒数千万言,不甚经思……” (《停云集·祈伯玉条》)(富士川英郎,1983:3)。雨森芳洲也曾形象地刻画南海的这一风格:“吾党祗夫子,高才本不羁。穷年唯有酒,开口便成诗。”(《钟秀集》)(富士川英郎,1983:91)南海追忆纵酒狂歌的年少岁月:“轰饮百斛气如虹,不惜日费千万钱。醉后大言惊四座,兴来雄笔扫九天。傲睨宇宙高歌里,世人观者言是仙。”(《赠对州松浦子仪》)(富士川英郎,1987:416)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李白的取径效法。木下顺庵门下还有松浦霞沼,与南海交好,亦与李白诗风接近。南海曾以李白比拟霞浦:“文采风流忆昔时,青莲去后有君诗”(《赠对州松浦霞沼二首》之二)(富士川英郎,1987:416)霞沼则吟诗:“祈子工文兼好仙,忆与余订采大药”,“诗酒追逐无虚日,临风霞举态仙仙”(《钟秀集·次韵伯玉词兄寄怀却呈》)(富士川英郎,1983:46),流露出二人对仙的神往。
从南海的诗中不难发现他心中的“谪仙”李白是纵酒享乐、狂放不羁的天才式诗人。对李白形象的受容主要在超凡飘逸的仙姿仙态与沃酒赋诗的文采风流上。而对李白那种“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反抗风骨、“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的哲思玄理的受容尚难觅踪迹。
(三)江户晚期汉诗中的李白形象
江户晚期,幕府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谪仙”形象受到渴望逃离现实社会的喧嚣、希求过上隐遁生活的文人喜爱。他们在吟咏李白时多沿袭唐人说法并加以发挥、比附。有的日本诗人甚至以整首诗描绘李白,讴歌其谪仙风采。如村上醒石的《题醉李白图》 (《宜园百家咏》卷七)云:
仙乐飘扬骊宫开,不知渔阳起尘埃。哲妇倾国岂忍见,终日颓然举酒杯。文章无人得比偶,未审少陵相敌否?巍巍高冠谪仙人,唯有明月堪其友。何羡紫绶与金章,大醉如泥是君乡。请看此中未肯忘社稷——白发缘愁如个长!(转引自马东歌,2004:52)
这是一首题画诗。第一、二联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刻画了忧国忧民、举杯消愁的李白。第三、四联称李白为与明月为友的“谪仙人”,赞誉他诗情横溢。最后两联化用李白诗,写醉乡中的李白仍心系社稷、愁绪万千。诚然,李白曾作文:“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上安州裴长史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达入世之心 (詹瑛,1993:3973-3988)。显然,村上对太白的安邦之志是比较了解的。诗文表面写李白忧国,实则隐射幕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诗人自比生逢乱世、报国无门的“谪仙”李白。
还有江户中晚期儒者薮孤山的长篇《拟晁卿赠李白日本裘歌》(《孤山先生遗稿》卷二)颇有几份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风采,情浓意重地描绘李白的“谪仙”形象。诗文如下:
天蚕降扶桑,结茧何煌煌。玉女三盆手,丝丝吐宝光。机声札札银河傍,织出云锦五色章。裁作仙人裘,云气纷未收。轻如三花飘阆苑,烂似九霞映丹丘。世人懵懵苦尘网,安得被服游天壤。六铢仙衣或不如,何况狐白与鹤氅。我求神仙无所见,远至中州之赤县。东京西京屹相望,五岳如指河如线。君不见岁星失躔落上清,化为汉代东方生。又不见酒星思酒逃帝席,谪为本朝李太白。太白何住太白峰,手提玉杖扣九重。九重天子开笑容,满廷谁不仰清丰。片言不肯容易吐,才逢酒杯口蓬蓬。百篇千篇飞咳唾,大珠小珠走盘中。长安城中酒肆春,胡姬垆上醉眠新。长揖笑谢天子使,口称酒仙不称臣。忽思天姥驾天风,梦魂飞度镜湖东。百僚留君君不驻,纷纷饯祖倾城中。我今送别无尺璧,唯以仙裘赠仙客。仙裘仙客一何宜,醉舞跹跹拂绮席。昂藏七尺出风尘,已如脱笼之野鹤。从是云车任所至,弱水蓬莱同尺地。西过瑶池逢王母,云是日本晁卿之所寄。(转引自马东歌,2004:59)
该诗前半部分塑造美丽的玉女、华丽的仙裘、缥缈的仙境、诗情横溢的岁星等审美意象,为超凡拔俗的“谪仙”出场做铺成。紧接着写酒星降临人间,化为“谪仙”李白。并通过营造酒后醉吟、身披仙裘、适意自舞、飞升仙境、遨游瑶池等一系列意象,神话般地歌颂了李白的来历与去向及其诗难以企及的奇逸。表达了作者对太白仙风傲骨和传奇性经历的敬仰和追慕。
有的江户诗人对李白“谪仙”形象的受容则是间接的,李白之于诗人的影响乃是精神上的潜移默化。如大田南亩的《将进酒》借李白诗题,沿袭太白诗风:
君不见扶桑百日出海天,惊风倏忽没虞渊。人生虽寿必有待,莫将大年笑小年。不知何物解纷纷,唯有清樽动微醺。樽中竹叶绿堪拾,何可一日无此君?为君沽取十千酒,一饮应须倾数斗。已当玉杯入手来,胸中复有垒块否?世人汲汲名利间,欢乐未极骨先朽。千金子,万户侯,于我如蜉蝣。与君乐今夕,一醉陶然泻百忧。满酌劝君君满饮,有酒如海肉如丘!(转引自马东歌,2004:53-54)
此诗不仅词语风格,旨趣情怀亦沿袭李白。全诗虽未提及李白,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人生如梦、宠辱不惊、名利如蜉蝣的思想。诗人向往的是如李白一般及时行乐、放浪形骸的诗酒人生。
江户汉诗中对李白的受容,大多数只是诗中的一两句。如梁田蜕岩的《野中清水歌》(《蜕岩集》卷一):“蓬莱盏,海山螺,坐来未饮已欲倒。安得酣畅风流李青莲,醉后挥毫掞词藻!”刻画了纵酒享乐、诗情豪迈的李白。江户文人还热衷在画中描绘李白并题诗。菅茶山题画诗《江月泛舟图》(《黄叶夕阳村舍诗》后编卷五):“半空峰影半轮秋,谁棹金波数曲流。想昔青莲李供奉,思人思月下渝州。”受容了李白《峨眉山月歌》的诗语与韵律,据图遥想李白当年顺流而下,出蜀游历的情景。释六如的《李白观瀑图》(《六如庵诗钞》卷五):“才卧匡庐又夜郎,尘颜洗尽奈愁肠。银河空挂三千尺,十倍输他白发长。”诗后两句受容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塑造了被贬谪的愁苦的李白。
综上所述,江户汉诗不仅那份飘逸狂放、幻入仙境的风韵颇似太白,江户诗人受容李白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李白所具有的非凡的诗才,特异的个性和传奇的经历,使他本人或其诗有被仙化、神秘化的倾向。体现了日本文人对李白“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
五、日本汉诗对李白“谪仙”形象的取舍
“谪仙”缘自道教的神仙观念,原是道教对被谪人间的神仙的称谓,并将其视为隐居的仙人。《南齐书·高逸传·杜京产》:“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謫仙’”。(萧子显,1972:72)唐代文献开始借“谪仙”指怀才不遇的诗人,并在与李白相关的诗文中被反复借用。“谪仙”是李白引以自豪的称号,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统计,李白诗中共引用“谪仙”四次,而他身前由他人所写资料中也使用了两次。(李艳丽,2008)笔者认为,中国典籍中称李白为“谪仙”,主要有几点含义:其一,称誉李白才学优异。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载:“(天宝元年深秋)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其二,指李白乖张狂放、愤世嫉俗的性格与特异经历。纵观李白一生,虽有“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三,反映出李白的道教神仙信仰与道家思想。遍览李白诗作,不难发现老庄的批评意识、自由精神、超旷哲学、虚无思想都给李白打上了甚深的思想印记。
然,正如蔡毅先生所言,日本文人对“谪仙”李白的接受却主要表现在文学趣味上,可以说是文学精神与风格趣味的追步李白。(蔡毅,2007:34)纵观其接受史:奈良平安时代,“谪仙”形象尚未引起关注,对李白的受容停留在神仙思想片段的摄取和语言典故的借用。五山时代,受容李白往往“李杜”并举,李白诗作以及李白的形象已零散出现在五山禅僧的作品中,且大多夹带着仙家畅想,透露出李白式点凡成仙的发想。直至江户时代,李白及其诗作才得到日本文人的重视与全面接受。如果说江户早期和中期对李白的接受还仅限于诗酒人生的文采风流。那么,到了江户晚期,对李白纵酒狂歌性格的外在模仿就已转为了对其超尘绝世风度的内在神韵与道家思想的追求。
这种变化应和当时日本文坛喜爱道教、道家的风潮密不可分。尽管道教在日本始终未能成为独立的宗教,但林罗山等江户大儒都对道教神仙思想、道家的老庄哲学持有浓厚兴趣;松尾芭蕉在俳句中表现出受容道家思想的倾向;还有徂徕学派开始对老庄思想学问进行研究。至江户中期,崇尚老庄已经俨然成风。但,日本文人在接受李白时明显抽去了中国典籍中“谪仙”李白的第三层含义——即老庄思想中对统治者的批评精神、对儒家思想进行审视和反思的怀疑哲学,而仅侧重于对飞天成仙、出世虚无的自由精神与超旷哲学的汲取。这种接受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本民族文化的特点。
注释:
①早稻田大学日本古籍研究所“平安朝漢詩文総合データベース”(平安朝汉诗文综合数据库)。
蔡毅.2007.日本汉诗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
池田四郎次郎.1920-1922.日本诗话丛书:卷六[M].东京:文汇堂书店.
多纪仁之助.1928.南海先生后集[M].东京:和中金助发行.
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1983.词华集·日本汉诗[M].东京:汲古书院.
富士川英郎.1987.诗集·日本汉诗[M].东京:汲古书院.
花房英树.1957.李白歌诗索引[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金子彦二郎.1995.平安时代文学和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M].东京:艺林舍.
李艳丽.2008.论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李白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寅生.2009.日本汉诗精品赏析[M].北京:中华书局.
马东歌.2004.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矢岛玄亮.1987.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
萧子显.1972.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
玉村竹二.1967-1981.五山文学新集:第三卷[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与谢野宽,正宗敦夫.1926.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M].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詹瑛.199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