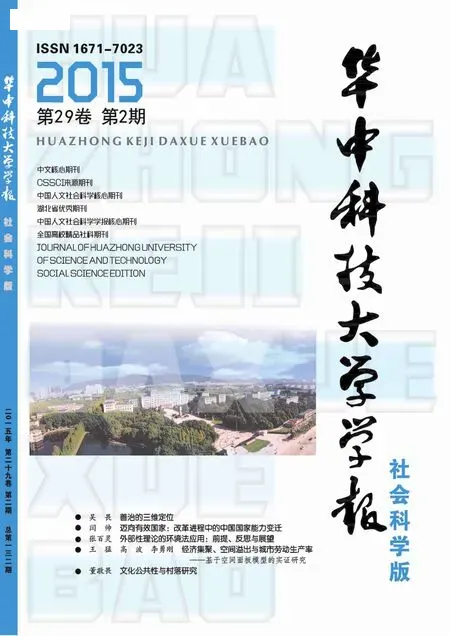超越二元对立: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结构的批判
赵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超越二元对立: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结构的批判
赵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自反性矛盾结构,主要表现在权利与责任、平等与差异、个体与共同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排斥与包容等五对基本范畴中。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导致“弱”责任观衰减公共资源、抽象的普遍平等观压制实际差异、个体自由绝对化消解共同体联系、公私领域分界僵化遮蔽私域不平等现象、对外排斥性削弱移民的实质公民身份等弊端。探寻二元张力中存在的创造性,以人的主体性、分化的普遍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私域政治、世界公民身份等理念整合二元范畴,是超越公民身份二元对立结构的关键。
公民身份;自由主义;二元对立;自反性
公民身份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兴于近代欧洲启蒙主义,先后形成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传统。自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自由主义逐步奠定了其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导地位,并对现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代表学者T.H.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1]15。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其内部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在政治实践中逐渐暴露出缺陷,使得公民身份的实际结果与理想目标不断偏移,甚至背离了自由、平等的初衷。
一、二元对立: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自反性结构
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矛盾结构,主要表现在:权利与责任、平等与差异(或曰普遍与特殊)、个体与共同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排斥与包容等五对基本范畴中。它们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造成公民身份内部的分歧和张力,不仅妨碍了理论自身的圆融和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这即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自反性所在。正如福克斯认为的那样,“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许多优点很大程度上被其二元论的假设所破坏。”[2]68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下,公民身份不仅在理论上呈现出自反性的张力,在实践中也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消除这种自反性风险,突破理论和实践的“瓶颈”,就要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二元对立结构及其矛盾范畴进行反思和批判,寻找整合的可能性。
(一)权利与责任的对立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以个体权利作为理论支点,从天赋于人的自然权利推演出公民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陪审团、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并且认为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这种视权利为公民身份之生命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洛克和密尔的学说中,也实践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政治法案中。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可以自由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私人利益,并且这种自由通过国家保护的权利得到保障,而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仅在于遵守法律、纳税等非常有限的几个方面,对于其他公民也不存在明确的责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表现出“强”权利、“弱”责任的特征,并且认为过多的义务会妨碍公民自由和个体权利的实现,因此将公民义务规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二)平等与差异的对立
从“人生而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为公民获得平等地位和普遍公民资格提供了理论支点。公民身份被认为是每一个人都平等拥有的资格和地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每一个个人和其他最微贱的人都平等地受制于那些他自己作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所订立的法律。”[3]58自由主义由此建立起法律意义上的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地位。而在对待人们固有的社会差异上,“自由主义倾向于把由于个人之间在才智、价值观和选择方面的差别——即除非国家损害公民自由,否则就不可能消除的差别——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4]190那些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社会歧视、排斥、压迫等不平等现象,被划属为私人领域个人自由选择的后果,并被认为是正当的、可容忍的、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从而将其排除在公民身份的话语体系之外。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
以约翰·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奠定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发端,对个人自由首要性的强调和对于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国家权力的深深怀疑和戒备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最突出的特质。洛克认为个人是自然法则之下理性驱动的个体,并将这一个人理性预设作为政治文明社会中个体行动的基础;而密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个人自由是通往真理和社会进步的可靠路径,自发性和自由选择是个人追求自由的工具,这种动力比法律或其他社会强制形式更可取,并主张通过一种公、私领域分界的法则设定,将个人自由的空间最大化和国家干预的范围最小化[4]179-182。对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自由主义认为,以共同体中的集体身份来对个体进行判断有可能造成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公民身份应当坚持保持个体地位。总的来看,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处于相互对立的紧张境地。
(四)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
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密尔提出将个人行动按照影响范围区分为主要影响个人自己的利益和影响他人的利益两类,从而将公民的社会生活划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个领域。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行为只要不影响他人,就有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而国家政治管理的范围被严格控制在那些可能影响他人利益的“公共领域”中,并且必须承认私人安排的优先性而不可随意插手[4]18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分明,个体如果没有参与公共领域的意愿,他也就没有一定要去这样做的义务。”[5]3通过这样的设定,自由主义为个人自由和私利追求划出了一片与政治绝缘的“安全区”,“强烈主张支持和保护隐私权、市场和其他私人自行安排决断的形式”[4]182,而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则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
(五)排斥性与包容性的对立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念引导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促成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成员资格的公民身份依据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划定所属,表现出明显的疆域隔离性,由此具有了对外排斥性和对内包容性两种特征。公民身份的对内包容性体现在民族国家对其内部成员公民资格的法律认可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对外排斥性体现在移民准入、居留许可制度,以及对境内非公民居民的国籍授予、法律保障、公共资源提供等方面[6]65。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社会的跨界交流与融合逐步频繁,这种将一部分人包容在内,而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的对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沟通与合作。移民、难民、原住民以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工等许多人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做出了社会贡献,却由于僵化的制度设计,长期无法获得完全或实质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及权利,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无法得到保障。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必须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加多维的层面上提升其包容性。
二、二元对立的弊端:自由主义对公民身份二元对立结构批判
(一)“强”权利、“弱”责任导致公共资源衰竭
自由主义这种赋予公民广泛的权利和仅要求其承担最小的义务之间的严重不对等遭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本位思想导致了人们自私自利甚至拒绝承担必要社会责任的弊端,这使得政府提出的一些有益的社会政策一旦涉及要给个人增加义务(哪怕是非常有限的义务)就会受阻重重难以推行。“在1996年的美国福利法改革中,要求以工作(或真正努力去找工作)来代替接受福利帮助,或作为获得福利帮助的条件,可能是最富有争议的一个因素。”[4]189共和主义者苏利文、桑德尔、皮特等人批评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人们过于追求不受干扰的自由和个人私利,缺乏引导人们履行公民义务等公民美德方面的培育[4]199,这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衰竭,并终将失落公民自由和权利本身。自由主义的“弱”责任观以及认为责任必然会妨碍权利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民权利的更好实现。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福利国家危机已经显示了这种政治弊端的社会后果,人们开始思考通过倡导公民参与的积极公民身份而非仅仅专注于个体权利保障的消极层面来改善这一状况[7]76-77。
(二)抽象的普遍平等观压制实际差异
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面精神旗帜,“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为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和争取普遍而平等的公民身份地位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曾经被广为倡导和推行,但它在当代却遭到诸多诟病,尤其是来自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忽视了少数特殊群体的文化差异和不同需求,在其平等和普遍的政治宣言下隐而未言地将“男性”、“白人”、“身体健全者”等作为对于“标准公民”的默认要求,长期将女性、黑人、残障者等群体排斥在“二等公民”和“他者”境地,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新的压迫。自由主义对于普遍平等公民身份的许诺,由于其对事实存在的差异和特殊性的忽视而成为一句空话。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提出了著名的价值多元论和主张“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干预地去活动”[8]122的消极自由观,主张以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来避免价值普遍主义对多元文化的压制,但这一创见并没有挽救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破产危机,反而为推翻其普遍主义神话提供了依据[7]166-167。由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必然推导出无法设计一种对所有文化都适用的制度规则,而消极自由本身也只能是诸多善中的一种而已,自由主义提出的其他核心价值原则也将为之颠覆[7]169。这种理论内部的自反性证实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的脆弱性。然而,对这种普遍主义的批判并非是要否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它的普遍原则在近代以来的贡献,而是试图对它的抽象普遍主义及其带来的教条、绝对和独断风险进行修正[7]141,以实现更真实意义上的“普遍平等”。
(三)个体自由绝对化消解共同体联系
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者们显然对个人理性寄予了过高的盲目乐观的预期,个人理性并不足以使他们在追求个人私利的同时保持对公共利益的足够美德。且不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论导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两极分化所带来的阶层矛盾已经危及了共同体团结,仅仅是出于公共秩序的考虑要求个人不能以大多数人所反感的方式使用公园、地铁、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和设施,或者试图实施一项要求那些易感染的孕妇进行艾滋病检测并告诉其性伴侣的法律,也很困难[4]189。更有批评者指出,自由主义理论对个人本性的理解是变化的、不完全的,它无力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权威陈述,而只能直观地从表面上来理解个人[4]179。这更加导致其个人主义的不稳定性和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自由主义对共同体的天然戒备心理和个人社会联系的薄弱性,则进一步扩大了其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风险。事实上,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共同治理方案,必须对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予以承认和关注,更何况早有自古希腊伊始的共和主义传统在前。虽然密尔也认为“正义的制度在人人只有私心没有公心的社会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9]26,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关系,实际情况可能正是他所担心的那样。因此,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将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不可越过的重要课题。
(四)公私领域分界遮蔽私域不公正现象
共和主义的倡导者汉娜·阿伦特认为,自由主义将公民的自由与幸福都理解为私人领域的事情,最终导致了公共空间的消失[10]112。事实上,公共领域的完善和发展是必要的,没有良好运作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和幸福追求也将难以为继。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公、私领域二元分界方式导致了两种弊端:一方面,没有完善健全的公共领域,就没有充分的社会公共资源来保障人们追求私人领域的个人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私人领域范围划定过大,可能导致对社会不公平的遮蔽和忽视,有悖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自由主义将客观存在于社会中的性别、种族、文化等“先天”差异对个体的影响忽略不计,将多元、差异和冲突统统划入私人领域,并主观地将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认为是合理的。这种脱离社会实际、无视弱势群体种种不公遭遇的做法,使得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被蒙以污名。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指出,公、私领域二元划分的方式隐含着性别歧视,妇女被排斥于公民身份之外的历史直接与她们归属于公、私二分中的私人这一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公、私领域二元对立的刻板划分使得家庭内部的压迫与不公被作为私人领域事务而忽略,例如婚内强奸、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等。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平等和公正是以掩盖和压制私人领域的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为手段的“假面秀”。
(五)对外排斥性削弱移民的实质公民身份
在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意义上,公民身份的实质层面并未与其理论和法律形式相符合。移民在移居地国家遭到的种族歧视、骚扰和暴力就是一种公民身份的排斥过程,这导致他们的公民身份在实质层面被削弱甚至取消。“对移民之正式公民身份的排斥或自我排斥就等同于对人口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的公民权的剥夺;是对比例相当高的体力劳动者的公民权利的剥夺;被剥夺者群体的利益在政治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6]74。由于这种对外排斥性,作为“非正式”公民的人们只能拥有某些相当有限的权利和地位。这些非正式公民不仅包括国际移民和难民,也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内部拥有正式国籍和法定公民身份的“城市移民”——大规模的进城打工者和相当比例的失业流浪者。由于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地方势力和区域文化的排斥性,农民工等“城市移民”群体的实质公民身份很难得到落实。这些由于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阻隔,尤其是跨国移民者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以民族国家为惟一主权框架的理论设定;而城市移民者在国家内部遭遇的地方性排斥,也有必要从城市公民身份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因此,必须拓展公民身份的内涵以提升其包容性,引入超国家、亚国家两个层面以弥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一维视角的不足。
三、超越二元对立:张力中的创造性与整合的理念
尽管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弊端遭遇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质疑,但它作为一种公民身份理念仍然具有存在和延续的合理性,因为其追求的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以及权利、责任等要素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矛盾和张力的所在,通常也是理论创新的突破点所在。探索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创造性要素,在新的维度下加以整合,是公民身份理论超越与创新的关键。
(一)整合权利与责任:人的主体性、公民收入和非正式对话论坛
公民身份需要通过权利及其提供的资源才能得到确证和实现,自由主义应当被批判的是那种一味强调权利并将其与责任对立起来的思维,而非权利本身。因此,必须跳出将权利和责任对立起来的思维怪圈,在审视时代趋势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寻找整合二者的新维度。首先,以“人的主体性”来综合公民身份的两个层面。里斯特主张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对公民身份做出新的理解:“作为参与的公民身份表达的是人的主体性;作为权利的公民身份使人能够作为主体而行动。”[6]56权利使人们成为公民,而责任和参与使人们作为公民而行动,在此意义上,权利与责任通过作为主体性的人的方式,在公民身份中达至融合。其次,通过“公民收入”的形式确保公民身份基本权利的实现,从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责任感的提升创造条件。福克斯从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理论角度提出“公民收入”(citizen income)概念,主张通过给成年人(不论是否就业)发放一笔资金(来源于商业和个人缴纳的税收)作为基本收入来实现一种普遍的、与市场限制脱钩的、稳定的社会权利,以避免经济效益、就业形势、官僚体制、性别区分等因素对公民权利资源的限制[2]99-102。最后,在非正式的对话论坛中培养公民对于与自身权利紧密联系的责任的重视。相对于国家、省和市的议会等正式的政治对话方式,学校、企业、村委会、志愿者社团等社会组织在工作场所、生活社区、公共集会等日常生活场域中的非正式对话方式更能通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议题来带动公民参与,培养责任意识。以这种非正式对话论坛作为公民身份的舞台,在自治与共治的公民实践中促进公民身份行动,有助于实现学者米歇尔曼所说的“可创生法的政治”[11]210-212,形成权利与责任一体的良性循环。
(二)整合平等与差异:分化的普遍主义、对话原则与公民身份关系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高度抽象的普遍平等观导致了平等与差异的对立,但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而非差异。平等与差异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矛盾,二者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非对称的互补关系而非彼此对抗,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并非不可调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张力”。首先,采取“分化的普遍主义”的平等观,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在关注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具体的平等。里斯特提出了“分化的普遍主义”(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6]141-142,主张通过对差异和分化的分析来拓宽对普遍平等的理解,在对具体差异的关注中实现实质性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应当包含对差异的关注、尊重和包容。艾丽斯·杨主张通过特殊团体权利反抗普遍平等对差异者的压制,将差异群体及其因差异而被排斥和压迫的问题引入公共视野。金里卡提出以少数群体权利作为普遍个体权利的补充,主张国家赋予少数民族以自治权、多族类权、特别代表权等特殊权利以体现对民族差异的尊重。其次,超越个体或群体本位的公民身份设定,建立一种以关系而不是以抽象的个人或固化差异的群体为基础的公民身份。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将公民身份建立在普遍抽象的个人或基于差异的群体基础上的做法,或将导致抽象平等,或将导致固化差异,都不能真正解决平等与差异的冲突。福克斯认为,“以关系为本的公民身份(relational citizenship)把平等与差异看做是相互补充的价值”[2]82-83,这种公民身份的关系原则可以消解单一的平等原则或差异原则带来的对立格局,避免公民身份的内部区隔及由此带来的支配性社会结构。最后,基于对话原则促进社会沟通,以文化间对话的形式处理差异、寻求共识。帕雷科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群体分化思路存在差异固化、群体分隔和国家分裂的危险,他主张“把对话原则置于中心地位,拒绝给某个文化观点(包括自由主义)以特权”,通过对话的方式“从差异中创造出一个共同文化”,通过公共论坛和对话制度处理文化间的矛盾[12]65-67。这一主张其实是基于罗尔斯的交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理念,仍然延续了自由主义的规范普遍主义思路,是对抽象普遍主义的修正。虽然自由主义所谓的“价值中立”总是为人所诟病,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念仍然为解决多元价值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使人们可以按照各自认可的政治观念来进行对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固然是必要的,但若要否定一切普遍性或者共性,岂非是要否定人类共同治理的必要性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要彻底消除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在各种不同理念中寻找具体情境下最适用的那一个。
(三)整合个体与共同体:社会个人主义与沟通性社群
无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共和主义传统中,公民都是通过抽象的、脱离现实的个体而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试图回避其特殊性,而后者试图超越它[6]110。事实上,作为公民的个体,客观上仍是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是特定的国家、民族、城市、社区或家庭的成员,是特定历史经历的承受者和具体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无论是自由主义将个体抽象为消费者、工作者的做法,还是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将个体认为是共同体或社群成员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个体的特殊性(或曰现实性)。致力于某种理论抽象而无视实践的复杂性,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却对现实无用的乌托邦。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只有将个体置入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才会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真实动力。由此,公民身份可以基于一种“社会个人主义”的立场展开:一方面为了承认个人自由的价值,防止团体内部的压制,公民身份需要界定为一种个体身份;同时,为了防止绝对化的个体消解公共精神和共同治理,需要将个体公民身份置入共同体的社会性联系及其实践中来理解。沟通性社群的理念正体现了这种兼容的思路。德兰惕基于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提出一种结合了“强”公民权概念和“弱”社群概念的沟通性社群理念,对共同体做一种社会性和关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理解[4]233-234。正如格尔德·鲍曼指出的那样,“社群的观念完全可以容纳争执的观念,而不一定要建基在文化一致性或单一的象征秩序之上。”[4]229现代社会的法律取代文化成为社群维系信任的基础,而社会互动和沟通又成为信任再生产的动力,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成为维系后现代社群的纽带。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将个体纳入社会性的联系中,是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良性循环的有效方式。这种基于社会个人主义的沟通性社群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弹性空间,可以允许个体以各种形式介入、表达和参与团体事务,在参与团体内的互动和沟通中体现个体的差异性价值,同时形成一种基于关系的认同,从而调和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
(四)整合公私领域:私域政治、动态分界与微观政治学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如它们在实际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而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事实上,私人领域从未与政治绝缘,而是一直被其影响和决定着,应当拒绝那种把政治理念作为与其他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具体化的抽象”[6]187-188。私人领域的政治性事务理应被纳入公共视野,公共领域的成长和成熟是政治民主完善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来说,划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决定何为公共领域事务、何为私人领域事务这个问题上是无法保持价值中立的。公/私领域的界线“不能被视为一个固定的被给予之物而加以对待……它的立场和意义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是特定的,它们是不同的国家形式的反映”[6]40,二者的划分受经济、文化、性别、身体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公、私领域的对立性划界导致了对“政治”和“公民”理解方式的偏狭,最终在社会生活的更大范围上失落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因此,应当对这种界线进行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思考,坚持一种动态的公、私领域划界法则。最后,通过“以个体的日常生活为根基”的“微观政治学”[6]40-41拓宽对“政治”的理解,促进社会生活中的公民身份实践,增进公、私领域的互动。参与民主理念的拥护者们认为民主不仅在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是必需的,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组织和关系中也同样是必需的”[6]40-41。事实上,在所有关于资源的使用及分配问题上都存在着政治性,需要人们通过合作、谈判(不得已才以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为生活而投入斗争,以捍卫生活的空间”已经成为城市公民权实践运动的诉求之一[4]425-426。通过参与“微观政治学”层面的社会运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行为可以相互影响,并提升人们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使他们能够反抗私人领域中的压迫和不公,这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成长和民主政治的完善。
(五)整合包容与排斥:世界公民身份、全球治理与城市空间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国际范围的经济合作、政治商谈和文化交往活动愈加密集而深入,移民活动众多而频繁,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由于其疆域隔离效应,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这一现实情况。此外,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的扩散、地理资源的共享、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也要求人们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来共同应对。自由主义基于民族国家基本框架的公民身份产生的排斥性导致了诸如国际劳工、移民等群体的不平等待遇,而全球化社会的事实则表明自由主义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理解只是公民身份多种形式的其中一种而已。世界公民身份、全球治理和城市空间等观念的提出可视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其一,世界公民身份思想继承了世界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是世界之公民,主张“要在一个分化为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强烈地倾向于将其自身的利益置于人类整体的福利之上)的世界上,保留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意识”[4]438,包括对人类和平、全球资源、可持续发展、地球生态等问题的关注。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公民身份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二,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后国家秩序,不仅要克服人权理念的抽象性,将世界公民权利实质化,使公民的权利在全球维度得到保障,还要强调国际间的参与和全球责任感,促成一种包含人类共同治理理念的、在参与中实现权利和责任互动的全球共同体身份。在此方面,联合国和全球治理委员会业已进行了不断地探索,欧盟的政治实践和欧洲公民身份理念的提出更代表了一种前沿的尝试。其三,全球性城市(如纽约、巴黎、伦敦、上海等)作为全球化推进的空间单元和全球联系的网络节点,也在不断形塑着公民身份的轮廓。城市空间不仅是“政治权力、媒体控制和管理精英的空间和场所”[12]73,也是移民等流动人口和被排斥的群体聚集的地方,财富和贫困作为全球化这枚硬币的两面在城市空间中同期上演,公民身份的排斥与包容产生的冲突也显得尤为激烈。城市空间通过城市规划、教育计划与民主对话,发挥着建立公民共识、弥合社会分裂、促进共同治理的功能,以此作为公民身份社会整合的平台,可以建构起一种多元和共享的全球性城市政治文明。
[1]郭忠华、刘训练:《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美)福克斯:《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英)伊辛、特纳:《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英)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6](英)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的视角》,夏宏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7]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9](英)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0](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11](美)米歇尔曼:《法律共和国》,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2](英)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体的问题》,王晓燕、王丽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Transcendence on the Dualism Structure:the Criticism of Liberal Citizenship Theory
ZHAO Ying
(School of Marxism,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211189,China)
There are some contradictions in the dualistic structure of Liberal Citizenship Theory,which mainly include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equality and difference,individual and community,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exclusion and inclusion.It has brought many practical problems,such as the lack of public resources,the coercion on the actual differences by universalism,the poor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the neglect of inequalities in the private realm caused by public-private division,the exclusion to immigrants,etc.It’s a key to exceed the dualism that finding creativiti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s,such as man's subjectivity,citizens’income,informal forums,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principle of dialogue,relationship of citizenship,social individualism,communication communities,informal politics,dynamic delimitation,micro-politics,cosmopolitan citizenship,global governance and urban space,and combining them to reorganize citizenship theory.
citizenship;liberalism;dualism;reflexivity
赵颖,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身份与认同理论。
2014-06-06
D0-02
A
1671-7023(2015)02-0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