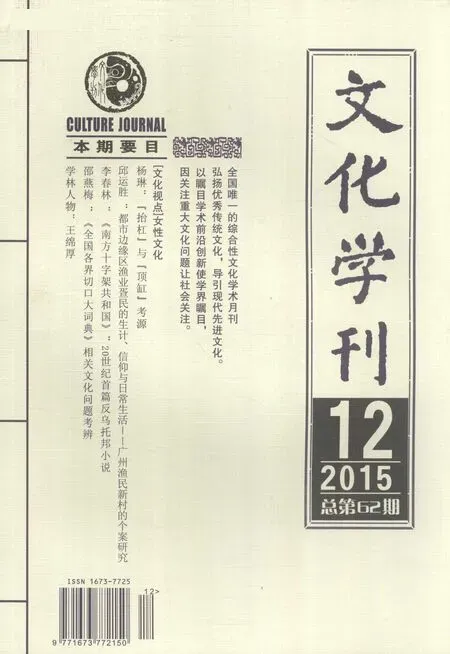《南方十字架共和国》:20 世纪首篇反乌托邦小说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谈及反乌托邦小说,通常都会指出其代表作有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英国作家奥尔多斯·赫胥黎的《啊,神奇的新世界》(又译为《美丽新世界》,1932)和同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美国作家列依·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 度》(1953)等。学界还认为,两位英国作家的作品受有扎米亚京的《我们》之影响,甚至奥威尔都说赫胥黎的作品明显受有《我们》之影响,尽管赫胥黎本人并不认同,然而,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在上述名单中,《我们》问世最早,因此被认为是20 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连俄罗斯文学史家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亦持此种观点:“扎米亚京早在1920 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我们》,它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20 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1]
事实上并非如此:写于1905 年的勃留索夫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国》,才是20 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
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1873-1924),俄罗斯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文艺学家,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其成就不独表现在诗歌方面,在小说领域亦多有建树。短篇小说《南方十字架共和国》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作品写于俄国1905 年革命之际。其主旨在于揭示乌托邦国家的荒谬性和溃败的必然性。尽管作品最后也安设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国家还是被拯救,但显然并非作品所要传达的主旨。
在此作中,作家仍采用以“面具化”的叙事策略来叙述故事的创作方法,以一位记者的新闻报道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借以增强其现实性和现场感。这个南方十字架共和国位于离南极地区不十分遥远的南半球,与澳大利亚较近,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新西兰——新西兰的国旗上即有南十字星座的图案(其实与新西兰风马牛不相及)。作品重点描绘共和国的溃败过程及场景,同时回叙了共和国的种种惊人之举,其乌托邦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设施和举措。
在政治方面,“共和国的宪法仿佛是极端人民政体的体现”[2],但实际上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冶金工厂(当然是“国企”)的劳动者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从这些劳动者中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进入共和国立法院,它了解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有问题,但无权改变国家的基本法律。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原托拉斯创建人成员”(南方十字架共和国本是由坐落在南极地带的铸钢厂托拉斯所组建)的手中,他们把自己人选任为工厂经理,由经理们组成委员会,领导整个国家。立法院只不过是委员会的意志的执行者。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依凭着“无情规章制度”。“在自由的外表下面,对公民的生活进行了极严格的限定。”[3]委员会保持着庞大的密探编制及秘密警察。“工厂里到处都是委员会的爪牙”,“市面上由民卫队维持秩序”[4],委员会也绝不放弃政治凶杀手段。这个国家事实上是以“民主的外貌”掩饰着的“纯粹专制政权的暴政”[5]。
在经济方面,劳动者不领取任何薪金。在工厂工作二十年的公民的家庭以及死亡的或工作期间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家庭领取丰厚的养老金。经理们执掌着工厂的经济命脉。数以几十亿的钱款流经他们之手。而其收支差额往往大大超出国家预算。经理委员会确定价格,而他们确定的价格制约着整个世界上几百万劳动者的工资。他们甚至可以使得一系列国家崩溃。
在文化方面,最突出的一点是极为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所有出版物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任何旨在反对委员会专制的文章不可能被放过,而且整个国家都确信这个专制有着良好的作用,排字工人自己就会拒绝排印批评委员会的文字。同时,这个国家又吸引着全世界的名人都把自己的才华带到这里。这里上演过最优秀的歌剧,举办过最优秀的音乐会和展览会。
在社会生活方面,国家为工厂劳动者的生活安排了所有可能的方便设施,甚至包括奢侈品。漂亮的房间、精致的桌子、教育机构、娱乐场所、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音乐会、体育场馆,一应俱全。孩子的培养和教育、医疗与法律服务、举行各种宗家仪式,均由国家负责。而首都星城的居民更是幸福,他们根本不用工作,是国家的“食利者”(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寄食者”)。他们从国家领到的钱使他们可以阔绰地生活。对于形形色色的生意人和企业主来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因之,星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城市之一。
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的最大特色还是它的张扬共性、泯灭个性。所有建筑物的高度和外形都相同,而且墙上没有窗户(一律在内部用电照明)。提供给劳动者的所有住室的装饰式样高度同一。大家都在同一时间领取同样食物。国家发放的衣服也是从无任何变化的同一式样。每天在固定时间之后禁止外出。
以上种种令我们想起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
让人更加深长思之的是勃留索夫对南方十字架共和国溃败的初始原因的剔挖:一种致命的流行性传染病——“矛盾躁狂症”。
此种“矛盾躁狂症”初名“矛盾病”。但早在20 年前在共和国已有偶然的单发病例。其症状主要是病人们总是自己与自己的愿望相矛盾:想要一种东西,却说着和做着另一样东西;本想说“是的”,却说出“不是”;本想往左转,却转向了右边。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美丑易位。对于矛盾和斗争更是情有独钟,整个社会充满了焦躁和暴戾情绪。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的话变得不可理解,其行为变得很是荒谬乃至残忍暴虐。许多人自杀,儿童被任意虐待,在首都,市幼儿园两个阿姨居然割断了41 个孩子的喉咙。两个警察用榴弹炮向散步的人们射击,死伤惨重。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对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的不可遏止、不由自主的恐怖中。于是大逃亡开始了。高官和富人是始作俑者。后来,军队、警察、医护人员等都参加了逃亡者大军。“逃跑的企望成为一种狂症。所有的人,只要能跑都跑了。”[6]很快,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都离开了。然而,城市仍是到处能看见“矛盾躁狂症”患者,他们杀人、抢劫、纵火、强奸,无恶不作。城市食品、药品、日用品等严重匮乏。在“矛盾躁狂症”的控制下,火车司机本想避免翻车,却总是将列车颠覆,结果导致交通断绝。人们开始大批死亡。同时,还有一些人到赌窟、淫窟等处垂死狂欢,借以忘却可怕的现实。世纪末情绪弥溢国中。随着电站职工在“矛盾躁狂症”发作时捣毁了机器,整个城市陷于黑暗。“随着黑暗的降临,城内残存的纪律彻底崩溃了。恐怖与疯狂完全控制了人们的灵魂。[7]”“所有的人身上极迅速地暴露出道德感情的沦丧。文化修养仿佛是几千年长出来的薄皮,从人们身上脱落了。”人们不单杀人,而且吃人,“用孩子的肉来满足自己身上苏醒的吃人的本能”[8]。男女之间像畜生般淫乱,他们异化为“人状生物”。整个首都溃败了,并且迅疾波及到全国。
在这溃败过程中,唯一的亮点就是首都星城市委员会主席奥拉斯·基维尔欲挽狂澜于既倒而不得的最后斗争。他也是整篇作品中唯一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他坚定、果断,牢牢地掌握着经过合法授受的权力,实行一系列非常举措,对整个城市实行专制统治,将全市的资金、民警和企业均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于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他恢复了已经中断了三个世纪的死刑。他下令为了减轻“几千人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让他们“在医院里,在精心护理下死去”[9]。当伍埃金格建议杀死所有病人,认为在此之后传染病将会停止流行,并且他及其支持者将此种主张付诸实践,开始大开杀戒之际,基维尔则把自己的工作人员编成义勇队,与之进行斗争,尽管双方死伤惨重,最后还是捉到了伍埃金格。
其次,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同时,他又禀赋着一种浓烈的仁爱精神。正是由于他坚定地维护社会法纪,才使得几十万人获救,从而得以安全地离开这个城市——他并不阻碍这些人们的离去,而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当食物严重短缺之际,他为留下来或者未来得及逃亡的人们建立了城市面包房和大众食堂。交通断绝之后,有2000 人拟步行出城,基维尔极力劝阻无果,于是,亲自为他们提供衣食。基维尔虽说不能帮助所有的居民,但在市政局大楼里为所有仍保留着理性的人安置了栖身之地。在市政局闭门不出的人们中间也极少出现病人。这就是说,他试图设置一块没有“矛盾躁狂症”的理想乡,并且得以短暂地实现。基维尔在自己的不大的团体里维持了纪律,直到最后一天。
第三,基维尔具有一位领导者高度的责任感和为大众利益而英勇献身的自觉的悲剧意识。他“关注一切,领导一切”,“不知道休息”。基维尔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城市早晚有一天会整个停电,提前准备了火把和燃料仓库。诚然,他的所作所为并非绝无使人非议之处,例如他对几千已经毫无救治希望的人实行“安乐死”,不知彼时南方十字架共和国是否有此种立法。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仅要对当下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他对溃败过程中的种种均记录在案,以作为向历史的交代。最后一次记录写于7 月20 日,这一天,疯狂的人们开始向市政局猛攻。基维尔写道:“春天之前等到援助是不可能的。春天之前靠现在处于我支配下的储存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我将尽职尽忠。”这是他最后的话。后来他英勇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其所昭示出来的不独是一种韧性战斗精神,更是一种自觉的悲剧意识和英雄情怀。
这篇作品给人以如下警示:
其一,乌托邦的理想虽然美妙,但真正地实践起来却问题多多。就以此作而言,那些高福利始终未能在全民中实行,仅在所谓国企中保有。另外,名实不符之处繁多,号称工厂归国家所有,其实广大工人根本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经理们才是工厂的实际所有者。
其二,在乌托邦国家,所谓平等、民主等均是美好的词汇,实际上往往倒是其反面。在作品中,高官们拥有种种特权,普通民众却只能俯首帖耳。民主徒具外貌,实质上是专制暴政。
其三,笔者以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乌托邦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它将人异化为物和机器。而人总要有表现自己个性的强烈欲求,但又总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必然会产生种种焦虑感,或曰如作品中所表现的“躁狂症”。而被更具体地称之为“矛盾躁狂症”,这是由于这个国家到处是名实不符、言行不符的矛盾所养成。“小说中所幻想的那种‘矛盾嗜好病’,本来是人的意识受压抑、心里受挫折而生成的一种生理病症,它表现为那种丧失理智后的人身上一种惊人的偏执狂:一个劲地要破坏(既自我摧残又摧残他人)的欲望。”[10]人们的心理矛盾冲突与整个国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事实上是一种同构关系。两者互相发明、互为因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溃败的心理动因。
其四,乌托邦国家社会危机很难化解,即便出现了基维尔这样的优秀政治家,也只能局部地、暂时地解决某些问题,无法改变国家溃败的基本趋向。社会一旦开始溃败,是很可怕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国》由于是个短篇,容量有限,写得比较简略;其另一短篇《最后一批殉难者》侧重写社会变革中的暴力与恐怖,可视为《南方十字架共和国》的补充和姊妹篇。而在俄国白银时代另一位代表性作家索洛古勃的《创造的传奇》中则对社会溃败过程有更为精详的叙写①参见拙作《索洛古勃:预言俄国革命的先知——以<创造的传奇>为中心》,《文化学刊》2014 年第3 期。。
作品结尾开出的药方仿佛是多个外国的帮助。这恐怕也很难奏效。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乌托邦国家、乌托邦社会。乌托邦的某些理想虽然美妙,然而实际上它是反历史的,其泯灭人的个性的作法是违背人性的。当统治者强使人们整齐划一,将“我”都变成“我们”时,或许初始原因在于如是为之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便于统治,其实适得其反,为社会溃败积蓄了势能——人毕竟不是木头,表现个性和追求自由乃是人的本质属性。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好,群体事件也好,尽管是以“群”的形态,但其中每一个参与者往往并非仅仅由于从中可以获取经济的解放,也在于从中可以获得久被压抑的个性的释放,哪怕是短暂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所以,乌托邦国家和社会是反历史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正确之途应是通过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建立一个如马克思所说的使得人的个性能够充分得到发展的社会(至少应向这个方向努力),减少和逐渐消弭民间普遍存在的“躁狂症”和暴戾气,社会才会真正趋于稳定,才会从根本上避免溃败。
作为20 世纪首篇反乌托邦小说的《南方十字架共和国》,在今日仍有着极为深刻的警示意义。
[1]符·维·阿格诺索夫.20 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2.
[2][3][4][5][6][7][8][9]. 勃留索夫. 南方十字架共和国[A].刘尘译.安德列·别雷,等.吻中皇后[M].刘尘,周启超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 社,1994. 207. 208. 209. 208. 212. 218.219.213.
[10]周启超.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6.
[1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