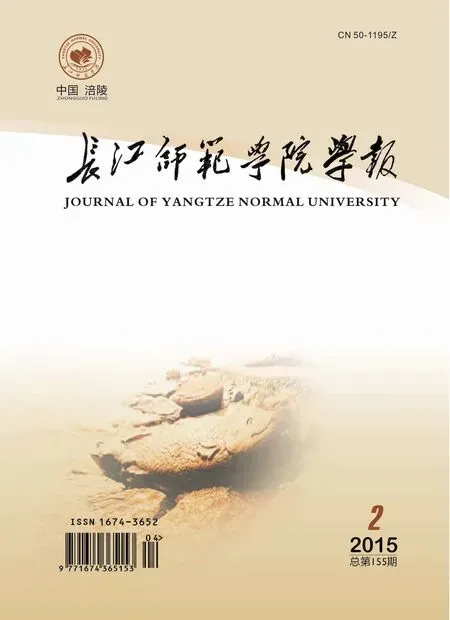巴楚墓葬中“毁兵”现象的考察及相关认识
巴楚墓葬中“毁兵”现象的考察及相关认识
朱世学
(恩施自治州博物馆,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战国到两汉时期,在巴楚地区墓葬考古中发现存在较多的青铜兵器被毁的现象,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实际上是西周以来中原地区“毁兵”葬俗的继承和延续,除受西周时期所谓“驱鬼辟邪”“人鬼之器有别”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之外,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巴族;毁兵;考察;认识
[收稿日期]2014-12-23
[作者简介]朱世学,男,湖北来凤人。恩施自治州博物馆研究馆员(三级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抢救、保护和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2-0030-06
在战国时期的巴楚墓葬中经常出现剑、戈、矛等随葬青铜兵器被人为损毁的现象,学术界通称为“毁兵”或“折兵”,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丧葬习俗。现依据考古学材料对其略作分析与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巴楚墓葬中的“毁兵”现象实录
在战国时期的巴族墓葬中,青铜兵器被毁的现象较多。在秭归兵书宝剑峡战国巴人悬棺葬出土的20件青铜兵器中,其中有8件铜矛、2件铜戈的前锋有人为折断的痕迹[1]。
在云阳李家坝战国巴人墓群出土的77件青铜兵器中,其中有剑20件、矛19件、钺13件、戈3件、镞22件。发现各类兵器均有不同程度的锋残、刃残或铤残的现象[2]。
在开县余家坝战国巴人墓群出土的20件青铜兵器中,有巴式剑5件、戈7件、矛5件、钺3件,各类兵器均有部分损毁的现象[3]。
在巴东西瀼口和东瀼口战国巴人墓葬中出土的3件铜戈以及3件巴式柳叶剑等,均有锋残或刃残的现象存在。
在巴东红庙岭战国巴人墓群出土的29件青铜兵器中,有剑23件、矛5件、戈1件。其中部分兵器,如剑—M87:1、M102:1、M34:1、M51:1、M50:3;矛—M80:1、M53:1等出现有锋残或茎残的现象[4]。
在巴县冬笋坝巴人船棺葬出土的铜兵器中也有被毁的现象,如巴式柳叶剑,标本M65:3,剑茎被折断,近茎处有人首、两角等符号,体长25、宽3.5cm。巴式矛有2件出现锋残的现象(标本M60:1、M65:1)[5]。
在涪陵镇安战国巴人墓出土的巴式剑、矛、戈、钺等青铜兵器中,也发现有锋残或刃残的现象[6]。
在四川郫县红光公社战国巴人墓出土的9件巴式兵器中也发现有巴式剑和巴式矛前锋折断的现象[7]。
在四川宣化县普光村一组发现的战国墓地中,出土的饰有虎斑纹、手心纹、蚕纹、鸟纹等多种纹饰的巴式剑(2件)、铜矛(3件)等,均有前锋折断的现象[8]。
在成都市凉水井街战国墓出土的18件青铜兵器中,有4件巴式柳叶剑、1件巴式虎纹戈、2件巴式弓耳矛有锋残或刃残的现象[9]。
此外,2005年,笔者在巴东西瀼口进行考古调查时,从一座被水冲毁的战国土坑墓中,也采集到一
件前锋残断的巴式柳叶剑。综观战国时期巴人地区墓葬中兵器被毁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有的系自然因素造成,但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系人为因素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毁兵”葬俗并非战国巴墓中所独有,在与巴族相邻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中也有较多的发现。
在河南淅川徐家岭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M3春秋墓有7件铜戈(M3:42、43、126、128、130、132、146)被毁,多为戈锋、内、阑、胡等部位被折;另有2件铜镞(M3:58、77)被毁,被折部位为锋部或铤部;M9春秋墓有1件铜剑(M9:147)、8件铜戈(M9:37、38、61、68、88、146、158、159)、2件铜矛(M9:22、30)被毁,多为剑、戈、矛的锋部被折[10]。又M1战国墓有10件叠放在一起的铜戈被毁(M1:44-52、71),援尖(戈锋)均被有意截掉。另有1件铜矛(M1:58)被毁,矛锋被有意折断;M10战国墓有1件铜剑(M10:92)、20件铜戈(M10:57、58、59、132、236、230、231、174、234、238、204、233、205、229、133、235、239、237、255、232)、1件铜矛(M10:142)被毁,多为剑锋、矛锋或戈锋等部位被折[11]。
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中,有4件铜戈(M10:16;M11:15、14、17)、3件铜镞(M10:29、30、31)被毁,多为戈锋或镞锋、镞铤等部位被折[12]。
在湖北赤壁祝家岭战国楚墓中,有3件铜戈(M24:5、M4:2、M15:2)、1件铜戟(M22:6)被毁,均为戈锋或戟锋被折[13]。
在湖北江陵九店战国墓中,有1件铜剑(M265:12)、1件铜戈(M50:10)被毁,均为剑锋或戈锋被折[14]。
在湖北襄阳王坡春秋战国墓中,有1件铜剑(M111:11)、3件铜戈(M47:1;M55:32、2)被毁,均为剑锋或戈锋被折[15]。
在湖北枣林岗与堆金台战国楚墓中,有4件铜剑(M152:4、M102:1、M20:1、M187:3)、1件铜戈(M26:2)被毁,均为剑锋或戈锋被折[16]。
由此可见,楚地与巴地相比,“毁兵”葬俗出现的时间更早,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二、“毁兵”葬俗的历史源流
从考古学材料看,“毁兵”葬俗并非源自战国时期的巴楚地区,而是源自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区。目前在陕西、山西、北京、甘肃、河南等地区的西周墓葬中均发现有“毁兵”现象。
陕西地区主要集中在长安、扶风、歧山、宝鸡、泾阳等地。如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和客省庄发现有17座西周墓,随葬的大部分铜戈在其援的中部弯曲成钩状,或者是折成两段,分置于两处。“这种现象不可能是因墓土下陷被压所致,因为和铜戈放在一起的陶器大都完整,而且戈都是平着放置的,即使被压也不能弯成约90度的角度。所以推测它们是被有意识弄弯或折断后再埋入的,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葬俗。”[17]
山西地区主要集中在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地。据统计,随葬有青铜兵器的西周墓共60座。随葬的铜戈共84件。其中,在入葬前被有意识砸弯、折断及残缺的铜戈就有71件,毁坏率高达84.5%。被毁的情况有局部残缺、砸弯变形、折断成两三截或上下放置或分开放置[18]。
北京地区主要集中在琉璃河遗址燕国墓地[19]。1973-1977年,该墓地共发现随葬青铜兵器的墓葬16座。其中戈、矛、剑、戟遭到人为破坏的现象较为明显,多数被折断、砸弯或局部残缺。1986年又在该遗址发掘出一座带4条墓道的大墓[20],其“北二层台上放置的……矛和戈的断尖残援。东、西台和南台上主要放置戈、戟、矛、盾、甲、胄等物。其中的戈、戟、矛等兵器,几乎都被折去援尖,有的则被砸弯。但所缺部分,大多可从北二层台的断尖残援中找到,说明它们可能是下葬时因某种仪式而将这些兵器砸断,然后分放于各台的。”“在墓室的东南和西南角分别竖立4根和6根长矛。铜矛头向上,矛尖皆已砍去,被置于北台。”其随葬兵器以铜戈数量最多,在出土时已经被全部折断,后经整理拼合为7件完整器,7件残缺,2件兼而缺内,另有戈尖5件,故铜戈总数应在20件以上。
甘肃地区主要集中在灵台县白草坡,共发现随葬有青铜兵器的西周墓4座[21]。以M2为例,共出土青铜兵器22件,其中9件虎纹戈集中在死者的头部、臂部左右。“所出铜戈大多折弯、残断。”“还有1件
铜戈被折成2截,分置南北端二层台下,用意不明。”
河南地区主要集中在洛阳附近。1963-1973年在河南洛阳北窑共发掘348座西周墓,其中有91座墓葬随葬有青铜兵器[22]。从年代上看,西周早期墓葬出土兵器318件,西周中期墓葬出土兵器112件,西周晚期墓葬出土兵器7件,在随葬品中又以铜戈最多。这些青铜兵器绝大部分受到人为的破坏,或砸成钩状,或刃部致残,或断成几节,或少援缺内,其受损比率达95%以上。
学术界通常认为,西周早期“毁兵”葬俗主要流行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开始衰退,西周晚期则很少见到[23]。如果追根溯源,很可能这与新石器时代的“毁器”葬俗有一定的关系。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6 100-4 400年)墓葬中,就有故意打碎陶器为死者陪葬的实例。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口部有很多被故意打破[24]。在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巫山大溪遗址的墓葬中也发现随葬陶器“有少量是打碎后再随葬的。”[25]
据学者们研究,在史前时期,“毁器”葬俗主要有陪葬、殓葬和祭奠三类,其“意图应是辟邪和为死者享用两者兼而有之。”[26]其后,这种葬俗仍然存在。如河南安阳戚家庄东的一座晚商墓葬,在墓内南二层台上放置有陶豆、陶簋各1件,“豆在西侧,豆盘残;簋在东侧,极为破碎,似为有意砸碎埋入。”[27]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2中,有随葬玉璜2件、玉柄形器3件,这些随葬品在入殓时被有意地折断成2节或3节,放置于死者的不同部位[28]。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代盘龙城遗址中亦出现“毁器葬”的现象,如盘龙城李家嘴四期M2腰坑出土“一件断成三截的玉戈,疑为下葬时故意打断。”[29]盘龙城杨家湾六期M7出土“一件玉平刃柄形器被打成三段,一段置于墓主人右侧,另两段置于左侧。陶器放在棺外侧,有的打碎后成排放置。在棺外西南角平铺一排陶片,器型有盆和大口尊;在棺外东北角也铺有陶片,主要是一件灰陶罐。”[30]
由此可见,“毁器”葬俗的延续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对西周时期的丧葬观念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西周早期墓葬中流行的“毁兵”葬俗与以前流行的“毁器”葬俗比较,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在西周墓葬中仅有兵器的毁坏,而其他随葬品如陶器、青铜礼器等却无人为破坏的迹象。因此,对于西周墓葬中存在的“毁兵”现象,如果仅是从“毁器”葬俗的延续和影响所致来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还得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具体分析。
武王克商后,借鉴商纣亡国的惨痛教训,周人则利用“礼制”,企图凭借道德的力量以维系新确立的社会统治秩序[31]。《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曰:“武王克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是子孙无忘其章。”[32]《荀子·儒效篇》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33]有学者认为,在西周立国之初,所谓的“戢兵”或“偃五兵”体现在丧葬礼仪上就是在死者下葬前将随葬的兵器人为地加以毁坏,以示“禁暴”[34]。由此,“毁兵”葬俗被认为是丧葬制度在西周初期进行整合的产物,它反映出西周统治者的“礼制”思想,并在丧葬礼仪中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广为传播。
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巴族墓中出现的“毁兵”现象,很可能是对中原地区西周时期这种特殊葬俗的继承和延续,因为商末周初,巴人曾经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战争。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战国时期巴族地区出土的巴式兵器,如巴式柳叶剑、虎纹戈、弓耳矛等,其形制最早均源自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
以巴式柳叶剑为例,在考古实物中,柳叶形青铜剑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其出土地是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宝鸡与岐山、西安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南洛阳等地。其形制特点是:剑身较短,呈柳叶形,扁茎,无格,无首,无箍,茎上有一至二个小圆孔。据统计,西周早期柳叶形剑的单件出土数量大约在25件左右,其中以陕西宝鸡地区出土柳叶剑最多,占总数50%以上[35]。据此,柳叶形青铜剑的分布,主要以宝鸡地区为中心,且在该地使用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因此,我们认为,从巴式柳叶剑出土的时代早晚以及文化演进的规律看,它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中原一带,尤其是陕西宝鸡地区。据研究,这一地区也曾为早期巴人的分布地域。夏商时期一支以捕鱼为生的巴人,离开三峡祖居之地,向北迁徙,顺任河,进入汉水,很快地到达汉中盆地,后又向渭水流域发展,建立正式的国家,演变成为西周诸侯之一,从而融入了先进的周文化。古代巴人既以勇武善战而著称,同时又作为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国,对先进的
周人文化自然是崇拜不已,尤其是西周早中期发达的青铜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深远。战国时期,尽管中原地区已进入社会大变革时期,由青铜时代逐步地进入到铁器时代,但巴人所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十分低下,依然对西周文化十分敬仰,这种敬仰体现在随身佩戴的宝剑依然习仿西周时期柳叶剑的形式而铸造,只不过在借鉴西周柳叶剑形制的同时,将虎纹、蝉纹、手心纹等巴族地区独特的纹饰符号铸入剑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式柳叶剑。这种习仿西周早期铜器的现象,不仅在巴蜀文化中出现,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中也有发现。吴越文化中的青铜器,有西周早中期的,也有大量东周时代的模铸品,但从所仿铸的选择标准看,均为西周早中期之器。
除柳叶剑外,戈的形制也是如此。巴族地区出土的戈多长胡内虎纹戈,与商代晚期中原戈的形制大体相同。古代巴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善于驾舟、习于佩剑是巴人的生活习性,依照古代“生有所用,死有所葬”的丧葬习俗,随葬兵器也是巴族墓葬之一大特点。巴族既然继承了商周时期中原兵器的形制,那么与兵器有关的“毁兵”葬俗也极有可能被继承和延续。无独有偶,商周时期盛行于中原地区的“腰坑”葬俗,自东周开始在中原地区逐步消失,但在巴族地区的两晋时期的砖室券顶墓中却依然可以见到[36],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毁兵”葬俗与“腰坑”葬俗一样,均是受中原地区商周文化余波的影响所致。
三、对“毁兵”葬俗文化观念的认识
对于墓葬中的“毁兵”现象,民间盛传得沸沸扬扬,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墓主厌战、仇家复仇等。学术界也有多种不同的推测或解释。
其一是认为“毁兵”葬俗与方相氏驱鬼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郭宝钧在发掘辛村墓地时认为是“殴墓”,说“古人畏忌甚多,新墓作成,恐有厉鬼作祟,必先行厌胜之术,葬者始敢入。”[37]据《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38]郑玄注:“圹,穿地中也。”即墓穴。“方良,罔两也。”罔两,通“魍魉”,一种鬼怪。据此,他推测浚县辛村卫国西周墓出土的诸多残戈是方相氏“击四隅,殴方良”所致,目的是为了驱鬼避邪。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传统的观点。
其二是认为毁坏兵器是显示成功和富有。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有关学者,通过对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大量兵器的创伤程度进行分析,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认为这“绝非因方相氏在墓中驱逐魔鬼、两戈相击才受到破坏的”“毁兵随葬的葬俗,很可能是周人认为毁坏的兵器可以显示战功,也可以显示富有。”[39]
其三是认为“毁兵“葬俗可能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它们可能是下葬时,因某种仪式而将这些兵器砸断,然后分放于各台的。”[40]
其四是认为“毁兵”葬俗与武王克商后的“偃五兵”有关。“独特的、砸弯兵器的葬俗,估计很可能是从武王克商以后开始的。也就是《荀子》等著作中所说的‘偃五兵’。”[41]
其五是认为“毁兵”葬俗是周朝“示民疑也”与“尊礼尚施”思想观念的反映。“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所见‘毁物’、‘折兵’现象,正是周人所持随葬器物要‘示民疑也’与‘尊礼尚施’观念的又一种表达形式,以‘人器’作‘祭器’,两者兼顾。不过,到列国并存、诸侯征战时期,‘僭礼’情况严重,不再受周礼约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人器’入葬,‘毁兵’、‘折兵’现象,逐渐消失。”[42]
其六是认为“毁兵”葬俗是“鬼器”观念的体现。“用毁器或折兵之器随葬可能就是礼书中所见的一种‘鬼器’观念,使人为对器形的改变达到与‘人器’或‘祭器’相区别。”“所谓人器,即实用器;鬼器或称明器,即有形而无实用性,也就是礼书上所谓的‘神明之器’。将器物的有意损毁,其实就是将实用器而明器化,使人鬼之用器有别。”[43]
上述诸种观点,似乎都有依据,但都没有充分的依据。也正因如此,才引起学术界多年来更多的争论。
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在中原地区逐渐绝迹的“毁兵”葬俗,之所以还在巴楚地区频频地出现,除受西周时期所谓“驱鬼辟邪”“人鬼之器有别”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之外,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形态由奴隶社会向封
建社会过渡,其丧葬制度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随着厚葬观念的不断发展,盗墓之风也在不断地加剧。正如吕思勉所言:“春秋以前,敢于违礼厚葬者,盖亦寡矣。礼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战国之世,则有难言者也。……当时之制度,牵于流俗,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44]我国自古以来有“墓而不坟”的说法,春秋以前的墓葬均是“不封不树”,盗墓者的目标不明确,加上当时“礼制”盛行,故盗墓之风少有发生。但从战国开始,坟丘墓流行,打着“仁义”旗号的贵族大肆营造坟墓,所谓“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45]厚葬使诸多宝物积聚于地下,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当传统观念逐渐地被破除,贫富差距日益显著时,很自然就成为盗墓之风盛行的起因之一。《吕氏春秋·节丧》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46]这说明当时盗墓已经成为执政者严厉禁止的行为,但因为盗墓之风日盛,已经无法控制,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此其(墓)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47]所谓“抇”,即发掘。可见,正是这种期盼通过掘墓实现一夜暴富的心态,导致当时各诸侯国“无不抇之墓”[48]以及“大墓无不抇也”[49],特别是“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50],可谓是当时最典型的盗墓案例。在宋国和齐国未亡之前而宋文公和齐庄公的陵墓竟然已经被盗掘,可见当时的盗墓风习已经蔓延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因如此,巴国和楚国作为当时的东周列国之一,势必要受到这股盗墓之风的影响,而人们为了防止祖骨被扰、器物被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下葬之前将随葬器物有意毁坏,断绝人们掘墓暴富的贪念,使盗墓者望而却步。这也许就是自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已逐渐消失的“毁兵”葬俗在战国时期的巴楚墓葬中依然犹能见到的真正原因。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战国到两汉时期,在巴楚地区墓葬中发现存在较多的青铜兵器被毁的现象,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实际上是对中原地区西周时期“毁兵”葬俗的继承和延续,除受西周时期所谓“驱鬼辟邪”“人鬼之器有别”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之外,与战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秭归县兵书宝剑峡悬棺清理简报[M]//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五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8.
[2]四川大学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M]//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71.
[3]山东大学考古系.四川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发掘简报[M]//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515-517.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巴东县红庙岭遗址出土一批重要青铜器[J].四川文物,2007(4):17-22.
[5]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58(1):11.
[6]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M]//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769.
[7]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J].文物,1976(10):91.
[8]马幸辛.试探川东北出土的巴蜀式铜兵器[J].四川文物,1996(2):34.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水井街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M]//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06.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淅川徐家岭一号楚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4(3):21.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考古报告集[J].江汉考古,2008(增刊).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118.
[18]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20.
[2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J].考古学报,1977(2):114.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3][34]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与文物,2006(4).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25]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J].考古学报,1981(4):462.
[26]黄卫东.史前碎物葬[J].中原文物,2003(2).
[27]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J].考古学报,1991(3):325.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9][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55、231.
[31]张仲立.周礼编缀中的丧葬礼仪[M]//周秦文化研究编委会.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32] [先秦]左丘明.左传[M].四库全书本.
[33] [先秦]荀况.荀子[M].四库全书本.
[35]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J].文物,1983(2):12.
[36]朱世学.巴东沿渡河发现的腰坑葬俗及相关研究[J].巴文化,2005(2):44.
[37]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M]//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8]周礼[M].四库全书本.
[3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20.
[41]王恩田.沣西发掘与武王克商[M]//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虢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43]黄凤春.毁器与折兵[J].楚文化研究通讯.2010(11).
[44]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5] [先秦]墨翟.墨子[M].四库全书本.
[46][47][48][49][50] [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M].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