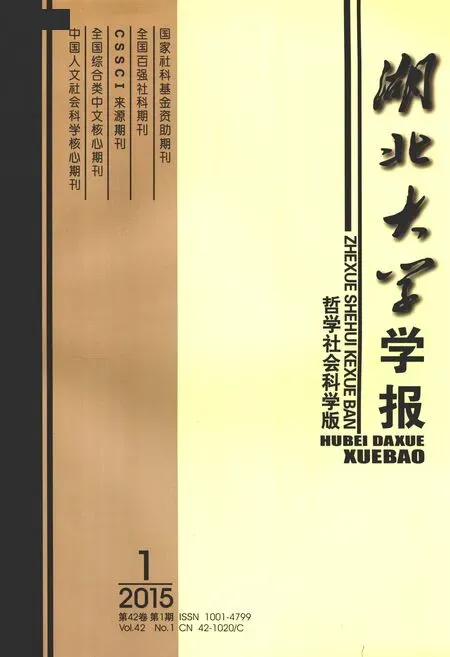苏格拉底与伽达默尔对话思想比较
——以善为切入点通向源始的对话
帅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苏格拉底与伽达默尔对话思想比较
——以善为切入点通向源始的对话
帅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善”同时是苏格拉底和伽达默尔各自的对话发生的动力和目的,对于“善”的不同理解和态度直接决定了二人不同的对话思想的发生结构。伽达默尔对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有着诸多继承和发挥,然而前者对于后者的对话思想结构进行了一种奠基性的超越,而且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只有在前科学、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中,以“善良意志”为前提的源始对话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式的以认识“善”为目的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善的共同体”的实现也才是可能的。此外,二人对于“善”的不同认识也决定了两种对话各自所遵循的内在逻辑结构(形式逻辑与问答逻辑),进而决定着何种对话为一种源始的对话形式。
善;对话;形式逻辑;问答逻辑
“善”无论是对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还是伽达默尔的对话思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正是“善”决定了二人的对话的开启、对话的形式与目的。作为对话辩证法的开创者,苏格拉底对伽达默尔的对话思想有着较深的影响。其中尤其是以“善”作为对话的动力和目的,其次就是对话的态度、问答的方式等。然而,伽达默尔的对话结构对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的超越与奠基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善与两种对话的开启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苏格拉底与伽达默尔对于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态度开启了他们对于“善”的追求以及以“善”为动力和目的的对话。苏格拉底早年研究了自然知识,但后来他发现自然知识只能解释物质世界的因果联系,而并不能说明自然世界的终极目的与动力,更不能用来说明和指导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因此他是想“扭转人们关注自然世界的本质的眼光……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人的生活问题上”[1]97。他提出,“人应该关心自己的灵魂,应该就自己生活的正确道路提出问题”[2]125。而且按照传统哲学的观点,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即是说,从对世界结构和自然事件的研究下降到了对人的研究,即在无休止的和不知疲惫的谈话中追问善”[3]114。
苏格拉底相信既然宇宙的创造者为自然界赋予了完备的秩序,同样在人的灵魂中也必然存在通向完满秩序(善)的可能性,这样就为人接近自然和人伦社会的终极目的与动力提供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以“善”为目的的理性(nous)。人的这种理性(nous)是以“善”为目的的宇宙理性(宇宙nous)或理性神所设定的。这个理性神既是自然秩序的终极原因与目的,也是人伦秩序的终极原因与目的,“如果看不到这方面,却将人和社会的复杂活动也归结为简单的物质因果联系,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机械论了”[4]374。进一步说,与自然秩序相比,人伦秩序是理性神实现自身,实现“善”的更高的阶段,甚至说只有在人伦秩序中实现了至善,理性神的最终目的才实现了。
但人的行为首先并不完全是受nous(以善为目的的理性)指导的,他们往往因受各种意见和自身的特殊价值判断标准的支配,而生活在感性欲求与混乱的社会秩序中,因此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发现并凭借自己灵魂中的nous去认识善。然而要从被遮蔽的灵魂中恢复这种理性的力量去认识善,仅靠个人的能力是很难的,就连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苏格拉底也感到“自知无知”,由此他便以“自知无知”的谦虚态度开启了对他人的“精神助产”式的对话,苏格拉底也自认为对城邦的人进行“精神助产”是理性神(宇宙nous)对他的启示和要求,因为理性神的目的是要在人伦社会中达到至善,实现自身。这种“精神助产”式的对话首先使人忍受放弃先前的各种意见的临产似的痛苦后,才能生出精神的胎儿,恢复对善的认识。这种对善的认知,具体来说是要向善的定义,即向善是什么靠近。而当人认识到善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行善,因为没有人愿意过不善的生活。这样,以善为目的和动力的对话就由此被引出了。
同样,“善”也是伽达默尔一生从事哲学解释学研究的动力,而自然科学以及认识论中的经验概念也受到了伽达默尔的批判,也正是在对以往的经验概念的批判中,伽达默尔揭开了前科学、前理论的源始的解释学经验的对话——一种以“善良意志”为基础的源始的对话。
对经验概念的考察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对于他来说,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和解释本身就是解释学的经验。由此对经验概念的考察显得尤为必要,这其中便涉及到了他对于传统经验观的批判。在传统哲学中经验概念被隶属于“认识论的解释图式”,并且以往的经验理论都是从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的,而从未注意到经验本身内在的历史性、自否定性以及开放性。在现代科学方法里“一切经验只有当被证实时才是有效的。因此经验的威望依赖于它原则上的可重复性。但这意味着,经验按其自身本性要丢弃自己的历史并取消自己的历史”[5]450。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经验”只是被当作可重复的、可被证实和预测的概念。对此,胡塞尔有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验作为生活世界的经验在它被科学理想化之前就发生着”[6]353,即是说科学理论是源于前科学、前理论的“生活世界”的。但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的理解还不彻底,因为他在生活世界之上还存在一个“先验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个“先验自我”,“经验”的历史性、自否定性和无限开放性仍然还受到一种理论认识的束缚。伽达默尔认为“经验本身从来就不能是科学。经验永远与知识,与那种由理论的或技艺的一般知识而来的教导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经验的真理经常包含与新经验的关系”[5]461~462。由此,真正的“经验”(或称解释学的经验)在伽达默尔看来犹如一条永不复回的“赫拉克利特之流”。
伽达默尔批判的是那种自然科学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将经验当作固定的对象来认识,这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规定了主体必为一个无任何偏见的、无任何立场的纯粹观看者,如果主体具有任何前见或立场,便不能保证对象完全真实地得到把握;而客体也必定是一个固定的考察对象,如果是流动的,它便无法被把握。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经验的真理经常包含新经验”,经验应该是不断地进行着自否定的,是流动不已的,是不能被当作固定的对象加以把握的。
从海德格尔角度来看,所谓认知或意识主体不是一种绝对的静观者,而应当是具有时间性的并且拥有其在之中的世界的此在,而且它早已理解了它的视域——时间性与世界性,这种理解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将来的筹划,可以说理解就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这一思想,指出理解和解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历史经验就显现在人作为存在方式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并且被理解者并不是如海德格尔理解的那样只是由于在人的存在中显现而被领会的(在此,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对于被理解者还是持一种独白式的态度),而毋宁说被理解者自身也带有自身的视域,这种视域具有解释学的经验,而人对于被理解者的理解就是与被理解者进行视域融合,在这种视域融合中,双方的原有视域都得到了改变,并且逐渐拥有更大的共同视域。可以说,这种视域融合正是实际生活中的源始的对话,但这种视域与源始的对话所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作为对话的解释学经验的本质结构——“我—你”关系,伽达默尔将这种对话中的“我—你”关系以康德的道德法则来说明:“康德在解释无上命令时曾经特别这样说过,我们不应该把其他人之作为工具来使用,而应当经常承认他们本身就目的。”[5]466因此,“我—你”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关系,它的基础是一种康德的道德法则,即伽达默尔提出的“善良意志”。可以说对“道德法则”的遵循或持“善良意志”是对话者的本性,而理解(对话)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正是这种“善良意志”保证了解释学经验的自否定性与开放性,保证了源始的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即理解着的存在——一种源始的对话的展开。这样伽达默尔就从源头上发现了善的本体意义的基础,及以之为前提和目的的源始的对话。
由上述对苏格拉底和伽达默尔的善与对话的开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和伽达默尔都是以批判自然(科学)知识而引出各自对善与对话的思考,而且,善是作为两种对话展开的动力:苏格拉底进行的对话主要目的是要让人认识到善是什么;而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是源始对话得以发生的动力,因为对话双方(理解者和被理解者)本质上是具有“善良意志”的,而“善良意志”本质上意味着理解者将对方视作与自己平等的理解者,并且它要求在与对方的视域融合中不断否定自己,以使共同视域不断扩大。
当然,这里还未涉及伽达默尔的对话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构的具体的区别与关联,这就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善与两种对话的发生结构之间的关联,以及两种对话结构之间的关联、异同、源始性。
二、善与两种对话的发生结构
由于善与两种对话并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毋宁说善是两种对话的发起者和最终归宿,因此对善与两种对话的发生结构进行探析尤为必要,进而通过对两种对话的发生结构的比较,就能发掘出一种源始的善与对话。
首先,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构)是在善的要求或引导下展开的。如前文所述,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受了理性神(nous)的启示,要去引导他人认识善(善的定义),其中对话方法就是苏格拉底帮助他人遵循理性的指导去认识善的主要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这种通过对话来启迪他人向善的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坚信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存在这种“善的胎儿”(善的知识、善的定义)。然而对于善是什么,经过冥思苦想的苏格拉底还是感到“自知无知”(实际上他是有很多既成的思想的,可能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妄度神意。所以对于善的确切定义只能不断地接近,而不能完全达到),而“自知无知”则是以善为目的的对话开启的必要条件,因此苏格拉底便以“自知无知”的谦虚、开放的态度向他人“求知”。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谦虚的态度让一场富有启发意义的对话得以展开。
由于理性神的目的(善)不可能自相矛盾,因此善必定要求这种对话要朝着那个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善本身前行,苏格拉底必然以善本身的要求来开展对话。在对话中,他首先向对方提出善是什么,对方往往在这种谦虚的求知下会“不屑一顾”地给出一个命题,苏格拉底便根据推理或举出相反的例子揭示出对方命题中存在的内在矛盾,这迫使对方再提出一个较为普遍有效的定义,苏格拉底再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驳,对方再总结出一个更加普遍有效的定义……如此循环往复,苏格拉底便不仅使对方不得不否定了一大堆不具普遍有效性的对于“善是什么”之类问题的一般定义,而且还使对方归纳出了一个较为有效的定义或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善是什么”之类问题的无知。可见,这种问答式对话不仅是一种归纳有效定义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否定意见的有力途径。但这种对话法不是一般归纳论证,而是一种否定性的归纳论证。并且这种否定性的归纳论证以及这种对话形式正是在善的定义的必然要求下发生的。
这表明苏格拉底的对话一开始便是以善本身的要求和认识善为目的而展开的,且它还具有伦理性质、实践性质。但在伽达默尔看来,它仍然只是停留在方法论、认识论层次的对话,因为这种对话本身并不是前认识、前理论层次的实际生活经验或生活世界中的源始对话,它只是以对话作为认识善的手段,而认识善并不意味着就真正实现了善,因此还是需要回到实际生活中去应用才能真正达到善。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要认识善是什么,他就会行善,因为没有人愿意过不善的生活。
对于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始终是没有定论的。这个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由康德完成了,他提出了能够保证公平交往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在伽达默尔看来即是为“我们不应该把其他人作为工具来使用,而应当经常承认他们本身就是目的”[5]466。而这种道德法则也正是伽达默尔在解释学经验中发现的源始的对话关系所遵循的原则,由此伽达默尔将这种纯粹形式的道德法则拉回到了源始的作为实际生活的解释学经验的对话之中。因此,在这种源始的对话中,不仅人与人之间,而且人与历史流传物之间也都是遵循这种道德法则的,这种道德法则在伽达默尔看来也就是一种源始的“善良意志”,也正是它促发了作为源始的解释学经验的对话。下面我们就来看这种道德法则或善良意志在解释学经验中是怎样一种法则和善良意志?以及他们是如何展开出对话的?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验与流传物相关,且流传物是可被我们经验之物。“但流传物并不只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Geschehen),而是语言(Sprache),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5]465。因此,流传物与我的关系犹如伙伴关系,我和他的伙伴关系也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而“你”的经验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因为“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经验对象本身在这里具有人的特征,所以这种经验乃是一种道德现象,并且通过这种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他人的理解也同样是道德现象”[5]465。可见解释学的对话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现象,是一种将“他者”当作和“我”一样的“你”来进行对话的现象,而这种“我—你”关系所遵循的正是康德的道德法则,即以对方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应该说只有在这样一种平等的、相互开放的关系中,解释学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康德的这种道德法则在这种“我—你”关系的对话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无法实现的幻想,而是人的源始存在方式。因此,这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我们时时都需要有意识地以这种道德法则或善良意志去与流传物或他人发生对话关系,而实际上只要我们生存着,我们便时时都在(无意识地)善良意志的促发下与他人或流传物进行着对话,而这种对话具体说来就是带着自身有限视域的“我”与带着有限视域的“你”进行着的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话游戏(Spiel),在这种对话游戏中,重要的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本身规定了参与者(对话者)的存在方式。据此,善良意志从根本上说是这种游戏的发起者,因为它促使对话双方,游戏的参与者不断否定自身,相互开放并进入一个共同的视域中不断地进行视域融合。
当然,人们也可以以理论的态度、固执己见的态度对他人进行宣讲、询问。这种态度实际上是现代科技社会的弊病,它使人逃避,甚至不顾前科学、前理论的本真的生活世界经验中的善良意志的所展现的态度,而以一种理论的态度、控制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对待他者(他人或他物),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伽达默尔也一再强调一旦离开了善良意志,读者与文本的解释学的平等身份就会被打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理解,理解的公正客观性也要受到影响。
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更是如此,倘若我们固执己见地与他人进行对话,或者是我们在谈话中完全臣服于他人权威,那么真正的对话,真正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从实际生活经验中认识到的善良意志或康德的道德法则作为对话的基本态度应用于有意识的对话、交往之中,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理解),并从中达成共识,才能真正建立“善的共同体”。伽达默尔也非常强调应用,如果没用应用,那仍将是纸上谈兵,与理论无异。因为理解(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生存实践活动,通过这种生存方式达成的共识,还需要返回到生存实践本源上去不断深化这种共识(融合的视域),才会产生真正效果,善才能真正实现。这与苏格拉底认为认识善就可以实现善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也是更为深刻的。但伽达默尔这种以“善良意志”为前提的实践性的对话最终仍然和苏格拉底一样是以达到“善”为目的的,伽达默尔也曾言,正是柏拉图的“至善”思想一直激励着他从事解释学实践。只不过伽达默尔强调的是达到理论共识后还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并且在对话共识与应用之间不断循环才能最终实现“至善”。
伽达默尔的以“善良意志”为基础而发生的对话不仅为真正实现“善的共同体”寻找到了根基,而且为“善的共同体”的实现指明了有力的途径。这与苏格拉底以“善”为目的而进行的对话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他将苏格拉底以认识善为目的对话,引向了更深层次的前科学、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对话,并在这种实践性的对话中切实地向善。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只是在善的定义的要求下所展开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是认识善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实践善的方式;而伽达默尔的对话则是一种本体论层次的,由“善良意志”所促发的对话,由于人的生存实践本身就是对话,因此伽达默尔的对话既是源始的实践性的对话,也是通过认识后采取某种态度的对话,但不管如何,以“善良意志”促发的源始对话都始终在进行着。
三、善与两种逻辑
苏格拉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形式逻辑的先驱,他在其对话中使用了多种形式逻辑规则引导对话的前行,因为在他那里只有形式逻辑的方法才能真正引导对方最终认识到真理,认识到“善是什么”。而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的经验是在以“善良意志”为基础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中展开的,而这种“我—你”关系的对话的经验自身就具有一种比独白式的陈述所遵循的形式逻辑更为源始的逻辑形式。那么伽达默尔发现的源始的逻辑形式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形式呢?善与这两种逻辑形式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两种逻辑形式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而理解首先就意味着提问,而非对某物进行对象化的独白式的陈述。而即使是独白式的陈述在伽达默尔看来也是对某问题的回答,“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它自身的意义只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5]471。问题为回答提供了视域、方向,而回答又会引起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的问答结构即为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
伽达默尔的这种问答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中的问难于答,问先于答的思想。对此,伽达默尔曾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5]471。但伽达默尔的这种问答结构比苏格拉底与人进行对话的问答结构要更深一层,因为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对话)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因而人首先是在其存在中就与其他存在者进行着对话,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刻意进行的对话。但两种对话都不是先以一种对象化、理论化的方式对其他存在者作命题、陈述,而都是以提问为重的。海德格尔也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能向其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来接近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此在。此在向来超越其他一切存在者并向存在发问,因此,此在向来已在其生存实践中对存在有所理解、筹划。可见,人的存在本源地就是一种对于存在的理解,也本源地就是对于存在的发问。伽达默尔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解释学的经验只能通过理解者的提问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提问才能开启被理解者的存在,才不是对被理解者进行封闭化的对话的认知。
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经验的否定性、开放性同时也表明了“所有经验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6]368。因为“提问就是进行开放(ins Offene stellen)。被提问的东西的开放性在于回答的不固定性(Nichtfestgelegtsein)。被问的东西必须是悬而未决的,才能有一种确定的和决定性的答复”[5]471~472。因此,“如果没有问题结构我们是不能有经验的”[5]470。而经验源于理解者的理解,理解本身也就是一种发问。同时,这也正表明了被理解者的不可对象化、不可封闭性,以及正是提问对被理解者的敞开才使被理解者有可能被对象化的打量、认识。进而,发问是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的前提,是生存实践意义上的对被理解者的揭示、开放,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理论化的打量的前提。这样一种关联结构即为:生存、实践优先于理论认识;作为实践层次的理解优先于认识层次的对象化、理论化的考察;同样,开放性的解释学经验的问答结构也优先于认识论层次的对象化、理论化的独白;因此,解释学经验的开放性所具有的问答结构——“问答逻辑”也是优先于与认识的对象化、理论化、封闭性的独白相应的形式逻辑的。
但尽管如此,问答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还不明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虽然从整体形式来看是一种以谦虚、开放的态度引出的对话,它也显示了提问优先于并难于回答,但苏格拉底在与他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却运用了多种形式逻辑方法,“甚至在不少地方已经阐述了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则以及逻辑推理和论证的若干理论问题,有目的地引导人们进入比较严整的逻辑思维;特别是他驳斥智者的种种违反思维规律的诡辩,校正了逻辑思维进展的方向”[4]514。此外,苏格拉底还初步在对话中反复要求对方遵守形式逻辑的一些重要规则,如“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总是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保持同一、确定的意义(内涵)和外延,每一概念和判断必须保持同一性。他在讨论种种美德的定义时总是要求明确限定讨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样才能准确地探讨概念的定义。他指出‘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不能既是又不是’”[4]515。而且“他在定义活动中使用了种种推理和证明的逻辑方法,主要是一种归纳论证。他要求对话者提供某种美德的定义”[4]401,然后对方往往给出一个具体例子或不具普遍性的定义,苏格拉底便根据概念的同一性、不矛盾性等原则举出相反的例子或定义,使对方不断地否定自相矛盾的观点,对方就在这种否定性的归纳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善的无知,并被激起了向善的力量。
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定义,它只能是一个确定的规定、只能与自身同一,它不能是它自身的否定,也不能既是又不是。因此,他在对话中会反复使用一些推理的形式逻辑的规则来保持概念的同一性,这样才能保证获得善的知识。也正是因为定义是唯一的,他在对话中才能不断地启发他人否定他的诸多逐渐普遍化的意见,而最终有可能达到一个绝对普遍有效的定义。由此可见,形式逻辑的规则引导着苏格拉底对话的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概念的同一性原则,因为善是“一”,而不是“多”。而且善自身就是不同于人们日常以特殊目的为行为准则的诸多意见,这些意见因为是特殊的,所以是相互矛盾的、混乱的;而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可以说善就是那绝对同一的东西。而形式逻辑的规则正是善的定义自身的要求,也正是这些要求保证了对话朝着善的定义,善的真知前行。
由此表明:苏格拉底的对话尽管是采取实际生活中的对话形式,但它明显带有以启发认知为目的并以形式逻辑规律作为手段的色彩。伽达默尔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尤其是以“无知”而“提问”的方式,但伽达默尔使苏格拉底的对话从认识论、方法论层次回溯到了本体论层次,认为人的前科学、前理论的生活世界或实际生活经验本身就是不断进行着视域融合的对话。而这种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对话具有一种以发问引起的问答逻辑结构。因此,问答逻辑是一种本体论层次的解释学的逻辑,而作为认知手段的形式逻辑,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使用,它只有以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对话结构———问答逻辑为基础才得以可能,尽管我们的各种理论活动都是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
最后,如前所述,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经验是一种在“我—你”关系的对话中展开的经验,其中被理解者具有人的特征,因此这种经验是一种道德现象。具体地说,它是一种以康德的“道德法则”或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为前提的对话。这种“道德法则”或“善良意志”使得解释学经验具有了自否定性、开放性,而解释学经验的自否定性和开放性本就意味着它具有一种问答结构,即“问答逻辑”。可以说在伽达默尔的对话中,同样是以善为前提促发了问答逻辑,问答逻辑同时也体现了善的原则,只是这种问答是不断地展开着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即是通过对话形成一个“善的共同体”,但它体现的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的生存实践过程,因而这种问答逻辑是一种没有最终认识目的的伦理性实践活动的结构;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以认识“善”作为最终目的的,从这方面说它是有限的。然而,苏格拉底也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善,只能不断地前行。所以,从这方面看,这种对话又可能是无限的向“善”逼近。最终,伽达默尔将苏格拉底千方百计要认识的善在实际生活的解释学经验中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源,并试图以之为基础在人类社会中真正实现一个“善的共同体”,而不再是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只要认识“善”,就可以行善、实现善的思想。
四、结论
综上,苏格拉底和伽达默尔的对话思想的之间的关系与区别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二者对于自然科学理论有着相似态度。(2)“善”是二者对话思想的目的和动力。只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还只是为达到对“善的定义”的一种手段,还处于方法论层次;而伽达默尔的对话则是人的存在方式,其本质上就是善的表现,这是一种本体论层次的、源始的对话。(3)伽达默尔在源始的对话中发现了与派生的独白式的陈述所遵循的形式逻辑不同的“问答逻辑”。(4)“问答逻辑”是基于“善良意志”才可能的,“善良意志”从根本上决定了“善的对话”与“善的共同体”的可能性,甚至发展方向。
[1]W.K.C.Gruthrie.Socrate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3]Hans-George Gadamer.Vernunft im Zeitalter der Wissenschaft,Aufsätze[M].Main:Suhrkamp Verlag,1991.
[4]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Hans-Georg Gadamer,Hermeneutik.I: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M].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90.
[责任编辑:黄文红]
B1;B82
A
1001-4799(2015)01-0105-06
2013-05-07
帅巍(1981-),男,四川眉山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