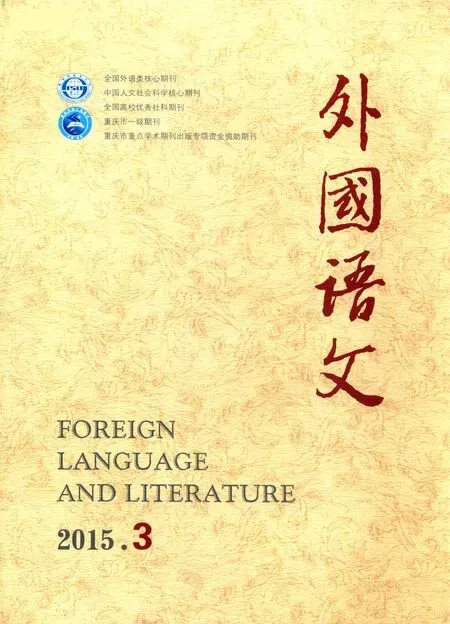边缘叙事策略及其表征的历史——朱利安·巴恩斯《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之新解
赵胜杰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
1.引言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因写作手法新颖、作品风格多变被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誉为“小说形式的革新者”。(Poole,1998:10)创作于他而言,“不仅对于个人(你)而且对于整个小说史都是一个新起点”(Holmes,2009:12)。凯拉威曾坦言,虽然“创作是在一个封闭形式的规则结构之内活动……但是,我喜欢打破规则”(Kellaway,1996:7)。他作品中的形式实验因此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高度关注。在1989年发表的《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Chapters)中,他表现出极大的实验性和革新性。小说中,他不仅将看似互不相连的故事拼贴在一起,形成反写实的非线性叙事,而且还采用一些边缘叙事策略颠覆了主宰西方的宏大历史叙事,诸如:历史的进步说和乌托邦说,并以这种“新”的美学策略表述了新的历史内容。本文认为,巴恩斯采用的边缘叙事艺术形式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因为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也常以一种边缘性的、异质的方式来颠覆占据中心的西方宏大历史叙事,这在王岳川(1999:155-6)关于新历史主义的论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请看如下引文:
正是通过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些趣闻逸事、意外的插曲、奇异的话题,去修正、改写、打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码(社会的、政治的、文艺的、心理的等),以这种政治解码性、意识形态性和反主流姿态,实现解中心(de-centered)和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权力角色认同,以及对文学思想史的重新改写和阐释的目的。
综上而言,作为影响后现代主义巅峰形式实验大师,巴恩斯并不仅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亦不是一味地“为解构历史而书写历史”的解构家,相反,他的这部“世界历史”在带有外部经验世界影响的烙印的同时,还向读者呈现出另一种潜在的历史真实。一句话概括,巴恩斯并不是一位关在“象牙塔”里的纯形式实验者。
2.历史再现中的边缘声音:边缘与中心
《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中,边缘声音主要表现为:“偷渡者”中木蠹的自反式叙述声音和后记中作者的声音。通过前者,巴恩斯促使读者一起参与反思官方档案记载中的《诺亚方舟》故事的真实性,颠覆了《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这一传奇故事的权威性;通过后者,他以边缘性的声音质疑单一主体叙事的权威性,同时,还因将现实世界的“真实材料”融入虚构作品中而让读者难辨真假。本文认为,巴恩斯通过设置边缘与中心对话的叙事技法,实现去中心化、包容差异与多元共存的后现代艺术创作思想。
2.1 木蠹的回顾性自反叙述与《诺亚方舟》
第一章中,作者采用偷渡到方舟上且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木蠹的边缘视角重述《诺亚方舟》故事。木蠹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出现于叙述层的叙述者,且作为同故事参与者的身份增强了其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于它们是偷渡到方舟上的物种,因而没有与上帝或诺亚订“任何可疑的契约”(Barnes,1990:28)①以下引自巴恩斯的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Chapters中的文字仅标注页码。。它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与《圣经·创世纪》中不一样的《诺亚方舟》故事。首先,它们质疑官方记录中关于雨水持续的时间和大洪水淹没世界的时间,按照木蠹的算法,雨不是下了“40个日日夜夜”,而是“下了约一年半”,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仅仅是一个平常的英格兰夏天了”;同样,大水淹没世界也不是150天,而是“大约4年”(4)。其次,航行中,方舟上承载的动物物种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它们反倒成了诺亚和其家人餐桌上的佳肴。于诺亚和他的家人而言,它们“就像是一个海上漂流的自助餐厅”(4)。可谓雪上加霜的是,“驴被缚于船底施以拖刑、医护船的丢失、清除杂交动物的政策,还有独角兽之死……”(26)。此外,木蠹描述的诺亚不再是一个保护者的英雄形象,它以第一人称“我”的声音告诉读者:“我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将这告诉你,但是诺亚不是个好人。我明白这种说法很难看,因为你们都是他的后代,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怪物,是个自命不凡的老昏君,一半的时间讨好上帝,另一半时间拿我们出气。”(12)独角兽“强健,诚实,无所畏惧,仪表整齐,而且从不晕船”激起了“脾气坏,体臭难闻,不可信赖,嫉妒又胆怯”的诺亚的嫉妒和不满,最终难逃被“炖”的厄运(16)。
叙述过程中,拥有自我意识的木蠹不断中断叙事进程进入叙述层提醒读者回想官方档案中的《诺亚方舟》故事:“当然,你不必相信我;但是你们的档案说了些什么?”(16)木蠹在叙述层通过反复申述他们描述的诺亚是亲眼所见,强调他们的叙述是真实的以赢取读者的信赖,进而颠覆官方文献中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因此可见,木蠹在叙述层“游说”读者的目的在于消解官方档案中《诺亚方舟》故事的真实性,可以说,“叙述引导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故事’设下的圈套”(王丽亚,2008:43)。与此同时,拥有对这一观点——学者们为了维护诺亚的英雄形象便否认“第二个”诺亚不同于《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第一个”诺亚——的自我意识,木蠹自我申辩道:“可这‘第二个’诺亚的故事——酩酊大醉、卑劣、随意处罚孝顺儿子——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奇怪,因为我们了解方舟上的‘第一个’诺亚。”(30)叙述者表现出对所述故事、读者以及学者们的评论的自我意识,印证了巴恩斯(2006:70)在接受苏莎·古比(Shusha Guppy)的访谈中论及的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观点:“由于传统历史小说试图模仿式地重构人物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因此本质上而言是保守的,但是新历史小说却以一种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自觉意识接近过去,并试图与今天的读者建立一种更加明显的联系。”显然,巴恩斯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强调的是对已发生事情和读者的自我意识,这与木蠹表现出的自觉意识相契合。
由上可见,木蠹描述的《诺亚方舟》故事与官方档案中记载的这一神话传奇形成边缘与中心的对话关系,而且作者通过木蠹的边缘视角消解后者的权威性以及诺亚的英雄形象。生为木蠹的它们,连登船的权力都没有,这是它们的莫大悲哀,但是面对这种歧视,它们驳斥道:“说到底,生为木蠹,不是我们的错。”(30)它们最后这一自我辩解无疑说明它们是被自动驱逐出了权力系统之外,因而从一开始便不具有话语权威,这不仅暗示它们所述故事是被档案卷宗拒斥在外的且具有真实性的边缘化历史,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历史书写与话语权息息相关。
2.2 “作者注释”中的边缘声音与主体叙事
小说最后部分的“作者注释”,是法国著名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所指的类文本形式之一。热奈特最早在《类文本:阐释的临界》(Seuils,1987)一书中将类文本划分为两种:边缘或书内类文本(peritext)和外类文本(epitext)。在该书英译本前言中,理查德·麦克赛(Richard Macksey,1997:xviii)认为前者包括,“标题、副标题、笔名、前言、致谢、题词、序言、字幕、注释、结语和后记”;后者包括成书过程中的“公开外类文本”(作者或出版者提供的)和“私密外类文本”(由作者的通信、口头密语、日记和前文本等组成)。由此可见,巴恩斯小说中的“作者注释”属于前一类。这一边缘文本作为主体文本的延续,是对文本内容进行的补充说明,并以其边缘性的声音消解单一主体叙事的绝对中心地位,左右着读者对文本的阐释。
作者在后记中附上的注释,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文学现象,请看如下内容:
作者注释
第三章根据的是E.P.伊凡斯1906年著的《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一书中所描述的法律程序和案例。第五章第一部分中的素材和语言取自萨维尼和科里亚合著的《塞内加尔远征记》一书1818年伦敦译本;第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洛伦茨·艾特纳的典范之作《籍里柯:其生平和作品》(奥毕斯1982年版)。第七章第三部分的素材取自戈登·托马斯和麦克斯·摩根-维茨合著的《亡命之旅》(霍德1974年版)。我感谢丽贝卡·约翰在研究方面的大力帮助;感谢安妮塔·布鲁克纳和霍华德·霍奇金审阅本书有关艺术史方面的内容;感谢里克·奇尔斯和杰伊·麦金纳尼审阅本书有关美国方面的内容;感谢杰基·戴维斯博士对本书中有关外科手术方面的内容提供的帮助;感谢阿兰·霍华德、盖伦·斯特劳逊和雷德蒙·奥汉隆;我还要感谢赫米奥那·李。
朱利安·巴恩斯
在这一边缘类文本中,巴恩斯指出部分章节故事的来源,将文本的人为建构性公然暴露于读者面前。从引文可见,第三章与伊凡斯(E.P.Evans)1906年出版的《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构成互文性关系。以此类推,第五章第一部分与萨维尼(Savigny)和科里亚(Corréard)合著的《塞内加尔远征记》(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Senegal)形成互文关系,第二部分与洛伦茨·艾特纳(Lorenz Eitner)的典范之作《籍里柯:其生平和作品》(Géricault:His Life and Work)互文;第七章中的第三个故事与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和麦克斯·摩根-维茨(Max Morgan-Witts)合著的《亡命之旅》(The Voyage of the Damned)构成互文性关系。关于这种互文现象,琳达·哈琴(1988:172)如此阐释:“所有的互文本都质疑了人文主义唯一性和独创性的概念。”那么,由“作者注释”揭示出的种种互文性关系便自动消解作者的著述权威,颠覆了该作品的唯一性和独创性。另外,这些隐匿作者——伊凡斯、萨维尼和科里亚、洛伦茨·艾特纳以及戈登·托马斯和麦克斯·摩根-维茨——的存在质疑了主体叙事中叙述者的叙述权威,揭露出叙述者的叙述权威和所述内容的虚构性。
这里,类文本中隐匿作者与主体叙事中的叙述者并置也形成边缘与中心共存的文本空间。虽然两者都宣称各自文本内容的真实性,但同时却又抵消着彼此的真实性,使读者陷入真伪难辨的尴尬境地。毋庸置疑,这一技巧为我们解读文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消解单一主体叙事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多元共存的画景。
3.历史再现中的非理性:非理性与理性的历史
在第四章“幸存者”和最后一章“梦”中,巴恩斯以凯丝的幻想和“我”的梦境这两种被传统历史书写排斥的、非理性的形式,分别拆解了西方宏大历史叙事中关于文明史的进步说和乌托邦说。笔者认为,通过这种非主流的、边缘化的叙事手法,巴恩斯不仅自觉挑战既定文学创作成规,而且还间接地批判以黑格尔历史理性哲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历史观:“历史是单一线性化的、进步的、决定论的。”(Eagleton,1996:45)这再次印证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巴恩斯并不仅是一位纯粹的后现代审美实验者,他的作品还服务于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正如他在《福楼拜的鹦鹉》中探讨文学创作问题时所做的自反式评论:“文体是主题的一种功能。”(Barnes,1990:88)
3.1 凯丝的幻想:质疑文明史的进步说
在以瓦尔特·司各特(Walt Scott)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被隐含作者赋予了上帝般的、绝对的叙述权威,文本意义呈现为一元性。但是,在《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第四章中,巴恩斯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女性人物凯丝·菲利斯(Kath Ferris)的视角交替进行叙述,消解了前者绝对的叙述权威。文章认为,作者通过将凯丝的幻想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并置,隐含了这样一种创作构思:通过被压制的、女性的、非理性的叙述声音来颠覆西方宏大历史叙事的线性发展说。
一开始,全知叙述者便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向读者揭露凯丝的内心活动,“接下来呢?她记不得了”(83)。她无法记住的是:1492年哥伦布航海探险之后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这暗讽了遵循因果逻辑、线性发展的传统历史观,间接地反映出隐含作者对这种历史观的嘲讽,同时,也与新历史主义者对“线性时序和发展的历史”的抵制不谋而合(Veeser,1989:xv)。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叙述者接着强调说:“但驯鹿她却记得很牢。”(83)可见,凯丝并不是一位完全不可靠的叙述者。作为非理性的象征,她甚至相信:“驯鹿会飞。”(83)接下来,叙述者继续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揭示了她的意识活动:“一切事物都相连,且驯鹿会飞。”(84)自由间接引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是以叙述者的叙述话语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巧妙结合的结果。
关于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两者之间的关系,著名叙事理论家多罗泽尔(Lubomír Dole el)于1980年发表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的文章《叙事中的真实与认定权威》(“Truth and Authenticity in Narrative”)在借鉴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奥斯丁(J.L.Austin)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叙事言语行为二元模式:“隐叙形式叙述者的言语行为承载着认定权威(authentication authority),而叙事代理(人物)的言语行为缺乏这种权威。”这里认定权威是一种特殊的言外行为,类似于奥斯丁所描述的言后行为(performative speech act)。换句话说,在文本世界中隐性叙述者(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叙述言语行为被赋予上帝般的、绝对的认定权威,因而他所说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真实的,由此产生的真实的效果便是一种言后行为;而人物叙述者的言语行为的认定权威却要从属于叙述者的认定权威,且人物叙述者的言说内容只有与隐叙者言说的内容一致时才具有真实值(truth-value),否则就不具有真值,也即真实性。简言之,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言语行为具有认定权威,人物话语的言后行为从属于这一认定权威,因而不享有这种绝对的认定权威。由此可见,作为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相结合的自由间接引语,使得蕴含其中的人物话语具有了真值,因为隐性叙述者所具有的认定权威间接地赋予人物话语以真实值。也就是说,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自由间接引语产生的叙事效果是:使所表达的人物主观世界得到隐含作者的默认并具有真实性。因此,“幸存者”中,第三人称叙述者以自由间接引语来呈现凯丝的内心思想活动,便间接地赋予了她之后展开的第一人称叙述以一定的叙述权威,再次印证了她并非一位完全不可靠的叙述者。
该故事主要以俄国人投掷核炸弹为历史背景,而将边缘女性人物凯丝的内心活动前景化,凸显出作者对大历史潮流面前小人物表现出的人文关切。在凯丝的第一人称叙述中,作者主要通过意识流手法来再现她的幻想活动。从她的意识流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她在私生活中饱受丈夫格雷格(Greg)的压制,例如:当描述格雷格时,她谈及:“他上班,回家,闲坐,喝啤酒,和朋友出去再喝啤酒,有时在发薪日晚上扇我一通耳光。”(87)因此,她的思想活动不仅揭露出丈夫的劣行,而且还是对格雷格象征的男性强权的抵制。除此之外,她还遭受核战争给她带来的严重的身心健康威胁,如:掉头发、脱皮和患有幻想综合征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她梦魇中与一位男子的对话了解一二。
“你又怎么解释我掉头发?”
“恐怕是你在拔头发。”
“我的皮肤脱落呢?”
“你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你经受了严重的压力。这没什么不正常。但是,会好起来的。”
“你又怎么解释我样样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从得到北方爆发战争的消息到在这岛上度过的日子?”
“嗯,用技术术语说是虚构(fabulation)。你编造一个故事来掩盖你不知道的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尤其是在双重压力的病例中。”
……
“嗯,我很佩服你的虚构,”我说,把这技术术语反过来用到他头上,让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感觉你编造得很灵光”。他当然是自己露了馅。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他完全是这么做的。(加粗部分原文为斜体)(109-110)
通过这一嵌套式的梦魇片段可见,那位男子认为凯丝头发脱落的原因是她自己拔掉的,与核战争毫无关系,他的解读无疑影射出官方叙事对这一战争事件的虚构和伪造;然而,她反套用他的术语将他的解释斥为虚构。从上述可见,凯丝并非一位“疯癫”、缺乏逻辑、糊涂的叙述者,她的幻想活动因而也并非是毫无意义、不具有真实性的主观臆想活动。笔者由此得出结论:作者借幻想这一保护外衣揭示出另一种可能的历史真实,质疑了这一官方历史叙事的权威性,进而批判了背景化的核战争。
综上所述,凯丝遭受双重压力:丈夫的虐待以及核战争带来的灾难,根本没有享受到所谓历史进步带来的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本文认为,作者借这一幻想叙事策略,委婉含蓄地批判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宣扬的以理性为核心的历史进步说。
3.2 “我”的梦境:解构乌托邦
小说最后一章完全是对梦境的描写。这一章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讲述“我”在梦境中来到一个现代消费者新天堂的故事。梦境中,“我”的一切需求和欲望都得到满足,而且一切都是自动化,非常便捷。“购物车是用马达驱动的金属网脚轮车,像躲闪碰碰车来回转悠,只不过从不相互碰撞,因为有某种电眼装置。你正觉着要碰上去了,却发现自己闪到一边,躲过了迎头撞来的购物车。”(285)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购物结束回到家之后,“我……倒不是疲劳——你不会疲劳的——就是有点厌腻了”(286)。在休息了一晚上之后,“我以为醒来会感觉疲劳,但又是那种愉快充实的感觉,就像购物之后那样”(290)。虽然人的任何需求在这里都会得到满足,但是当“我”问玛格丽特(Margaret)“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做出死的选择?”时,玛格丽特的回答是:“哦,当然是百分之百。……但是,确实每个人早晚都会做出这一选择。”(303)
尽管在死后的新天堂里“一切都非常的舒心:购物、高尔夫、性、会见名人、没有什么感觉不好、永生不死”,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主人公觉得“一直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跟一直要什么就没什么两者几乎没什么差别了”(307)。天堂里的人的唯一出路便是选择死亡。结尾,“我梦见我醒了。这是最古老的梦,而我刚刚就做了这个梦”(307)。显然,这里梦境已不再是人们想象的美好的天堂、田园或其他非常美妙的事情,后工业的消费社会成了梦境的内容,梦也因其具有的这种当代性而不再被人们心向往之。
巴恩斯以梦境的形式展望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乌托邦”。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最早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他的拉丁语作品《乌托邦》(Utopia,1516)中创造。这个词由两个希腊语的词根组成:“没有”(ou)和“地方”、“处所”(topos),在拉丁文中意思是“乌有之乡”或“不存在的地方”(崔竞生、王岚,2006:613)。自莫尔以降,乌托邦已成为一个类指名词,“泛指人类有史以来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思想文化和实践活动”(同上)。乌托邦因此演变成了构想理想社会美好愿望的代名词,象征了“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和“幸福”等。文学中,描写乌托邦的作品不乏少数,有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德国安德里亚尔的《基督城》、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巴恩斯却以陌生化手法构想了一个奇异的“乌托邦”,一个“异托邦”(dystopia),因为“我”并没有感到被救赎,相反却感到极端的疲倦和厌烦,最终被迫选择逃离。
本文认为,“我”在这一“异托邦”中的“境遇”照应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和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分析和阐释的“末人”问题。福山(1992:312)指出,“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后的“末人的生活是一种物质上有保障且丰裕的生活”;而且由于“末人”没有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而已沦为一种没有抱负的人,也“不再是人类了”。显然,文本中的“我”也是福山所指的“末人”。因此,尽管“我”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对这样的生活却没有丝毫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最终放弃这种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上的丰裕生活,这体现出作者“质疑科技发展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罗小云,2007:102)。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代消费社会发展的隐忧,以及他对“历史终结”这种宏大历史观念发展到顶峰时的“末人”问题的忧虑,从而颠覆了这种“末人”乌托邦世界。
“梦境使得作家可以摆脱小说当中只描写现实生活的平面维度,实现对人的意识、潜意识以及现实与意识之间关系的深度挖掘。”(刘象愚等,2003:453)由此推断,巴恩斯通过梦境的形式面纱,自觉摆脱现实生活平面维度的束缚,想象性地展望西方民主社会终极形态之“乌托邦”世界,消解了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构想,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这里,梦境被赋予新的内容,直指后工业的消费社会,变得不再让人殷切期待。
4.结语
纵观全文,在这部关于“世界历史”的消解式注释(footnote)中,巴恩斯建构出一个多元边缘叙事形式共存的文本空间:木蠹的自反性叙述视角、类文本中作者的声音、幻想和梦境。这些叙事手法不仅表征新的历史内容,向读者提供历史阐释的新路径,而且还说明巴恩斯是一位不拘一格、自觉挑战文学成规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大师。当然,承认历史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应辩证地审视其对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性,绝不应将其奉为解读历史的《圣经》,否则,就会陷入多元主义包容性的陷阱之中,淡化历史意识,甚至遗忘历史。众所周知,历史之镜有助于人们避免重蹈覆辙、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应忘记客观历史事实,而应持“信仰之眼”(eyes of faith)来维护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从而不迷失前进的方向(Barnes,2005:355)。
[1]Barnes,Julia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Chapters[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
[2]Barnes,Julian.Arthur& George[M].London:Jonathan Cape,2005.
[3]Barnes,Julian.Flaubert’s Parrot[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
[4] Dole el,Lubomír.Truth and Authenticity in Narrative[J].Poetics Today,1980(1):7 -25.
[5] Eagleton,Terry.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M].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
[6]Fukuyama,Francis.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
[7]Guppy,Shusha.The Art of Fiction CLXV,an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rnes[J].Paris Review,2006,(157):54 -84.
[8]Holmes,Frederick M.Julian Barnes[M].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12.
[9] Hutcheon,Linda.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M].London:Routledge,1988.
[10]Kellaway,Kate.The Grand Fromage Matures[J].Observer,1996(7):7.
[11] Macksey,Richard.Foreword [M]//Gérard Genette.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Trans.Jane E.Le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2]Poole,Steven.Why Don’t We Make it All Up?[J].Independent on Sunday,1998,(30):10.
[13]Veeser,H.Abram.The New Historicism[M].London:Routledge,1989.
[14]崔竞生,王岚.“乌托邦”[G]//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5]刘象愚,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6]罗小云.震荡的余波——巴恩斯小说《十卷半世界史》中的权力话语[J].外语研究,2007(3):98-102.
[17]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J].外国文学评论,2008(2):35-44.
[1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