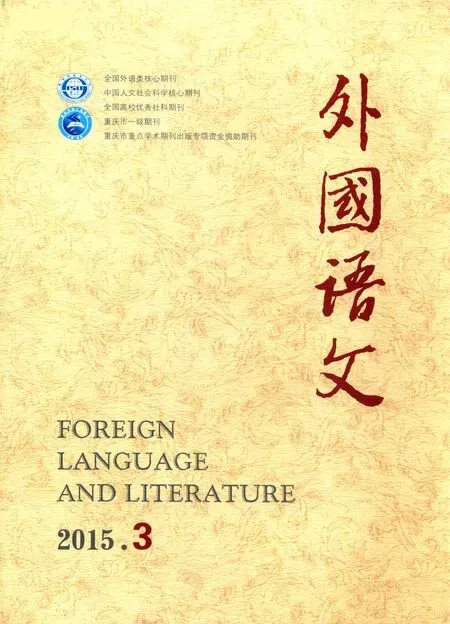从文化记忆视角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哥萨克形象
冯 俊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重庆 400031)
1.引言
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俄罗斯文学家,特别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别尔等文学大师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哥萨克形象,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人们或从认识哥萨克历史角度分析作家塑造的哥萨克形象,如张达明和杨申的《“静静的顿河”与哥萨克》,或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作家笔下的哥萨克形象,如王蒙和王天兵的《关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或从道德价值角度梳理哥萨克形象,如米·库图佐夫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中的哥萨克形象》。然而,未见有人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对俄罗斯文学长廊中的哥萨克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对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别尔等人塑造的典型哥萨克形象进行梳理和解说,更能加深人们对俄罗斯文学厚重的历史感的认识。
2.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的哥萨克形象
2.1 文化记忆的功能与文学文本
文化记忆的功能是日益成为显学的文化记忆研究特别关注的内容。研究文化记忆的德国著名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不仅具有集体同一性构建功能,而且有‘评判和反思’的功能。”(冯亚琳,2013:6)
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文本是文化记忆的媒介,也同样具有集体同一性的建构和评判反思功能。正如阿斯特莉特·埃尔所指出的:
在文学的记忆形成领域可分两个功能潜力:一个是对现存记忆文化中想象结构的肯定或是加强,另一个是对其的解构和修正。文学作品可以产生新的,但是与记忆文化中象征的意义世界有联系的虚构的现实。在其中可以塑造自我形象,历史想象或是以一种简洁和形象的方式表达价值观和标准以及被忘却的事物,和记忆文化中不可表达的东西。它们也可以询问、解构,或者明显地改造已有的记忆叙述,并且修正历史形象、价值结构或是有关自我和他者的想象。(冯亚琳,2012:242)
2.2 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的哥萨克形象
哥萨克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列夫·托尔斯泰就明确说过,哥萨克创造了俄罗斯。哥萨克曾为沙皇的开疆拓土充当先锋,功勋卓著,又是俄罗斯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让统治者心惊胆战,倍加提防。
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中,哥萨克的形象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极具特色的草莽英雄和令人恐怖的刽子手。作为草莽英雄,哥萨克桀骜不驯、崇尚自由、极具反抗精神,并且粗犷豪迈、尚武好斗、英勇善战。在俄罗斯历史上,哥萨克多次发动农民起义,反抗沙皇政府,成为农民起义的主力,成就民间文学中哥萨克绿林好汉的形象,也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严加提防。
作为刽子手,哥萨克冷酷凶残,杀人不眨眼。实际上,由于执政者的笼络利用,18世纪后,哥萨克成了一个特殊的军事阶层。哥萨克军队逐渐以沙皇驯服工具的面孔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沙俄帝国巩固国防、对外扩张、镇压民众的重要军事力量。哥萨克在屠犹活动中充当急先锋,对犹太人毫不留情地杀戮,在镇压革命中充当沙皇帮凶,双手沾满普通民众的鲜血。
3.俄罗斯文学中典型的哥萨克形象的文化记忆
由于哥萨克在俄罗斯社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历史作用,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中形象矛盾,自然成为俄罗斯文学关注的对象。关于哥萨克形象的作品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的《顿河哥萨克围攻亚速城记》。第一个选择哥萨克作为作品主人公并留下作者姓名的是著名的乌克兰诗人伊·彼·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但是描写哥萨克形象最为著名的恐怕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别尔等人的作品,他们为俄罗斯人文化记忆中的哥萨克形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使得哥萨克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1 颠覆性重构——普希金笔下的普加乔夫
在俄罗斯文坛上,第一次真正让哥萨克形象引人注目的是普希金在《大尉的女儿》中塑造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在普希金笔下不再是沙皇政府认定的妖魔鬼怪、凶残暴徒,而是追求自由、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普加乔夫被赋予许多美好品质。一是知恩图报、重情重义。普加乔夫因为接受小说主人公彼得赠送的皮袄和酒,不仅给予立场对立的彼得以自由,后来还亲自陪同彼得去白山要塞营救彼得的未婚妻。二是勇敢。普加乔夫在攻打白山要塞时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三是深受民众拥护和爱戴。普加乔夫攻下白山要塞,人们拿出面包和盐欢迎他,向他致敬,称他为父亲、皇上。四是性格刚毅、宁折勿弯。普加乔夫借助卡尔梅克童话表达心声,宁作痛痛快快喝足一顿鲜血的老鹰,也不作吃死尸活三百年的乌鸦。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普希金重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至少有两方面值得关注。
一方面,重构的颠覆性。按照文化记忆理论,“重构从当下出发,同时又服务于当下的需求,因此其选择具有政治性。它可以服务于主流记忆,证明当下社会的合法性,也可能质疑甚至颠覆主流记忆,证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冯亚琳,2013:56)。显然,普希金重构的普加乔夫形象与官方主流认定的强盗、暴徒形象迥然不同,可以说是对主流记忆的根本颠覆。普希金正是用这种颠覆性重构来强调官逼民反的俄罗斯社会急需改革,以避免普加乔夫式的危及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难怪别林斯基会把《大尉的女儿》称为着眼过去、说明现在、预防未来的作品。
另一方面,重构的价值取向。按照文化记忆理论,文学形象一旦成为记忆形象,就“凝聚了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它不仅显现为一股群体的自身形象和‘家园’,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定义这个群体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处于变化中——的本质、特征、弱点以及价值取向”(冯亚琳,2013:171)。在普希金对普加乔夫的形象重构中,隐含着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大帝国的渴望。
对强大帝国的渴望和自由的理想之间的矛盾是16世纪后俄罗斯文化中的贯穿性因素。费多托夫把这个贯穿性的文化哲学的非此即彼进退两难的选择叫作帝国和自由的对立。新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家中很少有人躲得开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包括普希金这位俄罗斯经典时代的奠基人。普希金的创作的主要力量集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帝国和自由(Федотов,1992:142)。费多托夫认为普希金是帝国和自由的歌唱家,既讴歌个人自由,又憧憬伟大的帝国。这反映在普加乔夫形象的重构中,甚至贯穿整个《大尉的女儿》的主题。一方面,普希金在小说中同情人民的疾苦,正视官逼民反的俄罗斯社会现实,并通过塑造普加乔夫这一形象,肯定了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和权力;另一方面,普希金又把帝国看作一种秩序和制度,是用理性和意志因素不断克服混乱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强大力量,而普加乔夫式的暴动与帝国的理性和意志因素对立。因此普希金在《大尉的女儿》中更强调普加乔夫暴动动摇强大帝国的根基的危险。
3.2 率真的英雄——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
紧随普希金之后,果戈理又为俄罗斯文化记忆长廊增添了一位光彩夺目的哥萨克英雄形象。
果戈理在其浪漫主义史诗性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塔拉斯·布尔巴。在果戈理笔下,塔拉斯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热爱自由、珍惜荣誉、忠于祖国。对他而言,哥萨克的荣誉和祖国俄罗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为此,他义无反顾地献出了一切。他不顾妻子反对,毫不迟疑地将两个儿子送往兵营,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保家卫国的忠诚战士。他毅然决然率领哥萨克联队,奔赴战场,以反抗异族压迫,捍卫祖国自由。
塔拉斯·布尔巴勇猛彪悍、英勇善战,他率领的哥萨克联队所向披靡,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的无情,甚至在哥萨克们看来也显得过分。他对亲人背叛祖国也决不饶恕。当次子安德烈经不住美色诱惑投敌叛国,他毫不犹豫亲手处决了这个不肖子。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形象”承载着一个集体(比如民族)的记忆,从而具有身份认同意义。与此同时,“记忆形象”在集体记忆的时空与交往形式中产生出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关联不断得到重构(冯亚琳,2013:171)。从承载民族集体记忆、身份认同意义的角度看,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是一个率真的民族英雄的真实写照。果戈理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虚构历史和人物,肯定旧时的哥萨克勇士精神。这种带有率真的英雄主义与主流意识提倡的爱国主义血脉相连。正因为这一点,苏联时期塔拉斯·布尔巴被视为弘扬民族正气、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独立的英雄。果戈理这部小说入选中小学课本,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在卫国战争时期,塔拉斯·布尔巴更是成为激励战士们前赴后继奋勇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者的经典之作(Голубков,1954:235)。
值得指出的是,果戈理对哥萨克嗜血的野性,常常表现出的残忍凶暴的人性恶的一面,也不隐讳。《塔拉斯·布尔巴》中有这样的描写:
塔拉斯率领着自己的联队游逛了整个波兰,烧毁了十八处小镇,将近四十座的加特力教堂,并且已经达到克拉叩甫了。他杀了很多波兰贵族,劫了许多城郭;哥萨克们把密藏在贵人仓库里的多年的老蜜和陈酒打开洒到地上了,把从箱柜里搜出的值钱的绸缎、衣服和装饰品都割裂了,烧了。“不要怜惜一切!”塔拉斯只是重复地说。哥萨克们也不尊重那些黑眉毛的波兰女人,白胸脯的、嫩脸蛋的小姐。她们就是躲在圣殿里也不能被救,塔拉斯把她们和圣殿一起烧了。许多雪白的胳膊从火焰里伸向天空,发出悲惨的喊声,这喊声使那潮湿的大地也要颤抖了,连原野上的青草也要因为怜悯而低头了。但残酷的哥萨克们并不注意这些,而且用长枪从街上挑起小孩子们,把他们也照样投进火焰里。(果戈理,1997:388)
显然,果戈理对哥萨克的嗜血与野性欣赏多于评判,也许,作家把这种嗜血野性视为英雄率真的表现,似乎对敌人越是冷酷无情,越是显出英雄本色,这样的英雄才血肉丰满。而死气沉沉的俄罗斯社会似乎更需要嗜血、野性的爱国英雄。这显然大大超出人们对人性的认知。难怪在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社会思想意识走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塔拉斯·布尔巴就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爱国者,还有人干脆把他看作是种族歧视者、残酷无情的恐怖分子。
3.3 美的化身——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丽雅娜
在果戈理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在杰作《哥萨克》中又为俄罗斯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光辉的哥萨克女性形象玛丽雅娜。在《哥萨克》中,玛丽雅娜是自然中一切美的化身,蕴含着哥萨克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也凝聚了托尔斯泰对诗意人生的全部追求。在托尔斯泰笔下,玛丽雅娜不仅具有外表美,更是高尚道德的象征。从外表看,玛丽雅娜“美丽窈窕”、“结实匀称”,一双美丽的黑眼睛略带稚气与野性,步伐坚实、目光不驯。从内在品格看,玛丽雅娜更是哥萨克优秀品德的化身。她质朴自信,当她看到主人公贵族青年奥列宁时,神情表现出愉快,表现出她对美的一种领悟。她勤劳善良、洁身自好,对女友乌斯坦卡与公爵经常在一起很是不齿,认为是“一桩罪恶”,使得在聚会作乐场所任意向其他姑娘调笑的轻浮军官们对她敬而远之。她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当未婚夫鲁卡沙嫉妒她与奥列宁的友谊时,她骄傲地说:“我高兴爱谁就爱谁!”(托尔斯泰,1997:352)她高尚、正直、坦率,像大自然一样质朴。当奥列宁说鲁卡沙坏话时,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对他射出严厉而敌意的光芒”,让奥列宁自惭形秽,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但鲁卡沙在捕捉车臣山匪时中枪身亡,她为他“眼泪汪汪”,并且从此拒奥列宁于千里之外。
从文化记忆角度看,托尔斯泰在《哥萨克》中重构的玛丽雅娜这一光辉的哥萨克女性形象具有极强的观照性。记忆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观点:“文学作品的演示不局限于个体记忆,而是往往也将个体记忆纳入民族文化记忆的框架之中,对个中反映出的包括价值体系、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同一性问题等进行反思和观照。”(冯亚琳,2013:110)因此,可以说,在托尔斯泰看来,正是高加索充满诗意的大自然用其洒脱无羁、淳朴浑厚、崇高宁静保存着淳朴无伪的美,赋予哥萨克人质朴、善良、正直,也成就了玛丽雅娜的高尚与完美。
3.4 公正自由的探索者——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
俄罗斯文学记忆长廊中最为典型的哥萨克形象是肖洛霍夫的史诗性著作《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静静的顿河》以葛利高里个人生活为中心,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和现状,力图表现俄罗斯人对社会公正、自由不倦的探索。在肖洛霍夫笔下,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的代表,他个人及其家族的生活现状和发展历史反映了整个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及其特点。
在肖洛霍夫笔下,葛利高里个性鲜明。他正直、善良,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充满农民本性对土地和家乡强烈的眷念之情。在战场上葛利高里还惦记着地里的农活,即使当了叛军的师长,还想着回家和牛打交道。他热爱自由,敢爱敢恨,他与阿克西妮亚的爱情在世人的眼中是罪孽和乱伦,但葛利高里仍然大胆追求和坚持。葛利高里是个杰出的军人,极具军人的荣誉感。他把参军履行军人职责看得重于一切。当情人阿克西妮亚请求葛利高里带她远走高飞,葛利高里以要参军为由加以拒绝。在战场上,葛利高里是机智勇猛的典型,把哥萨克骁勇善战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政治上,葛利高里摇摆不定,一会儿参加红军,一会儿投入白军,三番两次,反复无常。
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肖洛霍夫重构葛利高里这一典型的哥萨克形象,对其命运的描述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观照和反思。
第一,肖洛霍夫对战争的反感和否定。在《静静的顿河》中,在描绘葛利高里的命运轨迹时,肖洛霍夫毫不掩饰自己对战争的反感,强调战争对和平生活的破坏,对生命的伤害,使人的人性灭绝,兽性泛滥。肖洛霍夫甚至用血淋淋的恐怖场面来强化对战争灭绝人性的谴责:
活着挖出了他的眼睛,砍掉双手,割下耳朵和鼻子,用马刀在他的脸上砍十字。他们解开裤子,往他身上尿尿,污辱、糟蹋他那英俊、壮大的身躯。他们污辱够了这血肉模糊的残肢,一个押送兵用脚踏在还轻轻哆嗦着的胸膛上,踏在仰面躺着的残躯上,斜着一刀,把脑袋砍了下来。(肖洛霍夫,2005:3-140)
独臂的阿廖什卡劈死三个被俘的红军伤兵后不无吹嘘地说:“看,我把三个变成六个啦!”而其他哥萨克则“抽着烟,仔细察看那几具尸体”(肖洛霍夫,2005:3-162)。
第二,对现有价值的怀疑。肖洛霍夫精心刻画了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轨迹,变化中最主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对现存的一切价值的怀疑。国家派他们去死,可是国家把自己的公民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这样的国家值得忠诚吗?“父亲的意志”毁灭了爱,强加了一个不爱的女人给他,使他对哥萨克的习俗和古朴的生活方式也充满了质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葛利高里是普通士兵,结束时已是哥萨克的大尉、乔治勋章获得者、英勇善战的指挥官。他力图弄清自己存在的实质,他常常为“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而牺牲什么”而苦恼。他找不到答案。被他看作是哥萨克的优点的英勇善战在第一次战斗后就被他否定了。当他站在被打死的一个奥地利人旁边,他不能理解也不能给自己解释为了什么样的高尚目的和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上帝赋予人的生命。他的许多战友在前线无谓地牺牲,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最终导致葛利高里加入革命的哥萨克队伍。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红军的有些做法他也无法理解和认同。葛利高里不再企图弄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只遵循自己对公正的理解。
第三,敏感地察觉到哥萨克作为高度自治的军事群体的生存危机,甚至可以说,预见了哥萨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军事群体的历史终结。
在肖洛霍夫笔下,葛利高里在红军和白军中摇摆不定。葛利高里有着哥萨克崇尚自由的天性,深受哥萨克自治思想的影响,反对外人染指哥萨克自由的土地和奴役哥萨克人。因此,他像候鸟一样,一会儿参加红军,一会儿投向白军,反复无常的行为万变不离其宗,除了哥萨克追求自由的天性之外,就是不愿听任他人任意染指哥萨克土地的初衷。然而,最后葛利高里站在白军一边阻止红军占领哥萨克土地的企图破灭了。在诺罗罗斯克,大部分哥萨克部队被打散,葛利高里和很多哥萨克不得不投向红军。但是红军不信任他,葛利高里又悄悄地离开了。小说结尾时葛利高里又回到了家乡,他又重新处在艰难而又不平凡的生活道路的起点。这似乎意味着自由的土地难逃被染指的命运,延续了几百年军民合一的哥萨克部落自治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内战结束之后,苏联政府一方面对哥萨克实行自治政策,另一方面推行非哥萨克化,对哥萨克实行大分化、大移民,不允许哥萨克参加苏联任何兵种。在高压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哥萨克逃亡国外。哥萨克作为军事群体的历史就此结束。这种社会现实不能不影响到肖洛霍夫对《静静的顿河》的构思和立意。
3.5 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反讽——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骑兵群像
如果说,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这些文学大师为俄罗斯文学长廊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哥萨克艺术形象,那么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则为世人记录了哥萨克骑兵群体的鲜活生动的故事。
《骑兵军》是巴别尔在战地日记基础上创作的30多篇小说结集而成的。1920年巴别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率的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亲身经历了空前惨烈的骑兵大会战。苏波战争结束后,巴别尔根据自己的战地日记,陆续创作发表了30多篇短篇小说,长者三五千言,短者只有几百字。既有军旅故事,又有战场速写,后结集成《骑兵军》。在《骑兵军》中,巴别尔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真实地再现哥萨克骑兵鲜为人知的风貌,深刻地展示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在巴别尔笔下,哥萨克骑兵既有革命激情,又有尚武精神,还有反犹太倾向,更有嗜血的野性。通过狂热与冷酷、残忍与悲悯、坚强与软弱浑然一体的原生态描述,巴别尔对战争残酷的感受,对人性善恶的思考跃然而出。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看,巴别尔对哥萨克骑兵形象的描述应该说有着特别的观照和反思。
从记忆重构的当下选择性角度看,巴别尔描述的哥萨克形象对当时革命英雄主义有着意味深长的反讽。尽管巴别尔对哥萨克骑兵的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钦佩不已,也毫不掩饰地记录下他们抢掠杀戮嗜血狂暴的兽性行为。在《小城别列斯捷科奇》中哥萨克士兵平静杀死一个犹太老人,《家书》中父兄血腥相残,《普里绍帕》中普里绍帕疯狂报复,把仇人老婆一个个钉死。一个个凶残恐怖的画面让人毛骨悚然,也将哥萨克的嗜血野性生动展现出来。这种原生态描写与官方的革命英雄主义话语相距甚远。难怪小说一出来,以骑兵第一军军长布琼尼元帅为首的一些红军将领指责巴别尔诽谤污蔑红军骑兵,把他们描绘成真正的马赫诺匪帮,巴别尔也因此遭受被逮捕秘密处死的厄运。
从互文性角度看,巴别尔对哥萨克形象的描绘继承了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传统,但更多了些人性思考和评判。
首先,巴别尔是以一个向往革命的犹太青年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描述哥萨克骑兵的。这种独特的视角使巴别尔更能感受到哥萨克本质的东西。在俄罗斯历史上,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好几次充当大规模屠犹活动的急先锋。巴别尔亲历过犹太人遭受哥萨克驱逐与杀戮的情景,这在巴别尔的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谢春艳,2009:63)。因此,尽管巴别尔受哥萨克原生态的生命激情所吸引,渴望融入扬刀立马、快意恩仇的哥萨克世界,但是犹太情结让巴别尔对哥萨克骨子里的仇犹情绪特别敏感,因而对哥萨克屠犹多了一些他者和异质文化的观察和思考。其次,巴别尔是用悲悯的眼光和情怀来描绘形形色色的哥萨克群像,力图超越战争伦理,从人的角度来叙述革命、战争、人、民族之间的复杂关联。
著名作家王蒙(2005:27)认为,巴别尔能够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炼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让人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
更不寻常的是巴别尔用悲悯的眼光和情怀来看待哥萨克世界,描绘的是阶级斗争旗帜下的人性,他把人性恶展示得越残忍越无情,越能唤起人们的悲悯之心。
俄罗斯文学长廊中有许多以哥萨克为主题的作品,除了上述分析的作品外,普希金、果戈理、列·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都还著有其他以哥萨克为主题的作品。另外19世纪上半叶的乌拉尔哥萨克И.热烈兹诺夫写了两部关于乌拉尔哥萨克的中篇小说《巴什基尔人》和《瓦西里·苏尼亚舍夫》。在19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哥萨克人自己描写哥萨克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库班哥萨克诗人和作家В.С.莫瓦(发表作品时使用笔名利曼斯基、米古茨基等)最为著名,著有《哥萨克骨头》等作品。20世纪的小说作品有:К.Ф.谢德赫的《道乌利亚》、《家乡》、Д.И.彼得罗夫的《哥萨克的传说》、Г.И.米罗什尼琴科的《亚述》、А.В.加里宁的《在南方》、М.А.尼库林的《最高水位》、П.Н.克拉斯诺夫的《从双头鹰到红旗》、В.М.舒克申的《我来给你们自由》,等等。在20世纪末最为著名的恐怕要数Н.沙姆索诺夫创作的史诗性三部曲《顿河荒原》、《哥萨克浪人》和《顿河的春天》。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Вече出版社出版了系列丛书《哥萨克小说》,再版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创作的30多部哥萨克小说,如《阿塔曼·普拉托夫》、《库班的黎明》等。
此外还有不少描写哥萨克的诗歌作品,如莱蒙托夫的《哥萨克摇篮曲》、《哥萨克》、А.图罗维罗夫的《携带着行军褡子的战马》、Н.Н.图罗维罗夫的《诗集》、А.В.索夫罗诺夫的诗歌《熊的耳朵》、《马鞍》、《哥萨克的荣誉》、《山冈那边的哥萨克》等。
4.结语
哥萨克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其形象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中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极具特色的草莽英雄和令人恐怖的刽子手。作为草莽英雄,哥萨克桀骜不驯、崇尚自由、极具反抗精神,并且粗犷豪迈、尚武好斗、英勇善战。作为刽子手,哥萨克冷酷凶残,杀人不眨眼,成为沙俄帝国巩固国防、对外扩张、镇压民众的重要军事力量。哥萨克在屠犹活动中充当急先锋,对犹太人毫不留情地杀戮,在镇压革命中充当沙皇帮凶,双手沾满普通民众的鲜血。
俄罗斯文学长廊中不乏哥萨克形象,而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别尔等文学大师塑造的典型哥萨克形象特别引人注目。其中普希金笔下的普加乔夫是对俄罗斯社会有关哥萨克的集体记忆的颠覆性重构;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是率真的英雄;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丽雅娜则是美的化身;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是公正自由的探索者;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骑兵群像则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反讽。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与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的哥萨克形象相比较,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对哥萨克形象的重构是继承大于批判,而肖洛霍夫、巴别尔等人的重构则是批判大于继承。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梳理和解说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别尔等人塑造的典型哥萨克形象,对于加深人们对俄罗斯文学厚重的历史感的认识不无裨益。
[1]Голубков В.В.Гоголь в школе[M].М.:Изд.Академии педо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1954.
[2]Федотов Г.П.Судьба и грехи России[M].Т.2 СПб.:“София”,1992.
[3]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M]//果戈理精选集.孟十还,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6]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M]//中短篇小说(1857-1663).草婴,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
[7]普希金.大尉的女儿[M].钟锡华,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8]王蒙、王天兵.关于巴别尔的《骑兵军》[J].书屋,2005(3):27-31.
[9]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0]谢春艳.《骑兵军》与巴别尔的双重文化情结[J].俄罗斯文艺,2009(3):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