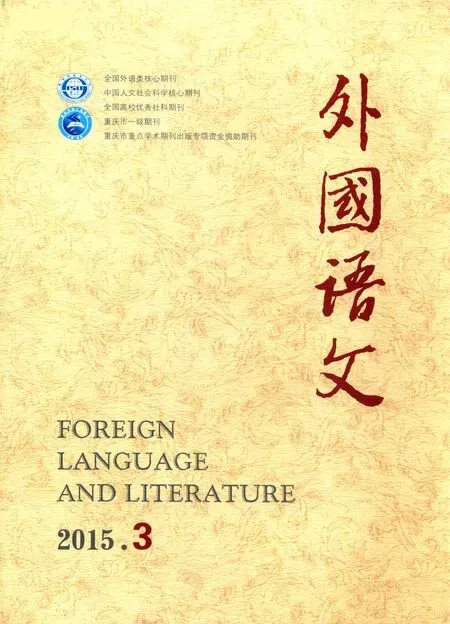《红死病的假面具》的伦理批评
李显文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1.引言
《红死病的假面具》(以下简称《面具》)是爱伦·坡(Allen Poe)的恐怖名篇,其所彰显的“恐怖美”被广泛认可,深度阅读这种“美”会发现其背后的伦理之“真”。就“美”与“真”的关系而言,坡从文类上作过精辟论述:“诗歌在美,小说在真”。坡小说中的“真”是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之“真”算是其一,《面具》可谓典型,它完美有效地整合了恐怖“美”与伦理“真”,这既符合坡的创作观:艺术作品永远得有点儿复杂性和暗示性,即“隐喻”或“寓意”之意(Poe,1994:1542),也符合他对精神世界的划分:精神世界分为理解力、审美力和道德感三部分,审美力居中,它与左右两端都关系密切(Poe,1994:1546)。在研究坡小说的美学时恰当地关注其中的伦理也切合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学的认知,陆建德就认为:“文学里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是相通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政治的最丰富细腻的体现。”(王松林,2007:3)事实上,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坡在小说中追求唯美主义效果时,无不流露出“惩恶扬善的道德痕迹”和“对人性乃至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和忧思”。《面具》无疑就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某种映射,足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许广洁,2008:79)。除了显性的恐怖美外,《面具》中伦理上隐性的“真”值得深入解读:政治主体对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的背离、民众对生存伦理的诉求、伦理中权力“弥散”所致的权力冲突和权力转换。通过“恐怖美”的外在表征,坡隐晦地表明了他所坚持的伦理取向和政治立场,告诉人们:封建统治的灭亡和资本主义民权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政治主体的伦理背离
所谓政治主体,是指在社会政治关系或政治过程中具有主体身份并以其存在或行为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产生作用的政治决策者和政治参与者(施雪华,2001:83)。据此,《面具》中的亲王普洛斯佩罗无疑是政治行为的决策者,骑士、淑女、乐师、诗人、舞女等是政治行为的参与者,这些政治主体有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诉求。然而,任何统治都必须以信用为基础,必须坚持向善的伦理。亲王对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的背离决定了其统治的覆灭。
亲王背离了政治主体的信用伦理。西方社会制度在更迭中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诚实守信、恪守诺言、践履义务的信用伦理一直是传统政治学中不可缺乏的价值要求(熊玲君,2005:157)。尽管在中世纪出现了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无信用伦理,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如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提出社会契约论后,政治信用伦理再次被肯定。坡所在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确立不久的时代,这种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政体自然需要培育和保护。作为作家,无论他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作品既有作者个人特点,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产物,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趋向暗中参与了创作”(王松林,2007:2)。《面具》表面是恐怖,深层也有作者意识形态的取向:对亲王背离政治信用伦理的批判。坡借用公共灾害——“红死病”对政治主体进行了考验。作为一种公共灾害,“红死病”来袭时,普通民众可选择逃避也可选择抵御,但以亲王为代表的政治主体的唯一选择应该是积极率队救治,因为这是政治主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无论这种救助是出自维护其统治还是保护民权。可是亲王“没有站在他的臣民一方”,而是选择了“自我保护”和“逃避”(Santi,2012:99),致使“‘红死病’蹂躏这个国度已有多时”,这是政治主体对公共灾害的不作为。不作为导致了连锁反应:“红死病”肆意蔓延,其域内的民众不复存在,政治主体无统治对象可言,其统治也就自行瓦解。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民众始终是政治主体的根基,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怀。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启发下,政治信用伦理被一再凸显,政治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都必须遵循对责任的信用承诺。现代政治是“个人、集体的合作性和策略性的互动”,“信任的理性问题无可避免”(郑也夫,2003:99)。由此看来,信用是政治形成和发展的道德基础,一个政治主体合法权利的获得,本身就是相互信任的结果,其合法权利的性质和范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信任及幅度。准确说来,被统治者对政治主体的信任及幅度又在于政治主体自身的表现,即对什么作为和对什么不作为及其程度。亲王的作为与不作为都表明他对政治信用伦理的无知与无视。在佛克斯(Folks)看来,亲王所召集的1000名骑士淑女看似一种作为,但它只不过旨在为其自身活命(Folks,2005:11),王的逃跑是责任的放弃。“任何事他都可以逃避,但唯一不能逃避的就是责任。”(Mabbot,1978:668)逃跑是失职,是信用伦理的丧失,反映了政治主体的冷漠无情,惠特(Wheat)认为:“随着城门的关闭,他们也关闭了自己的同情心。”(Wheat,1982:51)亲王的自私既是政治主体信用伦理背离的心理根源也是其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自私遭到了叙述者强力的反讽:“他快活,无畏而精明。”大难当头,他竟“快活”得起来:率领随从在远离“红死病”的城堡里举办了异常豪华的假面舞会,大有末日狂欢之味!他无畏:面对头戴“红死病”假面具的陌生人,他勇敢地扑了上去,可是,他对域内的“红死病”却闻风丧胆;他精明:在防卫“红死病”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无懈可击——坚固的高墙、钢铁铸就的大门、熔死的门闩等,竟连淑女们也可以藐视瘟疫的蔓延。可他终究没有逃脱“红死病”的惩罚:亲王所害怕的事情终于如期而至,而且在它面前不堪一击,这表明政治主体一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甚至成了民众的对立面,其曾经的外强就显得无比的虚弱。从小说看,叙述者似乎给了亲王背离信用伦理改过的机会,但他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对亲王而言,如果说“红死病”曾经只是一个传说,他没有依照信用伦理而实施救治,在偏僻的城堡里自行作乐也就罢了。可如今,“红死病”已悄然蔓延到宫廷的假面舞会上来了,亲王不但没有号召政治的参与者实施救治,反而摆出与“假面具”决斗的架势。他“飞身冲过了六个房间”,拔出短剑刺向“陌生人”,“只听一声惨叫”便倒地而亡。亲王彻底地而且冥顽不化地背离了政治主体的信用伦理,叙述者的反讽语调暗示了其所在的政治立场。
亲王背离了政治主体的向善伦理。人类的政治行为自古以来就内含特有的道德要求,政治伦理是对政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进行评价的根本尺度(高振岗,2008:46)。在构建优良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要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张方华,2009:38)。作为政治主体的亲王,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置身于一个伦理世界之中,审慎地关注自己所采取的每个行动与可预见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并勇于为这种结果担当责任。可是,他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信用伦理,更背离了向善伦理,作者也予以了批判。向善伦理的背离表明亲王的道德想象力不寻求理解他的同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最完善的公正,他的行为失去了道德良知的控制,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从小说叙述和情节来看,亲王的不作为和作为暴露了其丑陋的品格:欺软怕硬。“红死病”是一种恐怖的瘟疫,面对强大的“恶”的势力,亲王不是“无畏”,而是“恐惧”、胆怯、逃跑。但当假面舞会上出现了戴着“红死病”假面具的陌生人时,亲王先是“恐惧”、“厌恶”,接着其“生性粗野豪放”立即彰显。他先是指挥,然后,因胆怯而怒不可遏地追了六个房间,欲置陌生人于死地。因为亲王心里明白:舞会上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红死病”,这位“陌生人”只不过是“他手下的另一位侍从,一位愚蠢的侍从”,其行为太过放肆,竟敢“超越宫廷中大家必须遵守的安全底线”而“僭装为红死病之象征”(Wheat,1982:55),亲王面对弱势的“侍从”表现出罕见的强势。“欺软怕硬”正是政治主体背离向善伦理的体现。一方面,他在公共灾害来袭时逃跑并举办豪华的假面舞会,表明他的自私、冷漠、怯懦和同情心、怜悯心的缺失,即善心的缺乏。民难当头还莺歌燕舞,“他是一个无情的亲王”(Bell,1973:101),勒文(Levine)感叹道:“罗马起火时,贵族们却在胡搞,亲王有过之而无不及。”(Levine,1972:99)荒淫、腐朽即是善的背离。另一方面,他对有忤其心愿的“手下”实施其惯用的戕杀,表明他不仅没有善,甚至凶残至极。亲王的行为表明其一切行动皆以其个人的嗜好为取向,他不仅没有“共同善”的追求,就连基本的善也丧失殆尽,成了典型的暴君。如惠特所发现的那样,叙述者的措辞和语气暗示了对亲王的否定(Wheat,1982:54),这无疑也暗示了叙述者的伦理取向。
3.生存伦理的诉求
政治的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旨在维护人权,其中人身权是人权的基础,这是罗尔斯认为的基本权利中的第一项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这是由最低限度的道德所决定的。米尔恩将尊重人的生命作为共同体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任何人不得被任意杀戮;任何人的生命不得遭受不必要的危险的威胁(米尔恩,1995:155-56)。在个体人身权的外围保护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主体肩负着最主要的责任和义务,放弃则意味着“恶”与“非正义”,其合法性将深受质疑。就自我保护而言,任何个体在不妨碍他人人身权的情况下都有权维护自己生命的存在,这是生存伦理的基本诉求:命重于理,生存第一(修树新,2012:109)。失去外围保护时,个体出自本能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权。
《面具》中的民众遭遇“红死病”时,以亲王为代表的政治主体既背离了信用伦理也背离了向善伦理。当国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得不到保护时,民众自发维护自己的人身权也就理所当然了。故事中民众对生存伦理的诉求正是通过这位陌生人——一位披着裹尸布戴着“红死病”假面具的陌生人在假面舞会上的登门拜访来展现的,这种拜访事实上是对政治主体的不作为的声讨。这位陌生人的身份看似一个谜,他被叫作“新来者”、“陌生人”、“大人物”、“不速之客”等,这些称谓暗示了他与舞会的不协调或是舞会的异化力量。叙述者利用假面舞会巧妙地掩藏了陌生人的身份。舞会上,他的“身影比希律王(Herod)还希律王”。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据《圣经》记载,历史上有四位希律王,但叙述者并没有指明究竟是哪一位希律王。不管哪一位,希律王都算得上是一位难以界说的复杂人物。对大希律王来说,其名字的意思是“英雄世家”,但其曾经为了杀死耶稣而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也曾下令杀死自己的三个儿子。叙述者对这位陌生人的称谓和以希律王作类比,是否就意味着对他的否定呢?第一,从叙述者对陌生人所使用的近指限定词,“这位(this)”和“那个(the)”,暗示了叙述者对他的亲近之感。第二,人群对他的情感由“畏惧、厌恶”转变为“一种莫可名状的敬畏感”,表明叙述者对他的肯定。第三,对陌生人可圈可点的作为的描述暗示了叙述者对他的赞赏和崇拜。说他是陌生人,实质上暗含了叙述者对亲王的强力反讽:亲王远离民众,既不体察民情也不知民众疾苦,对亲王而言,当然就陌生了。亲王自以为不可一世,可是在与陌生人交手时不堪一击。陌生人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在人群中,他高视阔步如入无人之境、迈着庄重而平稳的脚步,一一走过舞会的各个房间,他无须出手,亲王便倒地而亡。当狂欢者们鼓起玩命的勇气冲上去抓住他时,发现“他们死死抓住的那块裹尸布和僵尸般的面具中没有任何有形的实体”。第四,陌生人成了民众求生或正义死神的化身——生存伦理诉求的点化。小说隐喻得最深的就是结尾处的“这个没有任何有形的实体”。破解这个“无形实体”的关键在于小说中被作者特意添加的那块裹尸布,这一特殊的文体现象必然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对文本中独特的文体进行细查是解读作品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手段。因为“文体研究应该知事论文,洞察文体表征背后的时代性、文化性等影响因素”(刘立辉,2013:115)。研究坡小说的文体同样必须考察意象背后的时代性和文化性。裹尸布是坡偏爱的意象,在诸如《丽姬娅》、《厄舍府的倒塌》、《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等作品中屡见不鲜,具有增强恐怖效果、暗示人物身份、揭示主题等作用。坡无疑深谙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世界里,裹尸布是一件圣物,这既可从《圣经》里见到诸多描写,也可从后来的文献记载和博物馆的收藏得到明证。“裹尸布”可以说是耶稣的象征——一个神性的符号。《面具》里的这块裹尸布既增强了恐怖效果、满足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暗示了人物身份——因“红死病”而死的民众的“冤魂”或为讨回公道而来的死神。裹尸布的添加使“无形实体”得到了合理解释:魂魄或死神自然“无形”。被恐怖化了的陌生人实则是复仇者或者说公道的讨回者:“死神完胜——一场对贵族身体和心灵的完胜”(Wheat,1982:56)。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位陌生人的塑造——民权的化身,凸显了民众对人权的基本诉求,生命第一的生存伦理就这样从反面被揭示出来。
4.伦理冲突的权力转换
在理想状态下,政治伦理与生存伦理在本质上可以和谐地统一起来。《面具》中的亲王身份表明了该社会的封建性(Vora and Ramanan,2002:1521),这样的社会里,政治伦理与生存伦理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实质是尖锐的阶级对立,最终获胜的是对生存伦理提出诉求的一方。坡支持生存伦理的民权诉求并不奇怪,一方面他在欧洲游历多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权思想无疑浸润了他的思维;另一方面,坡所在的美国1644年就由宗教激进人士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提出了民权主张,比洛克早46年。1776年,弗吉尼亚殖民地通过的《权利法案》更是美国民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坡时代的美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久的美国,坡用文学的方式来铲除封建社会对民权的剥夺顺理成章,这是“文本的历史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文本的历史性”强调文学不只是历史或权力政治的产物,更重要的在于它也参与意识形态的塑造,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颠覆性。
坡的小说绝不缺乏颠覆性,《面具》便是典型。小说看似由“红死病”引起的恐怖,然而,恐怖与权力在本质上紧密相关。对此,佛克斯在研究《面具》时作过深刻论述:人类普遍存在一种排外和死亡的恐惧,应对措施便是攫取权力,然而,对权力的抢夺常常导致控制与死亡的永恒循环。那些通过获得权力而获生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常常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来确保自己生存的专制者。坡认识到,只有清醒地理解到权力的“本能性”本质,人们的愿望——打破循环的恐惧与压抑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Folks,2005:14)。《面具》的意识形态不言而喻,其中的权力意识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即福柯(Foucault)所说的权力的“弥散”特质:权力不是简单的奴役关系,而是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既表现在宏观层面的政治舞台上,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Foucault,1990:94)。维塞尔(Veeser)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权力是多样的,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操纵着所有的参与者。普罗大众看似无权无势,却并非任由统治阶级摆布的群氓,相反,它孕育着巨大的颠覆性力量(Veeser,1989:43)。假面舞会象征着权力关系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延伸。舞会上,亲王处于权力的绝对高度,他下令对陌生人的捉拿表明了他的话语权;对舞厅的设计、舞会氛围的营造、甚至对“不可逃避的死亡的假装冷漠”和置身于“血色窗格的棺材式房间”以及“报丧的黑钟”的人造性都表明他试图拥有对环境的绝对控制力(Wheat,1982:53)。《面具》里高墙内以亲王为首的政治主体与高墙外饱受“红死病”蹂躏的普通民众分属两大阶级阵营,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权力对抗,亲王及其随从与面具的决斗体现的是阶级间的对抗。小说中的一个独特意象——黑钟,每到关键时刻总是如期敲响,成了“死亡和敌人的提醒者”。对抗的结果是“镇压”与“颠覆”的最终逆转。
《面具》对权力角力和权力转换采用的是曲笔。小说没有通过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事件来展示政治斗争的残忍性和复杂性,而是假借了“红死病”这样一件公共卫生灾害来拷问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红死病”来袭时亲王所举办的假面舞会具有隐喻意义,它是一个多种政治力量交汇、角力的场所。反观政治,它无非也是假面舞会,政治人物就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人,他们合谋把舞会开完,当舞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异己力量,他们群起攻之。根据小说叙述,只有普通民众才会感染“红死病”这种瘟疫,因为亲王等权贵们早已逃之夭夭并做好了一切防卫措施。舞会上戴着“红死病”的假面具的陌生人具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抢了亲王的风头。首先他超越了亲王那“大胆热烈”的构思,即他超越了亲王的想象能力,招来嫉恨必不可免。佛克斯发现:“亲王的本能反应就是他的疯狂遭遇了陌生人的挑战,因为其化妆嘲笑了所有在场人都必须遵守的秘密。”(Folks,2005:12)这个秘密就是亲王自认为不可一世,其他人都不得僭越。皮彻(Pitcher)评论道:“亲王以自我为中心……傲慢、冷漠、疯狂地高高在上和专制。”(Pitcher,1976:72)其次,他转移了侍从对亲王的注意力。亲王举办舞会的目的在于满足他的虚荣心,在于赢得骄赞和敬畏,因为与之接触交谈过的侍从们明白,亲王确实没疯,而是他的“思想闪耀着野蛮的光辉”。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整个舞会的轩然大波,侍从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抢风头的实质是抢影响力,自然会招来亲王的扑灭。这印证了维塞尔所发现的权力特征:“权力体现的是各种社会势力对影响力的争夺,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源头。”(Veeser,1989:43)权力被“弥散”到了影响力上,即凡是存在影响力的落差,就存在权力的争斗。由此看来,权力的“弥散”实质上是权力的泛化,它从狭义的政治权力泛化到影响力,从而表现为权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第二,陌生人具有异己性,意味着他至少与民权势力有关或本身就是民权势力,是亲王严重的异己力量,难怪亲王表现出厌恶、恐惧直至恼羞成怒,拼了命也要铲除,因为他严重地威胁到亲王的威望和安全。不过,亲王的举动,尤其是只有“与他接触了的追随者们才觉得他的确没有疯”反面暗示了亲王在民众眼中就是个疯子,因为民众无法与之接触,在民众看来,亲王就是异己力量。如此一来,亲王与陌生人互为异己,他们之间的矛盾势必零和。
政治主体对颠覆力量常采取一种特殊手段——“抑制”。“抑制”与“颠覆”始终是权力场一对相生相克的孪生兄弟。统治者通过适当地刺激大众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颠覆,在不危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利益和不改变统治关系的基础上,使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从而达到对颠覆进行“抑制”的目的(马广利,2007:14)。然而,亲王对“颠覆”的“抑制”近乎歇斯底里,“简单而粗暴”(Wheat,1982:54),过头的“抑制”必然招来过头的“颠覆”。《面具》的叙述者给了亲王缓冲的机会,但亲王要彻底铲除陌生人:他“高举一柄出鞘短剑,心急火燎地追到了那退却的身影只有1米左右的地方,这时已走到黑色房间门口的那个身影猛然转过身来面对追上的亲王”。言下之意,陌生人在亲王穷追猛打、毫无退路的情况下被迫奋力反击,“只听一声惨叫,亲王的尸体也面朝下倒在了上边”。亲王的过度“抑制”与陌生人强大的“颠覆”较量的结果显而易见。由此看来,英明的统治是“颠覆”与“抑制”适度平衡的统治,决不能过度“抑制”,否则“颠覆”力量的激增会导致“抑制”失效。可是,亲王不懂得“含纳”,超越了“抑制”与“颠覆”之间的平衡度,导致了自己的覆灭,权力相应地出现了转换。
此外,权力是“匿名”的,因为权力的对象处在边沁(Bentham)所说的“全景监狱”里,表现为无处不在而且常常无形:看不见也摸不着。小说对此诠释得最为可信的就是结尾处“那块裹尸布和僵尸般的面具中没有任何有形的实体”。从亲王和其随从的死来看,他们并非死于刀光剑影的物质武器,而是被“吓死”了的。这与坡一贯强调的“心灵恐怖”相通,不过坡似乎更有远见,他预示了一百多年后福柯的一大发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道破天机:“惩罚应打击灵魂而非肉体。”(福柯,1999:17)这是出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即资产阶级要的是在思想上与其一致、身体健全的劳工以便为其生产服务。因而,作为民权象征的陌生人对亲王及随从的惩罚与亲王对他的追杀在方式上完全不同。亲王使用的是利剑——一种物质武器,其结果是身体上的摧残。福柯总结道:“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却用民众的思想束缚他们。”(福柯,1999:113)《面具》犹如福柯对惩罚史的揭露,即从君主权力走向生命权力,然而,资产阶级对生命权力的保护,尽管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其用心却是险恶的,因而,其前途必然是黑暗的,坡对此表现出了深度忧虑。《面具》如此结尾:“三角支架上的火盆全都熄灭。黑暗、腐朽和红死病开始了对一切漫漫无期的统治。”此处的隐喻意义十分明显。“三角支架”可理解为基督教的“三圣”,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产物,其所发之光消失了,即封建社会被推翻了,然而,人们迎来的民权社会并不那么光明、理想,而是黑暗、腐朽和恐怖。光明、理想的社会坡无法看见,因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还没来得及流传到美国,1849年他就告别了凄苦的人生。
5.结语
《面具》表明:坡在创作恐怖小说时不只是“为恐怖而恐怖”,恐怖美学的表征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社会的思考,其伦理意义不言而喻,难怪斯里克(Slick)感叹道:浪漫主义时代的艺术家们在教会我们如何应对诸多疾病时要比同时代的道德家们还要多(Slick,1989:26)。《面具》内外双重身份的叙述者不仅在对死亡提出警告,更重要的是带给读者们某种政治伦理启示。政治主体既要坚持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更要顾全民众的生存伦理。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发生伦理冲突,“抑制”与“颠覆”一旦失去平衡,权力关系势必逆转。
[1]Bell,H.Jr.‘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An Interpretation[J].South Atlantic Bulletin,1973,(38):34-46.
[2]Folks,Jeffrey J.Edgar Allan Poe and Elias Canetti:Illuminating the Sources of Terror[J].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2005,(37)2:1-16.
[3]Foucault,Miche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Vol.I,trans.,Hurley,R.New York:Vintage Books,1990.
[4]Levine,Stuart.Edgar Poe:Seer and Craftsman[M].Deland,Fla.:Everet/Edwards,1972.
[5]Mabbot,Thomas Ollive.Intro.to‘Masque of the Red Death’[M]//Collected Works of Edgar Allen Poe,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6] Pitcher,Edward Taylor.Horological and Chronological Time in‘Masque of the Red death’[J].American Transcendental Quarterly,1976,(29).
[7]Poe,Allen.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M]//Nina Baym,etc.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Company,1994:1542.
[8]Poe,Allen.The Poetic Principle[G]//Nina Baym,etc.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Company,1994:1546.
[9]Santi,Lauren Lynn Delli.Prince Prospero:The Antithesis of‘The Beautiful Death’[J].ANQ: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Notes,and Reviews,2012,(25)2:98-102.
[10]Slick,Richard D.Poe’s 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J].Explicator,1989,(47)2:24-29.
[11]Veeser,H.Aram.The New Historicism[M].New York:Routledge,1989.
[12]Vora,Setu K.& Sundaram V.Ramanan.Ebola-Poe:A Modern-day Parallel of the Red Death?[J].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02,(12)8:21-23.
[13]Wheat,Patricia H.The Mask of Indifference in‘Masque of the Red Death’[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82,(19)1:51-56.
[14]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5]高振岗.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方式[J].求索,2008(9):46-48.
[16]刘立辉.巴罗克文化与17世纪英国诗歌的文体生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8-116.
[17]马广利.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下的《李尔王》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7(5):14-18.
[18]A.J.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9]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20]王松林.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陆建德研究员谈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7(2):1-9.
[21]熊玲君.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57-161.
[22]修树新.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生存伦理[J].外国文学研究,2012(2):108-114.
[23]许广洁.红死魔的面具解读[G]//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4]张方华.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J].伦理学研究,2009(5):38-42.
[25]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