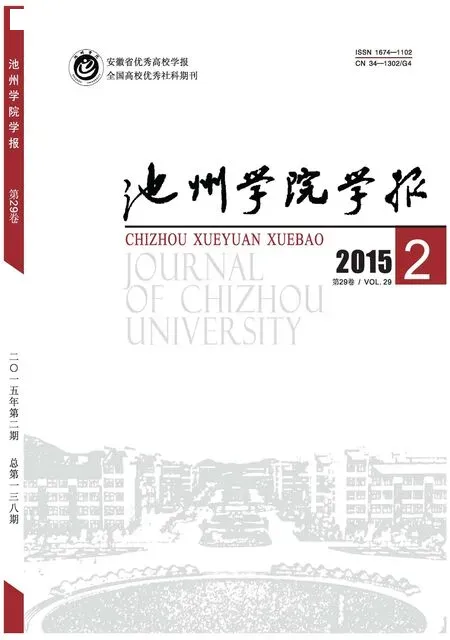论中国文人画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程多耀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合肥230000)
文人画是一种在我国宋代开始兴起,元代形成高潮,一直到明清时代都占据主导地位的绘画类型,其基本特征是以水墨写意为主流,讲求诗书画的统一,注重笔墨趣味,不求形似,注重抒情性和意向性,笔致超逸,气韵生动,意蕴丰富,格调高雅。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绘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画派和画风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为什么会在宋元时期兴起?深入地研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艺术史和中国艺术精神,探寻绘画艺术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在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艺术现象的兴亡存续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文人画的兴起也是如此,它之所以会在我国宋元时期勃然兴起,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1 文人画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社会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原因导致了文人画在宋元时期的兴起。
1.1 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社会动荡不安
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既存在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又有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并且交织在一起。北宋建立以后,通过征战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此后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苛捐杂税,奖励耕植,从而经历了一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但至北宋中期,政治积弊又开始日益显露,赋税加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激烈,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加上民族矛盾此时也十分尖锐,外患日益加重,辽兵频频入侵,战争不断,终于至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攻破汴京,并掳走徽、钦二帝,北宋宣告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偏安一隅,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建立以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加上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促使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但由于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南宋政权在偏安150余年之后又被元兵覆灭,代之以元朝。元朝建立之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复杂,政治腐败,统治者穷奢极欲,土地兼并严重,赋税沉重不堪,由此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于在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由此可见,从北宋中期开始,至元代,整个这一时期都是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这必然要对当时的社会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种动荡不安和背负屈辱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上的知识群体普遍产生了一种厌倦政治和世俗生活,寻求逃避现实的心理和情绪。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性敏感的文人雅士和画家来说,这种逃避的心理更重,他们哀民生之艰难,愤民族之压迫,忧愤交加,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栖息之地,而以山水花鸟为题材,以写意为表现手法的文人画,正是他们此时遣情抒怀的最好手段,是他们达到乐以忘忧的最好的心灵栖息地,于是,社会上的许多文人雅士纷纷拿起画笔,投入这种类型的绘画之中,这就推动了这一时期文人画的兴起。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社会的动荡不安,可以说是我国宋元时期文人画兴起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
1.2 新的社会阶层士人集团的形成
在中国绘画史上,作为绘画主体的画家的身份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在晋代以前,社会上以绘画为职业的是被认为身份卑微的画匠,其绘画题材大都是与神话和宗教有关。进入魏晋和隋唐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绘画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仅职业画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一些达官贵人也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参与到绘画之中。至宋元时期,这种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参与绘画艺术的新的群体,即士人集团。所谓士人集团,是指社会上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群体,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时代,他们都有做官的机会,而面对这种机会产生了两种态度,因此就形成了两类人。一是士人,他们虽然进入了“龙门”,身居官职,拥有王公贵族或者官员的高贵身份,但在内心深处又保留着隐逸情怀,厌倦政治,喜爱书画,以书画来自娱自乐,遣情抒怀;二是隐士,他们干脆隐居不仕,不愿做官,完全逃离现实政治和世俗生活,息影山林,浪迹江湖,以书画来抒发闲情逸志。这两类人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喜欢绘画艺术,但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不愿以书画来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作为寻求自己精神独立和自由的手段,因而前者也被称之为“朝隐”,即在朝的隐士。这种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创作的士人在宋代以前和宋代初期虽然已经出现,但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在绘画风格上与那些画工差别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因而影响不大。到了北宋中、后期,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这个群体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一个对于绘画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以至占据了绘画艺术主导地位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人数众多,(如仅北宋时期的《宣和画谱》中就载有一大批这种具有文人贵戚和士大夫身份的画家,其中包括“文臣”画家、“武臣”画家、“宗室”画家以及“内臣”画家等名目[1]),更重要的是在绘画观念上有着共同的审美趋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都主张绘画不应追求形似,而应追求神似,喜欢萧散简淡的水墨表现,主张依性之所至,意气所到作画,以达到“得意忘形”,“象外传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优秀的画家,否则只能算是工匠。如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迹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2]。在这个士人集团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声名卓著的领军人物,包括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他们带领士人集团改变了画坛的风格,推动了文人画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画兴起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根源。
2 文人画兴起的文化根源
除了上述社会历史根源以外,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导致宋元时期文人画兴起的还有一系列文化艺术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2.1 绘画题材上人物画向山水画的转变
中国绘画包括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等多个类别。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人物画占据主导地位。如唐代就认为:“凡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楼殿屋木次之”[3]。这种格局是由绘画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宋代以前的绘画主体主要是一些画匠和宫廷画家,他们大多是奉命作画,绘画的目的主要是为皇家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或是对社会进行教化,这样就必然要以人物和人事作为绘画的对象。到了宋元时期,绘画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集团作为一个新的主体加入了绘画,而且逐渐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如上所述,这些画家原本就是将绘画作为一种个人自娱和遣情抒怀的手段,不愿将之当作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加上处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他们对于现实政治和世俗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厌倦和逃避情绪,不愿再以人物和人事作为绘画的对象,只是钟情于山水,借助山水来远离俗世,疏于人事,以达到自娱和遣情寄怀的目的,这就导致山水画逐渐代替人物画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3]。明代批评家在论画时更加明确地指出:“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4]。山水画取代人物画占据第一的位置是绘画艺术的重要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以山水画为主要题材的文人画的兴起。
2.2 绘画手法上写实向写意的转变
宋代以前,包括宋代初期的山水画基本上都是写实风格,画家刻意追求的是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山水原来的形貌,而很少有画家的主观意识贯穿其中,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宋代以前,社会文化相对紧张封闭,画家的主观意识被禁锢压抑,难以表达抒发出来,表现在绘画中,只能是刻意求工,以还原山水原貌为能事。到了宋元时期,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曾有学者指出:“两宋的文化艺术生态是在既十分动乱、又相对松弛,既十分压抑、又相对兴盛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而这种矛盾的时代氛围,反而为两宋的艺术家群体提供了一个广泛的驰骋领域,使他们的艺术感觉相当敏锐而独特,使他们的审美感悟相当细腻而高迈,使他们的创作感受相当睿智而雅致”[5]。这种时代艺术氛围为画家主观意识的苏醒和勃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画家们开始摒弃以前完全写实的手法,将形似放在次要地位,遗貌求神,以简洁为上,如北宋书画家苏轼就曾直接指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1]。这一时期的画家们由追求神似转而重视绘画创作中主观意识的抒发,把自然景物当作抒发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有意识地将个人情感与山水景物融合成一体,构成统一的审美对象,使山水景物具有人格化、理念化的体现,折射出人的意识与社会生态,这就导致了绘画风格由写实向写意的转变。如南宋画家马远和夏圭常以“残山剩水”为题材来表现山河破碎的时代忧患,故号称“马一角”和“夏半边”。元代画家黄公望主张师造化,见到好山好水便随时模记,但又不是以刻划真山真水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终点,而是借山川之形,通过笔墨以抒情。他的画作《九峰雪霁图》笔墨简练,意蕴深邃,一派静谧朴茂而高洁清寒之气,充分表现出画家当时处于异族统治下的复杂心绪。元代画家倪瓒以画竹著称,他曾说自己画竹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1]。总之,写意代替写实成为北宋中、后期以至元代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这无疑对于该时期文人画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从我国宋元时期的社会文化史中可以看出,导致这一时期文人画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以及形成了士人集团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其文化根源是在绘画艺术领域出现了人物画向山水画的转变,以及写实手法向写意手法的转变。这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终于导致文人画在这一时期以崭新的风貌登上了中国绘画艺术舞台,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邓白,注.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49.
[3]高建平原.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M].张冰中,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4]文震亨.长物志[M]//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73.
[5]王琪森.中国艺术通史[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