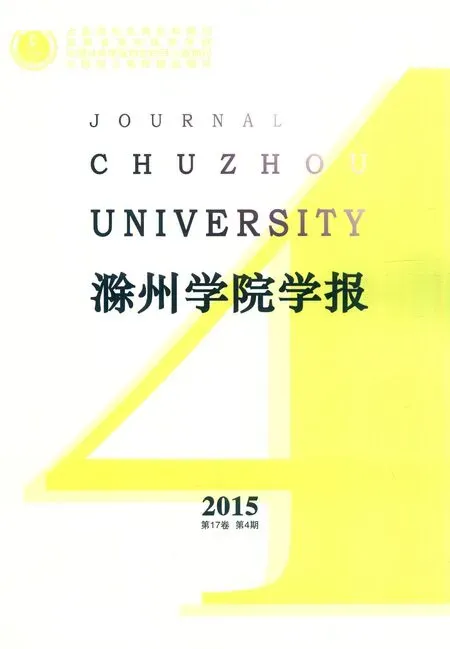论王夫之婚姻伦理思想
仇苏家,郑根成
论王夫之婚姻伦理思想
仇苏家,郑根成
婚姻伦理是个人生活的基础,是规范人伦关系的根本。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阐发了对婚姻伦理的理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他据此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婚姻伦理的基本内容:“族类必辨”的民族性要求;“才质必堪”的相称性要求;“年齿必当”的婚龄要求。他的婚姻伦理思想对现代人的婚恋观、择偶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夫之;婚姻伦理;族类必辨;才质必堪;年齿必当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幸福,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婚姻会有不同的看法,婚姻伦理的要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婚恋观和择偶观受到强烈地冲击,婚姻形式也出现了变化,试婚、闪婚、婚外情等现象日益增多,婚姻伦理观念因此日益淡薄乃至陷入混乱。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婚姻伦理思想对当代人的婚恋观和择偶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婚姻,人道之大者”
婚姻伦理是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婚姻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婚姻首先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承担着延续家族血脉的社会功能,因此受到古人的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婚姻是人伦关系的起点,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中国文化传统认为:“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礼记·昏义》)婚姻的重要伦理价值在西方传统中也倍受重视,婚姻在某些思想家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关系。黑格尔明确指出了婚姻伦理的实质:“婚姻是以性爱为基础,排斥其他因素,它既不是一种纯粹性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婚姻的实质是一种伦理关系。”[1]因此,不难看出,婚姻伦理是个人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展开的重要结构性环节。
王夫之的婚姻伦理思想继承了传统文化关于婚姻的基本观点,强调婚姻是人伦关系的根本:“婚姻,人道之大者也”。[2]读通鉴论·卷16:605这也就是说,婚姻在人伦关系的构建中居于基础地位。伦理秩序的建立以婚姻为前提,因为伦理秩序的原型在家庭中得以确立,而家庭产生的前提就是婚姻。婚姻伦理直接影响家庭的产生及其维系,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婚姻伦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怎样的两性结合是适宜的,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对于婚姻当事人而言,这个问题就演变成择偶问题,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家庭联姻,选择什么样的个人作为结婚对象,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事。婚姻伦理作为历史范畴,产生并发展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特定的内涵和要求。王夫之正是针对婚姻伦理这个核心问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婚姻伦理的基本要求:“族类必辨,年齿必当,才质必堪。”[2]读通鉴论·卷16:605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王夫之婚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族类必辨——婚姻完善之民族性要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整个文明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作为家庭关系核心的男女两性关系上得到反映。他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3]他的这一论断表明规范两性的伦理,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主要内容。“在自然的状态下,男女之交往往呈现无序性,体现文明形式的婚姻,使男女之间的交往由自然形态下的乱而无别走向了社会之序,日常生活本身也由此从一个方面超越自然而获得了人化(文明)的意义。”[4]212不难看出,作为男女结合的必要形式,婚姻会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
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受其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制约和塑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它们反映了各民族对其生存发展客观环境的适应性,因此不同民族的婚姻伦理也会呈现或多或少的差异。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异族通婚的情形,如汉高祖刘邦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匈奴首领单于,又如历史上流传的昭君出塞,便是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故事。唐朝极力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为吐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流传千古的一段佳话。在这段时期,异族通婚成了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民族间矛盾激化,和亲政策遭到极力反对,族际间通婚不再被允许。
王夫之也反对异族间通婚,但其理由并非是民族矛盾,而是民族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化差异,专以文化的视角来谈论民族,认为与华夏的根本区别并非在于种族(人种)的差异,而是在于文化的不同。而在王夫之看来,文化就是礼,他把礼看成是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准。王夫之指出:“中国之与夷狄,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也;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2]读通鉴论·卷14:502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民族生活环境不同,从而各地的风俗习惯也相异,有着各自的特点。既然华夏与夷狄存在着差别,那么异族间理所当然就不应该通婚。王夫之强调,如果异族通婚,就会导致“风俗以蛊,婚姻以乱,服食以淫。”[2]读通鉴论·卷6:248族性会因此陷入混乱,自己民族的特性逐步丧失,故而“古之圣王忧之切,故正其氏族,别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风俗,维持之使若其性。”[2]读通鉴论·卷7:272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生成和变化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因此,必须认识到那些民族差异也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形成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民族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同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而演变,表现出暂时性。承认民族之间存在差别无可置疑。[5]尽管王夫之反对异族通婚的理论基础是民族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出于异族对汉族威胁的考虑。他强调说:“夷狄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2]读通鉴论·卷2:90在王夫之看来,夷狄愚蠢而彪悍,未经教化,不知礼义,会威胁到汉人的文化和生存。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倾向性,同时也难免民族歧视的嫌疑。
不难看出,王夫之“族类必辨”的观点显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现如今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已经成为平常之事,我们不应该对此持有偏见。尽管如此,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各个民族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性,这对不同民族男女双方的交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王夫之对于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强调对于现代社会异族通婚特别是跨国婚姻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婚姻当事人应该重视、协调或避免这种差异性。
三、才质必堪——婚姻完善之相称性要求
为何男和女总是在相互找寻并试图结合在一起?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给出了解释:很久以前,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宙斯害怕他们向神造反,就将他们剖成两半。剖开的两半都非常痛苦,每一半都迫切地扑向另一半,拼命拥抱在一起,渴望重新合为一体。[6]因此,男和女都竭力找回自己相配的另一半,以求完善自身。
个人找寻另一半,不仅是为了获得情感上的完整性,更是为了获得人格上的完整性。情感上的完整性由爱来补充,因为爱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永恒的情感。人格上的完整性便需要我们通过另一半的道德品质来完善。因此,王夫之认为考察嫁娶的对象,必须以个人的品德为标准,“才质必堪”正是不断追求完善的体现。究竟什么是才?王夫之说:“耳聪、目明、言从、动善、心睿,所谓才也。”[2]读四书大全说·卷5:717这里的才就是指人的能力,特别是道德能力。什么是质?王夫之说:“乃其为质也,均为人之质也,则既异乎草木之质、犬羊之质矣。”[2]读四书大全说·卷7:860这里的质可以理解为人的素质特别是道德品质等。因此,才质必堪,就是婚姻当事人双方必须要在“才”和“质”两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从而相互匹配。
为什么“才”和“质”这两个方面如此重要?王夫之认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王夫之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兽所无也。”[2]读四书大全说·卷10:1072王夫之指出善恶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其才。能尽其才,情得其善而性得其理;不能尽其才,则情荡而行恶。在这里,他也充分肯定道德能力对于调控人的情感、指导人的行为的重要意义。[7]为了说明“质”这个概念,王夫之打了个打比方:“以物喻之,质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笛子的材料有好有坏,“如虽不得良笛,而吹之善,则抑可中律……故偶值乎其所不善,则虽以良质而不能有其善也。”[2]读四书大全说·卷7:858不难看出,“质”或者说道德品质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有如笛身、笛孔之于笛本身。这里借助笛子的比喻来进行解释,意在说明道德品质是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的。
具体说来,“才质必堪”包括具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婚姻当事人的道德能力和内在品性到达一定标准。“天与人以气,必无无理之气。阳则健,阴则顺也。一阴一阳则道也,错综则变化也。天无无理之气,而人以其才质之善,异于禽兽之但能承其知觉运动之气,尤异于草木之但能承其生长收藏之气。是以即在梏亡之余,能梏亡其已有之良心,而不能梏亡其方受之理气也。”[2]读四书大全说·卷10:1076人的道德能力、道德品性主要取决于才质的发挥。既然人性是善的,人发挥其才质之善不就可以了吗?为何还需要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这就涉及到“才质必堪”的第二层含义:婚姻当事人的道德教育背景(包括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等)要接近。因为人在不同的道德教育中,受不同环境的熏染,会渐渐形成不同的价值观。
古代的婚姻一般非常重视“门当户对”,这既包括双方财力相当,同时要求双方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道德能力也较接近。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实例也可以证明,当婚姻双方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道德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时,即使生活在一起也很难和谐。悬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差异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得到弥补,但“才质”方面的差异通常无法弥合。王夫之“才质必堪”观点的最大借鉴意义也在于此。
四、年齿必当——婚姻完善之婚龄要求
俗话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究竟男子多大当娶,女子何时当嫁?这就涉及到婚龄的规定。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岂不晚哉?”孔子回答:“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这里可以看出,古人认为,男子二十左右,女子十五左右,就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中国各个朝代礼法婚龄,男子是15到20岁之间,以16岁居多;女子是13到17岁之间,以14岁居多。从现代观点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早婚观念。
中国古代都提倡早婚,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政治需要。有的是因为统治者扩充军备,为求人多势众,鼓励生育;有的是为强兵富国而推行早婚制。第二,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生产方法落后,耕种、收割皆以人口多为好。第三,宗族斗争影响。历代宗族斗争中,往往是人口少,壮男少的宗族吃亏,因此为了发展宗族势力,必须提倡和贯彻早婚。[8]此外,结婚较晚在古代通常都是一些不利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也可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家庭困苦,经济状况差。第二,社会的不稳定。如春秋战国连年的战乱,青壮年从军入伍。第三,品貌不端。如女子相貌丑陋,便会延误迎娶时间,又如男子人品不好,也无人愿意下嫁。因此,选择晚婚常常会导致当事人和家庭背负一定的舆论压力,古人通常会选择早婚。
王夫之的“年齿必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男女结婚年龄要适当;二是指夫妻年龄要相当,即婚龄差适合。男女的结婚的年龄,从生理的角度看,过早的结婚对身体是不利的。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禁早婚议》,强烈抨击了国人的早婚习俗。他在文中指出了早婚的种种危害:一害于养生;二害于传种;三害于养蒙;四害于修学;五害于国计。从优生学的角度看,梁启超的观点不无道理。适婚的年龄究竟该如何界定?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早有说明:女子最合适的结婚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男子的适当婚龄则介于25岁到55岁之间。[9]柏拉图所界定的婚龄区间显得过于宽泛,因而缺乏明确的指导意义。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有发言权。在综合分析世界各国的法定婚龄后,学者徐宝山认为,“结婚适当的年龄,须在男女双方心身俱达于成熟期,判断力和品性已经十分发达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男女青春期以后四五年或七八年为最适宜。……过早和过迟,都是有损而无益的。”[10]按照这种观点,结合相关科学知识,可以推算出男子的适当婚龄介于23岁到27岁之间,女子的适当婚龄介于20岁到24之间。这个结论似乎对现代社会的男女更具参考价值。婚配要考虑很多因素,其中年龄差距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男女的婚龄差多少合适,中国古代并无定论,现代社会也观点不一。在王夫之看来,男女婚龄差距显然不宜过大,“年齿必当”正是强调这一点。
男女结婚为什么要“年齿必当”?首先,我们可以从王夫之的人性思想中获得部分解答。在王夫之看来,人在初生时,“人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犬之性”,[2]周易外传·卷5:1006此时人性与动物之性并无太大差别,而人性是后天生成的,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生日成,故有“性日生日成之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2]尚书引义·卷3:299随着人的成长,人性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因此,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性才能够相对成熟,男女才能具备必要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能在处理婚事时做出正确判断,才能在婚后承担对家庭、子女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也唯有如此,男女才能够结婚。其次,年龄要求意味着时间的考量。就社会层面而言,时间的意义首先在于历史的生成,这也就是社会过程的历史展开。就个人层面来说,时间的意义则通过实际的生活过程得以呈现。时间意义本质上是前后相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以人类生活的连续性为其现实内容;这种生活连续性既使得个人能够实现自我认同,理解自己的统一性,也使得他人能够他人把握这种统一性。[4]242因此,王夫之强调结婚的年龄要求,实际上也是强调男女双方在自我认同、把握自身统一性的基础上实现彼此认同、相互结合。
传统社会中,无论恋爱择偶还是夫妻关系,男性都主导女性,女性成为男权的附庸,处于被支配地位。现代婚姻关系中,男女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婚姻主体的婚恋观出现了根本变化,婚姻的重要性被淡化;婚姻主体对家庭的责任感因此弱化,权利意识则被强化;利己主义观念在婚姻主体中盛行,婚姻有时甚至被视为一种利益交换;婚姻生活中出现了普遍的非道德主义倾向,等等。王夫之婚姻伦理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仔细审视和研究这一思想,既能够为婚姻主体提供指导,实现美好的婚姻生活,也能够为建构合乎人性、体现时代要求的婚姻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77.
[2] 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9.
[4] 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 彭传华.王船山民族差别论及其种族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片论[J].学理论,2010(21):.
[6] 柏拉图.理想国[M].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8-49.
[7] 蔡志良,蔡应妹.道德能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3.
[8] 吴诗池,等.中国性别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1:14.
[9]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97.
[10] 吕文浩.中国近代婚龄话语的分析:从清末至1930年代[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9.
责任编辑:刘海涛
仇苏家,浙江财经大学伦理研究所硕士生;郑根成,浙江财经大学伦理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传媒伦理研究(杭州 310018)。
2015-03-21
B82-09
A
1673-1794(2015)04-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