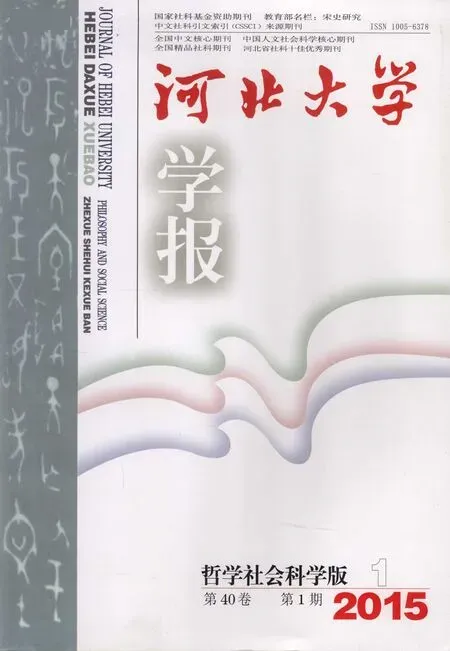何以不“团圆”
——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薛熹祯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何以不“团圆”
——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薛熹祯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 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鲁迅;张恨水;雅俗文学;大团圆;悲剧艺术
在中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往往是相同的结局,通常以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收场。因此,很难脱离“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并且在结构上注重叙事的完整性,故事必须要有头有尾。陈陈相因、僵化的团圆模式作为继承封建文化的消极文学形式,被提倡自由民主、抗争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看作是旧小说的典型特征,他们对此有许多批判,如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的文学,胡适称之为“说谎的文学”。鲁迅还把文学的这种封闭、凝固、粗糙的“团圆”模式上升到国民的“劣根性”,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明确地表示:“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1]从这一点上看,“‘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旧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许多旧小说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不但毫无新意,面目可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2]。张恨水也打破了这个僵硬的模式,强烈要求摆脱历史的枷锁,他在小说创作中极力改掉千篇一律的小说形式。他在《长篇与短篇》中说:“长篇小说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3]对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是中国现代作家反思传统文学、批判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 鲁迅:鲁迅式“大团圆”和“走”与“死”的悲剧人生
鲁迅抛弃了传统的“大团圆”模式,《阿Q正传》就体现了鲁迅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革新,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式“大团圆”。他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结尾也如此。鲁迅的小说可以分为悲剧、喜剧、悲喜剧交叉等几种类型。这里所说的悲剧不是作为戏剧本身的悲剧和喜剧,而是一种艺术中的审美特征。鲁迅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概括了悲剧作品的审美内涵,尤其在其作品的结尾中有具体表现。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结局要么“死”,要么“走”,要么“忘却”,都是他所说的“悲剧”结局。
从《阿Q正传》里阿Q的“大团圆”结局中,可以看到鲁迅式“大团圆”的深刻内涵。《阿Q正传》第九章“大团圆”的取名,就反映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设计。在《阿Q正传》的结尾,就情节发展来看,阿Q被枪毙等于已经结束了他的“正传”,这个故事可以这样结束了,但作者继续描述阿Q被枪毙这件事引起的社会舆论,以此作为小说的真正结尾,鲁迅这句话的含义耐人寻味。小说的前一段,通过对赵太爷、举人老爷两家所受影响的描写,揭示了地主阶级对革命的敌视态度,认为其有“遗老的气味”,而后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4]。
联系阿Q的外在形象和这段话的深层内涵,可以进一步思考鲁迅有意设计的农民对辛亥革命的不理解,从而深化了对国民性批判的思考。未庄的“革命”已经完成了,而第一个站起来高喊“造反了”的阿Q的结局却是悲惨的。革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他因革命成了新政权的牺牲品。对于阿Q的牺牲,未庄的人们统统认为阿Q是“坏”的,所以他受侮辱是活该。甚至认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还讥笑阿Q临死前没唱一句戏,后悔自己白跟了一趟,这种结局包含着鲁迅当时不可抑制的愤恨之情。而阿Q此时此刻的“圆圈”开阔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因而在读者的脑海里深刻地留下了这副可怜的“惨相”。
“大团圆”是鲁迅精心设计的“正在进行中”的或“未定”式的结构。对鲁迅而言,这样的设计与美学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在古代小说中,“大团圆”往往是美满、和谐的象征,是大欢喜的结局,那温馨和睦的场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情节。许多作家常常在创作构思中择取这种思维定势,以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鲁迅的“大团圆”构思实际上违背了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阿Q正传》的结尾是一种凄惨冷落的“大团圆”,试想阿Q被“枪毙”后满地流下了鲜血,那血却红得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结局有着某种期待读者感到失望的心理,背离了传统的审美意识,使熟悉的艺术结构陌生化。这股力量打破了读者心里的平静,总觉得不舒服,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的感觉正是震撼灵魂的开端,是鲁迅改造人生的起点。正如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所说的:“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得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弄清楚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灭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5]当我们深入思考时,会发现文中的一串省略号、惊叹号和问号留下的空白,给予了深远的意义——如“如何实现美好的生活?”“新的生活在哪里?”,沿着这样的思路,让读者自觉地弥补新的空白。因此,多层次的“大团圆”的未定式结构,让读者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有关改造国民灵魂的时代命题的同时,使得我们进一步明白鲁迅有意设计的“未定式”结构不会是他固定的结局,而是一种新故事、新生活的开始。
除了对“大团圆”的重新诠释和演绎,鲁迅小说的结局还有很多特点,鲁迅的作品要表现的通常都是“凡人”的悲剧,鲁迅把人们熟悉、不以为奇的悲剧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进而对小说结尾做平静的叙述处理。他的悲剧艺术拓展了悲剧创作的领域,告诉我们如何捕捉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题材;如何塑造悲剧性的小人物;如何把悲剧和喜剧巧妙地结合起来;如何展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闹剧等。鲁迅小说结尾的复杂多样,无论是冻死的、病死的、饿死的,还是被狼吃的、被人砍头的、跳河的、被枪毙的、精神忧郁而自杀的、被巫婆害死的,鲁迅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的出场不同,其结局也不同。《伤逝》结尾是男主人公涓生的独白。最后他选择的是“走”,“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6]这里涓生打开了新的生路,选择默默地前行,这对他而言,几乎成为面对现实挫折的最好寄托,每次遇到精神打击就以这样诉说苦楚的方式来掩盖内心的茫然无措。涓生为探索“暂时的平安”,有时不得不自骗,也不得不骗对方,他只能靠自欺欺人与说谎来鼓励自己的前行。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新路”,而前行的方式要靠遗忘过去,但毕竟踏出了新的一步,这大约是他的“新的”生路。这段结尾做这样的处理,既完成了涓生懦弱的性格的塑造,又照应了整个作品的主题,是对无知的浪漫主义情怀的讽刺。《头发的故事》的结尾写“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7]。这种忘却未尝不是幸福,因为不能忘却,所以在生活中一直挣扎并感到吃力,正是命运终归逃离不了悲剧的某种恐惧和幻想。《白光》中的陈士成不像孔乙己那样穷困而死,而是疯狂而死。他满脑子幻想着考场得意,升官发财,但连续16回的落榜,粉碎了他的升官梦,带给寒门士人的他各种压迫感。最后陈士成追着白光,孤独中疯狂,溺死在湖中。他的死亡是咎由自取的结果。《孤独者》的结尾叙述更深刻地体现了鲁迅的自我矛盾心理。鲁迅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自暴自弃的“孤独者”的死因、办丧事的经过。鲁迅笔下从狂人到魏连殳,都是社会的异类,他们前进的道路是悲惨的。但他们又是很坚决的,也有过犹豫甚至颓唐。但对孤独者而言,转了一个圈子站着的终点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又再试图跨出一步,尽管没有明确的目标,再出来绕一圈,这确立着他们在绝望中抗争的形象。所以,“孤独者”是破旧立新的改革者,决非游离社会的多余者。这是知识者思想存在的方式,鲁迅肯定了“孤独”的价值。因此,作者在看到魏连殳不可避免的悲剧后却感到“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8]。在这一时期,鲁迅已经不再像《呐喊》里的一些小说结尾添上一点亮色,而是深深感到绝望,既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绝望,又对被启蒙者能否被启蒙的怀疑。所以这部作品的结尾,可以说是鲁迅真实情感的透露,也可以看到鲁迅一方面又不甘于绝望,一方面又无法放弃绝望,这种矛盾心理使他更透彻地感悟到时代的悲凉。因此,《孤独者》可以看作是对世俗人生中的“孤独者”可悲命运的嘲讽。
如上所述,除了“死亡”与“妥协”,“走”也是鲁迅的生存选择,就要走没有路的地方,创造出一条路来,这便是反抗绝望的最好方式。这种反抗“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9]。至于“如何走”“怎么走”是鲁迅在小说结尾表现出的思考。从对《呐喊》《彷徨》小说结尾叙述的多样化处理中,可以看到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受制于时代却又超越时代的,他始终带着面具在呐喊,比同时代的人多作了一份对社会现实的审视,这对体现鲁迅思想内涵与反映当下心境有重要意义。
二、张恨水:回味悠长——没有结局的结局
在张恨水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自觉的“改造”思想。他说:“长篇小说中的关节,的确不容易,由这事渡到那事,必须天衣无缝,使人丝毫看不出来,这才是高手,否则硬转硬拐,不仅接不上气,读者也不能聚精会神了。旧小说多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或者是‘按下不表,且说……’,可谓其笨如牛。新的小说中,另有办法。然而弄好了的也不多。”[10]张恨水始终相信语言上造成的空白,于是为读者的思索提供了无数的想象空间。而进入作品的阅读后,读者又不断调整自己的审美期待,把注意力投射到能体验到愉悦的地方去,这就是读者立体审美的自由选择。正因为如此,张恨水基本放弃了“大团圆”的结构形式。其多数作品没有所谓的固定“结局”,也没有交代清楚人物的出场和退场,反而多用暗示,以虚实相济的语言把未言的空间放大,引发读者一起思考,达到耐人寻味的目的。“任何一部作品,不论它多严密,对接受理论来说,实际上都是由一些看来靠读者去解释的成分。这种情况通常见解不同的是作品提供的说明越多,作品的意义就越不确定”[11]。张恨水并未刻意满足读者对情节的某种期待,因此他小说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是非常罕见的。这种“无结局”的结尾是传统章回小说里并不十分突出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啼笑因缘》。张恨水让读者有点余味不尽之意,并明确表示没有续写的打算。后来在谈到《啼笑因缘》结局时,他曾说道:“我不能象做‘十美图’似的,把三个女子,一齐嫁给姓樊的,可是我也不愿择一嫁给姓樊的。因为那样,便平庸极了。看过之后,读者除了为其余二人叹口气而外,决不再念到书中人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宇宙就是缺憾的,留些缺憾,才令人过后思量,如嚼橄榄一样,津津有味。若必写到末了,大热闹一阵,如肥鸡大肉,吃完了也就完了,恐怕那味儿,不及这样有余不尽的橄榄滋味好尝吧!古人游山,主张不要完全玩遍,剩个十分之二三不玩,以便留些余想,便是这个意思。”①张恨水的《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载于上海三友书社1930年12月初版本《啼笑因缘》.樊家树与三个性格不同的女子的感情纠葛到底如何,作者只是用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结束。这样“言不尽意”的语言造成的空白,就强化了其作品的情趣韵味和深层意义。所以,《啼笑因缘》的结局众说纷纭。而张恨水本人坚决表示“不能续”“不必续”。由此看来,张恨水还是承认旧章回小说“大团圆”的各种弊病而自觉加以克服的。当时,《新闻报》要求张恨水写续集,更多读者一直问主人公的下落,他回答道:
(一)关秀姑的下落,是从此隐去。倘若您愿意她再回来的话,随便想她何时回来都可。但是千万莫玷污了侠女的清白。
(二)沈凤喜的下落,是病无起色。我不写到如何无起色,是免得诸公下泪,一笑。
(三)何丽娜的下落,去者去了,病者病了,家树的对手只有她了。你猜,应该怎样望下做呢?诸公如真多情,不妨跳到书里去作个陶伯和第二,给他们撮合一番吧。
(四)何丽娜口说出洋,而在西山出现,情理正合。小孩儿捉迷藏,乙儿说:“躲好了没有?”甲儿在桌下说:“我躲好了。”这岂不是糟糕!何小姐言远而近,那正是她不肯做甲儿。
(五)关、何会面,因为她们是邻居,而且在公园已认识的了。关氏父女原欲将沈、何均与樊言归于好,所以寿峰说:“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又秀姑明明说:“家住在山下。”关于这一层,本不必要写明,一望而知。然而既有读者诸君来问,我已在单行本里补上一段了。②张恨水的《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载于上海三友书社1930年12月初版本《啼笑因缘》.
张恨水的众多作品都脱离了传统小说中“大团圆”的怪圈。《春明外史》的杨杏园因重病英年早逝,而文中个性不同的三个女性也摆脱不了悲剧命运,妓女梨云来不及赎身就得病而死;才女李冬青因身体有残疾,最终放弃这段爱情,离开北平南下独自生活;史科莲为成全杨杏园和李冬青的爱情离开北平;杨杏园最终没有和他所钟意的女性结成一对,这一男三女的多角恋情仅仅是“开花不结果”,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中作者给这可怜男的一生添了一种纪念,那首诗是:“人亡花落两凄然,草草登场只二年。身弱料难清孽债,途穷方始悟枯禅。乾坤终有同体日,天海原无不了缘。话柄从今收拾尽,江湖隐去倩谁怜。”[12]这种结局表明了审美接受是通过读者的想象,以一种生命的投入直接领悟的创造活动。《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冷清秋被花花公子金燕西抛弃后,与外界隔绝,带着幼子失踪,在街头以卖文为生。《杨柳青青》(又名《东北四连长》)的桂枝和赵自强的婚姻是因丈夫战死而悲剧收场,而这部作品以大量暗示和景物描写来突出审美效果:“可是上格窗户,在屋梁下,还有两块玻璃敞着,露了亮光进来。由那里可以看到前院的两棵大柳树,摇着青青的影子。那正是表现着窗子外是一篇明媚的春光呀。”[13]《艺术之宫》和《啼笑因缘》的女主人公李秀儿和沈凤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被形形色色的男人戏弄,失去了真爱,最后被逼致疯。其中,《艺术之宫》的结尾富有寓意特色,因走投无路发了疯的裸体模特李秀儿向巡警要一份“不再受人家欺侮”的“凭自己卖力换钱”的合法工作,然而“看到这些人,眼珠转了一转,似乎有点省悟,扭转身却向斜角落里飞跑。巡警在后面叫道:‘你胡跑有什么用,那是死胡同呀!”[14]《美人恩》中的常小南做他人妾之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一番捉弄后又被始乱终弃,落得个惨不忍睹的下场。作者认识到当时这群女性的可悲下场,文中这样总结:“他们,又这样合拢了,将来少不得又有一番悲欢离合。但是那一番悲欢离合是另一番事,这也就不必提了。此所以天下多事也,此所以言情小说屡出不穷也。”[15]《北雁南飞》的美少女姚春华和美少男李小秋的爱情注定了一场无望的折磨之后,姚春华屈从了父母的安排,嫁为人妻,李小秋参加了革命。张恨水在文章的结尾以“题外话”细加回味,引导读者对文章情蕴做更深一层的理解:“对河永泰镇庙的晚钟,隔了江面,一声声的传了过来。太阳带了朱红色,落下树林子里去。江面上轻轻的罩了一层烟雾,不见一条船只。除了那柳树叶子,还不断的向水里落下去而外,一切都要停止了。钟声在那里告诉人:今天是黑暗了。向前的人,镇静着吧!明天还天亮的呵!”[16]《夜深沉》的女伶杨月容和车夫丁二和难成眷属,丁二和企图刺杀阴谋害人的陈经理,雪夜之中,因想到卧病在教会医院里的老娘,最后放弃了冲动行为。小说结尾只说:“二和站在雪雾里,叹了口长气,不知不觉,将刀插入怀里,两脚踏了积雪,也离开俱乐部大门。这地除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冷巷长长的,寒夜沉沉的。抬头一看,大雪的洁白遮盖了世上的一切,夜深深地,夜沉沉地。”[17]《天河配》的白桂英和王玉和的爱情也得不到世人的祝福,丈夫被迫于生存的困窘远离了心爱的人,白桂英又恢复女伶身份,不知何日才有夫妻团圆的希望。这样的开放性结尾,深化了主题思想,使小说显得精致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张恨水作品常用的“回味悠长”的结尾方式,立足于引发读者对作品的主要内容、主体情感的回顾,调动读者再次折起感情的潮水,去领略悠悠之情。由此,读者在文本的空白与未定点上找到了重构的空间,这些空间由读者的想象去填补,以完成读者自我体验的实现。于是读者可以真正领会它,努力去追踪人物的思路,还可以积极参与许多不同细节。正如朱光潜在《谈文学》一书中所说的“文章有一定的理,没有一定的法”。由此看来,鲁迅和张恨水在其创作中想让我们多体验长留余味,还应致力于法外之法的探索,或许这是他们写作的基本规律。
三、总 结
横向比较来看,在对待传统小说“大团圆”结局的观念上,鲁迅与张恨水双方已达成共识。甚至从尊重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角度看,张恨水的小说结局观念及其创作,相对比新文学作家更合情合理。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打破旧章回小说的团圆框架,也符合“五四”现代作家的审美追求。就二人的作品而论,他们对传统文学“大团圆”结局的打破重新纠正了传统文学创作中的平庸面,深化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此同时,扬弃虚假性的团圆使得现代作家们对大团圆结局的认识更为全面、客观。如张天翼在《创作谈》中对当时某些革命小说的公式化写作进行了反思:“现在有一篇小说。大意是这样。话说一个痛苦的主人公有一天忽然跑去革命。原来革命是轻易得像在柏油路上散步似的。革命者又都是些全智全能的上帝。不是血肉做成的凡人。于是革命马到成功,恶人完全被消灭。常言道得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于是一时人心大快。这是一种团圆主义的手法。事实上是不是这么轻松容易呢?那可管不着。这种团圆主义的手法,古今中外都有的,从前中国的传奇,现在花旗国的‘写情巨片’,多半是这么一套。”[20]鲁迅与张恨水对大团圆结局的摒弃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品应该扎根于生活的真实性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在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全依赖偶然因素获得悲喜逆转,可这不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
从鲁迅和张恨水二人对小说结局的处理中可以发现,虽然其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是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等的思考,打破了读者的审美期待,给读者带来不舒服的真实体验,引导读者去思考新的出路;而张恨水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意味深长的结尾,如同没有结局的结局,给人留下无限的回味空间。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坟·论睁了眼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2.
[2]温奉桥.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59.
[3]张恨水.长篇与短篇[N].世界日报,1928-06-05/06.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阿Q正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2.
[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答有恒先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4.
[6]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伤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3页.
[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头发的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8.
[8]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孤独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0.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250411·致赵其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8.
[10]张恨水.小说的关节炎[N].新民报,1946-04-17.
[11]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6.
[12]张恨水.春明外史:下[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1381.
[13]张恨水.杨柳青青[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390.
[14]张恨水.艺术之宫[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428.
[15]张恨水.北雁南飞[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536.
[16]张恨水.夜深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482.
[17]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9卷:创作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0.
【责任编辑 王雅坤】
Why not “Reunion”——On the Tragic Ending in Lu Xun’s and Zhang Henshui’s Novels
SUL,HEE-JU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e ending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the whole art, is to unite the author’s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and measure the writer’s artistic skill, and a good literary works always has a well-designed ending. In China ancient novels, the hero is often dependent on the accidental factor to get a happy ending reversed from sadness, but Lu Xun and Zhang Henshui abandoned the reunion model for processing the ending, keen to end in tragedy. They think, works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real soil, the ending should fit the objective logic of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plot development, and a happy ending is not a real life experience, while the tragedy is more emotional so it can more easily shock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wo people have abandoned the happy ending, the underlying thinking has varied: in thinking the ending Lu Xun takes the “concealment and deception”, the criticism on liking the happy end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m and personal “go” philosophy of life into consideration; whereas Zhang Henshui is more starting from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readers’ curiosity, to carry out the layout of the ending from the fine art of plot conception. In any cas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the treatment on the ending of two people virtually hav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readers.
Lu Xun; Zhang Henshui; the refined literature; reunion; tragic art; aesthetic imagination
2014-11-22
薛熹祯(1978—),女,韩国首尔人,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国语言文化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韩现代文学研究。
I206
A
1005-6378(2015)01-0025-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