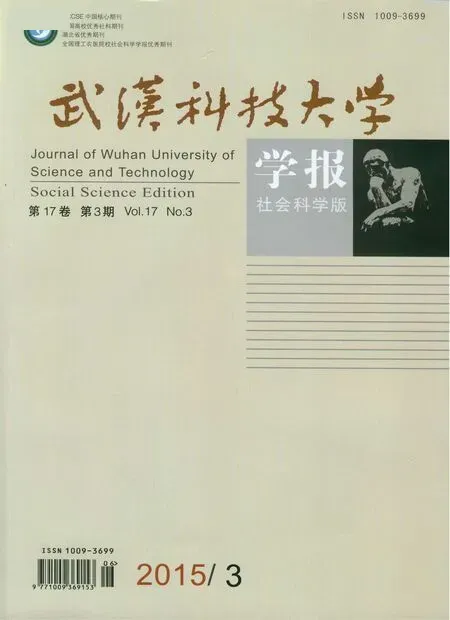论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
王 天 楠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 辽宁 沈阳 110004)
论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
王 天 楠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 辽宁 沈阳 110004)
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连接人们相互关系的纽带。信任的基础由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和世界观等因素决定,其中平均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本体。在信任体系中,并非所有类型的信任都能成为社会资本,仅有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人际信任才符合社会资本的条件。人际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民主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产生合作意愿和参与热情,培养宽容精神和公民认同,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完善司法体系和行政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促进政治昌明、社会和谐。
社会资本;人际信任;制度绩效;民主
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连接人们相互关系的纽带。博·罗斯坦等指出:“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中心,因为它是任何民主文化整体的、不可替代的部分。”[1]恩斯特·费尔等认为,“通过相互合作、避免搭便车,人际信任成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要素”[2]。詹姆斯·S·科尔曼明确指出:“人际信任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改善交易环境,提高了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效率。”[3]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更是把人际信任抬高到社会特征的高度,他认为:“人际信任是特定社会的一个相对持久的特征:它反映了一个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传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4]81由此可见,人际信任不但是衡量社会资本存量和质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制度绩效、推动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际信任的本体:从平均主义到乐观主义
信任的基础由社会经济和世界观等因素决定,其中平均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本体。通过本体论解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信任的根本属性和本质内涵,进而解读构建人际信任的深层次根源。
第一,社会经济条件与信任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其中平均主义对于塑造人际信任起着关键作用。平均主义具有多重含义,最主要的是社会平均主义和经济平均主义。
社会平均主义强调全体人民拥有平等权利、享有同等尊重、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使陌生人之间乐于相处、易于合作,进而增加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平均主义是构成信任的客观要素。首先,社会平均主义主张权利上的平等,这为人们消除社会地位差异、均等进入社会创造条件,并展现出某种民主社区思想。奥兰多·帕特森指出:“民主社区思想的核心,是兄弟般的平等,至少分享具有共同传统、共同现状以及共同命运的共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相互平等。”[5]148对于普通人而言,民主永远意味着在某种形式上分享权力,意味着个人对国家集体权力的体验。分享权力的体验从外部经验上增进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而民主社区则从内部把人们凝聚为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在心灵深处搭建信任的平台。其次,社会平均主义与政治参与相连。民主生活需要某种形式上的参与,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入性直接影响民主的质量。平等的社会权利为民众广泛的公共参与提供机会,进而培养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信任观念。最后,社会平均主义培养了公民的认同意识。所谓公民认同意识就是在一个特殊共同体内吸纳一些人又排斥一些人的观念。如奥兰多·帕特森所言:“与那些不是政治共同体的人比较,所有民主国家都被认为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团结契约。”[5]149社会平均主义能够逐步扩大公民的认同范围,使公民认同从狭小的封闭团体扩大到以地域为界限的庞大政治共同体,进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建立公民的普遍信任,为民主发展提供社会土壤。
经济平均主义与社会平均主义具有同等价值。埃里克·尤斯拉纳指出:“信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越是均衡,这个国家的人民信任感就越高。”[6]296这是因为,经济等级阶梯阻隔了人们彼此间的联系,不同阶梯的人们总是处于相互怀疑之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带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利益追求上的差异,进而增加了彼此隔阂。只有经济地位平等,人们才能消除思想上的疑惑,建立共同的生活志趣和价值理念,构建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很难想象在一个阶层断裂、贫富分化严重的地方会存在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也很难想象民主制度会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国度良好运行。因此,平均主义构成了人际信任的本体。
第二,人际信任并非基于博弈的考量和客观的生活状况,而是建构在更深层次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之上。埃里克·尤斯拉纳指出:“普遍信任来自于乐观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最初是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学到的。即使我们发现了任何个人、群体甚至‘大多数人’有什么新情况,我们也不容易从信任转变到不信任。”[6]98人际信任根源于生命的早期阶段,父母对儿童世界观的形成尤为重要,一旦信任感建立起来,不会随时间随意变化。但是父母并非全部的影响因素,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以及长大之后也会受到其他理念的影响。因此,成年人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混合物,混合着幼年受到的价值熏染和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理念。在这些价值和理念中,乐观主义对信任的塑造要远远大于经济成功的客观量度。乐观主义培养积极向上的公民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为普遍信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悲观主义者则退缩到自己的群落中,把外部人一律视为不怀好意者或潜在的威胁者。这种怀疑意识极易在封闭的群体内部孵化出权威主义,因为悲观主义充满了对外界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心,只有建立绝对权威才能保护自身。在与外部作斗争的同时,悲观主义者坚信,只有把别人压在下面,而自己位于权力阶梯的更高层才是安全的。这就使悲观主义不能协调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平衡,进而使民主和平均的价值丧失作用。因此,悲观主义无法营造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也无法适应民主政治。而乐观主义与之相反,它产生信任并推动民主发展。埃里克·尤斯拉纳概括了乐观主义者的四种表现:一是认为未来比过去好;二是相信可以控制自己的环境,使它越来越好;三是个人有幸福感;四是社群有支持作用[6]103。尤氏的前两种概括说明个人对于未来和自身的自信,对自身的信心是对他人信任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怀疑那么何谈与他人建立普遍信任关系。对未来和环境的信心让人们更愿意相互合作、彼此信任,共同改变世界。而悲观主义者看不到摆脱自己命运的途经,容易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他人并把关注点聚焦于自己的家庭,他们的信任半径缩小到极小范围。乐观主义者拥有个人幸福感,对陌生人持积极态度,并把个人的情绪转化为对待世界的普遍态度。乐观主义者生活在友好的社群中,人们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总之,乐观主义世界观产生了对未来的信心、自我控制感和反权威主义意识,从而成为构建人际信任的重要要素。这些要素本身具有促进政治参与、提高民主水平的潜在功能,并与信任的价值观念一同构成推动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本力量。
二、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类型: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人际信任
作为社会资本组成要素的信任不同于普通信任,它是一种具有道德主义的、普遍主义的人际价值系统。然而,在信任系统中却存在诸多类型,从来源、范围和对象上辨析信任的类型有助于深化对社会资本广延性的认识。
第一,依据产生的根源,信任可以区分为策略性信任和道德主义信任。所谓策略性信任是基于个人经验进行的策略选择。它形成的基础是博弈论,尤其是囚徒困境理论。博弈与选择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多次反复尝试积累的经验结果。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发现,相互合作和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正如囚徒面临困境时发现,相互合作与彼此信任可以取得利益最大化。最开始这种选择仅限于个体或小群体之间的经验,后来经验扩展为社群生活的共识,进而整个社会依据策略建立信任关系。策略信任并不构成社会资本。首先,策略信任预示着风险,它很容易被搭便车或投机取巧的人利用,社会陷入潜在的风险之中。其次,策略形式千差万别,并非所有合作者对任何策略都感兴趣,这大大降低了策略信任的适用范围。最后,策略信任以个人经验为依据,只对有过合作经验的人保持信任,而对陌生人持谨慎态度。但是,个人经验既不可靠也不持久,一次合作失败可能导致长期营造的信任体系崩溃。而道德主义信任与策略信任不同,它不涉及对具体人或人群的利益选择,而是一种对人本性的普遍看法。普遍主义把信任看作一种信仰体系,相信他人与你共享价值观念。福山指出:“当一个社群分享一套道德价值观,借此建立彼此诚实行为的期许之后,信任就产生了。”[7]埃里克·尤斯拉纳总结道:“道德主义信任后面的核心概念是,这种‘信任产生于一个群体共有一组道德价值系列时,其表现形式为,对惯例性的诚实行为产生出惯例性的期望’。如果他人共有我们的一些基本前提,我们在集体行动中遇到问题要寻求一致时,面临的风险就比较小。”[6]21道德主义信任让社群成员坚信彼此之间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与宏观期许。因此,在对具体政策、策略持有不同看法时,彼此能够相互妥协、宽容。道德主义信任建立起人们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似性,这种深层次相似性弥合了政治分歧与党派分裂,有助于政治稳定。
第二,以信任的范围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个别信任与普遍信任。肯尼思·纽顿认为:“‘个别’被用来描述‘信任’,在这里,社会信任同特殊的人和团体联系。普遍信任并不被这种方式限定。它用更抽象的方式扩展到非选择性的、非特定的整体社会之中。”[8]福山则用信任半径(trust radius)作为区分普遍信任与个别信任的标准。他认为:“所有体现社会资本的团体都有一定的信任半径,即在多大的圈子中人们的合作规范是适合的。如果一个团体的社会资本产生积极的外在特征,那么信任半径能够比团体本身更大。如果合作规范只在等级森严和拥有固定成员的团体中发生效力,那么信任半径比组织本身还要小。”[9]普遍信任具有庞大的信任半径,它是相互重叠、具有包容性的不同信任半径组成的宏观信任体系,可以对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产生信任感。个别信任则以较小群体为半径,封闭在单一的群体范畴中。在个别信任中,人们进行严格的分类,区分为群体内人和群体外人。个别信任对于群体内部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对群体之外则持有消极负面的看法,他们所认可的道德共同体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埃里克·尤斯拉纳认为:“个别信任者和普遍信任者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世界观,以及陌生人能够提供什么。个别信任者认为,外部世界是危险的,他们很少能控制。他们甚至会认为有针对他们的阴谋。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害怕局势对他们不利,有独断专行的倾向,对把握前途的能力持悲观态度。”[6]36而“普遍信任以道德主义为基础,所以大都是由乐观主义和控制感塑造”[6]40。这两种信任在罗伯特·帕特南那里被界定为“连接性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合性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连接性资本可以产生出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而黏合性社会资本则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10]职是之故,个别信任极力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它实质上并不构成社会资本,只是封闭于小团体中的个别忠诚。爱德华·班菲尔德在《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描述的“非道德主义家庭”是个别信任的典型,他写道:“在蒙特格兰人的观念中,任何给予他人的好处都必然以自己家庭为代价。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给予他人多于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的这种慈善行为是奢侈的,他们支付不起,或者说,给他人以应该得到的东西这种公平行为甚至也成了奢侈品。”[11]家庭的小圈子是蒙特格兰人仅有的信任半径。而普遍信任具有开放性,能够把不同群体联系起来,产生具有广泛凝聚力的社会资本力量。普遍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它提倡不同团体的宽容、融合,共同参与民主的游戏规则。而个别信任阻隔了团体之间的联系,其自闭性与狭隘性加剧了团体间、派别间的隔阂,人们无法在民主程序下进行政治协商与相互合作。
第三,依据信任的对象,可以区分为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制度、现任政府以及领导人的信任,而人际信任则是社会之网中结成的信任关系。政治信任建立在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以及领导者的政治业绩基础之上,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时效性和变动性。而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信任网络,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与人际间的关系网络相连。人际信任对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它是大规模经济组织的先决条件,也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要素之一。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对人际信任与民主的关系进行测量,他发现:“在1972年至1997年期间,公众之间的人际信任水平与一个社会的民主水平是密切联系的。总的相关系数是0.50,而且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是重要的。在大多数稳定的民主国家,至少35%的公众表示了‘大多数人能够被信任’的意见。在差不多所有非民主的社会或那些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民主的社会,人际信任水平低于这一水平。”[4]95政治信任作为政治资本对于民主制度的作用同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相似,正如肯尼思·纽顿所言:“像人际信任一样,政治信任看起来是外在的客观条件的反应。它并不是具有信任感的个人特性的反应,而是对政治世界的评价。”[12]依据肯尼思·纽顿的研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同样增加了公民纳税的主动性与数量。因此,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都改善了社会合作,减少了公众搭便车和精英剥削的机会。同时,政治信任对于民主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代议制政府的较低评价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对政府不信任或缺乏信心直接导致政治措施难以执行。此外,政治信任同人际信任的作用方式不同,人际信任间接作用于民主,而政治信任对于民主和稳定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形式出现,是构筑公民社会的土壤;政治信任作为政治资本存在,是对现行政府与政策的评价和期许。在研究社会资本的时候,不能把政治信任纳入其中,因为政治信任是政治资本的组成部分,社会资本作为道德资源而存在。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是连接社会网络的重要纽带,是社会主观价值的重要内容,同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一起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衡量指标。
总之,作为社会资本组成要素的信任具有独特的属性,它是建立在道德主义基础上、具有较大信任半径的人际信任体系。道德主义让信任成为持久的信仰,普遍主义把整个共同体连接起来,人际间的信任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因此,信任只有具备这三种属性才符合社会资本的要求,成为推动民主发展的力量。
三、人际信任的功能:从优化社会资本到提升制度绩效
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要素,提高人际信任有助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进而优化社会资本、改善民主运行的社会环境。埃里克·尤斯拉纳指出:“信任产生了巨大的回报,这就是,更具参与精神的公民、更大的宽容以及更具创造性的政府。公民的信任感越强,就越具有合作精神,政府也运转得越顺利。”[6]284信任具有天生的民主气质,虽然它并不必然产生民主制度,但是被人际信任优化了的社会资本能够大大提高民主的制度绩效。
虽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但故意无视或选择性失明的现象却非常多。例如,在乡村学校中,老师有时会对调皮学生的一些行为故意无视,这种态度会使学生最终走上辍学的道路[15]。另外,在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时[16],在报刊编辑工作中[17],在企业管理中[18-19],都存在故意无视或选择性失明的现象。旅游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后继旅游开发商无视前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因利益冲突而退出当地的情况,仍然限制居民的参与权,忽视居民的“决策”“经营”“享益”的权利[20]。
第一,人际信任有助于民众产生合作意愿和参与热情,优化社会资本,进而提升政府运转的效率。首先,信任与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社会资本存量。罗伯特·帕特南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社会资本的稳步发展,正是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良性循环的关键部分。”[13]政府通过扩展公民权利在公民中建立信任,如为生活欠佳的人提供社会保险,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当个人与群体出现对抗时,政府扮演缓冲器和中立仲裁者的角色,确保每个人得到公平待遇。政府通过自身的行动促进人际信任的建立,同时人际信任在政府运转中也起着沟通和协作的作用,这使民众与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其次,具有信任感的社会往往是参与型社会,民众的参与是社会资本优化的重要指标。尽管光有信任还不足以产生参与行为,但信任培养了人们潜在的参与意识,营造了积极参与政治的外部环境。因而,相互信任的人更容易结成志愿团体,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政治输入过程中,团结起来的人们更有能力提出利益诉求,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也更加有效,并且积极参与对政策、措施的反馈,进而完成政府过程。民主运转来源于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人们有能力与政府进行沟通、博弈,进而促进政府在输入、输出、利益综合、反馈等诸环节的良性循环。最后,信任他人与信任政府具有相同的世界观,这是社会资本的优化有助于提高制度绩效的原因。由于信任他人的人是友善的,他们会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广泛联系,同社群中的人和平相处。在民主社会,具有信任感的人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公民,他们与社会环境保持良好关系,因而在面临繁琐的政治事务时能够保持合作状态,不会轻易产生对抗情绪,进而提高制度绩效。
第二,人际信任有助于培养宽容精神,而宽容(尤其是对政治反对派的宽容)既是优化社会资本的重要要素,也是民主运行的必备条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民主制度依赖于一种信任,即信任反对派会接纳民主过程的规则。你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对手看作是一个‘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不会在你转交权力后监禁或者处决你,他们能不负期望依法治国,而且会在你赢得下一轮选举时交出权力。”[14]此外,人际信任的前提是对社会异质性的包容,高包容性的社会是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会。因为社会由各种复杂的因素构成,只有对异质性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包容,人们才能构建平等的社会地位,培养相互信任的情感,达到社会资本的优化。缺乏对异质人群的宽容容易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转化为政治上的冲突与对抗,处理不好可能演变为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形成累进式分裂社会(Cumulative Segmented Societies)。罗伯特·达尔认为:“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可以分享相同的价值并具有相应的行动、互动与‘归属’方式的状态中。”[15]而相互宽容、彼此信任则是化解矛盾、达成合作的前提。人际信任体现在平均主义情感之上,并且表现为不同群体间的宽容与合作。信任本身包含着对异质人群的接纳并且意味着能够在异质人群中最大程度地找到共识,这使人们愿意达成妥协并愿意在民主制度的统一规范中开展政治生活。宽容精神是民主制度的前提,缺乏宽容的人们将无法容忍异质党派的存在,不能认同异见人士的批评与质询,更不能信任其他政党或政治精英的统治,进而影响政治领导人的周期轮换。由此可见,人际信任与政治宽容、政治认同是相通的,人际信任在社会层面建立起相互平等、相互合作、相互宽容的结构型社会资本,而政治宽容和政治认同则在政治层面培养民主所必需的忠实反对派,建立起具有统一权威的领导体系,进而有益于提高民主制度的绩效。
第三,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有利于完善司法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埃里克·尤斯拉纳指出:“一个有效率的司法制度取决于社会信任基础的支持。”[6]308这是由于在信任他人和信任法律制度之间存在联系,优化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制度资本。具有人际信任感的社会培养出对法律的信任,人们愿意把法律作为调节人际关系、指导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人们相信法律能够公正地解决纠纷,而在不具信任感的社会,人们更相信社会中的潜规则和隐形规范,希望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相互信任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社会的平等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相通的。社会平等是法律平等的基础,法律平等是社会平等的保障。信任营造了法治的社会环境,提升了法治水平,进而为民主遵循法治轨迹发展奠定基础。因而,人际信任通过优化社会资本的方式完善司法制度,贯彻法治精神,综合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在高信任感、高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能够培育人们的守法意识,比如依法纳税的意识。人际信任使人们相信政府同其他人一样是可以合作的,并且可以共同构建互利双赢的交易体系。依法纳税意识强调政府与民众达成的契约,依法纳税同其他交易一样是值得信任的,民众向政府缴纳赋税,政府通过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式回报民众,双方构建起相互信任的交易契约。这种契约体系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民众守法意识和民主政府的法治水平,让民主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第四,人际信任从社会资本层面压缩腐败生存的社会空间、提升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提高制度绩效。政治腐败主要表现为官员寻租、权钱交易,民众之间的不信任给官员寻租创造了机会。由于缺乏人际信任,每个人都想依靠政府的帮助在交易中取得更大的实惠,通过权钱交易,借助官员的力量在相互交往中取得好处。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人们依据公开、平等、统一的规则交往,无需借助官方的力量提高竞争力。权钱交易虽然可以使少数人短期获得竞争的优势和更多的交易利益,却在长期交易过程中破坏了交易规则,从整体上增加了交易成本,这既不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培育,也不利于有序的政府运作。人际信任还会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官僚机构往往不会把公共政策仅仅停留在口头宣传和“红头文件”上,而是尽快把政策落实下去,及时取得民众的反馈,从而赢得民众更多的支持,以便在下次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信任虽然并不一定产生民主,却是民主有效运行的有力保障。它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减少腐败、提高行政效率,从整体上提高民主制度的绩效。
总之,人际信任对于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民主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产生合作意愿和提升参与热情,培养宽容精神和社会认同,而且能够完善司法体系和行政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有利于政治昌明、社会和谐。
[1] Bo Rothstein ,Dietlind Stolle.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ate and destroy social capital: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generalized trust[EB/OL].[2014-10-03].http://www.docin.com/p-695358951.html.
[2] Ernst Fehr, Herbert Gintis.Human motivation and social cooperation: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foundations [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7, 33(8):43-64.
[4]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M]//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 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 奥兰多·帕特森.自由反对民主国家:论美国人不信任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根源[M]//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 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53.
[8] Kenneth Newton,Sonja Zmerli.Three forms of trust and their association [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3(6):171.
[9] Francis Fukuyama.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EB/OL].[2014-10-03].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1999/reforms/fukuyama.htm.
[10]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11]Edward C.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110.
[12]Kenneth Newton.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22 (2):205.
[13]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0.
[14]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及后现代: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及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97.
[15]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7.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4-11-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BZZ011);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青年招标项目(编号:Indx20150021).
王天楠,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D621.5;C912.6
A
1009-3699(2015)03-02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