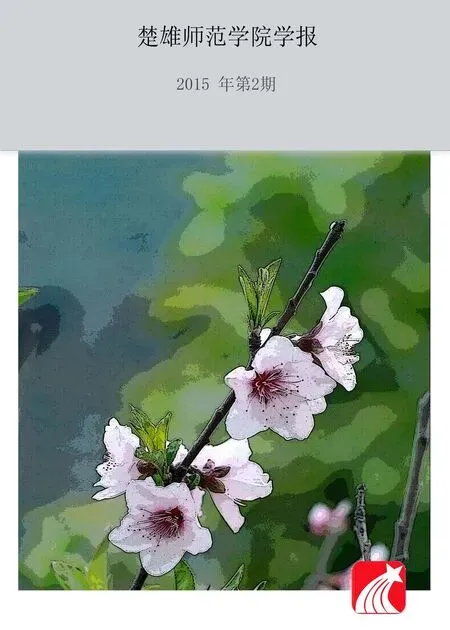论支格阿鲁文化源流
朱文旭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黑格尔说:“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性表现,远古神话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在其中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1]
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证明,神话只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约萌发于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发展和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直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奴隶社会初期。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虽然有时今天的人们觉得荒诞离奇,然而其中很多内容和现象则反映了今日人们很难理解的人类古代社会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可以这样说,支格阿鲁①“支格阿鲁”有的记作“支格阿龙”、“支格阿尔”、“翅骨阿鲁”、“支嘎阿鲁”。“鲁”贵州有的记作“楼”或“娄”。“龙”彝语没有辅音韵尾,故“阿鲁”更接近彝语读音。当时作为氏族、部落起源神话,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徽号,逐渐吸纳周围数不胜数的氏族、部落形成一定的族群,为后来民族族体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支格阿鲁与名称
从文化学角度来说,研究民族神话传说,首先必须搞清楚神话中神人名称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从源头开始搜索是非常必要的。支格阿鲁的名字在彝文文献中的记载为三种,第一种是两个音节如“阿鲁”、“阿龙”等;第二种是三个音节如“戈阿楼”、“告阿娄”等;第三种是四个音节如“支格阿鲁”、“支嘎阿鲁”等。
“哀牢”是祖先名、部族名,也是地名。“哀牢”就是后来的“阿鲁”。《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②哀牢族属问题,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3):“昆明族中,有一个部落在西汉时期以后称为哀牢。这个哀牢部落至近代被误为傣族或布朗族的祖先部落。其实,这是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个部落,是彝族祖先部落之一。哀牢部落当时居住在今保山、云龙、永平一带。”
“哀”即相当于“阿”,一些人和动物名词前缀。“牢”为彝语“龙”之记音。哀,上古影纽微部əi,中古影母咍韵ai。牢,上古来纽幽部ləu,中古来母豪韵lau。[2]彝语“龙”没有辅音韵尾,故“龙”记为“牢”。“龙”彝语喜德话lu,大方话lo,南涧话lu,南华话lu,弥勒话lo,墨江话lo,禄劝话 lu,双柏话 lo,威宁话 lu,盘县话 lu,隆林话 lo,牟定话 lu。彝语 “鲁”与“牢”一样是“龙”读音。龙,上古来纽东部lǐwəm;中古来母钟韵三lǐuŋ。彝语“龙”没有辅音韵尾,所以读“鲁”。据此,“阿鲁”缘自古代“哀牢”。
“哀牢”与“阿鲁”音近义通。哀牢山其义为“龙山”。与此相关的是,古昆明夷之地大理“洱海”的“洱”其义疑为“龙”,洱海疑其义为“龙海”。①大理“洱海”,洱,上古日纽之部riə,中古日母之韵riə,与龙“鲁”音近义通。海,上古晓纽之部xə,中古晓母海韵xai。海,彝语大方话xɯ21”,南涧话xai21”,南华、弥勒话xε33,墨江xm21(mo21)。“洱海”彝语即龙海。
“支格阿鲁”名称的“支格”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诠释过,这个名称本来是很简单明了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人不理解,有各种猜测,其中有提出地名说。说“支格、支嘎”来自于“支嘎山”,支格阿鲁出生于支嘎山故前缀支嘎。这些说法不成立,“支格阿鲁”名称来自“烛龙”。烛龙意思是火龙,彝族崇拜火,所以所崇拜的龙是烛龙。彝语“支格”是上古“烛”字的读音。烛,上古章纽屋部ȶiwok;中古章母烛韵三tɕiwok。那个时候彝语可能还有辅音韵尾-P、-t、-k。后来这些辅音韵尾-P、-t、-k就演化了。但是这种演化经过我们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辅音韵尾脱落消失;一种是分化后辅音韵尾构成一个音节形成甲乙两个后一音节。即声母章母成一个音节“支”,k辅音韵尾成一个音节为“格”。
“支格阿鲁”在云南彝族史诗《阿鲁举热》中叫“翅骨阿鲁”。贵州彝族史诗《支嘎阿鲁传》叫“支嘎阿鲁”。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说支格阿鲁是龙的儿子,生下来时,不肯吃母奶,不肯同母睡,不肯穿母衣,支格阿鲁住岩下,懂龙话、喝龙奶、吃龙饭、穿龙衣。其实“烛龙”与古代“五行”中“南方属火”的配置也是相合的。水火木金土“五行”最先见于《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以五方为基础,先完成了木火土金水分配于东南中西北。然后将十个天干两两分属于一方,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方戉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古代“五行”还配置“五味”、“五色”。“五味”是水咸、木酸、金辛、土甘。“五色”是东青、南赤、西白、北骊、中黄。[3]古代生活在“五方”不同方位的龙以其“五色”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东方的龙叫“青龙”,南方的龙叫“赤龙”等。南方属于火,所以生活在南方的龙是火龙,也就是龙演化为“烛龙”。支格阿鲁烛龙神话与彝族火崇拜文化现象是一脉相传的。
“九隆”神话中的“九隆”与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中“戈阿楼”或“告阿娄”相合。“九”古音读“戈”或“告”。九,上古见纽幽部kǐəu;中古见母幽韵三kǐəu。隆,上古来纽冬部lǐwəm;中古来母东韵三lǐuŋ。“隆”即“龙”的同义异写。九隆应该就是九龙。龙字读音因彝语没有辅音韵尾,故读成“楼、娄”。“阿”名词前缀。“戈阿楼”或“告阿娄”在贵州地区又称为“支戈阿楼”、“助告阿娄”等。这样又与凉山地区“支格阿鲁”称谓相合。”②李海明,唐春芳整理翻译《戈阿楼》,《南风》1988年创刊号。
“哀牢”与支格阿鲁名称在滇川黔彝族文化中的演化情况比较如下:
哀牢(“阿鲁”)→九隆:贵州“戈阿楼”→ (支嘎)阿鲁
哀牢(“阿鲁”)→烛龙:四川“支格阿鲁”→ (支格)阿鲁
哀牢(“阿鲁”)→哀牢:云南:“阿鲁举热”→阿鲁 (举热)
每个民族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心理素质因素造成了神话“变形”的某些特征。神话学和文化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多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接近作为客体的神话及其所载的文化实体和神话演化的过程。
二、支格阿鲁与神话
神话在原始社会中本是一种实体性文化,它不仅是远古先民对世界的解释,而且还具有礼仪规范和价值规范的效用,并在远古先民手中又是一种巫术实践的力量。而文献中所保留的神话是经过多次传递、压挤在一起的神话,它带有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痕迹。神话的“变形”现象深受神话思维和图腾观念的影响,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表达本民族审美意向的自然形象。
根据神话学、人类学、考古学各种资料证明,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神话动物,它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是在蛇原生图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次生图腾。蛇最早图腾崇拜来自于西南民族,而彝语支民族在中古时期就被称为“乌蛮”、“白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蛇,南蛮蛇种。”说的是该氏族部落图腾崇拜蛇。
支格阿鲁最初来源于彝族先民对蛇的崇拜。凉山彝族民间故事传说:古代泸山下住有母子俩,儿子上山打柴见泉池里有条小白蛇便用饭渣喂它。有天小白蛇给他说,将要山崩地陷赶紧上山躲避灾难。果然,山洪暴发山崩地陷,母子俩躲过一劫。第二天从山上一看,西昌坝子变成了邛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晋朝《搜神记》中记载道:“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载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食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不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土人谓之为陷河。”
邛海“头上载角”之蛇叫“角蛇”。凉山彝语称ʂ ɿ33ko33(史果)。汉语“角蛇”即龙的别称。传说中的角蛇也并非凡蛇,而是神力无边的蛇,邛人奉为图腾。凉山彝语称“龙”为lu33(鲁)和ʂɿ33ko33(史果)两种叫法。①藏缅语语音与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与词汇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22。该书中记录的“龙”,陈士林先生当年在凉山民间进行语言调查时发现两种说法lu33和ʂɿ33ko33,与传说中名称“史果”相合。“史”义为“蛇”,“果”疑其为“角”即“蛇角”,与汉语词序相反。杰觉伊泓《支格阿鲁音义刍议》一文也提到“龙”,民间有三种说法即“塔布”(tha21bu21)、“布哈”(bu21ha33)、“鲁”(lu33)。②杰觉伊泓,支格阿鲁音义刍议 [A].支格阿鲁文化研究论文集 [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三种说法中“塔布”其义不详。“布哈”民间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能吃人的巨蛇。《述异记》:“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虺是体型小且有毒的蛇。《洪范·五行传》郑玄注:“蛇,龙之类也。”
“烛龙”本形为龙,而龙的原形最初源于“蛇”。崇拜某一动物、植物,把它视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图腾崇拜是古代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那时人们不理解人类自身的繁衍问题,认为妇女怀孕是图腾物的魂灵进入体内而引起的,图腾物与自己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图腾的基本概念虽然是祖先,但不是人类自身的祖先,而是把它视为人与动物、植物共同的祖先。
蛇演化为龙,而龙随着各代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步神化。我国最早信仰龙图腾的是古代西南夷。先秦文献《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 《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峤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西岳”应该属于西南地区,“神农氏”与西南地区农耕文化有关。三国《广雅》中把龙分成好多种。《广雅》“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鲡螭龙,未升天者曰蟠龙。”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面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往往是以相互渗透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既有对自己传统文化因子的保留,也有对新文化因子的吸收,一般不会是同归于尽,而是以比较先进的文化为主出现新的文化而已。龙的后天形象具备中国东南西北文化的特征。宋代罗愿《尔雅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 (蛤蜊),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许慎《说文》中说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龙图腾崇拜传到各地后,采纳了东夷鸟图腾的爪、南蛮蛇图腾的身、百越鱼图腾的鳞、北狄犬图腾的头,从而形成各民族都认可的以蛇为主体的复合型龙图腾。因为彝族崇拜火,所以所崇拜的火龙也就演化为“烛龙”。
三、支格阿鲁与“九隆”
“九隆”神话发生在云南西南部哀牢山地区。①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5)说:“《华阳国志·南中志》在叙述了哀牢始祖九隆的传说故事之后,紧接着便说‘南中昆明祖之’,哀牢部落是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个最古老的部落。九隆不仅是哀牢部落的始祖,而且是昆明族各部落最早的始祖。昆明族是形成近代彝族的核心。”东汉《风俗通》、晋朝《华阳国志·南中志》、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云南永昌郡《九隆神话》:“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呼?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九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九隆居龙山下,九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九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九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像之,衣后着尾,臂胫刻文。九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南中”泛指滇川黔西南民族地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在其校注中说“此传说为乌蛮固有,非文人附会史书所编造。彝文典籍《六祖记略》中所载《洛举根源》也基本上与沙壶、九隆故事相合。是则白蛮亦祖哀牢。乌蛮、白蛮皆古昆明之后。”“九隆”与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中“戈阿楼”或“告阿娄”相合。“九”见母古音读“戈”或“告”。“隆”即“龙”的同义异写。九隆就是九龙。龙字读音因彝语没有辅音韵尾,故读成“楼”、“娄”。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 [M].成都:巴蜀书社,1984。关于“九隆”,史军超《九隆石雕初识》(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一文说,他在滇西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彝族崇拜祖先“九隆”,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保山的彝族仍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定期到“九隆山洞”杀猪宰羊祭祀九座九隆雕像,中间为九隆雕像。“文革”中雕像被毁,如今仅残留一头像。“九隆”可能为“九龙”同义异记。
“九隆”神话可以从中看出诸多神话内核信息:1.“九隆居龙山下”即崇拜龙;2.“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即图腾崇拜木和水。3.甲氏族“产子男十人”,己氏族“产十女,九隆兄弟妻之。”即实行的是母系氏族社会“普那路亚”婚姻家庭形态。4.“九隆”义为“九龙”。
支格阿鲁在“滇普殊诺”往返走婚的婚姻形态与“九隆”神话相合,凉山支格阿鲁和云南阿鲁举热说他在“滇普殊诺”北边有一情人,在“滇普殊诺”南边有一情人,他经常骑着有翅膀的神马在“滇普殊诺”上空飞来飞去,往返走婚。女子是氏族内的基本成员,而男子则不定期到女方过性生活。由于是群婚,故所生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九隆”和“烛龙”后来在凉山和贵州彝族神话传说中都演化合称为“支格阿鲁”。
四、支格阿鲁与“哀牢布”
张骞最早在大夏 (今阿富汗)见到“蜀布”,他问此物来自何处?得知蜀郡商人将其贩运到身毒国 (今印度)。从身毒再贩运到大夏。蜀郡商人经商的所谓“蜀布”是从哀牢夷地区贩卖来的“哀牢布”。因为当时中原地区没有种植棉花。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说:“哀牢地物产富饶,《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诸书备载之,其中以‘哀牢布’为著,《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诸书称‘桐华布’或‘白叠’,即木棉布,产于哀牢。亦有称为‘都布’、‘榻布’、‘答布’。《史记·大宛列传》所说张骞在大夏 (今阿富汗)见‘蜀布’,亦即哀牢布,有输至蜀而称蜀布。蜀贾人取自哀牢输至身毒国,亦以蜀布称之。哀牢部族对于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多有贡献,转运哀牢布,当始于汉以前。”[4](P21)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哀牢山,位于中国云南西南部,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水岭。哀牢山呈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殊立体气候。红河水奔腾湍急,哀牢山脉与戛洒江为平行走向,山川交错,山高谷深。云缠雾绕,巍峨壮观,植物分布区系复杂,古老名贵植物种类较多。
《后汉书·哀牢夷传》:“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毡、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说 (434页):“《御览》卷八二〇引华峤《后汉书·哀牢夷传》曰:“哀牢夷知染彩䌷布,织成文章如绫绢。有桐木华,绩以为布,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5]
“哀牢布”在西汉初年已闻名天下,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没有种植棉花,人们只是知道棉布是来自于哀牢地区,不知道棉花长什么样。由此引起了文人墨客在书中各种不同的猜测和假说,尤其对棉花一词的说法各异。①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给欧洲人说印度有一种奇怪的树可以长出羊毛,译作“树羊毛”或很滑稽的名字“植物羔羊”。笔者怀疑所谓的印度棉可能与哀牢棉有关。西汉时经印度到阿富汗之布都采自中国,未提印度有此物。
到了隋唐时期,棉花 (cotton)明确地记载为“娑罗”。但是“娑罗”在汉文史志中有的说“娑罗”是娑罗树,即观赏树木不结果的七叶树。有的说“娑罗”是木棉树,即“攀枝花”别称“英雄树”。有的说“娑罗”是“桐树”。
《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自银生城、拓南城、寻传、祁鲜己西,蕃 (即“濮”,笔者注)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通服之。骠国、弥臣、诺,悉皆披娑罗笼段。”《蛮书》中已经很明确说织成布的絮是从叫“娑罗”树籽中取得的。《新唐书·南诏传》:“大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沙罗树实,状如絮,纫缕而幅之。”
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七:“《博物志》云,今永昌有娑罗布者,亦自夷人所织,质粗而弱,并无笼段之名。《博物志》云:树子破其壳,中柔白如絮,则今之攀枝花也。然此花不堪纺织,并无织以为布者。《一统志》载永昌出桐花布,注中所言亦为此类,而永昌绝无所谓桐花布者,岂物产货殖亦随时而废欤?”
《太平御览》引《南夷志》:“南诏收娑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通服之。骠国、弥臣、诺,亦皆披娑罗笼段。”《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三引《云南志略》云:“莎罗树出金齿及元江地面,树大者高三五丈,叶似木槿,花初开,黄色,结子变白。一年正月、四月二次开花,结子以三月、八月采之。破其壳,如柳棉,纺为线,白氎兜罗棉皆此为之,即汉地之木棉也。”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六引宋沈怀远《南越志》:“南诏诸蛮不养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如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段。”李石《续博物志》卷七:“骠国诸蛮并不养蚕,收娑罗木子,破其壳,中如柳絮,细织为幅服之,谓之娑罗笼段。”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五:“莎罗布,出大姚县与新化州。”
古代凉山彝族也有与布打交道的史迹。凉山彝族地区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中已经进入农耕文明,到唐朝时期有了棉麻织品做成服饰的记载。樊绰《蛮书》卷一:“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彝族服饰用“黑缯”和“白缯”,即黑布和白布做成服饰反映了凉山地区乌蛮和白蛮彝族先民开发利用了棉织品做成服装史实。“缯”汉文一般指丝织品,但樊绰记录当时路经凉山地区时看到的百姓普遍着装的应该是棉纺织品而不应该是丝织品,或许古语“缯”同称丝绸和棉布。另外,凉山彝语“棉布”叫mu33sɿ33义为“棉丝”。
《支格阿鲁》传说中说:“濮莫列依啊,三年设织场,三月制织机,坐在屋檐下织布,机桩密集像星星,织刀辗转如鹰翅,梭子往来似蜜蜂,纬线弯弯如彩虹。”说濮莫列依是在院坝织布的时候被鹰血穿透裙子而怀孕的阿鲁。织布的情节可以说是远古历史事实的折射,濮莫列依织的布应该是“哀牢布”。
根据汉文史书中记载的棉花叫“娑罗”,首先排除了娑罗树 (七叶树),其次也排除了木棉树(攀枝花)和桐树。如上所述,从以上汉文史书中记述来看,“娑罗”应该是棉花无疑。
巧合的是,棉花叫“娑罗”、“莎罗”、“沙罗”这个称谓在今天中国所有语言里只有彝语和彝语支语言读音与这个称谓吻合。
娑,上古心纽歌部sa,中古心母歌韵sa;莎,上古心纽歌部sua,中古心母戈韵sua;罗,上古来纽歌部la,中古来母歌韵la。
“棉花”彝语和彝语支语言读音比较如下:
彝语喜德话sa44lɯ33,大方话so55lo33,武定话so55lo33,巍山话sa55la21,
撒尼话sa33la33,阿细话su33lo33,阿哲话so33lo33,新平话ʂo55la21,
石屏话so55lo55,红河话ʂo55lo33,隆林话sou33la55。
哈尼语 (碧卡)sɔ31lɔ31,哈尼语 (哈雅)sa31la31,哈尼语 (豪白)sɔ31lɔ31,
傈僳语 sa44la31,拉祜语 sa33la53;拉祜语 ɕα33lα53,独龙语 sa55la53。”[6]
有关学者认为哀牢夷地区是“亚洲棉”起源地之一。哀牢夷是中国最早培育种植棉花的民族。相关的资料可以佐证,一是在西南地区发现了野生棉种。二是在云南宾川县新石器遗址发现了各种纺轮,证明很早就有了棉纺业。还有汉文史志中“哀牢布”文献资料的记载等。专家由此断言“云南保山一带,自古就已经知道用棉花来作为纺织原料了。……我国的棉花有可能是独立起源的。起源地一定是在云贵高原一带。”①尤中.云南古代的种棉和养蚕 [J].云南日报 [N]1962—9—17。梁祖霞,棉花的起源 [J].种子世界1985,(10)。据介绍,令人惊奇的是世界唯一两大棉花即亚洲棉和陆地棉,南美洲起源的“陆地棉”其DNA26对,其中一半来自秘鲁野生棉DNA13对,一半来自亚洲棉DNA13对。亚洲基因远隔千山万水无边无际大海怎么去的美洲?海内外植物学家百思不得其解,成为千古之谜。
五、支格阿鲁生死地简析
支格阿鲁是如何诞生的呢?贵州《支嘎阿鲁王》说九万九千年才生下阿鲁。四川《勒俄特依》中也说支格阿鲁之母濮莫列依在院坝织布时,北方天空飞来一只老鹰,在濮莫列依的头上盘旋,裙子被鹰身上掉下来的三滴血 (精液)穿透以后而怀孕。可见支格阿鲁是彝族崇拜的龙和鹰的儿子。云南彝文史诗《阿鲁举热》中也说鹰与龙结合生下阿鲁。其母亲也叫“卜莫乃日妮”。“濮莫”与“卜莫”音近义通。
方国瑜先生说:“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诸书所载‘永昌郡’风土,有称哀牢,有称濮人,其事迹大都相同,可知永昌濮人即哀牢人也。古史所载之百濮,与哀牢濮人有别,不宜相混。”哀牢之濮,有三种观点:濮越说 (壮侗)、百蒲说 (孟高棉)、彝缅说。近年基本归于彝族说。濮,其义为“白”,濮蛮意为白蛮。[7](P22)
“濮莫”彝语义为“白女”即白蛮之女。“列依”义为“女大”即大女儿。“濮”有的记作“蒲”、“普”,“濮”不是某个氏族或某个部族,“濮莫”而是泛指西爨白蛮之女。后缀“濮”亦义为“白”。“倮倮濮”即白倮倮。”①《彝族简史》所载云南和贵州彝族支系自称后缀“濮”、“泼”、“巴”的有十多个.
《蛮书》卷四:“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西爨白蛮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西南部地区。但这种分布的格局也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西爨地区有乌蛮,东爨地区有白蛮。
彝语“白”两读:一读phu,一读thu。白蛮地区彝语“白”读phu33。乌蛮地区彝语则“白”读thu33。
云南彝语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即历史上白蛮地区彝语以及彝缅语多数语言“白”读phu33。“白”,彝语南华话phiu33,大姚话phju33,永仁话phu33,巍山话fu55,南涧话fu33。彝语支语言“白”读 phu。傈僳语 phu44,纳西语 phə33,哈尼语 phv55,哈尼语 fu33,拉祜语 phu35,基诺语pho33,缅文 phru2,缅语 phju22。[8]
再说支格阿鲁的父亲是鹰图腾的部落。彝族的“鹰”图腾显然是鸟图腾。凉山彝语雕和鹰、鹫同称不分,古语和书面语读为“雕”ti55,口语老鹰读为“鹫”ʨo55。“鹰”彝语喜德话ʨo55,路南话tɬe55,禄劝话ta55,双柏话tiə21,大方话ta13,威宁话ta13,盘县话ta21,隆林话ta13,牟定话ta55。“阿鲁举热”的“举”读音与凉山彝语口语读音ʨo55一致。
种种迹象表明,彝族先民融合了南方龙崇拜和北方鹰崇拜的部落部族而形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乌蛮崇拜鹰崇尚黑色,白蛮崇拜龙崇尚白色。在后来的彝族传统文化中黑白文化现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除了南方龙图腾崇拜以外就是北方鸟图腾崇拜,即“卵 (蛋)生”说。《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绒氏女,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鸟图腾也包括鹰、鸡、凤凰等。据说,东夷为鸟图腾。《大戴礼记·五帝德》:“东方鸟夷民。”彝族东来说说有部分彝族来自于东夷。凉山彝族尔比说“人起源于东方,迁徙于西方。”“东夷西渐”说东夷逐渐往西迁徙进入湘蜀黔滇地区。彝族火葬时人的头都要朝东方而焚,意为死后魂归东方。关于玄鸟的“玄”意为“黑”。玄鸟就是黑鸟。乌蛮尚鸟尚黑,彝语“鹰”ʨo55nɔ21(鹰黑)黑鹰与玄鸟相应。目前还不清楚彝族鹰图腾崇拜的来龙去脉,有待进一步研究。
支格阿鲁是如何消亡的呢?支格阿鲁的消亡也与他降生一样,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已,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消亡。那么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祭祖送灵”。卢占雄收集整理《支格阿鲁》中说:“支格阿鲁啊,劝阻他不听,是也要回去,不是也回去,走的说要走,劝的说留下,支格阿鲁啊,十三日后回,仙女阿乌啊,又剪二层羽。仙女阿乌啊,泪水哗哗下,支格阿鲁啊,骑着神飞马,飞过滇普殊诺海,飞了又飞啊,飞到海中央,神马都点呀,用力晃三下,用力叫三声,支格阿鲁啊,无法控制马,马掉深海里,阿鲁这样亡。史书又翻页,阿鲁的历史,代代有人传。”云南彝文史诗《阿鲁举热》中说:“阿鲁举热要去找妈妈,小老婆日姆暗暗设下毒计,偷偷剪下飞马的三层翅膀,阿鲁举热骑上飞马,飞腾在大海之上,谁知飞马翅膀被剪,力气渐渐弱下来,飞到海中央,人和飞马掉海里,海水淹到阿鲁举热脖子,空中飞来一群老鹰,阿鲁举热对老鹰说,我是老鹰的儿子,你们要为我报仇啊,说完阿鲁举热和神马消失在海里。”这里的死亡应该是暗指祭祀阿鲁神灵进行海葬然后部落分迁,各部落各走一方。
支格阿鲁经常骑着有翅膀的神马在“滇普殊诺”上空飞来飞去,往返走婚。以往有些公开出版的书中和民间有人把“滇普殊诺”说成是“东海”。后来大家认为把“滇普殊诺”说成“东海”是指鹿为马错误的。滇池古称昆明池。应该是古代昆明人在此居住而得名。支格阿鲁在海的北边飞到海的南边“走婚”,说明这个海周围彝族先民在此生活,而东海周围不可能有彝族。其次,“滇普殊诺”的“滇”应该是“滇”夷。“普”彝语义为“地方”。“殊”义为“海、湖”。“诺”义为“黑、大、深”。根据“滇普殊诺”本身的词义应该是“滇池”无疑。①戴世能,“滇濮殊罗”考 [J].毕摩文化论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支格阿鲁神话起源的地方在滇西哀牢山地区,支格阿鲁消亡地方在滇池一带。“消亡”其象征意义应该是在滇池一带部族共同祭祖把支格阿鲁神灵送走,我们怀疑祖灵不是送深山岩洞而是进行水 (海)葬。彝族传统习俗“祭祖分迁”也就是氏族部落祭祖以后就可以开始分迁到各个地方繁衍生息,这与《西南彝志》等彝文文献中所追溯的彝族先民“六祖分迁”事迹相合,其时虽不可考但应该相当久远了。与此同时彝族社会也相继进入奴隶社会时代。
综上所述,支格阿鲁既是彝族全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也是彝族全民认同的共同神灵。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民间有关支格阿鲁的所有事迹传说,希望收集整理以后用彝文版和汉文版对照分门别类出版系列丛书。最后,愿支格阿鲁神灵长久护佑所有子孙后代繁荣昌盛。
[1]黑格尔.美学 [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2]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庞朴.阴阳五行探源 [J].中国社会科学,1984,(3).
[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向达,蛮书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M].北京:中华书局,1992.
[8]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