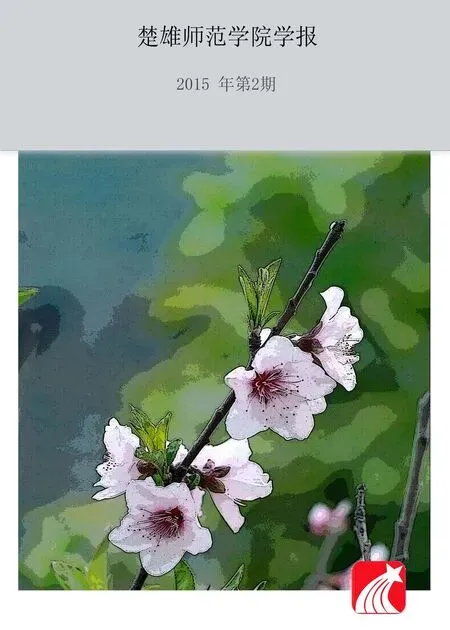“梦”与“病”的双重交构:《呐喊·自序》思想内涵再解读
孙拥军,马建荣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焦作 454000;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呐喊·自序》是鲁迅在1922年为其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所写的一篇序言。多年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过多地将视角关注于这部小说集的研读与解析,关注于小说集中的作品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部小说集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在思想与内容上的开创性。而很少去思索这篇简短精悍的序言对于这部小说集的整体价值,以及它在研究者探究鲁迅思想体系形成时所给予的史料学价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这篇序言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还无法全面呈现,从而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史上的缺憾。本文试通过对这篇序言的再度解读,重新探讨鲁迅前期思想体系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这篇序言之于《呐喊》以及鲁迅其他作品的史料学价值,为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借鉴,以丰富和完善鲁迅学的研究。
一
在这篇被鲁迅研究大家钱理群先生誉为“解读鲁迅小说的一把钥匙”[1](P138)的序言中,鲁迅先生以旧事重提的方式记述了青少年时代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及他从实业救国走上文学启蒙道路的曲折心路历程,并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其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
鲁迅先生开篇详细讲述了他和文学结缘的偶然性,在一次次对自己的理想的质疑、否定与重构中,最终由医学实业救国走上文学启蒙之路。从鲁迅先生人生经历的表述,我们在进行其早期思想形成历程研究时,不难看出他走上文学启蒙道路似乎出于偶然,那就是其在日本仙台医学专修学院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在课堂上所放映的时事幻灯片的深刻影响。当看到久违的中国同胞在日俄战争中因做俄国人的间谍,被日本军人抓住杀头示众的场景时,鲁迅深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拥有健壮体格而灵魂麻木的国民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与悲哀。“幻灯片事件”促使鲁迅先生重新思索自我的人生之路,再度思考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命运和前途,最终,鲁迅先生毅然放弃了自己原本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而走上文学启蒙之路。正如其所言:“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最后他放弃了对医学的追求,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展文艺运动,利用文艺来启蒙和拯救精神麻木的愚昧国民。因而,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者视乎可以说鲁迅的弃医从文、开展文学启蒙运动是出于偶然。
其实,从鲁迅先生的自述来看,我们可以感悟到其与文学的结缘看似偶然,但在偶然中也蕴含着一种必然。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鲁迅批评家李长之所说:“在这种视乎神秘意味之下,我们又见到鲁迅。他学过医,可是终于弄到文学上来了;他身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他生长于代表着中国一般的执拗的农民性的鲁镇,这视乎都是偶然的,然而这却在影响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艺作品。”[2](P2)在序言中,鲁迅先生开篇就叙述了其家族“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它给鲁迅先生的人生带来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鲁迅家道中落源于其祖父周福清的科考舞弊事件,因遭人告发,祖父被下监苏州,家族财产数次被抄。又加上鲁迅的父亲周伯夷也因此事重病卧床,年幼的鲁迅不得不每天往返于质铺与药店之间,使其在家道的变故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和世态炎凉。如其所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家族环境的变化给鲁迅带来深刻的影响,使鲁迅在思想深处不得不用新的视角来思索自我的人生历程。
由于科考舞弊事件,周家多次被查抄,鲁迅的母亲也因此经常带着鲁迅兄弟到乡下去避难。在这避难的经历中,鲁迅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感触到农民的生命体验和生活历程,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最了解农民的作家。他看到生活在宗法制乡土中国的农民所受的非人苦难和难以言表的人性摧残,同时也看到了数千年来封建伦理给农民思想深处带来的种种难以剔除的民族劣根与陋病。这些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和生存感悟,都成为鲁迅进行文学创作时取之不尽的源泉。
二
从鲁迅对生活琐事的讲述中,研究者不难看出这篇序言的两个关键词:“梦”和“病”。它们贯穿始终,并且鲁迅先生早期思想体系的形成也与这两个关键词息息相关。
《呐喊·自序》开篇,鲁迅先生就写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接着,依次叙述了其青少年时期历经的多次梦想的破灭与重新燃起希望的过程。鲁迅在其家道中落以前,也曾经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有着科举应试的梦想,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由于家道的变故,使其走科举应试这条人生之路成为一种奢望,而且由于家道的彻底中落,致使他继续完成学业都成为问题。因而,鲁迅最终无奈选择了与当时读书人相异的一条人生之路:“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一条被人称之为与科举制度相异的道路,“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鲁迅先生在科举应试理想破灭后,又在绝境中重新燃起新的人生梦想,诚然,这条学洋务之路也是鲁迅人生梦想中最无奈的选择。家道的中落,生活的窘迫与拮据,已经让其别无选择。鲁迅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办了八元的川资”,让鲁迅去矿务学堂读洋务。在南京读书期间,鲁迅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使其思想发生深刻的转变,原本完成学业的梦想又再一次被更改。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的人生之梦再次由完成学业转变为实业救国,他要学习医学,救治像父亲一样的病态躯体。从这段文字的表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其实业救国的梦想有着完美的憧憬。然而,由于仙台“幻灯片事件”,鲁迅先生不得不再次修正自己的人生理想,最终走上文学启蒙之路。由此看来,鲁迅先生早期人生之路充满着很多的梦想,在其人生的变故和不平凡的经历中,他不断修正着自我的人生方向,最终将自我的人生梦想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构建起早期的思想体系。
在文学启蒙的道路上,鲁迅梦想的实现也至为艰难。鲁迅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文艺运动,他邀约几个文学同仁共同创办《新生》杂志,想以文学的形式唤醒处于精神麻木的愚昧国民,对他们进行启蒙与拯救。而在当时众多的晚清留学生中,却难以找到几个从事文学的同仁,大多数留学生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选择实用学科“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种状况下,鲁迅还是找到几个有着文学理想的同仁,开展文学启蒙运动,但最终因为“逃走了资本”而使《新生》杂志夭折。这场文学启蒙运动的经历,使鲁迅深感在中国进行文学启蒙运动的艰难,以及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比寂寞与孤单。但他还是继续坚持自我的人生理想,坚定了自我的文学信念,与其弟周作人再度开展文学启蒙运动,进行翻译活动,合译《域外小说集》。从日本回国后,虽然沉寂近十年,应《新青年》杂志的约稿,他创作了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到1922年的《社戏》共十四篇小说,集结成《呐喊》小说集,重新走上以“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为核心的文学启蒙之路。鲁迅以“呐喊”为其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以期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面的麻木国民的灵魂,“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3](P212)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希望。同时,给革命的启蒙先驱以精神的慰藉和勇气,坚定他们勇往直前的不朽信念。在一次次受挫过程中,鲁迅不断对自我的人生梦想进行苦苦思索,不断进行自我的追问与反省,最终建构起以“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为核心的“人学”思想体系,完善着自我对中华民族最美人性的追寻。
在这篇序言中,鲁迅先生重复叙述着另外一个关键词——病。鲁迅从自己父亲的病谈起,对庸医误人的经历刻骨铭心,认为他们不仅无法消除病人的肉体痛苦,而且还给病者家人带来精神创伤。 《呐喊》中的两篇小说《药》、《明天》,描写了丧子之痛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当鲁迅先生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庸医误人的无比憎恨,这与其早年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渊源。但给鲁迅带来最深刻人生思索的还不是国民肉体之痛,而是数千年来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国民病态的灵魂。对于《呐喊》这部小说集里的人物,鲁迅曾说小说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P512)阿 Q、七斤、华老栓、闰土、单四嫂、孔乙己、陈士成……这群思想愚昧、精神麻木、满身陋病的旧中国国民,似乎从久远的历史中向我们走来,他们备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毫无觉醒,鲁迅正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以文学的启蒙唤醒这些沉睡中的愚弱国民的魂灵,探求着中华民族未来的脊梁。然而,鲁迅对病态国民的启蒙之路至为艰难,尤其是数次启蒙后,这些国民仍然表现出的“灵魂的沉默”,让鲁迅深感国民精神之病比肉体之病更可怕。因此,鲁迅在其作品中,也清醒地认识到对这些民众思想启蒙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要彻底改变愚昧民众的思想并非一日之功,在对国民启蒙的绝望中,他自身也进行着痛苦的思索与反省。《呐喊》中的几多篇章都体现着鲁迅对其文学启蒙运动的自我矛盾与自我质疑。如在《药》中,革命者夏瑜对狱卒红眼睛阿义进行启蒙时,我们难以忘却阿义“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是人话么?”的经典叫喊;在《故乡》中,鲁迅要搬家进城离开绍兴去北京,让童年的好友闰土来挑拣些需要的物品,闰土选择了“一副香炉和烛台”以及可以做沙地肥料的“所有草木灰”。闰土的这些选择使鲁迅深深体味到现代知识分子对民众启蒙的艰难,以及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在内心深处的巨大隔阂,鲁迅试图用自我的呐喊,唤醒闰土等这些沉睡中麻木国民的灵魂,催其走向新生。然而,闰土对鲁迅不理解,他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佑护中,以期来年取得好的收成。从这一视角而言,鲁迅以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并没有获得民众的真正理解,对民众的启蒙其实是知识分子实现了自我的启蒙,无奈中他们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哀叹这群“暂时坐稳了奴隶”[3](P212)的人们。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鲁迅这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众启蒙道路的无奈与无助,他们只能寄托于将来的知识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三
鲁迅的《呐喊·自序》,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窥视鲁迅内心世界的难得机会,一条鲁迅精神发展的明晰线索。”[1](P139)研究者在探求鲁迅早期思想体系发展历程的同时,探究出他毕生孜孜不倦地进行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真正原因。鲁迅以文学为工具对民众进行启蒙,总是将他的笔触聚焦于愚弱国民的灵魂深处,力求改变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深处的愚昧,唤醒沉睡在宗法制中国病态社会—— “铁屋子”里的沉默灵魂,洗涤、去除数千年来滞留于国民内心深处的封建思想,使他们成为精神和思想健全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未来“民族的脊梁”。
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已经开始思索国民性改造问题,那时鲁迅就常和他谈起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5](P39)由此而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这不仅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整体思考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也是其毕生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终追寻目标。正如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6](P226)为了这一历史使命,文学启蒙之路虽然艰难,面对国民“沉默的灵魂”,鲁迅并没有减弱国民拯救意识,他坚信“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痛苦,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7](P205)因而,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我的文学启蒙之路,探求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总之,通过对这篇序言的解析,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坎坷的人生经历,不断随时代、环境而变更的梦想。在感受生存的尊严与人生奋进的历程中,鲁迅精神一直充满着反抗与思索,对民族生存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变革抱着强烈的渴望。因而,要真正领悟到鲁迅先生忧愤深广的思想体系,就必须从这篇序言入手,以给予研究者更深层次的不懈思索。
[1]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李长之.鲁迅批判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许寿裳.回忆鲁迅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