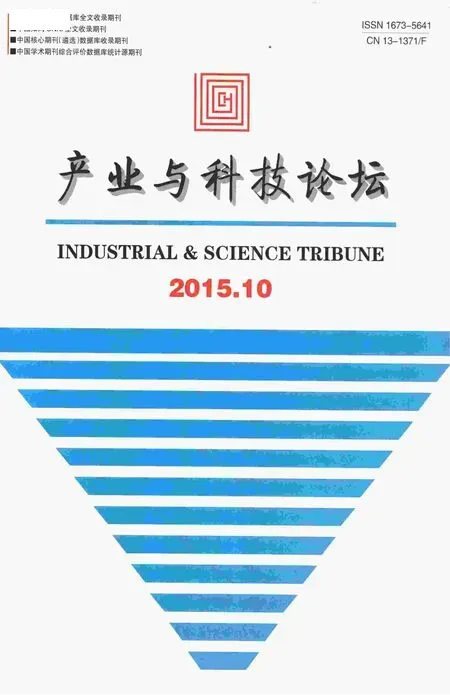宗法观念的悲剧:论《白鹿原》系列人物形象
□夏旭光
《白鹿原》这部家族小说不仅仅细腻地反映出50年间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纷争,更重要的是深层次地揭示出了传统宗法文化在时代变迁中与渐进的时代适应性问题。白鹿原人带着传统宗法观念立身行事,相应地导致了这样那样的悲剧。
一、“改良”陷入绝境
封建宗法制度历经动乱、革命、战争的冲击在中国大地的不同区域已经呈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崩溃与瓦解,宗法伦理的“吃人”本质已为觉醒的民众所认识,他们分别有相应的反抗和消解行为,老一代白鹿原人投入到了这个行列,进行了各自方式的“改良”。
(一)“圣人”之失路。朱先生是一位传统士绅的道德化身,立志要正民风,救民俗,对宗法文化进行全面的“改良”,使得“全身麻痹”的社会恢复到“浑身自如”的状态,并以自己的一生向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前进。可现实是,他空怀屠龙之技却到死都无真正施展之地,这是朱先生人生的悲剧。虽然他博学多闻,洞察世事,既具有历史的目光,又具有哲人的思维,甚至有预测未来(谶言其死后的一些情况)的能力,但在本质上他却还是一个在东方神秘传统宗法文化的面纱下矗立于白鹿原上的精神伟人。面对实际世务,在他的所有世界里找不到有效的疗救之法,悲哀地意识到已失希望之路。
(二)家族制约之失控。家族本位是作为地地道道农民的白嘉轩的主要思想依据,一生遵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信条,始终把它视之为治家、治族之法,他的“改良”也围绕着这个根本展开。他一生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把劳动当作了一种乐趣;修学堂让族人上学;力排众议,让女儿读书等等,用中国传统道德和规范“挺正,挺硬自己腰板”,以刚直构建着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可严峻的现实给了这个一生发展拓宽生存价值并使自己向更高层面整合的顽强农民一次次痛击:相当于他亲侄子的族人黑娃先带回一个进不了祠堂的下贱女人,后又干脆当了土匪;珍爱至极的女儿白灵脱离家族“离经叛道”去了;引以为傲的大儿子白孝文自甘堕落一度成为无赖;白鹿原上来来回回的政治风云变幻……作为族长一直坚持身体力行的族规所建树的威望动摇了;家族制约于人们失效了;“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般的中兴理想飘渺了……一身伤残的白嘉轩沉失在迷惘中。
(三)钻营投机之溃败。由厨师而来的发家史,决定了鹿子霖的“改良”和家族振兴观念中加入了很多的商业文化成分。他放纵自我享受人生,一味地追名逐利,为了像他祖先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人上人”,用尽心机,意识胆怯、卑琐。强迫大儿子鹿兆鹏与冷大夫女儿结婚,直接导致鹿兆鹏离家出走,儿媳常年独守空房。用计色诱白孝文堕落,损害白家脸面。他完完全全把女性当做泄欲的工具。不光从精神上折磨:借撒酒疯引诱儿媳妇直接导致其发疯,更主要是对弱势的女性肉体上的摧残——霸占堂媳妇田小娥,使原上许多女人成了他的情妇。借用商业手段,谋求“乡约”等职,勾结政府官僚,贪污粮款,鱼肉乡邻奸诈毒辣。用尽阴谋诡计的鹿子霖不仅在与白家长期的争斗中败下阵来,而且以疯狂、悲惨死去为最终的结局划上了悲剧符号,郑重表明了仅仅从家族本位和个人私利出发所做的“改良”显然是徒劳的。
(四)自发自觉之无奈。鹿三的一切自尊、自信和人生理念都被传统宗法家族观念所规劝,无论是情感还是物质他都只能依附白嘉轩而存在,他所能想到的前景就是作为传统宗法礼教和家族伦理典范的族长白嘉轩给他奴性自卑感以补偿(仁义的东家尊重他为兄弟一样的“人”、帮他安排儿子体面的娶亲等等)。在他东家白嘉轩的影响下,进行了不同于安分农民的“改良”:努力拔高自己,与东家白嘉轩几乎处成了兄弟;“交农”事件中自告奋勇代替东家冒着风险带头进城“交农具”;决绝地刺杀了伤风败俗的“儿媳”田小娥……最后的鹿三只能无奈接受自己的悲惨结局:儿子们没能有比他更好的生活际遇,自己在惊恐自责无望中猝死。
二、“叛逆”成了悖论
鹿兆鹏、鹿兆谦(黑娃)及白孝文等叛逆分子最先纷纷宣称要脱离旧家族、寻求自身独立发展,但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表明,传统宗法家族观念没能在他们身上完全摆脱,走向了以人为本位的叛逆道路,导致最后的悖论不得不引起人的深思。
(一)鹿兆鹏最终的“不了了之”。鹿兆鹏身处家族之中反家族,既对家族中的弊端表示出叛逆者的义愤,但无意中又意识到自己对家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愿做不孝的子孙。反对包办婚姻,却又屈从父亲完成结婚仪式,想要尽点为人子的孝道?对鹿冷氏的一生负不了责,却又把鹿冷氏从女孩变成了女人,想给鹿家留后?义无反顾地逃离鹿家,却又转身回原上引领革命,想荫及故里还是光宗耀祖?脱离鹿家断绝翁婿之情,却又甘于父亲鹿子霖及前岳父冷大夫的营救,亲情道义难以割舍?拥护自由恋爱,却又羞愧于对象白灵是名义上的弟媳身份,是有感于传统宗法里的孝悌之情?……最后,抛下了白鹿原上的一切远遁而不知所踪,是无法面对族人将要经受的煎熬?鹿兆鹏虽然从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传统宗法文化的回归,但几乎所有事情不了了之的结果证明了传统宗法文化与外来思潮在他身上的冲突,使他始终纠结在悖论之中,导致了失去家人、失去坚定、孤身一人不知所终的悲剧结果。
(二)黑娃的叛逆不是反传统。雇农这个阶级出身决定了和父亲鹿三一样,黑娃的血液里有很深的自卑情结。对这一自卑情结补偿与超越的不当,是导致他的人格分裂和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黑娃的悲剧人生经历可以被概括为:不安分的雇农——农运领袖——红军战士——聚啸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不管对黑娃的哪一个阶段进行分析,都不难发现他的所谓叛逆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反传统。大胆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的束缚,把真心喜欢曾为人妾的田小娥领回了家。掀起“风搅雪”运动、当土匪、砸祠堂和乡约碑,不断对富人和政府的权威发出挑战。特别是特意打折对他施尽仁爱的东家白嘉轩的腰杆,鲜明地显示出了他的畸形叛逆,他所要摧毁的正是白嘉轩的地主兼族长的富人优越地位形成的威严自他幼时起就开始的精神压迫。他拜朱先生为师,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诲,回归为顺民,到祠堂祭祖,让名字上族谱,彻底皈依为家族的孝子贤孙。黑娃前面所有的叛逆行为的最终目的,却是为挣得族人对他足够的尊严。这前后的对照,成为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现象。
(三)白孝文的“成功”不是喜剧。白孝文这个晚到的家族继承人是白家的希望和骄傲,严格的家教和传统宗法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他端庄、持重、文雅外形的同时,也搭建了其人性中的牢笼。如果说黑娃从压抑到爆发是渐进的过程,那么白孝文从压抑到裂变则犹如猛然从轰然倒塌的堤坝间一泻千里的洪水。他骤然间沦落为纵欲、吸毒、抛弃妻子、卖房卖地的败家子。与卑贱的黑娃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不同的是,白孝文沦落之后遭尽了世人的白眼和鄙视,濒于死亡的边缘挣扎之际,他的灵魂完成了异化。他画出了这样一段人生轨迹:压抑——裂变——异化——自强,制造出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悖论:宁愿堕落到卑贱,也要跟体面的传统决裂,可一有机会却又郑重地宣告对传统的皈依;本应是该遭唾弃鞭挞的卑鄙恶毒者,却堂而皇之地享受了胜利果实。
这样的两个悖论,给作品带来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来源于宗法传统的一个人性扭曲者失去道德的生存哲学为我们指引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白孝文的将来,但他那一套“翻云覆雨”在新现实中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所以说,白孝文的“成功”不是带泪的喜剧,而是一个时代悲剧。因为,个人不可能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当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对一个国家与民族造成悲剧时,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社会制度及它结构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就存在很多问题,作品正是以这样别具一格的视觉透视出了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法文化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困境。
三、敢问路在何方
白灵不仅仅是坚定勇敢无畏的女革命者形象,她的美丽和轻盈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是作品渲染出的亮色,其一生如同烟花绽放般短暂,但却散放出让人炫目的光彩。
作品构筑白灵这个清新新女性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阐释社会转型期女性要面对的解放和独立,而是更深层次地牵引我们的视线投放到宗法观念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上。不同于保守的改良做派和形式上的叛逆喧嚣,白灵的果决完全冲破了宗法观念的束缚,展开了全新的视野,爱情和事业演绎得轰轰烈烈。白灵就像呼啸奔驰的尖锐弹头,让我们看到了能撕破“宗法”这张大网的可能。但让白灵融入其中的革命阵营,也被裹入了这张大网受到种种的牵缠:盲目信奉、宗派倾轧、不切实际的冒险、原版照搬的教条行为、官僚享乐主义、不当的整风肃反运动……强劲的白灵也随之摆脱不了纠缠,深受其害而至最后的香消玉殒。
白灵这个独立、自主、抗争、坚韧、惹人无限怜爱女性消亡了,这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错误。只要宗法观念还在对革命发生着影响,一些类似的悲剧还将发生。作品给我们提出了疑问,突破这样的悲剧命运,真正的出路在何方?
不难发现,时代推进到了社会转型期,经过改良、叛逆或外来的新思潮影响下传统宗法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特质和本质内涵却充盈在作品的始终。族长白嘉轩极尽仁义地照顾他的族人,反复强调族群凝聚力和家族利益,黑娃和白孝文历尽艰辛也要把名字写上族谱说明了同宗、共谱、融融如春的血缘亲情是其基础出发点,鹿兆鹏转身回来领导原上的革命主要也是基于血缘亲情的考虑。朱先生反复劝说和感召黑娃,和白嘉轩一贯重视修订乡约督促乡民正视礼俗。白嘉轩定期带领族人郑重的祭祀仪式,黑娃和白孝文的回乡祭祖,原上诸人效法先祖“善”、“贤”、“功”等优秀品性,以祖宗在天之灵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力无不阐释了崇祖、法古在宗法观念里的分量。宗派主义等在革命队伍里蔓延,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错误。这种浓浓的宗法气息的包裹,从表面上显露出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和谐、执两用中、崇德利用、礼仪仁智信、温良恭谦让的影像,但内在的影响导致作品中的系列人物有了相应的悲剧行为和悲剧命运,表现出了相应的悲剧性,不得不引起人们对其本质内涵的质疑和其在新时代流变走向的郑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