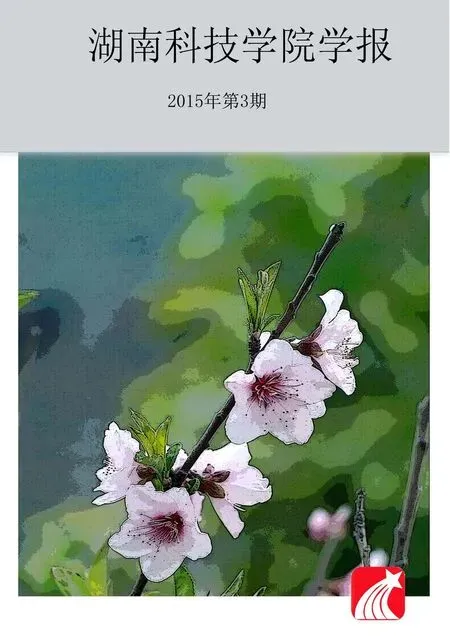鲁迅《伤逝》的叙事情境探析
周艳华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425199)
叙事学理论认为,任何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叙述者。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和故事的关系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是异常复杂的。故事讲述者和故事的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作品在读者身上唤起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因此叙 述者如何讲述故事非常重要。另外叙述者本身也至关重要。西方小说理论家把这种种问题归结为一个叙事角度问题,认为这就是小说技巧的关键,勒伯克认为叙事角度就是“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在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用“叙事情境”取代“角度”来阐明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叙事情境分为三种: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三项即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和叙事聚焦。根据叙事学的分类标准和对各个类别的内涵外延的界定我们可以判定鲁迅的小说《伤逝》属于第一人称叙事情境,是采用内部聚焦“讲述”(telling)型的叙事作品。
一
《伤逝》的第一段就写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里的“我”就是“涓生”。他是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的主人公,主人公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是完全统一的。这就构成了“主人公”类型的第一人称叙事情境。这种情境让我们跟着叙事者去经历他的经历,感受他的感受,幸福他的幸福,悲哀他的悲哀,我们自己似乎也经历了爱的期待幸福幻灭与悲哀。有时候甚至不知道那个“我”究竟是故事中的“我”还是正在阅读作为读者的我了。这种感同身受的真实感是第一人称叙事情境的优越性所在。
《伤逝》的主人公“我”即涓生是该小说的聚焦者,他存在于故事内部,是故事中的人物,因此该叙事作品是内部聚焦式的叙事作品。以下面一段引文为例: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同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在这段文本中,“我”就是一个“反映者”性格,读者是通过他的眼光来观看屋子、窗、屋内摆设和窗外的景色,通过他的感觉感受一年前和现在的寂静和空虚,读者还可以间接看到涓生内心的忧郁和怅惘。通观全篇作者采取的都是典型的人物内部聚焦,我们观察和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借涓生的眼光、感受思考获得的,决不比涓生所能知道的多一丝一毫。通过涓生我们看到了两位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慷慨激昂,看到了他们冲破旧制度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潇洒高傲,看到了他们爱的幸福。通过涓生,我们也看到在封建制依然牢固的情况下他们遭受的讥笑和轻蔑,经济窘迫,以及随着爱情追求的成功而导致爱的内容的逐渐虚空以至于完全丧失。同样通过涓生我们看到子君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果断与坚决到“怯弱”再到“凄然”一步一步丧失爱和奋斗的勇气变得平庸而懦弱的过程。作者采取这种内聚焦式的叙事方式显然有他的意图,通过涓生之口有选择有提炼地表达生活经历和感受,也就是主要围绕爱情的历程和子君的变化来叙事,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小说的主题——“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句真理似的话,涓生是早已明了的,不明白的人是子君,因此小说叙事这种内部聚焦式显然通过涓生的口和心批判了女性的不彻底觉醒,不独立,为爱而爱,失去自我,依附男人。
二
如果从叙事方式的角度来分析,《伤逝》显然是属于“讲述”型的。涓生从头至尾“始终以自己的名义讲话”,他记录、讲述,对他自己的爱情故事作出种种评论解释如“这些地方,子君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几句话很震撼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曙色的”。好像是在与读者交谈。小说具有明显的叙事者性格,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叙述偏向于叙述自我,对叙事行为本身有较清醒,较自觉的认识。叙述者涓生总是以“传达者”自居,时刻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传达给读者。他牢牢地控制和驾奴着故事,把他纷繁复杂的爱情经历串联为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写自己怎样与子君相知、相恋、结合、分手。涓生还经常抛头露面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加以解释,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穿针引线。如对于自己的爱上子君的原因他其实也已交代清楚——“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后面之所以不爱就是因为“她的勇气都失掉了”。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是为了使文本的意义更明确,涓生的“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都直接点明了文本的主题。故事的主人公涓生既作为故事人物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采用“讲述”的叙事方式,“我”的过去和“我”的现在通过“我”的讲述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我”时而直抒胸臆——“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表现出对爱情甜蜜时无比温馨的向往;“我想,多么容易改变呵”表现自己对于子君的怯弱产生的失落情绪——时而进行理性的反思——“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他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对自己的错误决定表示悔恨,现在才意识到女子大多因为爱才会英勇无畏,至于对待其他更宽广的内容,比如“生路”方面就不一定能那样了。“我”后悔自己把真实说得太快也失望于子君的不理解。“我”的“讲述”处处充满着强烈的情感和严肃的反思,使读者在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对比中看到“我”的成长和矛盾。
三
如上所述,诚然,第一人称的叙事情境,让我们似乎可以直接从叙事者的语言中得到故事的主题。我们感到涓生对于生命的真诚,感到他骨子里悲哀,爱导致了子君的空虚和死亡,涓生的空虚和悲哀。爱已成空虚。涓生需要像他自己一样的真诚勇猛的战士,否则就只有孤军奋战。整篇小说饱含着对真爱、觉醒的渴望和女性能够真正独立、觉醒、坚强的殷殷期望。然而,事实上读者并非真正会无条件的信赖叙述者尤其是他的情感与反思。从整体上说,这篇爱情小说采用此种叙事情境掩盖了爱情平等的另一方子君,这本身就意味着涓生一个人的片面之词。
西方的西蒙·波伏娃曾这样谈及婚姻和爱情:“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爱情必须建立在两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开放的社会生活中,否则就会倾斜和倒塌。”而《伤逝》则显然是涓生倾吐苦水般的悲怨后悔情绪,我们透过叙事中“我”的这一层屏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便可以发现虽然小说开篇就说“悔恨”,其实涓生并没有真正的悔恨,对于子君的死也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悔恨。在讲述中,涓生直呼其名——子君,是一种审视和居高临下式的语气。涓生对于爱情的期待是寻求完美的契合,一旦发现对方不合己意,就急于离弃,完全丧失了耐心,哪怕是想到了对方的死。仔细斟酌一下,子君的那一点“勇敢和无畏”大多由于涓生的觉醒及他的熏陶,因为起初她是个“总是微笑”、“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光泽”的善良,单纯,也可以说不怎么觉悟的大家闺秀。因此她受旧制度的禁锢和压迫更深,受封建礼教的管教更严密。然而,就为着爱,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丰足的家庭,蔑视鄙夷和不解愚昧的群众,她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她本身并不是怯弱的,或者说她是有极大的潜在力量的,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怯弱和日渐一日的庸俗化呢,她“凄然”、“凄惨”、“凄苦”的神情从何而来,涓生是以为怯弱了,经济窘迫而害怕了。这些并非是完全无关的因素,但我恐怕最根本的是失望于爱。涓生不能说没有责任,他一味地用自己理想中的模式去套子君,一开始之所以有那样热烈而纯真的爱,是以为在子君身上自己的理想对象化了,当真正结合后,他发现了隔膜也就是发现子君与自己理想不合拍。于是,采取家长式的教育甚至抱以责备的神情,最后干脆逃离,他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成长和觉悟需要一个过程,要长成像他那样的战士是需要时间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急于求成,不去承担爱的责任和人生的重担,反而一味想远走高飞,把自己没有走上“新路”的责任推到子君身上,甚至想到了子君的死也还是不顾后果说出了他的“真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怯弱。是他直接把子君推上了绝路。
总之,《伤逝》中的子君是涓生眼中的子君而不是真正的子君。我们应该得到启示——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哪怕是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而真正的爱,是一种意志行为,是两个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素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生命的呼唤和应答,生命的承诺和相托。因此,勇气、智慧、责任、沟通、合作、互补等等便是男女之爱,便是这种爱的结合形式——爱情婚姻不可缺少的内容。爱只有一个证明,两个自由、独立的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便是两个人的自由和欢乐,便是从生活实践中体验到他们自己,体验到他们身上的生气和力量,这是对相爱的人的勇气、智慧、能力、责任感的挑战。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美]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康格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凌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郑晓.从两性的自我意识解读鲁迅的《伤逝》[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