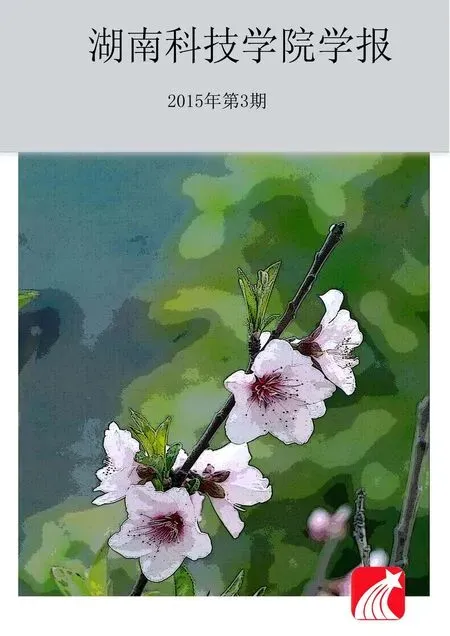明代心学家钱绪山的生死智慧
刘蓉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一 阳明心学与生死学
儒学自创立以来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蜕变出不同的形态,宋代儒学吸收佛道思想转化出“理学”,明代儒学将关注点由外在的“天理”转向内在的“良知”蜕变出“心学”,人把握本体的路径从吸取外在的知识转变为探索内在 的觉悟。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将儒家的学术形态开创出崭新的面貌,阳明心学在明朝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哲学里特别强调生命感的思想发展至高峰,“涵养心性”已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的议题,更是灵性整合的议题,灵性议题的“涵养心性”,更注重个人内在体验里对存有的领悟[1]。这种特质贯穿在王阳明个人的悟道经验里。
中国当代生死学由学者傅伟勋教授所创立,其来源是西方的死亡学(Thanatology),而傅伟勋结合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智慧,开创出了中国本土的现代生死学,与死亡学不同的是,生死学不只是关注死亡的问题,而是将生与死看作人的生命的一体两面,透过死亡来感悟如何更好的生存,完成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死亡是生命的终点,生死学的意义是教给人站在死亡的终点,回看人生在世的点点滴滴,产生带有灵性的生命态度。生死学的这种特性与心学中的悟道路径很相似,即破除自我的执着恢复自性的本真,在这条路径里,人所经历的生死考验都为促进自性觉醒有重要推动作用。
傅伟勋曾指出,宋明理学家已经不再依循孔子谈生不谈死的态度,有逐渐建立“新儒家生死学”的思维趋势,王阳明的心学为此一生死学的开展尽过最大的努力。[2]91我们检视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不难发现他所领悟到的心学观念,不论是被贬贵州后的“龙场悟道”悟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还是平定宁王叛乱之后的“致良知”,都是从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体悟出来的。因此,王阳明会说自己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所以他也告诫弟子们,不可只看到他提出的工夫的简易直截,就误以为心学这门学问容易。王阳明的悟道经历及谆谆教诲,对阳明后学的影响很大,使得他们也会注重透过生死问题来悟道。这种悟道的路径也深深影响着以阳明弟子群为主的阳明后学,从阳明嫡传弟子王龙溪、王艮以至晚明刘宗周、李贽等无不将生死问题视作儒家终极关怀的内在向度,死亡已经不再是儒者讳言的问题,而是成为关联于圣人之道的一项重要指标[3]131。彭国翔还提出,阳明学者关注生死问题,与当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导致他们经常要面临生死绝境,钱绪山即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位。
钱德洪,本名宽,字德洪,后改字为名,号绪山,世称绪山先生。钱绪山是浙江余姚人,出生地点正是王阳明出生的瑞云楼,正德十六年九月,率朋友子侄等七十四人在余姚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后成为王阳明晚年重要的弟子,并且在其师去世之后致力于整理心学的文献,在各地讲学,直至生命的终结。钱绪山跟随王阳明学习,所要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如何修养心性来领悟本体,王阳明围绕这个问题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工夫来教导人,每一种工夫的领悟都是由他在当时的生命境遇中所引发,钱绪山的悟道历程同样需要有这种因缘的触发,来发生突破性的进展,而不只是对王阳明的思想观念作知识性的吸收,在这些触发他悟道的因缘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分为两个向度:一是个人的面对死亡经历,二是面对亲人死亡的态度。
二 钱绪山的死亡体验
钱绪山本人面临死亡威胁的经验,是发生在嘉靖二十年(1541),钱绪山上疏弹劾翊国公郭勋,蒙帝召不往,钱绪山上疏弹劾郭勋罪状,被下锦衣卫监狱。王龙溪在《绪山钱君行状》里记载这件事:“是冬,严冰坼地,积雪盈圜,君身婴三木,自分必死,独念亲倚庐,无缘面诀,魂飞荧荧,遍照圜宇,乃自叹曰:‘吾在柙中,四肢且不能保,思亲数千里外,不亦幻乎?’洒然一空,鼾声彻旦,日与斛山杨侍郎、白楼赵都督读书谈道。”[4]410嘉靖朝君臣猜忌严重,朝政气氛紧张,钱绪山此次入狱,以为自己不再有生还的希望,唯一的挂念是家中的亲人,却很可能不能再相见,他坠入极度的痛苦中,然而在这绝望的痛苦中他却有一种超脱的感受:困在监狱中,四肢尚且不能保全,却思念千里外的亲人,难道不是一种幻觉?于是觉心中洒然一空,坦然入睡,并开始与狱中读书论道。这件事情对于钱绪山的生命转变有重要影响,后来他意外获得明世宗的赦免,回到家乡,在写给朋友赵贞吉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带给他的影响,说:“洪昔幸待,未尽请益,继遭罪难,颇觉有所醒悟……洪赋质鲁钝,向来习陋未除,误认意见为本体。意见习累,相为起灭,虽百倍惩克,而于此体终隔程途,无有洒然了彻之期。耽搁岁月,浑不自知。上天为我悯念,设此危机,示我生死真境,始于此体豁然若有脱悟,乃知真性本来自足,不涉安排。”[4]158-159他在这里说明了自己醒悟到,之前误认意见为本体,直到经历这次的生死危机,才体会到“真性本来自足,不涉安排”,这句话很容易和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悟道内容联系起来,可以说钱绪山有了这层体验,才真正领悟本体。如果将阳明心学学者的悟道之路视为个体经验为主的灵性探索之路,那么钱绪山的灵性生命到此时才获得开显。
然而,为何经历死亡的体验能够促使他产生这种质变呢?从生死学的角度来看,余德慧曾指出,生命实相有三个位阶:身体实相、自我实相、灵性实相,当身体实相开始毁败,自我实相也开始消融,灵性实相就会开始进行开显的过程。灵性这种存在状态,是面临死亡的人在心性上开显的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5]102,不同于往常以自我实相存在状态为主的是,在这个时候,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真实(财富、地位、知识、技术、社会关系),都不再重要,人开始愿意放弃这些自我的实相,转化到另一种活的契机,在灵性缔结的过程中,看到未来希望的微光[5]59。当人的自我心智瓦解,就不再害怕死亡,因为那个害怕死亡的自我已经不见了,接着会进入到浩瀚的宇宙感中。(前文已经提到,传统的儒家教育进行的是一种道德教化,意义在于完成人的道德人格,心学这种新儒家的出现开启了灵性整合的意义,心学也讲求善,而这种善已经不同于世俗标准的善恶。余德慧指出,一般世间性的道德属于自我实现的锻炼,而临终的良善属于自我的消融。阳明心学所讲的“至善”,即是属于消融自我之后的良善,它直接由“谛念”发出,不迎合于世间的善恶标准。)钱绪山在狱中备受身体的折磨,要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这个过程是他消磨掉自我实相的过程,他对地位名利之类早已置之度外,当他把最后的“社会关系”亲情也看破,就转入到了精神层面的灵性缔结里,他称这种实证本体的境界为“生死真境”,说明他彻底看破了自我意识,而到达超越个体的某种同体意识,也即余德慧所说“经历自我人格解组,却因而发现一种前所未曾经历过的存有风光”[5]60,也是宋明儒学家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状态,陈复先生称这种体验为“顿然与本体合一的彻念”。
钱绪山本人对这次突破性的感悟也非常看重,把它当作自己思想变化的分水岭:“龙溪学日平实,每于毁誉纷冗中,益见奋惕。弟向与意见不同,虽承老师遗命,相取为益,终与入处异路,未见浑接一体。归来屡经多故,不肖始能纯信本心,龙溪亦于事上肯自磨涤,自此正相当。”[4]153陈复先生指出,这段话反映了钱绪山体证本体前后的差异。这里的差异涉及到钱绪山与王龙溪两位重要的王门弟子对王阳明教旨的理解有所不同,王龙溪主张“悟本体即是工夫”,强调人的个人体悟,钱绪山认为应该通过做为善去恶的工夫来领悟本体,对于他们的意见分歧,王阳明曾嘱咐:“汝中(王龙溪)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王龙溪颖悟过人,早年便证得本体。(徐阶《龙溪王先生传》:“请终身受业于文成。文成为治静室,居之逾年,遂悟虚灵感寂,通一无二之旨。”[6]823)证悟本体时间的早晚,并不能作为判定二人思想高低优劣的标准,王龙溪也需要透过具体的工夫来使心性更为纯熟,钱绪山自此开始“纯信本心”,与王龙溪的观点交会融合,可以视作他思想成熟后的基本主张[1]。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一般世间性的善恶,走向了“依心性存有的善”,这种善是诚挚、清朗、正大、光明的本体,依照前者的准则做为善去恶的工夫,属于自我实现的锻炼,体悟到后者的善,是自我的消融后的显现。
钱绪山有多处文字记载了自己证悟本体前后思想的改变:“念庵曰:‘绪山之学数变,其始也,有见于为善去恶者,以为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又曰:‘向吾之言犹二也,非一也。夫子尝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也;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吾者常一矣。’”[7]225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钱绪山之前以为致良知是作为善去恶的工夫,当他实证本体后,才能理解到王龙溪对王阳明“四句教”所执的“四无说”,即本体本来无善无恶,对根本自性的证悟,并不是靠为善去恶的工夫来得到的。所以他会说自己之前的见解趋于支离,不是合于本体之“一”,在善与恶的意念发出之前的源头,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本体,有意念发出即谓之“动”,没有意念发出的“无动无衷”的状态,是“常一”的本体。所以,死亡经验产生的彻念让钱绪山有实证本体的领会,发生的改变就是他不再在意于人世间的标准区隔出的善恶,而是让精神收摄在意念未发之前的本体(良知)中,这一体会对他之后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钱绪山证悟本体之后更注重直入本心的体悟,从他晚年因为修订王阳明年谱与同门的往来书信中也可看出:“吾党见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证,未宜轻以示人。恐学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体,作一景象,非徒无益,是障之也。……至道非以言传,至德非以言入也。故历勘古训,凡为愚夫愚妇立法者,皆圣人之言也。为圣人阐道妙、发性真者,皆贤人之言也。”[4]207这段话可与早年王阳明告诫钱绪山的话作对比:“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8]132王阳明这段话可对钱绪山提出“为愚夫愚妇立法”的原因做很好的注解,愚夫愚妇没有知识的障碍,更容易活在直达本心的状态里,当一个人能够向愚夫愚妇传道,就掌握了圣学不落言筌的奥妙。钱绪山早年因为有知识障,所以会拿出一些高明的见解来讲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晚年证悟本体之后,则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障碍,才会指出真正的大道是不能用语言来传递的,能为愚夫愚妇设立教法的人,才是在说真正的圣人言论,只是顺着先前圣人的言论继续发明其奥义的人,说的只是贤人的言论。对于钱绪山这样的讲学方式,晚明儒学大师刘宗周评价他:“夫不离愚夫愚妇而直证道真,彻上下而一之者,其惟‘良知’二字乎!……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始。”[4]458刘宗周认为,正是由于钱绪山不在意自己提出的言论看上去是否高明,而是能否引领人直接领悟本体,才使得钱绪山的思想更容易让人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或许正是因为这一重要感悟,钱绪山的文献记录没有被大量完整的保存下来,因为他早已不在乎自己的言论能否留存于世,语言容易引起人在知识见解上的分歧,无助于对本体的体悟,所以他更愿意做实际的奋勉来实践大道。
三 钱绪山看待死亡的态度
关于儒家对待生死的态度,孟子曾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劳思光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只需要致力于修身,不应当忧虑寿命的长短,当人的超脱生死问题的困扰,就是在“立命”了。儒家看重的是人生在世,能否活出天命,注重生命意义在世间的实践,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并不是由物理时间来衡量,个体生命的死亡,也许并非生命的终结,他的精神不死,就是死而未亡。这种生死态度对钱绪山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钱绪山个人的生死观里,也体现在他面对亲人死亡时的态度。
钱绪山的一生中有数次面对亲人死亡的经验,这里说的亲人不止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包括他在精神上的亲人。钱绪山首先面对的,是他精神上的亲人——其师王阳明的去世。钱绪山与王阳明感情极深,从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归乡讲学,钱绪山跟随他学习七年:“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4]187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刻的情感,当听到王阳明去世的消息时,钱绪山“闻之昏殒愦绝,不知所答……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赎,而顾萎吾夫子耶!日夜痛哭,病不能兴”。可见王阳明的死亡对钱绪山是致命的打击,几乎到了生不如死的绝境。从生死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自我有一大部分是由他人映照在自我所构成的,他人的亡故可以使他们映照在我们自我的部分发生晃动,而变动我们的心情。他人的死亡也促动我的死亡急迫感。[5]85很显然,王阳明的死亡晃动了钱绪山之前所赖以生存的由“心智自我”所构成的世界,让他的生命掉落到深渊里,他原来所熟悉全部存在都在发生断裂,那个原本美好的存在,他不再能拥有与把握。[9]然而钱绪山对王阳明除了情感上的紧密连结,更有道业上的深度传承关系,这样的双重关系使得即使是王阳明去世后,他们的生命依然是连结在一起的,钱绪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他与老师的“共命”延续下去,具体的做法就整理阳明遗书,兴办书院,广开讲会:“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众,夫子遗书之存,《五经》有删正,《四书》有傍注,传习有录,文有文录,诗有诗录,政事有政事录,亦足恃矣。是夫子虽没,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遗书,百世以俟圣人,断断乎知其不可易也。明发踰玉山,水陆兼程,以寻吾夫子游魂,收其遗书。归襄大事于稽山之麓,与其弟侄子姓及我书院同志筑室于场,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4]217钱绪山后来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整理出了王阳明年谱,并将遗书整理出版,为阳明学的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若没有他的奋勉,后人恐难以看到王阳明思想得以如此完整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确完成了与其师的一体化的生命意义,使王阳明的肉体湮灭后,精神得以继续存在。
钱绪山晚年出狱之后,面临的又一场生离死别,是他的父亲钱蒙的去世。值得注意的是,钱绪山家族与心学的关系很密切,钱明指出,他的家族成员大都在他的影响下成为阳明的追随者或信奉者,他的父亲是阳明所倾心的地方贤达,也得到诸多阳明学者的认可,他们甚至在宗族活动中举办讲会[10]186-188。能够形成这样的宗族氛围,可见钱绪山很注重家庭和道业的结合。钱蒙对钱绪山学习心学这件事,起初心存疑虑,认为会妨碍他考科举:“公笃信阳明公,尽弃其学而学焉。心渔翁患妨举业,颇不乐。”后来钱蒙向王阳明请教这个问题,王阳明回答:“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之后钱德洪果然考中进士,钱蒙才疑虑顿消,并且很支持,从钱绪山为王阳明服丧的事件中可见一斑:“宽也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驰书心渔翁,具陈父生师教,愿为服丧。翁曰:‘吾贫,冀禄养,然岂忍以贫故,俾儿薄其师耶。’许之。”钱蒙十分理解他的儿子对老师的感情,因此愿意成全儿子为其师服丧的心愿,这种成全背后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亲情,别具一番“大道之情”的意味,钱绪山身上所承担的“师教”与“亲恩”得以“并行不悖”,钱山与他父亲的生命,也因此更无间的融合在一起,钱绪山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感情:“使亲知我易,使亲忘我难,吾父子之间,庶几其忘矣。”正是因为两人的生命不再有你我的区隔,才会“相忘”。当钱蒙去世后,钱绪山并没有按照当时的要求服丧三年,而是在各地讲学。因为钱绪山是一位心学家,他早就发愿要继承其师的遗志,不遗余力阐发并实践心学,这是他要延续王阳明的生命的方式,当他的父亲去世、后,他要做的则是将三人的生命共同延续下去,他要将父亲的生命放进自己的生命里,一起开展自己的志业,他要用这种方法打破生死的界限。钱绪山有这样违背世俗的举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在狱中洞见本体,使他不再刻意依循世俗的善恶标准来规范自己的举止,因为他已经看破世间的名相,直接由本体来发出至善的举动,这样的行为来自于他对本体的实证,所以当他因此受到抨击也不为所动。他的心愿是将先师的遗志、父亲的成全爱护之心,与自己的志向合而为一,让自己的肉身实践出三人共同的生命,这远比遵守世俗的道德秩序更有意义。钱绪山对本体的感应,使其对良知的认识完全超越社会价值与其道德规范,而是在天人交互感应里,觅得个体行为的自律标准。[1]
到了晚年,钱绪山面对的生死问题更为残酷,从嘉靖三十九年到嘉靖四十三年间,他先后面对五位亲人的过世,除妻子外,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钱绪山在写给妻子的墓志铭中说:“五年之内五丧相仍,谁兹卜兆,三丧并举且同穴也。使我以座老之年临之,将何以为情耶?造化脗茫,无心相值,入我以无何有之乡,示我以未始有生之始,其死若梦,其生若觉,觉梦代禅,昼夜相错,谁毁而成?孰悲而乐?惟吾良知,超生出死,为万物纪,历千载而无今昨,吾又乌能以尔动吾之衷,龊龊索索,为呰为唶也乎哉!”(《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文录》)面对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悲痛,钱绪山没有过度沉溺在个人的悲伤情绪里,他再度在上天给予的考验里获得超越性的体悟,唯有紧紧把握住良知(本体),才能超越生死、时间的限制。这里再次引用生死学的说法来看,心学谈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行事中获致“本我的锻炼”以成“大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其中包含了“社会伦理”以及“心性存有”两个方面,心性存有是把人处于世的困顿向上抒发,在浊世中获致一片青天,社会伦理则是在纷扰的人世间磨练,中国心学家面对个人的困顿受苦,一方面讲本心感通的精神出路,但却不因此而出离人世,而是在社会困局中磨练本我,将其视为个人转化“仁熟”的源泉。[5]231总之,心学的目标是在纷扰的世间获得心性的锻炼以完成本我,既能有超拔的心性,又能安身立命。钱绪山在如此艰难的困境里,透过深刻把握良知来超越痛苦。他的“无动于衷”并不是无情的表现,而是反应了他已经深度把握本体,跨越了生死的壁垒,不再因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动摇本心。
学者郑晓江说:“儒家在生死问题上一直避免谈死亡,直到阳明之学横空出世,生死之学才大明于天下。”[11]可见生死之学在阳明心学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死问题并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色彩,王阳明与钱绪山都是从生死体验中证悟良知,并带着良知的觉醒来面对生死。我们从钱绪山的个人经历来剖析他的生死体验与生死观对他生命的影响,对于王阳明良知学的探析有重要的启发。
[1]陈复.钱绪山心学的生命教育:死亡经验对其思想的反省与启发[J].本土心理学研究,2010,(34).
[2]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钱明.徐爱·钱德洪·董澐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余德慧.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M].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
[6]王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陈复.濒临死亡产生的彻念:钱绪山对生命意义的阐释与实践[J].生死学研究,2012,(13).
[10]钱明.浙中王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1]郑晓江.“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J].中州学刊,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