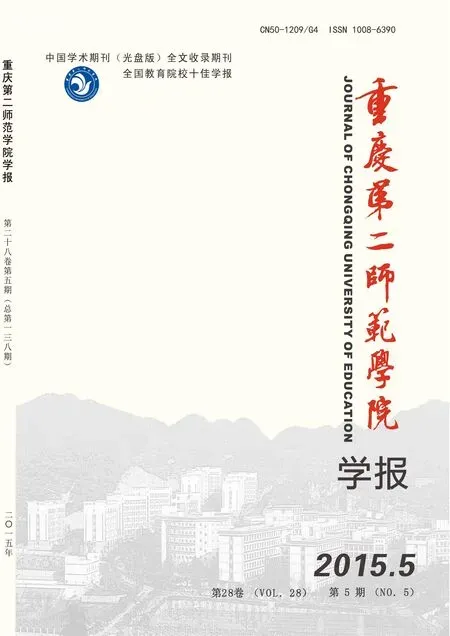“惊人之处在于发生的方式”——接受美学视角下《逃离》中的隐含读者
“惊人之处在于发生的方式”——接受美学视角下《逃离》中的隐含读者
谢晓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本文以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隐含读者为理论观照点,从文本语言的缺省及模糊性情节的留白、隐喻的使用、开放性的结局等三个层面,分析了艾丽丝·门罗小说《逃离》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肯定了文本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活力,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
关键词:逃离;隐含读者;接受美学
收稿日期:2015-05-13
作者简介:谢晓(1986- ),女,河南平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90-04
一、前言
英国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把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的阶段。”[1]可以这么说,20世纪文学理论界的成就之一便是把读者这一维度拉进文学批评,并肯定读者的地位和其在构建文学作品意义中的作用,弥补了作者、作品客观性研究倾向的不足。
《逃离》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并于小说出版当年(2004年)获得加拿大文学大奖吉勒奖。该书由《世界文学》杂志编委李文俊先生翻译,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翻译出版的门罗小说译文集。目前国内外批评家和学者对《逃离》这部小说集的文论批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的主题、叙事策略、女性主义、写作风格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2],本文拟从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理论出发,选取小说集《逃离》中的同名作品《逃离》作为研究文本,以伊瑟尔提出的隐含读者这一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来探究读者的阅读活动和文本的互动过程中文学作品意义的实现,挖掘门罗小说作品“惊人之处在于发生的方式”的内在魅力。
二、理论基础:接受美学与伊瑟尔
本文以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的隐含读者为理论观照点。
(一)接受美学
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接受美学一经问世便对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予以坚决否定,对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传统进行反驳,开创了“读者时代”的先河。接受美学批评家认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三者关系中,大众绝不是被动的存在。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它的历史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能动地参与和解读,作品才算真正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3]在伊瑟尔看来,作品意义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挖掘,未被读者阅读之前的文本,仅仅只是作者预设的图式化结构,包含许多“空白点”“未定点”和“否定性”,等待着读者自身的参与,同时也唤起读者对文本的持续关注和审美解读。
(二)沃尔夫冈·伊瑟尔和“隐含读者”
沃尔夫冈·伊瑟尔是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并称为接受美学的“双子星座”。他们一起建立了德国的接受美学,率先从事文学的接受研究,强调读者在文学批评和鉴赏中的地位与作用。伊瑟尔不同于姚斯站在社会历史的广阔视野下对文学接受作宏观的研究,而是从具体的阅读审美反应入手对文学接受进行微观研究,关注接受过程中文本和读者的交流性,采用现象学分析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
在《阅读行为》一书中,伊瑟尔论及“文学作品可以分为艺术极和审美极:前者是作家所创作的文本,而后者则是读者对文本的实现。”[4]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实现的,表明文本内部本身存在能够被读者接受理解的条件,允许文本意义在接受者头脑中显示,即文本结构中存在一种预先设计的交流模式以及读者在实际阅读中对这种潜在模式的实现。由此,伊瑟尔结合自己的阅读理论提出了“隐含读者”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独特的理论长处,它将关注点放置于读者所具有的交流潜势之上,而不再对实际读者本身进行理论概括,由此便摆脱了实际读者因其具有异质性而极难进行概括这一困境,使得隐含读者可以用来阐释一切读者及其阅读活动。伊瑟尔指出,分析理解一部文学作品所达到的效果和引起的反应,读者的存在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而读者的个性和其存在的历史情境又不能预先设定,我们姑且称此类读者为隐在读者。他是一部文学作品发挥作用的必要的先在条件,他不是由读者经验的外在现实决定的,而是受制于文本自身。因此,作为一个先在倾向性存在的隐在读者,是文学文本中的结构性存在;是思维的产物,决不可与任何实际读者等同。[5]在此,隐含读者概念的提出以E.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先验模式,隐含读者这一模型使我们得以描述文学文本的结构效能,其由互相关联的两个部分所组成——对文本潜在意义的预先建构和读者的阅读活动对这些潜在意义的现实化。
本文尝试运用伊瑟尔的隐含读者理论,即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分析艾丽丝·门罗小说《逃离》中自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构和机制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如何现实化,使读者领会到门罗小说“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冷峻与有力。
三、小说《逃离》中的隐含读者
本文通过探讨该小说中潜在的隐含读者,分析作者在小说中从文本语言的缺省及模糊性情节的留白、隐喻的使用、开放性的结局这三个层面,如何为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接受、审美空间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层面来召唤读者进行“填补”和“再创造”,探讨作者预先建构的文本潜在意义如何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现实化。
(一)文本语言的缺省和模糊性情节的留白
在阅读文学文本过程中,读者会发现语言的缺省(omission)和情节的模糊(ambiguity)是常见之事,这些缺省和模糊的出现,一般是作者的有意而为,以此来召唤读者进入文本,引发读者的阅读活动,唤醒读者的想象力并积极参与艺术的再创造(recreation)。
《逃离》的整个故事由四个章节组成,讲述的是小镇女孩卡拉(Carla)当初逃离家庭,想要追求一种“真正的生活”而与马术训练师克拉克(Clark)私奔。两人在乡下经营一个马棚并养了一只宠物山羊——弗洛拉(Flora)。因家庭生活中难以启齿的苦痛,得到邻居西尔维娅(Sylvia)同情和帮助的卡拉决定离开丈夫,出逃前往多伦多。但最终却因对离开克拉克之后未知未来的恐惧,在她乘坐的大巴尚未驶出三个城镇时就打电话央求丈夫接她回家,重新回到克拉克身边。而卡拉的邻居西尔维娅,在帮助卡拉出逃失败后,搬离了小镇,住进了大学城的公寓。而卡拉夫妇失而复得的小山羊弗洛拉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说情节简单,但门罗在故事中预先设置简练、无疾而终的对话,不动声色地白描似的刻画男女主人公零碎、断裂的生活片段,处处留白,以有限的文字激发读者无穷的想象力,给读者留下诸多参与的空间,引起读者好奇心,自动补充情节,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故事的绝妙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
在第三章中,卡拉通过邻居西尔维娅的帮助,乘坐大巴前往多伦多,然而逃离途中却半道折回,在本章结尾处,仅有一句对话:“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我这就来。”[6]36此处门罗对讲话人故意隐而不说,但读者通过上下语境,知晓这是“逃而未离”的卡拉与丈夫克拉克之间的一求一应。按照读者期待视野,下文无疑是克拉克接卡拉回家,夫妇俩的谈话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活动。然而,第三章戛然而止,克拉克到底对卡拉说了什么,读者无从得知。叙事进程中断,叙述者突然笔锋一转,第四章开头便是“西尔维娅方才忘了锁门”[6]36,紧接的却是第二章结尾处的叙事断点,即在帮助卡拉出逃并送别之后,西尔维娅归家却无法入眠,直至深夜刚要入睡却听到敲门声,叙述者以“卡拉?”独立成段,故事进程暂停,第二章就此结束。阅读到此的读者产生疑问:难道真的是卡拉?她不是去往多伦多了吗?怎么又半道折回了呢?在途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作家并没有给读者留下遐想和疑问的时间,随即进入下一个章节。第四章开始,叙事的镜头对准乘坐大巴前往多伦多的卡拉。从故事情节发展来看,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之间应是克拉克接卡拉回家。在前文中,门罗有意无意地描述克拉克易怒、性情暴躁,对于卡拉的擅自离家,他会有何反应呢?依照传统的叙事手法,作者惯常会在这个故事时间轴中的关键部分浓墨重彩,但门罗却大刀阔斧地砍断枝节,将此模糊并省略,营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刺激读者的想象力,留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作者预设的文本结构进行填补、思考和判断。
小说中模糊性情节的缺省还表现在故事临近结尾,山羊弗洛拉的最终丢失这一情节上,卡拉在秃鹫聚集的枯树林中对弗洛拉的最终去向寻思和猜测,“他说不定会把弗洛拉轰走。或是将它拴在货车后面,把它放掉……不让它出现来提醒他们。”[6]48门罗在小说《逃离》中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那么叙事者理应知晓故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然而关于山羊弗洛拉的丢失,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开始隐退,转而以卡拉第三人称限知的视角讲述故事进程,“小说中叙事视角的变化是一种典型的调整读者观察方式的手段。”[7]在这里,叙事者假装叙事视角受限,以情节的缺省营造无限的想象空间,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猜测和推断去填补文本之外的空白,以求阅读的完整性。
(二) 隐喻的使用
接受美学批评家朱立元先生指出,修辞手法的共性是舍弃语符的直接指示而设立中介,偏离惯常的表层意义而另有它意,有意识地在言与意之间设置空白域、不确定域和张力场。[8]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隐喻也不例外,它不仅在填补词汇空缺、增加表达准确性和形象性上发挥修辞功能,对整个文学语篇的组织、衔接和连贯的作用同样不可忽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小说文本中隐喻的把握,使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内涵、文学语篇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作品的文体效果和美学效应有进一步地理解和认知。
门罗在小说中运用隐喻的意象,预先设置文本的潜在意义,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挖掘和思考,诠释了她一贯的写作原则,“我想让读者感觉惊奇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
小说中的山羊弗洛拉(Flora)是一个拥有多重隐喻的意象,这一意象贯穿小说始终,故事中对其描述有八次之多,显然它承载着作者诸多意图和隐而不发的暗示语言。弗洛拉是克拉克在农场购买马具时带回来的,因“他听说在畜棚里养只山羊可以起到抚慰和安定马匹的作用”[6]8,同时克拉克也明白“它们(山羊)看着挺温顺,其实并非真是如此”[6]41,而这些关于山羊弗洛拉的描写,与女主人公卡拉外表温顺的性格相契合。小说中弗洛拉的丢失、回归、再丢失也惊人地与卡拉的逃离、归家、迷失保持一致。起初,在弗洛拉刚被克拉克买回来的时候,“它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在他跟前欢跳争宠”,然而,当弗洛拉“有了看透一切的智慧”后,反而对卡拉更加依恋。”[6]8这一情感变化与卡拉对丈夫克拉克的关系由依赖到淡漠直到逃离保持一致。可以这么说,弗洛拉是卡拉如影相随的映像,是卡拉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伴随着弗洛拉的出现、走失、再度出现、再度消失,这一意象不断引领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之呼应的是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心理变化,但门罗在小说中故意隐而不发,迟迟不给答案,让心头布满疑问的读者努力挖掘弗洛拉的隐喻意蕴,探究其隐藏的暗示语言,以此来窥探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尤其是女主人公卡拉的性格和命运发展。[9]
门罗除了运用山羊弗洛拉这一隐喻意象来预先建构文本的潜在意义之外,还通过梦境的隐喻方式书写卡拉在面对家庭、婚姻、现实生活时的内心矛盾和纠结的生存困境。门罗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讲了卡拉的两次梦境,在弗洛拉第一次丢失之后,接连两个晚上“卡拉都梦见弗洛拉。在第一个梦里,弗洛拉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6]6,而在第二个梦里,卡拉梦见弗洛拉受伤,在“铁丝网栅栏前……像一条白鳗鱼似的扭着身子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6]7。在卡拉眼里,弗洛拉俨然是卡拉在少人问津、内心渴望关注却极度匮乏、压抑无处排解的农场里仅有的慰藉,当其他牲畜都不正眼看她,只有小羊弗洛拉会挨蹭她,“那双黄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的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6]8。
门罗连续使用两个梦境来描述卡拉在弗洛拉丢失之后的心理状态,显然别有深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会被梦境这个“阻碍”意象牵绊,难免会有类似的疑问,为什么卡拉会做如此奇怪的梦?梦境里的弗洛拉叼着的红苹果有什么暗示吗?那么“类似战场用的铁丝网栅栏”有何指代呢?熟悉西方英语文学的读者都深知“苹果”“梦境”“山羊”这些隐喻意象的丰富含蕴,作者故意设置晦涩的阅读障碍和空白点,营造神秘朦胧的悬念,隐而不发,让读者在阅读中猜想和填补,联想梦境里的弗洛拉与现实中的卡拉之间的呼应与境况的吻合,启发读者对现代女性在面对家庭、婚姻和现实生活时的困境与纠结进行多角度地深层思考。
(三) 开放性的结局
门罗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她无意于给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一个明确的未来,她只是在书写她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实生活,留给读者一个始终保持开放性和理解的多角度性的未知结局。
小说《逃离》中,门罗对季节和天气的描述始终伴随着故事发展的进程和女主人公卡拉的心理变化,从故事开始时“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6]3,到故事的结尾,“晴朗的天气一直持续着。在街道上,在店铺中……夏天总算是来了。水坑变干了,湿土变成了尘埃。暖风轻轻吹起……到处都是鸟儿,蹲在枝子上,偶尔起身试飞一下,转上几个圈,接着又安顿下来”[6]44。由潮湿泥泞的雨水夏季转变成干燥晴朗,暖风吹拂的天气,像极了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心情遭遇。
而故事的女主人公卡拉,她重新回到克拉克身边,夫妻俩继续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之间的生活状态是:“一连几天,他们分头去干自己的活儿时,两人都会挥手作别,遇到正好挨近时……她便会隔着他薄薄的夏季衬衫,吻吻他的肩膀。”[6]44而克拉克呢,“他现在精神头很高,就像她刚认识他时那样让人难以抗拒。”[6]44一切似乎都回归如常,但是小说尾声处,在卡拉逃离、回归并开始她与克拉克新生活以后,“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6]47然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6]48虽然生活趋于平静,但逃离的诱惑却并未真正停止,这次逃离的回归是在为下一次的逃离做准备吗?卡拉和克拉克夫妻两人真的从上次逃离事件中走出来了吗?他们对此真的可以不旧事重提,像是什么都从未发生过吗?对于读者的疑问,门罗并未做任何的提示,也不帮助读者做明确的价值评析,显然,对他们未来生活的任何一种阐释都会落入绝对判断和框定主题的窠臼中。
这种开放式结尾体现的空白构成了潜在的文本,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和连续建构的过程。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源自于它开放的内在结构,文学作品是一个“过渡客体”,一个“潜在空间”,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与经验来填补和完善文本中不确定的空白与间隙。[10]
四、结语
门罗本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想用传统的方式讲述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故事,但……我想让读者感觉这事情是令人惊奇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11]在小说《逃离》中门罗通过文本语言的缺省、模糊性情节的留白,隐喻的使用,以及开放性的结局,构成小说《逃离》中“隐含的读者”的基本要素,形成一个潜在的开放性结构机制。正是这些缺省、隐喻和开放性的结尾,给读者指向一个没有明确说明的、暗含的、需要发掘的文本,从而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厚度,这正是门罗达到的效果,模糊后面隐藏着意义,沉默后面是无限可能的境遇,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文本中去经历那一场逃而不离的逃离和回归,而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门罗小说创作中预先潜在于文本结构中的“隐含读者”。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4.
[2]张芳.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艾丽丝·门罗研究述评[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3(2):236-241.
[3]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9.
[4][5]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2-183. 226.
[6]爱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8]朱立元.略论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J].学术月刊,1988(8):43-49.
[9]周燕.浅析《逃离》中山羊弗洛拉的象征意蕴[J].文学教育,2014(6):30-31.
[10]昌杨,何江胜.召唤结构视角下的《宠儿》解读[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2):78.
[11]A Conversation with Alice Munro.(EB/OL). http://reading-group-center.knopfdoubleday.com/2010/01/08/alice-munro-interview/,2010-06-28.
[责任编辑亦筱]